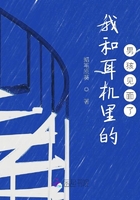楼上坐着老医生,还有两位探望鲁迅先生的客人。许先生一看了他们就自己低了头不好意思地笑了,她不敢到鲁迅先生的面前去,背转着身问鲁迅先生要什么呢,而后又是慌忙地把毛线缕挂在手上缠了起来。
一直到送老医生下楼,许先生都是把背向着鲁迅先生而站着的。
每次老医生走,许先生都是替老医生提着皮提包送到前门外的。许先生愉快地、沉静地带着笑容打开铁门闩,很恭敬地把皮包交给老医生,眼看着老医生走了才进来关了门。
这老医生出入在鲁迅先生的家里,连老娘姨对他都是尊敬的,医生从楼上下来时,娘姨若在楼梯的半道,赶快下来躲开,站到楼梯的旁边。有一天老娘姨端着一个杯子上楼,楼上医生和许先生一道下来了,那老娘姨躲闪不灵,急得把杯里的茶都颠出来了。等医生走过去,已经走出了前门,老娘姨还在那里呆呆地望着。
“周先生好了点吧?”
有一天许先生不在家,我问着老娘姨。她说:
“谁晓得,医生天天看过了不声不响地就走了。”
可见老娘姨对医生每天是怀着期望的眼光看着他的。
许先生很镇静,没有紊乱的神色,虽然说那天当着人哭过一次,但该做什么,仍是做什么,毛线该洗的已经洗了,晒的已经晒起,晒干了的随手就把它团起团子。
“海婴的毛线衣,每年拆一次,洗过之后再重打起,人一年一年地长,衣裳一年穿过,一年就小了。”
在楼下陪着熟的客人,一边谈着,一边开始手里动着竹针。
这种事情许先生是偷空就做的,夏天就开始预备着冬天的,冬天就做夏天的。
许先生自己常常说:
“我是无事忙。”
这话很客气,但忙是真的,每一餐饭,都好像没有安静地吃过。海婴一会要这个,要那个;若一有客人,上街临时买菜,下厨房煎炒还不说,就是摆到桌子上来,还要从菜碗里为着客人选好地夹过去。饭后又是吃水果,若吃苹果还要把皮削掉,若吃荸荠看客人削得慢而不好也要削了送给客人吃,那时鲁迅先生还没有生病。
许先生除了打毛线衣之外,还用机器缝衣裳,剪裁了许多件海婴的内衫裤在窗下缝。
因此许先生对自己忽略了,每天上下楼跑着,所穿的衣裳都是旧的,次数洗得太多,钮扣都洗脱了,也磨破了,都是几年前的旧衣裳,春天时许先生穿了一个紫红宁绸袍子,那料子是海婴在婴孩时候别人送给海婴做被子的礼物。做被子,许先生说很可惜,就拣起来做一件袍子。正说着,海婴来了,许先生使眼神,且不要提到,若提到海婴又要麻烦起来了,一要说是他的,他就要。
许先生冬天穿一双大棉鞋,是她自己做的。一直到二三月早晚冷时还穿着。
有一次我和许先生在小花园里拍一张照片,许先生说她的钮扣掉了,还拉着我站在她前边遮着她。
许先生买东西也总是到便宜的店铺去买,再不然,到减价的地方去买。
处处俭省,把俭省下来的钱,都印了书和印了画。
现在许先生在窗下缝着衣裳,机器声格哒格哒的,震着玻璃门有些颤抖。
窗外的黄昏,窗内许先生低着的头,楼上鲁迅先生的咳嗽声,都搅混在一起了,重续着、埋藏着力量。在痛苦中,在悲哀中,一种对于生的强烈的愿望站得和强烈的火焰那样坚定。
许先生的手指把捉了在缝的那张布片,头有时随着机器的力量低沉了一两下。
许先生的面容是宁静的、庄严的、没有恐惧的,她坦荡地在使用着机器。
海婴在玩着一大堆黄色的小药瓶,用一个纸盒子盛着,端起来楼上楼下地跑。向着阳光照是金色的,平放着是咖啡色的,他召集了小朋友来,他向他们展览,向他们夸耀,这种玩艺只有他有而别人不能有。他说:
“这是爸爸打药针的药瓶,你们有吗?”
别人不能有,于是他拍着手骄傲地呼叫起来。
许先生一边招呼着他,不叫他喊,一边下楼来了。
“周先生好了些?”
见了许先生大家都是这样问的。
“还是那样子,”许先生说,随手抓起一个海婴的药瓶来:“这不是么,这许多瓶子,每天打针,药瓶也积了一大堆。”
许先生一拿起那药瓶,海婴上来就要过去,很宝贵地赶快把那小瓶摆到纸盒里。
在长桌上摆着许先生自己亲手做的蒙着茶壶的棉罩子,从那蓝缎子的花罩下拿着茶壶倒着茶。
楼上楼下都是静的了,只有海婴快活地和小朋友们地吵嚷躲在太阳里跳荡。
海婴每晚临睡时必向爸爸妈妈说:“明朝会!”
有一天他站在上三楼去的楼梯口上喊着:
“爸爸,明朝会!”
鲁迅先生那时正病得沉重,喉咙里边似乎有痰,那回答的声音很小,海婴没有听到,于是他又喊:
“爸爸,明朝会!”他等一等,听不到回答的声音,他就大声地连串地喊起来:
“爸爸,明朝会,爸爸,明朝会,……爸爸,明朝会……”
他的保姆在前边往楼上拖他,说是爸爸睡下了,不要喊了。可是他怎么能够听呢,仍旧喊。
这时鲁迅先生说“明朝会”,还没有说出来喉咙里边就像有东西在那里堵塞着,声音无论如何放不大。到后来,鲁迅先生挣扎着把头抬起来才很大声地说出:
“明朝会,明朝会。”
说完了就咳嗽起来。
许先生被惊动得从楼下跑来了,不住地训斥着海婴。
海婴一边哭着一边上楼去了,嘴里唠叨着:
“爸爸是个聋人哪!”
鲁迅先生没有听到海婴的话,还在那里咳嗽着。
鲁迅先生在四月里,曾经好了一点,有一天下楼去赶一个约会,把衣裳穿得整整齐齐,手下夹着黑花布包袱,戴起帽子来,出门就走。
许先生在楼下正陪客人,看鲁迅先生下来了,赶快说:
“走不得吧,还是坐车子去吧。”
鲁迅先生说:“不要紧,走得动的。”
许先生再加以劝说,又去拿零钱给鲁迅先生带着。
鲁迅先生说不要不要,坚决地走了。
“鲁迅先生的脾气很刚强。”
许先生无可奈何的,只说了这一句。
鲁迅先生晚上回来,热度增高了。
鲁迅先生说:
“坐车子实在麻烦,没有几步路,一走就到。还有,好久不出去,愿意走走……动一动就出毛病……还是动不得……”
病压服着鲁迅先生又躺下了。
七月里,鲁迅先生又好些。
药每天吃,记温度的表格照例每天好几次在那里面,老医生还是照常地来,说鲁迅先生就要好起来了。说肺部的菌已经停止了一大半,肋膜也好了。
客人来差不多都要到楼上来拜望拜望。鲁迅先生带着久病初愈的心情,又谈起话来,披了一张毛巾子坐在躺椅上,纸烟又拿在手里了,又谈翻译,又谈某刊物。
一个月没有上楼去,忽然上楼还有些心不安,我一进卧室的门,觉得站也没地方站,坐也不知坐在哪里。
许先生让我吃茶,我就依着桌子边站着。好像没有看见那茶杯似的。
鲁迅先生大概看出我的不安来了,便说:
“人瘦了,这样瘦是不成的,要多吃点。”
鲁迅先生又在说玩笑话了。
“多吃就胖了,那么周先生为什么不多吃点?”
鲁迅先生听了这话就笑了,笑声是明朗的。
从七月以后鲁迅先生一天天地好起来了,牛奶,鸡汤之类,为了医生所嘱也隔三差五地吃着,人虽是瘦了,但精神是好的。
鲁迅先生说自己体质的本质是好的,若差一点的,就让病打倒了。
这一次鲁迅先生保持了很久时间,没有下楼更没有到外边去过。
在病中,鲁迅先生不看报,不看书,只是安静地躺着。但有一张小画是鲁迅先生放在床边上不断看着的。
那张画,鲁迅先生未生病时,和许多画一道拿给大家看过的,小得和纸烟包里抽出来的那画片差不多。那上边画着一个穿大长裙子飞散着头发的女人在大风里边跑,在她旁边的地面上还有小小的红玫瑰的花朵。
记得是一张苏联某画家着色的木刻。
鲁迅先生有很多画,为什么只选了这张放在枕边。
许先生告诉我的,她也不知道鲁迅先生为什么常常看这小画。
有人来问他这样那样的,他说:
“你们自己学着做,若没有我呢!”
这一次鲁迅先生好了。
还有一样不同的,觉得做事要多做……
鲁迅先生以为自己好了,别人也以为鲁迅先生好了。
准备冬天要庆祝鲁迅先生工作三十年。
又过了三个月。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七日,鲁迅先生病又发了,又是气喘。
十七日,一夜未眠。
十八日,终日喘着。
十九日的下半夜,人衰弱到极点了。天将发白时,鲁迅先生就像他平日一样,工作完了,他休息了。
1939年10月
几个欢快的日子
人们跳着舞,“牵牛房”那一些人们每夜跳着舞。过旧年那夜,他们就在茶桌上摆起大红蜡烛,他们摹仿着供财神,拜祖宗。灵秋穿起紫红绸袍,黄马褂,腰中配着黄腰带,他第一个跑到神桌前。老桐又是他那一套,穿起灵秋太太瘦小的旗袍,长短到膝盖以上,大红的脸,脑后又是用红布包起笤帚把柄样的东西,他跑到灵秋旁边,他们俩是一致的,每磕一下头,口里就自己喊一声口号:一、二、三……不倒翁样不能自主地倒下又起来。后来就在地板上烘起火来,说是过年都是烧纸的……这套把戏玩得熟了,惯了!不是过年,也每天来这一套,人们看得厌了!对于这事冷淡下来,没有人去大笑,于是又变一套把戏:捉迷藏。
客厅是个捉迷藏的地盘,四下窜走,桌子底下蹲着人,椅子倒过来扣在头上顶着跑,电灯泡碎了一个。蒙住眼睛的人受着大家的玩戏,在那昏庸的头上摸一下,在那分张的两手上打一下。有各种各样的叫声,蛤蟆叫,狗叫,猪叫,还有人在装哭。要想捉住一个很不容易,从客厅的四个门会跑到那些小屋去。有时瞎子就摸到小屋去,从门后扯出一个来,也有时误捉了灵秋的小孩。虽然说不准向小屋跑,但总是跑。后一次瞎子摸到王女士的门扇。
“那门不好进去。”有人要告诉他。
“看着,看着不要吵嚷!”又有人说。
全屋静下来,人们觉得有什么奇迹要发生。瞎子的手接触到门扇,他触到门上的铜环响,眼看他就要进去把王女士捉出来,每人心里都想着这个:看他怎样捉啊!
“谁呀!谁?请进来!”跟着很脆的声音开门来迎接客人了!以为她的朋友来访她。
小浪一般冲过去的笑声,使摸门的人脸上的罩布脱掉了,红了脸。王女士笑着关了门。
玩得厌了!大家就坐下喝茶,不知从什么瞎话上又拉到正经问题上。于是“做人”这个问题使大家都兴奋起来。
—怎样是“人”,怎样不是“人”?
“没有感情的人不是人。”
“没有勇气的人不是人。”
“冷血动物不是人。”
“残忍的人不是人。”
“有人性的人才是人。”
“……”
每个人都会规定怎样做人。有的人他要说出两种不同做人的标准。起首是坐着说,后来站起来说,有的也要跳起来说。
“人是感情的动物,没有情感就不能生出同情,没有同情那就是自私,为己……结果是互相杀害,那就不是人。”那人的眼睛睁得很圆,表示他的理由充足,表示他把人的定义下得准确。
“你说的不对,什么同情不同情,就没有同情,中国人就是冷血动物,中国人就不是人?”第一个又站了起来,这个人他不常说话,偶然说一句使人很注意。
说完了,他自己先红了脸,他是山东人,老桐学着他的山东调:
“老猛(孟),你使(是)人不使人?”
许多人爱和老孟开玩笑,因为他老实,人们说他像个大姑娘。
“浪漫诗人”,是老桐的绰号。他好喝酒,让他作诗不用笔就能一套连着一套,连想也不用想一下。他看到什么就给什么作个诗;朋友来了他也作诗:
“梆梆梆敲门响,呀!何人来了?”
总之,就是猫和狗打架,你若问他,他也有诗,他不喜欢谈论什么人啦!社会啦!他躲开正在为了“人”而吵叫的茶桌,摸到一本唐诗在读:
“昨日之……日不可留……今日之日……多……烦……忧,”读得有腔有调,他用意就在打搅吵叫的一群。郎华正在高叫着:
“不剥削人,不被人剥削的就是人。”
老桐读诗也感到无味。
“走!走啊!我们喝酒去。”
他看一看只有灵秋同意他,所以他又说:
“走,走,喝酒去。我请客……”
客请完了!差不多都是醉着回来。郎华反反复复地唱着半段歌,是维特别离绿蒂的故事。人人喜欢听,也学着唱。
听到哭声了!正像绿蒂一般年轻的姑娘被歌声引动着,哪能不哭?是谁哭?就是王女士。单身的男人在客厅中也被感动了,倒不是被歌声感动,而是被少女的明脆而好听的哭声所感动,在地心不住地打着转。尤其是老桐,他贪婪的耳朵几乎竖起来,脖子一定更长了点,他到门边去听,他故意说:
“哭什么?真没意思!”
其实老桐感到很有意思,所以他听了又听,说了又说:“没意思。”
不到几天,老桐和那女士恋爱了!那女士也和大家熟识了!也到客厅来和大家一道跳舞。从那时起,老桐的胡闹也是高等的胡闹了!
在王女士面前,他耻于再把红布包在头上,当灵秋叫他去跳滑稽舞的时候,他说:
“我不跳啦!”一点兴致也不表示。
等王女士从箱子里把粉红色的面纱取出来:
“谁来当小姑娘,我给他化装。”
“我来,我……我来……”老桐他怎能像个小姑娘?他像个长颈鹿似的跑过去。
他自己觉得很好的样子,虽然是胡闹,也总算是高等的胡闹。头上顶着面纱,规规矩矩地、平平静静地在地板上动着步。但给人的感觉无异于他脑后的颤动着红扫帚柄的感觉。
别的单身汉,就开始羡慕幸福的老桐。可是老桐的幸福还没十分摸到,那女士已经和别人恋爱了!
所以“浪漫诗人”就开始作诗。正是这时候他失一次盗:丢掉他的毛毯,所以他就作诗“哭毛毯”。哭毛毯的诗作得很多,过几天来一套,过几天又来一套。朋友们看到他就问:
“你的毛毯哭得怎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