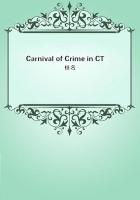十一月初,立冬节气。天晴,有暖阳。
立冬后,连续半个多月都是大晴天。最低温在零下三四度。柜子压的棉衣,母亲取出后拿在太阳下晒。薄丝棉被换成厚点的棉花被。
闲暇时候去秦伯父家,和他们一起逛菜场,秦伯父做饭手艺胜过我和母亲,夜晚包饺子,一家人围着电视吃晚饭,饭后去广场散步,他们等老伙伴。夜晚广场的四角,开着几个大灯,整个路面被照的如同白日,行人在下面走,身后影子跟随,小孩子在人群中穿梭,三五个玩耍。有人出来遛狗,几只小型犬,在广场草坪里打闹翻跟头。
第一场雪在十一月底,来自西伯利亚的一股寒流,气温骤降。一夜风雨,次日晨起,全城一片白茫。雪还在下,路上行人,不由得小心翼翼,车辆也放慢行进的速度,火锅在冬季里,客源旺盛,生意兴隆。这样的习惯,不论南北方,一概如此。
兰诺发来邀请函,要在来年五月举办婚礼。作为她最好的朋友,诚意相邀,希望我能前去赴会。电邮回复,愿意前往,喜贺新婚。他们在光棍节前顺利脱单。发来的邀请函另附几张婚纱照。一袭白裙,亭亭玉立,新郎帅气阳光,在冬季内景室拍照,选择古朴背景拍摄,气氛浓重,一如他们彼此的感情,深而长远。
夜晚在台灯下看照,心间喜悦,拿起笔,在相片背后写了四个字:岁月静好。墨迹干后,将相片夹在了影集,放回书架。
整个冬季,在接连的几场大雪中度过。由南至北,雨雪在不同的城市切换自己的身份。温度上有最可观的节奏,凉凉冷冷,与季节很相配。南方接连的几场冻雨,新闻上播报,部分地区,被冻雨的冰凌压断了电线,北方有一些地区,温棚遭到大雪摧残,有些垮塌受损,随之菜价上涨。新僵边远地区,暴雪覆盖道路,冻死牛羊。类似这一系的新闻,每天都在电视和网络上播报。
第三次降温,母亲患了重感冒。怕被传染,秦伯父不让我去照顾,他亲自侍奉汤药,煮饭洗衣。所以,在母亲生病那几日,我一直不曾去过秦伯父家。一个流感,持续了大半个月,病好已经是元月下旬。看日历,再有半个月,就到春节。今年的节日,对新家而言,别具深意。
年货置办,我没有参与太多,大部分由母亲与秦伯父购置。秦伯父原是知青下乡,后自学考试,读大学,毕业后,国家分配工作,离开原籍多年,在新地立业成家,由于祖籍不在本地,大多数亲友都失去联络。由外地迁居而来,一过就是大半生。过去过年时,老伴和两个孩子都在,后来,孩子出国,老伴去世,身边最亲近的人相继远去,退休后,围绕在侧的,除了同事,学生,便是几位尚在人世的老友,闲时打牌下棋,喝茶聊天,用老年人的方式消遣时光。
耳顺之年,再结新欢。彼此的内心都有了依靠。所以,那一年的春节,尤其的幸福。
过去,古人在除夕时,都有守夜的习惯。后来,由于生活方式的改变,守夜大多由麻将,纸牌,K歌等娱乐方式代替。除夕夜,钟声敲响后,我们在门前点燃冬季第一束烟花,远处,有大片空地的地方,上空炸响着色彩斑斓的烟花,爆竹辞岁,喜贺新春,新年就这样如期而至。伯父做的梅菜扣肉,酱肘子,母亲的蒸饺,时蔬炒,各色饭食,在正月轮换着吃。作为陪他们过节的女儿,心里有千言万语,不知该从何处谈起。
那段时间的心情,兴奋,激动,感动,日子与幸福相交,融汇一起。
正月拜新年,走亲访友。母亲与秦伯父忙的不亦乐乎。我则用大量的时间来记叙这些生活。柴米油盐,点滴瞬间,都被一行行写进日记中。所有的回忆方式,独独选择以文字记录。感受,心声,天气,饭食,熟客,娱乐,一应变换成文字,装进笔记。妥帖又安慰。
三月初,秦伯父接到街委会通知,旧城改造,要拆掉他们那条街道的老房子。政策一经批准,所有的人,开始忙着商谈拆迁补偿,各家测量自家房屋面积,街道办组织人参加听证会,赶着在拆迁期限之前顺利搬迁。秦伯父的小儿子在临近的城市曾购得一处房产,在听到自己父亲旧居拆迁的消息后,让秦伯父与母亲搬迁到他以前的住所,一来可以照料房屋,二,新屋所在的地段,环境舒适,非常适宜老人养老。秦伯父听从自己孩子的安排,忙完一切拆迁手续,带着母亲去了新城市。临走前一天,我们在一起聚餐,我提前下班,去酒店订位子,算是为他们乔迁饯行。
新城离自己所住的城市,有六个多小时的车程。由于还没有开通列车专线,来往都得坐长途大巴,虽说有些距离,倒也不妨碍我们日后见面。于是,送完母亲和秦伯父,一切的生活又回到正轨。
母亲走后,自己一个人忙不过来,在店门外贴了招聘通知,招聘了两位刚毕业的大学生来帮忙,她们在大学时曾就读园艺专业,对于插花很有概念,刚来那段时间,我带着做花束,后来,就全面放开,任由自我发挥。小姑娘心灵手巧,做好的花束,颜色搭配很漂亮,除了花店来买花的人,网上下单的也不少,三四月的生意很不错。
不知是因为母亲与秦伯父的联结,触动了自己对生命的重新感知,还是出于对人世间的留恋。春节后,独自去医院,找到曾经的主治大夫,在医生的诊疗下,重新开始了药物治疗。连续几个月的服药过程,四月时,体力渐渐恢复,整个人神色也有改观。当然,最重要的是心态变得正向和乐观。
这一切,为兰诺的新婚做好了准备,我总要以一个健康阳光的身体和心情去参加她的婚礼。我们的关系,正如她自己所讲的“故乡人”。没有血缘的亲人,友人。
清明时,母亲照例同我去为父亲扫墓,不同往年的是,这次同去的,还有秦伯父。他提前买好了纸钱,香烛。六个小时的长途大巴,下车后我们去父亲的墓地。从柏树林穿过,烟火气浓重,寒食清明,在春季尤其的冷清。
内心,似是静止了。清风扫墓,摆放水果,糕点,秦伯父还带了酒杯,亲自为父亲斟了一杯酒。三个人,彼此沉默,一切言语,尽在不言中。
父亲去世几年,我们像告别往事一样告别了伤痛。也在这样的一场无声告别中,理解了世间的痛苦,其实都是有期限,曾经以为,一生都要浸在悲痛中,然,在时间的推进中,深刻凛冽的那些部分,慢慢地失去了原色,这种失去并非意味要将前人遗忘,而是,明白了回忆和纪念其实还有另外的方式。后者与前者相比,同样深沉,曲异之处,后者背负的方式不再让人痛苦。
这样的方式,就像面对良善的早逝之人,大家怀念他,不再过分的思考命运待他的不公,而是,面对他的清悄离世,未经疼痛,没有久卧床,只一觉未醒,沉长睡去。
这样的方式,在众多的死亡中,是最体面,最安静的,我们这样宽慰自己,并且将过去的,从前的,一路路的悲喜,理顺后,全止在当天,以此来解除梦魇。
墓碑上,黑白照片,行书刻字。名讳,时间,年岁,一一写在其上。旁侧石缝,长着几棵嫩草,春风轻抚,叶片摇摆。离人远去,心有永恒。生命的一抹绿,在草长莺飞时,在春雨梨花后,渐渐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