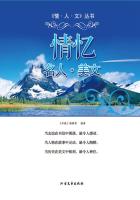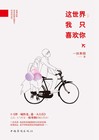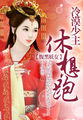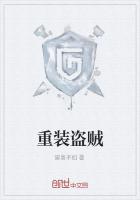叙述干预一般来说分成两种:指点干预解释叙述是如何进行的;评论干预提供补充信息,或阐明叙述者本人对被叙述事件与人物的态度。
这个说法只是大致上正确。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古典小说中的指点大部分是文体性的,并非在解释叙述方式。也就是说,它们实际上只是在指明叙述所使用的特殊文体。上一章已经说起“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等等实际上是不必要的解释:它们只是作为拟书场叙述格局的标记。
在某些情况下,叙述者用指点来召唤叙述接收者,让叙述接收参与到叙述中来,能使叙述中的事件得到一个客观的见证人,从而使叙述场景戏剧化。《水浒传》第一百〇三回,王庆突然有幻觉:
王庆看见庞氏出来,也要上前来杀。你道有恁般怪事!说也不信。王庆那时转眼间,便见庞氏背后有十数个亲随伴当,都执器械,赶喊上来……
叙述干预承认叙述接收者有理由不相信这离奇故事,从而预先消除可能产生的怀疑。
当然,真正解释叙述方式的指点还是有的,最常见的是当叙述者不得不离开一般的程式要求时,常有较长的指点来说明叙述方式的变异。《红楼梦》中这一长段指点:
且说荣府中合算起来,从上至下,也有三百余口人,一天也有一二十件事,竟如乱麻一般,没个头绪可作纲领。正思从那一件事那一个人写起方妙?却好忽从千里之外,芥豆之微,小小一个人家,因与荣国府有些瓜葛,这日正往荣府中来,因此便就从这一家说起,倒还是个头绪。
此段指点之所以需要那么长,是因为这样的叙述方式对中国古典白话小说来说是很特殊的,而中国古典白话小说,哪怕是《红楼梦》,不想以叙述方法上的创新来自炫,如此不厌其烦的说明可以使读者不至于对非程式感到难以接受。
因此,指点干预有三种作用:指示文体风格,召入叙述接收者,解释出格的叙述方式。在中国古典白话小说中,前两种居多数。
二
与指点干预相似,评论干预在口述文学叙述中本是顺理成章的事,叙述者理由十足地对叙述中的人和事发表评论或进行解释。在书面虚构叙述中,这种评论却很难处理。《金瓶梅词话》第三章有个例子:
王婆道,大官人,你听我说,但凡挨光的,两个字最难。怎的是挨光,比如今俗呼偷情就是了。要五件事俱金,方才行的。第一要……
这个评论干预塞在王婆的话中,王婆这段话在大部分《水浒传》版本中都有,文字大同小异,但是插入的这一句说明是没有的,那不是王婆的话,而是叙述者的说明。《水浒传》叙述时间是“彼时”,所以无。《金瓶梅》的叙述时间是“如今”,所以有。《金瓶梅》崇祯本删去了这段说明性评论,因为叙述者评论一般只能插在叙述语流中,在人物的话中插入叙述者评论很不自然。
在口头叙述中,这样的插入语调却很方便,叙述者只消把他模拟人物的语调转回叙述者自己的语调进行干预,然后再转回人物的语调继续转述下去即可。
而且,在口述文学中,叙述格局随时为这种说明性评论提供必要性:叙述者发觉听者听不懂了,即有充分理由加以说明。在书面文学叙述中,这种必要性只是假定。书面文字叙述可因其可重读性而“传世”为后代阅读。叙述干预的必要性只是在叙述格局中的一种抽象而且临时的必要性,并非是保证叙述信息传播的实际必要性。换句话说,这种必要性本身是叙述虚构的一部分。拿上引《金瓶梅词话》的例子来说,在转引王婆的话时,叙述者突然加入说明性评论,是拟书场叙述格局的一部分,也只有这样理解,它才是可接受的。换一个叙述格局,叙述者就毫无权力这样做。
说明性评论起的作用不仅是提供解释。在尽可能坚持叙述线性的中国古典白话小说中,它常被用来代替倒述,提供人物或事件的背景资料,或交代人物的未来或事件的结果。《三国演义》中每个人物出场时,叙述者均交代其籍贯、出身与行状,每个人物退出叙述时,则介绍此人后来官至哪一级,子孙为官情况等等,情节如此处理对叙述流干扰最少。
很多说明性评论并非用来提供情况,而是用来为看起来一荒唐不合情理的情节提供解释,是一种控制释义播散的努一力。这类评论大部分是所谓“老生常谈”。我们现在读到此类评论,往往发现它们很难“抹平”出格情节,因为“老生常谈”有时代性、社会性。在《金瓶梅词话》中,西门庆与仆妇宋惠莲通奸。宋惠莲后来自杀了:
月娘……叫他门不开,都慌了手脚,还使小厮打窗户内蹿进去,正是瓦罐不离井上破。割断脚带卸下来,救了半日,不及鸡鸣时分,呜呼哀哉死了。
这个老生常谈式评论抢在宋惠莲自杀被证实的消息之前出现,似乎宋惠莲惨死的下场是咎由自取。《金瓶梅》的叙述者对社会下层人物看来相当冷酷,但在当时,恐怕这类评论恰是社会下层读者认为可接受的。
传统白话小说,尤其是在改写期,一些长段评论经常被互相抄用。《金瓶梅词话》第二十七章有长达三页关于盛夏酷暑的评论,说是世上有六种入——王孙贵族、和尚、隐士等等——不受酷热之苦;同书第八章中有二页多长的评论,说和尚好色,原因是太闲。这些段落在某些版本的《水浒传》等其他白话小说中也可以找到,文字仅略有不同而已。这些段落有的不太公平(例如关于和尚好色的长段),而且都显得过分离题,长得不必要。由于它们被一再转抄,我们可以想象对于大部分当时读者(下层市民),这些评论很受欢迎。这种转抄,也是改编期中国白话小说的一个特征。崇祯本《金瓶梅》本中这些套式评论全部被删除。
判断性评论绝大部分是就道德问题发言,文学作品中所写的人和事,毕竟大多数是社会性的,逃不脱道德判断。即使是向现行规范挑战的作品也是道德性表意活动。如果解释性评论旨在帮助接收者理解一些出格的情节或人物,那么判断性评论则试图控制意义诠释。《金瓶梅》词话本第二十二章,西门庆与仆妇宋惠莲有私,叙述者插入了一条相当长的评论:
看官听说,凡家主切不可与奴仆,并家人之妇,苟且私狎,久后必紊乱上下,窃弄奸欺,败坏风俗,殆不可制,有诗为证:西门贪色失尊卑,群妾争妍竟莫疑;何事月娘欺不在,暗通仆妇乱伦彝。
崇祯本保留评论,仅删诗。
这首“证诗”当然是陈腐的打油诗。如果说,在口述文学中,叙述者可以用改变语调这样简易的手法来标明评论部分;在中国古典白话小说中,也有一种类似的改变语调式评论,那就是“有诗为证”。诗体评论的隔离效果非常强,似乎它们可超脱于叙述语流之外。例如《三国演义》第八回,王允以貂蝉设美人计宴请董卓:
卓见貂蝉颜色美丽,便问:“此女何人。”允曰:“歌伎貂蝉也。”卓曰:“能唱否?”允命貂蝉檀板低讴一曲。正是:
一点樱桃启绛唇,两行碎玉喷阳春。
丁香吞吐衠钢剑,要斩奸邪乱国臣。
如果这首诗是叙述的一部分,它就把关键情节悬疑——貂蝉是否能成功地害死董卓——透露得太早了,然而中国古典白话小说的程式使我们明白诗是诗,文是文,诗不在叙述情节链之内。
文学史家认为中国古典白话小说中大量引用诗歌作评论干预,是继承了口述文学的传统。这个看法自然有道理。但我想用诗作评可能有另一层原因,即诗歌作为文体,在中国文化的文类等级中,其“真理价值”远远高过叙述流本身所使用的白话散文。“有诗为证”这套语本身就说明这些诗是从高一文化层次对叙述进行说明,正因如此,诗本身的优劣倒是其次的问题。大部分这些诗式评论只能说是打油诗,但它们还是用来作为道德证词。
一般说来,评论干预的风格标记能力不如指点干预,往往一个程式性指点干预就足以标记出某种的叙述格局。但是,评论干预的长度、使用频率,仍是重要的风格标记。崇祯本《金瓶梅》所使用的评论干预,数量上就比词话本少得多,评论干预大量减少标志着一个新的叙述文体时期的开端。《儒林外史》在开场词后说:“这一首诗,也是老生常谈,不过说……”吴敬梓明白这类评论足以害文。《儒林外史》这本小说之成功,很大程度上在于叙述者评论干预减少到中国传统小说的最低程度,只保留了古典白话小说的一些起码的程式性干预。
传统白话小说中的叙述者一般说在作评论时很少节制。说书的这种半显人物化给了他超然的权力,可以假定叙述接收者对他的全控制地位完全认同,而且欣赏他毫不苟且的道德感。但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程式化叙述者并不着意炫耀其控制地位,不像西方18世纪一些“自我意识”小说中的叙述者那样玩弄机智。他的评论并不想使人吃惊,评论方式是程式化的,轻车熟路,有险无惊。评论内容也是恪守规范,而且始终一本正经,不苟言笑,哪怕是题材最不“严肃”的作品中,叙述者语调依然如此。《金瓶梅》绘形绘色地描写了潘金莲与西门庆的第一次性幽会之后,有一段评论:
却说这妇人,自从与张大户勾搭,这老儿是软如鼻涕脓如酱的一件东西,几时得个爽利。就是嫁了武大,看官试想,三寸丁的物事,能有多少力量,今番遇了西门庆,风月久惯,本事高强,如何不喜?
这可能是中国传统小说中允许走的最远的程度,最轻松最幽默的可能。我们很难想象狄德罗或塞万提斯会错过这样的好机会,不让他们的叙述者来个痛快淋漓的大笑。
三
晚清白话小说一个明显的特征是叙述干预数量剧增,远超过以前的白话小说。这问题似乎至今没有见到文学史家讨论。
晚清小说指点干预之增加,比评论干预增加更为醒目,原因在于在传统格局之内叙述不得不采取的种种变化造成的不安。
《孽海花》是个典型例子。作者曾朴可以说是晚清作家中对西方文学最了解的入,他可能认为他在写一部与传统小说完全不同的全新的叙述作品,但是他写出的《孽海花》却是晚清在叙述技巧上比较保守的一部小说。他用又多又长的指点干预来解释新的叙述技巧,不料正是这些干预把整个叙述拉回到传统程式中去。
话说上回回末,正叙雯青闯出外防,忽然狂叫一声,栽倒在地,不省人事,想读书的读到这里,必道是篇终特起奇峰,要惹起读者急观下文的观念,这原是文人的狡狯,小说家常例,无足为怪。但在下这部《孽海花》却不同别的小说,空中楼阁,可以随意起灭,逞笔翻腾,一句假不来,一语谎不得,只能将文机御事实,不能把事实起文情,所以当雯青忽然栽倒,其中自有一段天理人情,不得不栽倒的缘故,玄妙机关,做书的此时也不便道破,只好就事直叙下去,看是如何。闲言少表:且说雯青一交倒栽下去……
或许这是晚清小说中最长的指点干预了吧!《官场现形记》第十一回、《黄绣球》第六回,都有类似长指点,但没有这条长。显然这比中国传统小说中的指点干预长得多。它好像是在为一个新技巧辩护,实际上这技巧非常陈旧,即在紧要处断章,加一联,并提示下章。
许多晚清小说是缀联式的,其中一个接一个故事由人物讲述出来,而且人物的话多是直接引语式,如此长的直接引语给叙述布局带来不少困难。先前的白话小说中很少出现这样的情况。因此,长段指点干预经常用来帮助平衡这局面。《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一〇一回有这样奇特的指点:
且慢,从九十七回的下半回算起,叙这件事,是我说给金子安他们听的,直到此处,一〇一回的上半回,方才煞尾。且莫问有几句说话,就是数数字数,也一万五六千了,一个人哪里有那么长的气?又哪个有那么长的功夫听呢?不知非它,这两段故事,是分了三四天和子安们说的,不过当中说停住了,那些节目,我懒得叙上,好等这件事成个片段罢了。这三四天工夫,早又有了别的事了。原来苟才这两天病了……
这段指点奇特在混淆叙述时间与被叙述时间,更奇特的是试图用叙述干预来改造叙述行为:已经直录的引用被说成是经过叙述改造过的转述——把三四天中零星讲的故事接成一长段直接引语。
不仅指点干预增加,晚清小说中评论干预数量也增大。如果指点干预增加是自以为采用新技巧造成的不安引起的,那么评论干预增加则是因为叙述者感到解读常态受到威胁。题材范围扩大,自然也造成评论之需要:事件越复杂,道德评论就更有必要,而且评论的语调也更激烈,更急切,以使道德判断不容置疑。
尤其是,晚清小说的叙述者大都采取社会改造者的姿态,惩恶扬善的迫切性使叙述语调带上道德傲慢,老生常谈式的评论就显得更加扎眼。吴趼人《九命奇冤》第三十二回有一段很为典型:
看官!这几行事业,是中国人最迷信的,中国人之中,又要算广东人迷信得最厉害,所以苏沛之专门卖弄这本事,去戏弄别人。我想苏沛之这么一个精明人,未必果然也迷信这个,不过拿这个去结交别人罢了。
这个苏沛之是朝廷来的钦差调查谋杀案件,他装扮算命先生,以打入歹徒帮中。这是小说后半部分的主要悬疑,要到几回之后凶手全部落网,才能揭开。上引的评论干预几乎把悬疑过早点穿,为此评论花如此大的代价,只是为了表示叙述者道德立场的正确。
晚清小说中的叙述者对他永远正确的形象十分敏感。《九命奇冤》中另一段评论,也是关于迷信问题,叙述者以社会改造者姿态来加强他的意义权力地位。
看官!须知这算命、风水、白虎、貔貅等事,都是荒诞无稽的,何必叙上来?只因当时的民智,不过如此,都以为这个是神乎其神的,他们要这样做出来,我也只可照样叙过去。不是我自命改良小说的,也跟着古人去迷信这无稽之言,不要误会了我的意思呀。
类似的叙述者自辩,在许多小说中都可看到。例如《九尾龟》中,叙述者用大段篇幅讲了妓院中规矩,并且加上一句:“在下预先一一申明,免得要受看官的指摘。”
在吴趼人的《近十年之怪现状》第八回,一个人物把报上一段新闻指给其朋友看:
看官,难道那鲁、李两人就不曾看过新闻纸么?偌大的丰盛祥金店,难道就不看新闻纸的么?为什么他二人直到此时,被紫旒指点才看见呢?不知凡是看新闻纸的人……表白出来,免得看官们说是我著书的漏洞。(64页)
叙述者这种自卫需要,在先前的白话小说中从未出现过,叙述者从来没有如此担心传达的效果。我们不禁感到,晚清小说的叙述者不得不再三自辩,是感到其控制地位岌岌可危。
这种危险感产生的另一个原因,是一部分作品中叙述者的身份开始人物化,比过去的“说书的”个性化了,相反叙述接收者却比先前更加非个性化,他成为数量更大的读者“看官”,而不再是书场里有限的观众“看官”。在叙述格局难以变化时,叙述者/叙述接收者在旧格局中作这些变动,难免局促不安。传统白话小说的叙述者多少世纪从容行使其控制权,从而成为比作者更强有力的主体性出发点,现在却不得不用大量干预来为自己的全控制叙述方式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