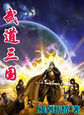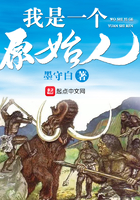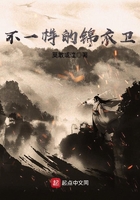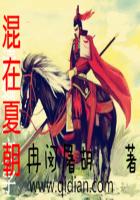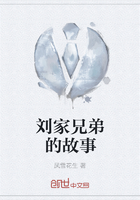这种虚张声势的架势使得伍举十分担心,他对楚灵王说:“我听说,诸侯不归附于特定的人,只归附于有礼之人。现在您已经开始得到诸侯的拥护了,要给他们一个好的第一印象,霸业的成功与否,就看您的表现了。”
“那寡人该怎么办?”对于在楚庄王年代就以智慧而闻名的伍举,楚灵王一直怀有敬畏之意——在他的世界中,能让他感到有所约束的,恐怕也只有伍举了。
“自古以来,明君都有让人铭记在心的标志性事件。夏启有钧台的晚宴,商汤有景被亳的政令,周武王有孟津的盟誓,周成王有岐阳的阅兵,周康王有丰宫的朝觐,周穆王有涂山的会盟,齐桓公有召陵的会师,晋文公有践土的盟约。您打算采取哪一种模式?宋国的向戌,郑国的子产在这里,他们都是诸侯大夫中的佼佼者,您可以听听他们的意见。”
“那寡人就学齐桓公吧。”楚灵王说。然后派人去问向戌和子产关于礼仪的问题。向戌说:“小国学习礼仪,大国使用礼仪,岂敢不进献?”将公爵会晤诸侯的礼仪完完整整地写在竹简上,一共写了六条,让使者带给楚灵王。子产说:“小国听从大国的调遣,岂敢不用心推荐?”将子爵、男爵会见公侯的礼仪教给了楚国人,也是整整六条。
楚灵王对照这些礼仪,好好地演练了一番,仍然不放心,又对伍举说:“举行仪式的时候,你就站在我后面,发现我有什么做得不对的地方,就赶紧提醒我。”
公元前538年六月十六日,由楚灵王主导的第一次诸侯会盟终于顺利举行了。所有的仪式都举行完之后,楚灵王暗自抹了一把汗,将伍举叫到一个没人的地方:“不是说好要你提醒我吗?怎么你没有任何举动?我是不是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对,让人家笑话啦?”
伍举说:“您做得很好,比想象中都好!”
“难道就没有一点失误?”
“说实话,今天您在台上实施的礼仪,起码有六种是我从来没有见到过的,太高深了,我哪里提醒得了!”伍举说着,忍不住笑了。楚灵王愣了一下,也大笑起来。
顺利举行完盟誓后,楚灵王心情大好,邀请大家前往武城打猎。这是他即位半年多来第三次举行大规模的狩猎活动,而且每次都邀请诸侯参加,一来炫耀武力,二来展示地大物博,三来增进感情,可以说是他争取诸侯支持的重要手段。
会议的正式代表之一、宋国的世子佐因故没有赶上盟誓仪式,直到大伙都去了武城才匆匆忙忙赶到申地。自知理亏的世子佐老老实实地呆在申地等候发落,然而一连十几天都没有等到楚灵王的指示。正当他心里七上八下的时候,楚灵王派了一位使者回到申地,却不是要他面壁思过,而是向他表示歉意。
“寡君在武城打猎,是为了给宗庙奉献供品,因此不能赶回来及时接见您,请您原谅。”使者对世子佐说。世子佐惊讶得说不出话来。不用说,在武城打猎期间,楚灵王就是用这样百无禁忌的方式对待各国诸侯,连子产和向戌之徒都对楚灵王的宽宏大度产生了严重的错觉——这,难道就是原来那个蛮横无礼的王子围?
但是,事情很快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从武城回到申地,诸侯们以为会开完了,活动也搞完了,都忙着打点行装,准备回家了。楚灵王突然又把大伙召集起来,说别慌,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会盟不是请客吃饭,不能光打雷不下雨,要拿出点实际行动才有意义。说着使了个眼色给身边的薳罢,薳罢拍拍手,一队全副武装的士兵冲进会场,不由分说,将徐国的国君徐子给拎了出来。
大伙被这突然的变故惊得目瞪口呆。楚灵王站起来,用一种阴鸷的眼光环视了大伙一周,被他盯到的人无不感到寒意油然而生。“诸位不远千里来到楚国参加会盟,为的是和平共处,建立没有刀兵的太平盛世,这也是寡人的愿望。”楚灵王清了清嗓门,“但是,大家想必也知道,吴国和少数几个国家不自量力,敢于与楚国为敌,企图破坏天下的和平。只要寡人有一口气在,就不会让吴国的阴谋得逞。”
话说到这里,大家心里都明白了七八分了,这会果然不是白开的,先前的歃血为盟、吃喝玩乐、架鹰纵犬,原来只是铺垫,真正的戏文还在下面。
“根据寡人得到的情报,吴国人得知我们在这里会盟,竟然突发奇想,要在我们中间安插一个眼线,监视我们的一举一动。而且,他们几乎要成功了。谁都想不到吧,这位看似忠厚老实的徐子,就是吴国人安排进来的探子!”
大伙都不说话,保持惊人一致的沉默。你说他是钉子,他就是钉子?但是谁都不敢开口争辩。最后还是子产站出来说:“大王,如果说徐子是吴国人派来的钉子,需要有确切的证据,道听途说恐怕会冤枉好人。”
“你要证据?”楚灵王快步走到徐子跟前,一把揪住他的衣服,“这个人的母亲是吴国的公主,他与吴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就是证据!”
大伙面面相觑。按照楚灵王的逻辑,只要谁与敌国有血缘关系,谁就有私通敌国的嫌疑,不,是谁就有私通敌国的铁证,这也未免太牵强了。这下连子产都不发表意见了,谁会去跟黄鼠狼比放屁啊?大堂上一片沉默。
“既然谁都没有意见,”楚灵王得意地笑了,“那请诸位整顿军备,准备随同寡人一起讨伐吴国吧。”
伍举私下对楚灵王说:“古代的明君之所以能够称霸天下,是因为以礼相待诸侯,因此诸侯也愿意为他们卖命。夏桀举行有戎之会,有缗氏叛变;商纣举行黎之蒐,东夷背叛;周幽王举行大室之盟,戎狄部落反水,这都是因为对诸侯无礼。现在您没有真凭实据就断定徐子与吴国勾结,这不是失礼于诸侯,引人背叛么?”
楚灵王瞪了他一眼:“寡人说他有问题,他就有问题,这事不许再谏!”
子产听说这件事,跑去找向戌:“我现在倒是不担心楚国了。这个人蛮横无礼而且刚愎自用,听不进善意的建议,横行不会超过十年。”
“是的。”向戌也说,“十年成不了大事,他的作恶不会太远,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同年七月,楚国大将屈申率领楚、宋、郑等国诸侯联军讨伐吴国,大军包围并攻克了朱方(吴国地名),将居住在那里的齐国旧臣庆封抓了起来,并诛灭其九族。
楚灵王认为这是一个树立正面形象的极好题材,命令在诸侯面前公开处死庆封。伍举再次劝谏:“我听说,自己没有缺点才可以指责别人。庆封因为违抗君命,大逆不道,所以流落到这里。他怎么可能乖乖就范?搞得不好,让他反咬您一口,会在诸侯中间造成不好的影响,那就太不划算了。”
楚灵王不听,命令庆封扛上一柄八斤重的大斧头,五花大绑地在诸侯营中巡游示众,并且要他大声说:“不要像齐国的庆封那样杀死他的国君,欺负国君的孤儿,来和大夫结盟!”这叫现身说法,现代多用在贪官身上,古代则多用于所谓的“贰臣”身上。而这里说的杀死国君,是指崔杼谋杀齐景公,庆封当了帮凶;欺负孤儿,是说庆封以齐景公弱小而轻视他;和大夫结盟,则是指公元前548年,崔杼和庆封在齐景公的即位仪式上,要求大家对他们表忠心,宣读“如果有不亲附崔氏、庆氏者……”这样的誓词。
庆封也不含糊,扛着斧头一路走一路喊:“不要像楚共王的庶子熊围那样把自己的国君——哥哥的儿子熊麇杀死,取而代之,还厚颜无耻地来和诸侯会盟!”诸侯们听了,想笑又不敢笑,楚灵王赶快派人把庆封拉下去杀了。
从吴国返回后,楚灵王马不停蹄,又带兵消灭了赖国。赖国的国君赖子双手反绑,嘴里衔着玉璧;国中士大夫光着上身,抬着棺材跟在后面,来到了楚军大营。楚灵王是个老粗,搞不懂这一套已经流传了几百年的投降仪式,只好又向伍举请教。伍举说:“先君楚成王攻下许国,许僖公就是这样做的。先君亲手给他松绑,接受了玉璧,烧掉了棺材,表示宽宏大量地接受投降。”
“有意思。”楚灵王心想。于是照葫芦画瓢,接受了赖子的投降,把赖国的老百姓迁到鄢地。
楚国的盟国中,许国最为死心塌地。早在楚共王年间,许灵公就因为不堪忍受郑国的欺凌,将整个国家搬到了楚国境内,客居在叶城,成为了受楚国保护的国中之国。楚灵王消灭赖国后,突发奇想,要把赖国的土地赏赐给许国,让许人重建家园,而且说做就做,马上派大夫斗围龟和王子弃疾带兵前往赖地筑城。
这件看似仗义的好事受到大夫申无宇的强烈批评:“楚国的灾难就要开始了,想会诸侯就会诸侯,想攻打别国就攻打,在边境筑城也没有提反对意见,国君肯定是称心如意了,可老百姓能够安居吗?长此以往,谁能够受得了?”
不用老百姓反抗,同年冬天,吴国为了报复朱方之役,派兵入侵楚国,劫掠了棘地、栎地和麻地。楚国派大夫沈尹射赶到夏口戒备,宜咎在钟离地方筑城,大宰薳启强在巢地筑城,大夫然丹在州来筑城。正好这段时间上述地区大雨延绵,导致筑城工作不得不停止,赖地的筑城也因此半途而废。
用人失察的灾难
前面说到,公元前544年,吴国公子季札奉命出访中原各国。在鲁国逗留期间,季札与叔孙豹有过一次交谈,季札当面提醒说,叔孙豹心地善良,却不善于识人,恐怕因为用人不当而遭受祸害。
季札所言并非危言耸听,而是有所指。事情还得从公元前577年的鲁成公年代说起。
那一年,叔孙氏的族长叔孙侨如因为与鲁成公的母亲穆姜私通,企图利用穆姜的力量消灭季孙氏和孟孙氏,独揽鲁国大权,结果事情败露,叔孙侨如全家逃亡到齐国。后来,鲁成公又派人将叔孙侨如的弟弟叔孙豹从齐国接回来,继承了叔孙氏的家业。
鲁成公对叔孙氏网开一面,一方面是体现自己的仁德,另一方面是为了保持“三桓”之间的势力均衡。而之所以选择叔孙豹,则是因为他为人诚恳,忠于职守,在鲁国享有良好的口碑。
然而,在这位至诚君子流亡齐国的途中,却发生了一件风流事儿。
《左传》记载,叔孙豹在逃亡途中和叔孙侨如的大部队走散,只身来到齐鲁边境的庚宗(地名),又累又饿,又怕被人发现,只好躲在田野里盼望奇迹出现。
庚宗当地的一个农妇,扛着锄头正好经过,看到叔孙豹奄奄一息地躺在一条小河沟边,不由得心生怜悯,便将自己随身带的食物给了他。叔孙豹吃饱了,喝足了,捧着小河沟里的水把脸洗干净,那贵族公子的气质便又重新回到身上。那农妇一辈子与泥土打交道,左邻右里不过是些山野村夫,哪里见过这么风流潇洒的男人啊?把持不住,主动投怀送抱,献身于叔孙豹。俗话说得好,男追女,隔千山;女追男,隔张纸。农妇虽然长得不怎么样,但是自有一番野趣,再加上叔孙豹逃亡多日,生理需求膨胀,两人一拍即合,当下便把事儿给办了。
当然,后世有好事者以为,鲁国礼仪之邦,女人如此随便,实在难以想像。于是有一本伪《孔子家语》转载此事,将《左传》中的“妇人”偷偷改成了“寡妇”。这样便说得过去了,寡妇嘛,闲着也是闲着,不干白不干,不算伤风败俗。
事情办完后,农妇很满足。她躺在叔孙豹怀中,不甚娇羞地说:“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呢!”
“豹。”
“好威风的名字啊!”农妇说,“你从哪儿来,要往哪里去呢?”
“这?”叔孙豹犹豫了一下。
“如果不嫌弃的话,就留在这里嘛!”农妇的眼中流露出一丝热切的神色。
叔孙豹环视四周。这是深夏时节的黄昏,田原一片宁静,远处寥寥几栋农舍,炊烟正在袅袅升起。“我又何尝不想留在这里,只不过我如果留下来,会给你们带来很大的麻烦。”叔孙豹长叹道。
“为什么?”
“因为……我是叔孙氏的后人。”
农妇脸上露出惊讶的神色。不用叔孙豹多说,她全明白了。前几日,村长才将全村人召集到一起,宣读了公室的命令——叔孙氏里通外国,阴谋叛逆,据悉正举族逃往齐国,如有发现其行踪者,必须立即向当地政府报告,协助捉拿归案。
“你快走吧,这里确实不安全。”农妇一把推开叔孙豹,眼泪却止不住流下来,她指着小河沟流去的方向,“顺着这条河一直走下去,翻过前面那座山,再走不远就是边境了。你赶快走,如果被别人发现,一定会把你抓起来见官。”
叔孙豹朝农妇作了一揖,郑重地说:“感谢你。”然后站起来,拍拍身上的泥土,头也不回地向着农妇所指的方向走去。
看着他渐渐远去的背影,农妇终于忍不住,“哇”的一声号啕大哭起来。
叔孙豹到了齐国,齐灵公见他独自一人,便将国氏的女儿许配给他,生了孟丙和仲壬两个儿子。但是,叔孙豹在齐国的日子过得似乎不太快乐,至少不如他的哥哥叔孙侨如快乐——侨如一到齐国,便和齐灵公的母亲声孟子搞到了一起,声孟子甚至想立侨如为卿,与国、高二氏平起平坐。
家族的变故使得叔孙豹忧心忡忡,侨如的荒唐行为更让他抬不起头来。有一天夜里,他竟然梦到天塌下来压在自己身上,眼看要顶不住了,回头看见一人,长相十分奇特。黑皮肤,肩膀向前弯曲,眼睛深陷,猪嘴巴。他顾不上许多,大叫道:“牛,快来帮我!”那人听了,快步上前,用肩膀扛住天,奋力向上一顶,将天又顶回去了!
第二天一早醒来,他将上至家老、下至厨子的所有家臣都召集起来,一个一个辨认,却没有发现谁和梦中那“牛”长得相像。他只好叫来画师,按照自己的描述,将“牛”的长相画到布上,保存起来。
后来鲁成公派人到齐国召叔孙豹回国。
对于叔孙豹来说,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早在来齐国之初,兄弟二人有过一次谈话,叔孙侨如说:“鲁侯顾念我们先人的功德,想必会保存叔孙氏的香火。但是我罪大恶极,肯定是回不去了。如果有那么一天,他们派人来召你回去,你可愿意挑起家族的重担?”
“这正是我所希望的事。”叔孙豹回答。对于给家族带来灾难的侨如,他没有丝毫好感,但仍然按照兄弟之礼给予尊重。等到鲁成公宣召其回国的时候,他甚至没有向侨如辞行,急急忙忙便跑回鲁国去了。
此后又过了数年。某一天,叔孙豹的府上来了一位奇怪的不速之客。从她的打扮来看,是所谓的“野人”阶层,手里拿着一只野鸡,说是要献给叔孙豹。
一个女人,既非贵族,又非国人,竟然胆敢要求面见叔孙氏!守卫大门的卫兵自然不让她进去。正在争执之际,一个家臣匆匆跑出来,斥退卫兵,将那女人迎进了府。
不用说,这个女人就是叔孙豹在庚宗田野里遇到的农妇。两人久别重逢,时过境迁,说过什么知心话,做过什么快乐事,史料已无记载。《左传》只是干巴巴地写道:
叔孙豹问她儿子的情况,她说:“我的儿子已经长大,能够捧着野鸡跟着我到曲阜来了。”
叔孙豹何以得知那一次风流便结下了果实?原来,周礼有明确规定,“士”阶层面见贵人或参加重要的政治活动,手执野鸡为礼(士执雉)。叔孙豹是个明白人,一看那女人送来野鸡,又提到儿子,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那个年代,卿大夫有个野合而来的私生子,不是什么丢人的事,何况庚宗田野那一幕,给叔孙豹留下了十分温暖的回忆。他马上对女人说:“把你的儿子叫来吧,我想见见他!”
第二天,那女人果然带着儿子又来到叔孙豹府上。叔孙豹一见那孩子,不由得大吃一惊,马上命人将那幅“牛”的画布拿来,对比着一看,可不就是同一个人!他又惊又喜,感叹这真是命运的安排,亲切地叫道:“牛,你就是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