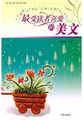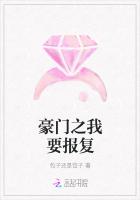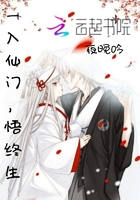耿翔
我那时不懂得,对于所有生命的死亡,如果你看见了,都得有个仪式。就像母亲对待这些虫子,要是能做出某个哀悼的手势,我想,这些虫子在简单的一生中,会因此获得一些尊严。
——题记
1
我的前面不是庄稼,也不是牛羊,是一个永远走在我前面的,不会回头的女人。我叫了她不足三十年母亲。那是在世间的幸福与痛苦的日子里,我幸福或痛苦地叫着她。
如今,她从这些幸福或痛苦中冰凉地退场了。
我也只能在自己心里,一个人冰凉地叫下去。
只是她在那么厚的乡土上,留给我的那些生活场景,不因她的退场而消逝。相反,它们从马坊的众多事物里漂浮出来,替我在接近故乡的每一次,都要生动地演绎母亲的过去。但我还是要伤感地说,我在三十岁之后所想见的母亲,都是她走在我的前面,并且不回一次头,给我的永远是一个背影。
按照简单地生活在马坊的人对生命的认识,所有从土地上逝去的人,都不会回头看他身后的人,特别是那些最想看见的亲人。这些暗含在生命里边的隐秘,我是说不清楚的,有时只能这样想:如果那些一代一代逝去的人,都在土地上不停地回头,我们行走着的前面,还不满是祖先的眼睛?我们说土地是温暖的,首先是从庄稼上感觉,更多更深刻的,恐怕还是从祖先的背影上感觉。
这样安慰后,我突然意识到这是有关生命的一种哲学。
它被一群庄稼人,像种庄稼一样地种在土地上。
我也学诗人艾青问自己:我的眼里为什么常常噙满泪水?我不会有简单的回答,正像我至今不敢给母亲的坟头立一块碑一样,因为我应该在心上镌刻给母亲的碑文,不会被简单地书写出来。
一个人的心,一生只疼一次,这是物理意义上的疼。而另一种超越肉体的疼,会是伴随一生的事。我对母亲的所有记忆,也就是她一直在精神上为我心疼。幸福时是幸福的心疼,痛苦时是痛苦的心疼。我不敢说,母亲是世上最懂得心疼的人,但至少在我身上,这种心疼是覆盖又覆盖,遮蔽又遮蔽。
甚或为了我,她用一生的时间,折磨她的日子。
对马坊在地理上的热爱,让我一提起母亲,就想到村子东边的一座土城。
可以说,土城两边的两个村子、两片土地和两户人家,甚或他们的两块墓地,构成了母亲一生的活动空间。她能够放在乡土上的记忆,就是围绕着这些,只过一种有粮食和衣物的日子,从而对生活,保持一种贫穷的方式。
我经常想,能够记忆的祖先那几辈人,怎么就这么安贫乐道,愿意过简朴的生活?他们一生在土地上,消耗不了多少东西,他们的日子,多数是女人缝补出来的。因此,我很热爱缝补这个词,还有被这个词表述的缝补场景。
这是属于母亲的场景。一年四季,都会看见她白天坐在场院里,晚上坐在油灯下,缝补着一些土布衣裳。特别是她裁剪一件新衣裳的时候,一个穷人心中的滋润,在剪刀和布纹清亮、细碎的声音里荡漾。被左邻右舍的女人围着,母亲一脸的喜悦,蓝花土布也是一脸的喜悦。更多的日子中,母亲是在一件件旧衣裳里,花费着一个女人的心思。她要把一些旧衣裳没有磨损的部分裁下来,再缝成另一件衣裳,或补在其他破了的衣裳的某个部位。那些破得不能再上到身上的碎布,也会被千纳百垫在我们的鞋底里。我从母亲手上看出,缝补带给穷人的幸福。你想,我穿的一身衣裳,有一些巴掌大的补丁,有可能是从父亲的旧衣背上、姐姐的旧衣袖上、母亲的旧衣襟上取来的布片,而他们留在这些布片上的气息,如果没有被风吹走、被水洗走、被阳光赶走,就会继续温暖我的胸膛、肩背和膝盖。衣裳里这些最容易磨损的地方,也是最容易接触到亲人的气息的地方。我在乡下成长时,经常一个人出没于马坊的大小沟里,斫柴、挖药、割草,没有孤独和惧怕,可能是我的身上,穿着带有亲人气息的补丁衣裳的缘故。今天,我坐在敞亮的书房里,一边翻着西方一些经典的绘画,一边想着母亲缝补过的衣裳,突然有一种她也懂得绘画的感觉。因为我在民间剪纸大师库淑兰的剪刀下,看见过毕加索的影子。库淑兰和我的母亲,都是生活在豳风里的人,一条流淌在诗经里的泾河,让她们在两岸的土地上,依靠一把剪刀,幸福而痛苦地生活过。
对于词语中的缝补,我有更贴身的认识。比如,母亲缝补一件衣裳时,从不量我的身体,但裁剪出来总是十分合身的。因为这双手,抚摸过我成长的每一个日子,而我身体上每一个骨骼的大小,都在她的记忆里,被感情编排得一清二楚。可以这样认为,母亲手中的剪刀,表面上是在一块土布上游走,实质上是在阳光的感觉里,在我的身体上游走。这种游走,落在我的心上,始终是一种幸福。
而落在母亲心上,是一生的隐痛。
让我再次提起,这座转换母亲生活场景的土城。她从东边一个破碎的家里,嫁到西边一个更破碎的家里。她一生的责任,就是想用自己的一双手,把两个对她来说,有如呼吸着的肺一样重要的家,缝补得浑全一些。事实是,她是带着一半浑全、一半破碎的心,放下她缝补着的最后一个日子,走进被庄稼、人迹覆盖得厚厚的泥土里去了。
她在我的感触里,浓缩成一位不会回头的女人。
她在一些熟悉的土地上走过时,我看见庄稼的身子,晃动得厉害,我也看见牛羊的目光深处,像噙着一个村庄里过去的雨水。我的身子和目光,也火气一样上升着一些疼感。我想说出有关她的许多,而气势强劲地吹过来的风,从田野上堵住嗓子,让我说不出她的许多伤痛。
我不会怀疑,她身上还有牵挂。一个村子的苍茫,在她藏下所有旧事的蓝花土布衣襟里,不回头也能翻出一些印象。跟着她,我像一匹栗色的马,把一片不记仇恨的乡野,一米不剩地踩踏过一遍。她用宽厚,不停打动土地的时候,总先打动着我。
而一切都在我的前面,跟她走着。她不能回头,因为在马坊这片乡土社会里,人们至今相信:如果梦见某位逝去的亲人回头了,这个人一定要病一场。这是被许多人验证过的事情,它带有马坊的神性,活在我们的生活里。
尽管如此,走出马坊多年的我,还想着母亲,在土地上给我回一次头。
只要她能回头,我就能再端详她一次。
只要能再端详她一次,我还惧怕生病吗?
我也很想在自己身上看一看,一个被母亲回头看过的人,他为母亲生病时是个什么样子?
其实,她也很想转身看我一眼,只是风吹得她回不过头。
2
对于土布的感觉,不是从心理上,而是从身体上早已滑落了。
很多年不在乡下生活,已经彻底淡忘了皮肤贴着土布,该是一种怎样的享受?更不敢想土布在与皮肤的触摸中,开始虽然有些粗糙,但最终会从棉花的秉性里,带给我们的那种温暖。
我是穿土布长大的。
在我身体成长的简史中,感恩地记着几种粮食、几样野菜和几棵果树,再就是几件土布做的衣裳。而在这些属于贫穷人家的物质中,几件土布衣裳,给了我一定的体面,使我在青春期来临之前,一直快活地走动在乡野上。因此,一提起故乡的土布,我就想起那些玄妙的织机声,怎样穿透着乡村的夜色?怎样穿梭出日子的黑白?怎样穿越一位少年的想象?而母亲,准会在这个时候,隐去一头白发,隐去一脸皱纹,隐去一身枯瘦,回到她年轻的日子里,给我们织染土布,给我们裁剪衣裳。
那时的乡村,应该活在一群会用手工织出土布的女人的尊严里。
我不知道今天在马坊,还有多少女人会织土布。记着只要遇到下雨天,只要在夜幕的遮蔽里,总会有几声织布声,从你想象不到的一座院落里,突然传出来。这是乡村看似简单的生活,曾经带给我的一些经验:要判断一个村子是否活着,最好的办法,是寻找它有没有一些声音的存在。这些声音,自然包括人的声音、牲口的声音、草木的声音和物件的声音,而织布声,则是马坊刻意留给我的,一种古物件的声音。
其实,从一块棉花到一块土布,再到我们身上的一件衣裳,这个过程是很漫长和艰辛的。一棵庄稼的成熟,也就几个月时间,麦子的成熟期最长,经过秋播、冬埋、春发,到了夏天,把一片黄灿灿的穗子递给镰刀,一种粮食的身世,又一次被大地完成了。而一块土布呢?我记着母亲先是用好长的时间,一斤一两地积攒棉花,由棉花到棉线,又要经过纺车一夜一夜的摇动。
那些纺好的线,像一家人过日子时的大部分喜悦,被小心地包在一个包袱里。
我经常看见母亲,选在阳光灿烂的时候,一个人静悄悄地打开包袱,在太阳下反复地比对每把线的成色、粗细和韧性,哪些是经线,哪些是纬线,被分得一清二楚。浆线的过程、打筒的过程、经布的过程,在织布这个手工工艺中,这些很讲精细的程序,确实是一种原生态的乡土文化,如果把它按工序写出来,就是一部讲述织布的乡土读物。如果把织布机子、纺车、缯绳、绞棍、育筒、木梭这些与织布有关的物件,从一个偏僻的村子里取出来,再看看打造这些物件的木匠,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而母亲每花两三年的时间,织出来的一匹土布,我不敢说它一定就像云锦,但一卷新布抱在母亲的怀里,我还是尽量往浪漫里想象。现在记忆起来,我后来对诗的许多感觉,或许在那时,就被母亲无意地织在她的土布里。
也想,母亲织的土布有多长,我对乡土的感觉就有多长。
事实上,许多织布的细节,比如拐线、纶绳、浆线,我都作为母亲的帮手参与过。特别是浆线,让我欣赏了乡土生活既朴素,又很神秘的另一面。
这些乡村女人,在用粮食喂养每一个生命的过程中,又智慧地发现了它们在织布中,会把柔软的棉线,一根根浆得硬锃锃地,便于手工操作。说真的,我在各种面食中,享用得最多的是麦子的味道。但在炽热的阳光下,把鼻子贴近正在浆洗的细线上,麦子挥发在棉花上的气味,却是如此诱人,甚至很多年后,要回忆乡村的气味,我会脱口而出:是麦子在棉花上,浆洗纱线的气味。
村里人说,母亲的手底下会出活,包括她手织的土布。
忙完织布机上的活,那双很会裁剪的手,又要忙碌我们的衣裳了。
这样的日子,在我心里充满了幻想:土布、剪子、母亲的手,三种不同的物象,都在母亲的目光下,变幻出一件件就要遮蔽我们身体的衣裳。现在,如果我说她那时就像裁剪着云朵,就像缝补着马坊的一块土地,也不会有人说我这是矫情。但母亲那时最真实的心态,是让我们穿得体面一点,用这些她还能织出来的土布,弥补日子的艰辛,带给一家人的贫穷。
看着她飞针走线的样子,心还没有长到能用善良、柔情观看世界的我,直接觉得阳光有多细密,这时母亲的心,就有多细密。她知道父亲一生是下负的人,常年把柴捆背在身上,要不是那一层衣裳,脊梁上都会磨出茧子来。
因此,要把织得粗厚的布留给父亲,要一律染成黑色的,要裁剪得宽大一些,这样结实的衣裳,耐磨也耐脏。乡村人穿衣,也有乡村人的审美标准,就是方便劳动。至于身体本身,那时的生活状况,还顾不了多少,只要一年四时觉着不饥、不冷,就是大地上最幸福的人了。可以说,我的父母一辈,就是为此劳累困顿了一生。直到裹着一身土布,回到泥土里去。
对于我的衣裳,就要讲究一些。选织得最细的布,怕磨伤了我的皮肤似的,剪最贴身的样式,让我穿得有精神一些。我从小时候穿过的衣裳里,看出一位乡村女人心里,如果还有一些艺术的质感,虽然嘴里说不出来,大多都通过剪子和针线,全表现在孩子的衣裳上了。因此,母亲缝衣的许多场景,我走到任何陌生的地方,都要熟悉地带在记忆里。首先是一块蓝花土布,落在母亲的手里,一尺一尺地流动着,很像阳光,在我开始拔高的身体上,一尺一尺地生长。我能准确地听见,剪刀从土布上走过时,会留下什么样的声音。心存对冷暖的那些敏感,正从一块蓝花土布上,传递出母亲,与棉花生死相依的气息。这肯定是我后来的感觉,假如当时能体察出的话,我会把母亲给我做过的大小衣裳,一件不缺地保留下来。
那些土布衣服上面,存在着那个年代里,阳光的气息,泥土的气息,更多的是母亲的气息。作为一件单纯的衣裳,它真实地记录着母亲给予我的那份爱,像棉花一样,像土布一样,透明在那个年代的阳光下。
可惜的是,我在这个世界上,不再拥有这些衣裳了。
我想,如果还有一件的话,今天吹过乡野的风,会绕过母亲留下的一些织布用的物件,从那件土布衣裳细密的针脚里,帮我吹出她的一些秀发。
要是我早年,贴身穿过的哪一件呢?
3
这是一个村子里最神秘的器物。
一只药锅,在十几年的时光里,揪住一个孩子的心,让它在成长的过程中,为一个人的命运紧缩一团,并在梦里反复幻想:谁能把药锅移走,谁就能把母亲身上那些藏着根须的病痛,替自己移走。
我就是那个孩子。
母亲十几年的病痛,让我觉出其中的神秘,认为这是一个贫穷的家庭,必须在大地上承受的磨难。而母亲的善良,在于她像祈祷一样,把一个家庭的疾病史,只写在她一个人身上。
现在想来,母亲的病是饥饿带来的,也是我的出生带来的。我对母亲身体的十个月的伤害,让我在有能力读懂她的时候起,就开始思索一个生命,对于另一个生命意味着什么。因此,伴随我成长的过程,就应该有一种悲悯的东西,像草木的一叶一枝,长满身体的每一个部位。不幸的是,这种心理的培育,依然要以母亲的磨难为代价。
应该是一个落雪的冬天。马坊的土地上,一切生命都因雪的到来,而进入一次长时间的休整。此刻的泥土里,除了小麦、油菜这两样农作物,还继续向更深的土层上,扎着来年起身时需要汲够充足营养的根,再没有埋藏下什么。更多的细小的生命,被雪用一种颜色,覆盖在大地的角落里,自己蕴涵自己。忙活了一年的劳动者,也要躺下身子,用最简单的生活方式享受劳动的喜悦。而母亲躺下身子时,一身的痛楚,从她的身体里蔓延出来,落在我们一家人的心上,是这个冬天的另一场大雪。
天就要黑了,被雪映得苍白的屋檐下,我为母亲熬药。
我的眼前,是一只像被火焰悬在半空中的药锅。在我成长得还不健全的心里,母亲的病痛,是一种揪心的疼,而为母亲熬药,则是一种对这种疼痛的减缓。坐在屋檐下,雪的寒冷,火的温暖,心的疼痛,一个复杂的世界,伴随着母亲在屋子里的呻吟,笼罩着我的童年。那些散发着淡淡苦香气味的草药,我能在马坊的田野上,认出它们好看的模样,可放在药锅里,一个也认不出来。我的手中,是一把依然带有麦香的麦草,它的洁白,使它燃烧时的火焰在我们家有些悲凉的院子里显得特别神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