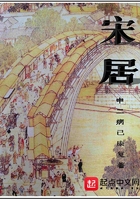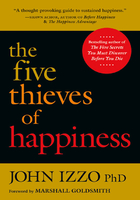二十五、入城
城门处,当兵的在例行盘查,快寿辰了嘛,霍大人早就吩咐下来,不要让可疑人等混入长安,兵士们可算是有个表现的机会了,整天便在城门处大呼小叫,以显示自己的权威。封斯兰不理这些,但他从来不提自己的使节身份以免多生枝节。便一个人装做是个普通百姓,走到了士兵跟前,没想到后面却发现了孔如兵和一个白衣少女也赶了上来,孔如兵一见封斯兰在前面,紧赶几步,大声叫道,“封大人,封大人,”士兵们一楞,见这个人穿衣打扮都不象哪个方形大臣,便问道,“您是哪个府上的大人?”封斯兰抬了下头,随口编道:“本人在匠作府做事,出城去采办些东西为皇上寿典上用,”士兵怀疑地看了看他,“可有牌照?”封斯兰道,“常出城去,因此没随身携带,”孔如兵赶上来一脸堆笑,“这位兵爷,这封大人是帮宫里做事儿的,你们不要难为,我可以作证!”士兵瞟了他一眼,“你有牌照吗?”孔如兵随手掏出来了西域胡酒家的号牌,西域胡酒家在长安城里的大酒家,兵士们都是知道的,忽然见他后面还紧紧跟着一个少女,便问道,“这又是谁?”少女刚要张口,孔如兵立刻先说了话,“这是我妹妹,这些天皇上寿典,酒店里忙不过来,我把妹妹带来帮着做些洗涮的活计。”士兵见他说得倒也在理,便挥了挥手,让几个人都过去了。孔如兵见到了封斯兰后,心里一喜,他只知道封斯兰是匈奴使臣,别的都不知道,不过有了封斯兰在旁,那少女虽然有些功夫,就不敢把自己怎么样了。封斯兰倒也高兴,他就怕孔如兵得了消息,从此躲开,要是再找也就难了,现在看来,孔如兵倒是什么都不知道,只是奇怪的是,孔如兵本该昨天就入城了,怎么今天才来,而且还带了个少女。孔如兵拉过少女来,介绍道,“这位封大人便是本店的常客,你这回信了吧?”少女戒备地看了一眼,象征性地行了个礼。封斯兰仔细打量了一下,随口问道,“你这妹妹可不象是个乡下干活儿的啊?”孔如兵一笑,“都是家父从小给惯坏了,因为家父宠着她,从小没做过多少活儿,但现在既长大了,也得出来学着做点儿事儿,要不以后如何嫁人呢?我这才把她领出来到酒店里长长见识。”封斯兰心想,这小子可真是说谎话不用打草稿,张嘴就来,谁知道他用这张嘴从哪里拐带来的少女,只是又有点儿怀疑,因为少女似乎对他与孔如兵多少都有些戒备。
少女叫婉儿,一直随着夫人住在敦煌郡,这次也是第一次与夫人等来到长安,虽说从小在大户人家长大,也不是乡下普通乡下姑娘,但对外面的事情还是知道得甚少。刚才这一路上都是听孔如兵讲长安的繁华与典故,也充满了好奇,而且见孔如兵与人周旋十分得体,反倒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佩服了。
三个人向酒店走去,但却各打各的算盘。封斯兰在想,自己是先动手制住孔如兵,逼他把他们的事情说出来呢,还是到酒店再说,但到酒店后,孔如兵可能随时得到孔家的消息,而随时逃走,但现在用什么办法,自己也还没想好。婉儿的想法是,如果到了酒店,孔如兵说的属实,自己就可以回去禀告夫人了。而孔如后也在想,去了酒店,虽说是可以与少女解释自己的身份,但自己还是不甘心,自己的身份已经让少女知道了,如果他在店里向韩兴问起青衣帮的事儿,却有可能给帮里惹出大麻烦来。
封斯兰想到,先设计把这个姑娘的身份搞清楚再说,先得探探他与孔如兵是什么关系。于是便道,“姑娘叫什么名字?”少女涉世甚少,也不会撒谎,只好说,“我叫婉儿,”封斯兰道,“婉儿,很好听的名字啊,”孔如兵马上道,“家父从小就宠着她,便给起了这样一个名字。”封斯兰没理孔如兵,又对婉儿道,“婉儿姑娘,孔老先生可是个慈爱的老先生啦,令尊今年贵庚多少啦?这样的人肯定会长寿有福的!”婉儿一楞,不知道如何回答,孔如兵一看要穿帮,赶紧说,“家父今年已经五十岁了,过了三十岁才得的婉儿,因此特别宠爱。”封斯兰又道,“婉儿姑娘,那你也一定心灵手巧了,对了,你哥哥原来腰带上总是打着个花结儿,想来你也一定会打的啰?”婉儿知道那是青衣会的标志,便脱口而出,“我可不是他们青衣会的人,”孔如兵知道封斯兰在查问青衣会的事儿,没想到还没等他张口,婉儿已经给说了出来,正暗自着急。没想到封斯兰倒接着说,“青衣会也没什么啊,不过是一群人常在一起互相帮助一下而已,”孔如兵听了,长出了一口气,但没想到婉儿却道,“但我家夫人说了,那里面都是坏人,他们尽做坏事,总是帮着一些朝廷里的坏人为虎作伥!”孔如兵一惊,也急了,“封大人,你可不能听小妹胡说,青衣会不过是一些手艺人而已。哪里能与朝廷扯上关系呢!”封斯兰听了,知道了原来这青衣会是有朝廷背景的,只是不知道父亲的死与这个是否相关。其实他此次来到汉朝,还肩负着一个任务,就是尽量联系各个江湖门派,因此对此类消息极为留心,继续问道:“那可是有趣了,请问姑娘,那你和你家夫人也一定是不屑于朝廷为伍的啦?”婉儿道,“那是,我们夫人说了,现在的朝廷,都是贪官当道,残害忠良之辈。我们岂能与他们是一伙儿,但这青衣帮,尽是些朝廷的狗腿子!”封斯兰转头笑着向孔如兵问道,“孔少爷,你说是吗?”孔如兵一阵脸红,“我们哪能和朝廷有什么瓜葛,我父亲一个匠人,一生本本分分地,最多不过是为朝廷调制些药物罢了,这也能说是朝廷的人了吗?”他刚想说狗腿子那个词,但一想不雅,还是咽了回去。封斯兰知道他还不知道孔府里后来发生的事情,心底暗笑,至少从那天孔有和冯子都的关系上就能知道,他们熟悉得很,肯定不是一般的帮着炼制药物的简单关系,便想再逼仔逼,“孔如兵,那么说,令尊大人是经常给大将军府上炼制药物了?我知道,令尊和冯子都大管家可是熟悉得很啊!”孔如兵被逼得一惊,但转念便来了主意,“也不只是与大将军府上有些走动,和其它的贵人们也会送些药物去。”汉代武帝时,好神仙之术,贵人们喜欢用药炼丹倒是常见。封斯兰又问,“令尊过去去匈奴也是为了弄些药物吗?”孔如兵对这事儿确实知道不多,只好答道,“可能是吧,有些中原没有的矿物丹草之类的也得去找的,家父过去曾经去过匈奴倒是不假,”封斯兰又问,“那你知不知道有个和你父亲在一起的姓封的,叫做封林的人呢?”孔如兵想了想,“这个倒是听说过,小的时候,听说他死在匈奴了,后来父亲领我去找过他在河南的家人,不过没有找到,”封斯兰听了心想,听他口气倒是不象撒谎,“河南什么地方,你还记得吗?”“好像在一个叫做什么南阳的什么地方了,”“哦,”封斯兰听了,轻轻地叹了口气,又问道,“那你知道他是怎么死的吗?”孔如兵也奇怪封斯兰为什么问得这样详细,便说道,“家父说他是病死的。”
封斯兰不由得想起了父亲当年死时的惨相。那一天他永远记得。头一天晚上,父亲还亲了他和母亲,然后,第二天就和孔有一同去回汉地中原,还说这次送完了货,再回来就不走了,就在这里永远陪着他们娘俩了。第二天一早,他和孔有喝完了奶茶,就骑马离开了,走之前还抱了他一下。但下午时,有人赶着牛车,送回来了父亲的尸体。父亲的死相很惨,七窃流血,而且右手食指还断了一根,别人说,那是中毒而死。一些草原上的年轻人骑着快马,去追赶孔有,但茫茫草原,哪里找得到?从此,父亲便永远在走了。这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除了孔有之外,没有人知道。父亲从此便长眠在了草原上。后来,遇到了师傅,学了武夫,再后来,有一天,单于的使者找到了他,领着他来到了单于的王庭,问起了他父亲的事情后,单于泪流满面,只是告诉他,说自己对不起他的父亲,从此他便留在了匈奴单于的大帐里,做了单于的侍卫,而且陪着单于的小王子哲保骑马、练武、打猎,直到有一天,哲保告诉他说,让他随着伊势顿的使团去给汉武帝贺寿。
听了孔如兵所说,他知道,那一天里发生了什么,只有孔有自己一个人知道了,孔如兵的声音里十分的轻松,说明孔有肯定没有告诉过他。于是,他有了一个新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