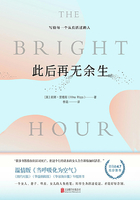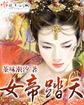(第一节)物欲与情欲的狂欢
一、“无名”的时代与欲望的释放
1976年底“文革”宣告结束,人们扭着秧歌,敲着锣鼓,庆祝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的时候,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状况,也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1977年8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宣布“文革”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而结束”。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展开了全国性的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这篇评论员文章引起了轩然大波,通过哲学层面的论争,谱写了中国当代历史上蔚为大观的一页。这一年的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肯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支持“思想解放”的命题,批评了维护僵化教条的“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规定,并决定撤销在1976年作出的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和“天安门反革命事件”的文件,为“四五”天安门事件平反。会议确定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提出中共全党工作重点转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面前,不存在什么“禁区”,不存在什么“金科玉律”。
这次会议在历史转折、各种力量交锋的时候,冲破了“两个凡是”,正本清源,拨乱反正。邓小平高瞻远瞩,及时提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切向前看”的思想路线。
1979年10月召开了第四次全国文代会。在这次会议上,“文艺民主”的要求和想象,得到强烈的表达。对有关文艺领导和控制的这一敏感问题,会议作出了这样的解释:执政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并重申在1956年提出,但一直没有得到真正实施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的有效性。
邓小平在《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中不失时机地指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提高文学艺术水平,创作出无愧于我国伟大人民、伟大时代的优秀文学艺术作品和表演艺术。”
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大潮,人们的生活观念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这种变化可以说是正负兼在的:从正的方面说,人们的思想观念更为活跃,更愿意接受新生事物,竞争意识、自我意识、优胜劣汰的思想开始深入人心;从负的方面说,理想退位,物欲膨胀,功利主义浪潮势不可挡”。
在1984年12月到次年1月召开的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上,以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名义在大会上宣读的“祝词”,更提出了“创作自由”的口号:“作家有选择题材、主题和艺术表现方法的充分自由,有抒发自己的感情、激情和表达自己的思想的充分自由”,“我们党、政府、文艺团体以至全社会,都应当坚定地保证作家的这种自由”。
邓小平时代与毛泽东时代的不同点,并不在于中国要不要现代化,而在于怎样现代化或在何种意义上现代化。“现代化问题本身不是一个新鲜提法,新鲜之处在于邓小平就实现现代化而做出的“改革开放”决策,这个决策意味着中国放弃了对现代化的诸多意识形态限定,而使之与世界的普遍认识和理解同步。简而言之,从邓小平开始,中国承认“现代化”作为社会历史的发展阶段具有共通性,其内容和指标是普适的,其诸种因素之间的关系也是有机的、整体的、不可人为割裂的,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必须与世界全面接轨。这就是“全面现代化”的概念。
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今天,中国不单在生产技术和手段、产业结构方面进行了适合现代生产方式的调整,也广泛引进了现代管理、现代金融、法律制度,对经济、政治、文化所有领域的运行机制加以改革。这一切,意味着中国接受了“现代化”的普遍标准,决心投身于全球一体化经济的现实。许多原先由意识形态而设置的障碍被排除了或搁置起来,姓“资”姓“社”的理论之争让位于现代化实践的过程并由后者来决定中国该怎样做。”
众所周知,在20世纪80~90年代以前,是传统的“共名”时代,而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则进入了真正的“无名”状态,“无名”时代真正来临。“这无疑都是传统的时代共名被消解的结果,人仿佛被突然抛入了无边无际的旷野,没有任何可以依赖的屏障,精神上只能是赤身裸体地摸索而前。人到这时候或许会为一瞬间的轻松感到庆幸,意识到以前思想所不堪的重负;但随即又不能不意识到这也是一种代价:释下重负的轻松不过是包裹在无名状态外面的表象,只要一思想,就会显示其万分紧张,因为你会看到一个真实的自己并不是全可依恃。也许在无名时代里人们并不会过于计较一些制约人类的统一标准,但问题是当事者并不会因为无人关注而不惊慌失措,这意味着一种内心的道德律在制约你。”
“无名”时代的作家与20世纪80年代前的主流作家、精英作家不同。如王朔的玩文学,借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主要是这么两条:一、“千万别把我当人”,二、“玩的就是心跳”。这是王朔奉行的基本的价值取向。而主流作家尤其是精英作家,他们对此的表现则分别是:一、“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北岛)二、“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北岛)因此,在“无名”时代,“城市不再只是“生产的城市”,城市文学也不再只是工业文学(“工业文学”已经成了一个历史名词)。城市作为生活空间与存在空间的意义被彰显出来,与“生活”密切相关的“私人性”(个体利益、生活趣、个人爱好、小我情感、私人空间)得到承认和尊重。”
此外,1978年底,知青一代开始了全面大返城,对这一代人来说,无疑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知青作家都生动地描述过大返城的情形,尤以黑龙江和云南两个生产建设兵团为最。邓贤回忆说:“在西双版纳,在德宏、红河、临沧、文山,每个农场都为知青返城敞开大门,成千上万的知青在场部办公室挤得水泄不通。在动撒农场,知青在场部外面围起里三层外三层的人墙,等待办理繁琐的回城手续:体检、政审、鉴定、提档、转组织关系、工资关系、粮食、户口,等等。其中唯有一项户口证明须由公安局盖章方才有效。于是农场唯一一辆破吉普车吱吱嘎嘎地开动起来,天天奔波于农场与县城之间。不料有天吉普车一去不复返,心急如焚的知青蹲在寒潮的霜冻里一连等了三天三夜,有人险些要放一把火烧掉场部。当那辆风尘仆仆的吉普车终于爬回农场时,年过半百的办公室主任一下子从车里滚出来,双膝跪在人们面前放声大哭:“不是我有意耽误大家回城,实在是别人放假不上班啊”。
因为在20世纪60年代初,尤其是“文革”中的1968年底开始,大批城市的初高中毕业生,遵循毛泽东发布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的“最高指示”。在毛80年代初期,中国城镇的经济逐渐繁荣,城市化进入了新的阶段泽东的号令下,或自愿、或被迫到乡村(或军队的“生产建设兵团”)去“插队落户”,这被称为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运动。
这一制度,一直持续到“文革”结束。知青插队的地区,一般为经济文化落后的省份,特别是新疆、晋北、陕北、云贵、海南岛的农村和山区,以及内蒙古草原、东北北大荒等地区。许多知青在“文革”中,经历了从“革命主力”到接受“再教育”对象的身份上急遽改变,经历了从城市到乡村、从经济较发达地区到中国贫困地区的生活变迁。
在20世纪50到70年代,文学延续着“根据地”和“延安文学”的传统。小说被认为是一种意识形态,是与欲望无关的“精神产品”。这个时代的文学观念和文学体制都被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文革”中,文学的这种“纯洁”性似乎达到未曾有过的境界。稿酬已被作为“资产阶级法权”的表现而取消,对文学的任何“消费”、“娱乐”成分的理解和阅读动机,都受到了批判。进入80年代以后,许多呼唤“改革”和“现代化”的作家,却对“改革”和“现代化”的“后果”——对中国政治、社会结构、文化形态和价值观念产生的深刻影响缺乏心理准备。他们面对一系列令其惶惑的现象和问题:当代社会的那种“统一性”(即使只是表面维持的)的瓦解;金钱、财富、经济活动在社会中的地位和重要性迅速加强;政治、意识形态至高无上的中心地位的削弱;国家对经济、文化活动控制的范围和有效性相对减弱;社会分层的趋势加速;个体的思想和生活空间的扩大,因社会经济地位和利益而形成的阶层,其生活方式和需求(包括文化需求)的分裂和多样化;“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学”的冲突,前者对后者的挤压;等等。上述诸种情形,规定了80年代,尤其是90年代中后期以后的文学(文化)格局。不仅是政治上的选择,而且面临“市场”越来越强大的选择力量,这对于作家的生存处境和写作道路的重新确立,构成了新的压力。”
但是,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当代城市吞噬着小说家,他们宣告了对于城市离心倾向,既承传着中华民族的精神传统,又反叛城市。“他们是城市人,即使他们的城市文明批判,他们对于城市的叛逆姿态,也是由城市培养和鼓励的。但他们又毕竟不同于消融在城市中与城市确然同体的城市人。更早一个时期颂扬吉普赛人,醉心于田园风情旷野文化的,也是一些困居城市备受精神饥渴折磨的城市人。他们未必意识到的是,只是在城市他们才奏得出如许的田园与荒野之歌,旋律中深藏着骚动不宁的狂暴的城市心灵。文学似乎特别鼓励对城市的反叛,这几乎已成近现代文学的惯例,成为被不断袭用的文学句法。因而作家作为“人”与城间的关系,又不仅仅是由其工作方式,也由其承受的文学传统、文学家家族的精神血统所规定。”
城市给人力量和美丽的憧憬,从而使它的小说家们为之倾恋,而满怀着美好期望,刚刚开始介入城市的小说家们也不可避免地陷入这种矛盾之中。“无论是任性地抗拒城市也好,还是坚定地走近城市也好,80年代之初的城市逻辑都逐步转化为一种普遍的历史实践。城市化以越来越快的速度走进越来越多的人的日常生活。城市开放而自由的精神在逐步地扩散,对于一个在闭塞而郁闷的乡村生活久了的国度来说,城市生活无疑传递出了最初的欢乐,就像直面新鲜而明媚的阳光。”
如诗歌《公共汽车售票员》所写:“我们希望翱翔于空中的鸽群/也像水上城市威尼斯的鸽子/像巴黎卢浮宫门前的鸽子(我们在电影和画片上见过)/收拢擦亮蓝天的双翼/悠然落在我们修筑的道路之上/落在喷泉飞溅欢乐的街心公园/落在大街拐角处的白色斑马线上/落在白塔似的交通岗亭顶端/安详地散步,并多情地/向老人和孩童喃呢咕咕……”
有学者说“20世纪80年代文学是个“共名的时代,20世纪90年代“无名”的时代”。
又有人说“如果20世纪七八十年代是一个从现实到虚构的年代,那么20世纪90年代则是一个“仿真”的时代”。
我们知道在这样一个“无名”时代,城市小说审美文本中的人物,已经从底层的革命者到建设者的积极分子,又演化为后革命时代的小市民阶层。城市小说文本中的人物形象的演变,“在现代中国现代审美文本历史中,勾勒出一幅生动的类型化审美形象群落的变化轮廓。当我们面对世纪末的欲望消费风起云涌的审美文本之时,不能不惊诧,似乎在一夜之间,操持革命大话的革命积极分子们,集体成为生意场、官场、情场协同操纵着的各类新的阶层。新的群众阶层“溶解”在各类斑驳陆离的叙事背景中,群众已经不是群众,而是个体户、小老板、股民、民工、下岗人员、小资、小偷或小公务员。革命的怒火熄灭了,而欲望之焰正成燎原之势。革命积极分子文化以神圣名义展开的施虐和受虐的游戏似乎结束了,以资本和市场为核心的大众欲望的虐恋表演在中国审美文本中刚刚拉开帷幕。”
“无名”时代的欲望之火,不是星星之火,而是燎原之火。如何描述和分析这个从1980年代后半期开始,首先在东南沿海和大中城市发展起来的“新意识形态”?“它们包括:“现代化”是人类共同的理想和必由之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是通往“现代化”的最佳途径;只有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才能实现自由民主;美国代表的西方是“现代化”的榜样;社会主义体制、计划经济、封建专制的传统:这就是中国“发展”的最大障碍;社会主义意味着神化“理想”和“崇高”,以精神压抑肉体;“世俗化”、“欲望”和改善物质生活的要求才是“现代化”的基本内容和动力;“市场经济改革”体现了“现代化”的潮流,只要这个方向不变,中国将很快赶上西方发达国家,变得富裕和民主;现在的所有社会弊病都是因为“现代化”不充分,没有真正与“国际”接轨,只要人均收入达到2000美元,这些弊病都不难消除;只要“现代化”了,所有的人都至少能成为中产阶级,有汽车和洋房……但应该看到,这些观念有许多并不十分清晰,边界模糊;它们也并不都有某一明确的学说作为公认的代表,而通常是散布在无数文字、图像和口头的表述当中。”所以,他说,“这十多年来,人们已经习惯于抱怨说,这是一个人心涣散、信仰失尽的时代,可你看上海,看那些与上海相邻或相似的地区,分明有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正在相当迅速地成形。它当然还没有完成最后的总结,还在不断地变化,但说它已经取代原有那一套“文革”式的权威意识形态,占据了这座城市或这些地区的精神生活的主导权,却是一点都不过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