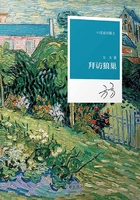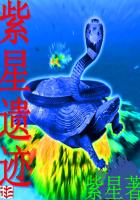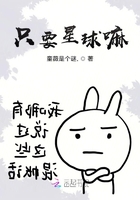岂只是“务头”必须使整体增辉才有意义,而且李渔认为,戏剧作品中的任何一个组成部分,都必须起到有利于戏剧作品有机整体的完整性的作用,而绝不能起相反的破坏作用。正是以此为出发点,李渔要求戏剧家重视每一个部分和局部的写作。他反复强调说:“一节偶疏,全篇之破绽出矣。”因此,他要求作家“每编一折,必须前顾数折,后顾数折。顾前者,欲其照映;顾后者,便于埋伏。照映、埋伏,不止照映一人,埋伏一事,凡是此剧中有名之人,关涉之事,与前此后此所说之话,节节俱要想到,宁使想到而不用,勿使有用而忽之”。他要求戏剧家“一笔”、“一针”都不可疏忽,因为“一笔稍差,便虑神情不似,一针偶缺,即防花鸟变形”,也就是说,“一笔”“一针”,都关乎整体和全局的完美。李渔对戏剧的开头、结尾、人物出场等等所提出的要求,也是从整体、从全局的观念出发的。他说,开头写得好,“破竹之势已成,不忧此后不成完璧”;而结尾必须“无包括之痕,而有团圆之趣”,自然、和谐、完美,“如一部之内,要紧角色,共有五人,其先东、西、南、北,各自分开,到此必须会合”,这就是要求戏剧自始至终的完整性。关于“出角色”,李渔认为,戏剧的主要人物因关乎整体和全局,不宜出之太迟;“即净、丑角色之关乎全部者,亦不宜出之太迟”。总之,要调动各种手段,写好各个部分,为创造完美的艺术整体服务。
为了使戏剧作品成为完美的有机整体,还必须注意戏剧的各个局部和部分以及各种组成因素之间的和谐统一。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学派有一种观点,认为美就是和谐。例如,他们认为音乐是对立因素的和谐统一,把杂多导致统一,把不协调导致协调。今天看来,如果把和谐看作是美的本质,当然是浅见的;但是,和谐,把杂多导致统一,这的确是美一一至少是形式美的一个重要条件。
李渔在许多地方阐述了和谐统一对整体美的重要意义。例如,他在谈戏剧中的情与景的关系时,认为只有情与景和谐统一,才能成为一个完美的整体。他说,那种单纯写景,“止书所见不及中情者,有十分佳处,只好算得五分”;他要求情与景的相互渗透,提倡“妙在即景生情”,情景交融。这里就涉及到中国戏剧美学的一个重要特点:意境,即讲究在戏剧中创造出一种完善的令人神往的境界,给观众以审美享受。这是中国古典戏剧发挥自己的审美作用的一个重要方式。关于这个问题,清末的王国维在《元剧之文章》中讲得最清楚。他说:“然元剧最佳之处,不在其思想结构,而在其文章。其文章之妙,亦一言以蔽之,曰:有意境而已矣。何以谓之有意境?曰: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入耳目,述事则如其口出是也。”有意境也称之为有境界。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还说过:“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因此,所谓戏剧中之意境、境界,主要是指抒情、写景、叙事,达到出神入化、完美统一、融为一炉的艺术境界。而李渔早在王国维之前二百多年,就对戏剧中的意境问题,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不过他用的不是“意境”这个名词。美的境界,当然包括情与景的统一;而与此相联系的,也包括神与形的统一,以及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同时,这美的境界也是作家的主观与被描写的对象--客观的完美统一,是上述诸对立方面的和谐一致。因此,不但情景交融对意境的创造十分重要,而且形神统一对意境的创造也十分重要。美的意境特别要做到神似。如果只是形似而没有神似,则如泥人土马,有生形而无生气,那就谈不上有什么美的艺术境界。戏剧意境中的情、神、内容,都属于内在的东西,并且是无形的,看不见,听不到,也摸不着;而景、形、形式,则属于外在的东西,是有形的,目可见,耳可闻,身可触。这两个方面,是不能各自独立存在的。无形的东西要通过有形的东西来表现。情离开景,神离开形,内容离开形式,本身就成为纯粹抽象的东西,不能被人感受,因而也就不能成为审美的对象;而景离开情,形离开神,形式离开内容,本身只是无生命的尸体,毫无存在的价值。这两个方面的脱离与分割,是对整体美的根本破坏。只有景中寓情,形足传神,形式充分地表现内容,两个方面契合无间、和谐统一,成为有机整体,创造出美的意境,才能给人以美的享受。当然,这两个方面也有侧重,那就是,重点在情,在神,在内容。李渔在《窥词管见》第九则中说,情景“二字亦分主客,情为主,景是客。说景即是说情。非借物遣怀,即将人喻物。有全篇不露秋毫情意,而实句句是情,字字关情者”。戏剧艺术只有以情、神、内容为主而做到形神、情景、内容形式的完美统一、和谐一致,组成一个有机的艺术整体,才能创造出鲜明、完美的意境,令人心驰神往,产生强烈的审美力量。
李渔还以塑佛开光,画龙点睛为比喻,说明一部戏剧作品作为一个完美的整体,其部分与整体、部分与部分之间,不能有任何不和谐的地方。为什么“塑佛者不即开光,画龙者点睛有待”呢?这是因为,只有等到全像告成之后,“其身向左,则目宜左视,其身向右,则目宜右观,俯仰低徊,皆从身转”。这也就是说,佛像(艺术形象也如此)的各个部分之间,以及各部分与整体之间,都必须保持和谐一致、浑然一体,才能收到良好的审美效果。特别是眼睛,那最善于传神的地方,更必须与整个形象保持最和谐的状态。如果眼睛与整个形象不一致、不协调,那就成了一个艺术怪胎,破坏了整体美。
李渔还非常重视和谐统一造成戏剧语言的韵律美。他认为,不论是唱词或是宾白,都必须讲究调音协律,以造成金声玉振的审美效果。唱词要合乎音律,自不待言;即使宾白,也须注意音律。李渔说:“宾白之学,首务铿锵。一句聱牙,俾听者耳中生棘;数言清亮,使观者倦处生神。”要求戏剧家做到声之平上去入,韵之清浊阴阳,都要和谐动听。当平者平,不用仄韵;当阳者阳,不用阴声。李渔以《南西厢》为例;批评戏剧创作中破坏和谐统一的韵律美的现象。他说,“词曲中音律之坏,坏于《南西厢》。”坏在哪里呢?李渔认为,主要是《南西厢》的作者在改编过程中,破坏了原作的和谐统一的整体性和韵律美,使一部“完全不破之《西厢》”,变成了“改头换面、折手跛足之《西厢》”。南本《西厢》,“聋瞽、喑哑、驮背、折腰诸恶状,无一不备于身矣”。
戏剧是名副其实的综合艺术。戏剧的整体美,还特别表现在舞台演出过程中,将舞台艺术的各个方面、各种因素,综合成一个统一的和谐完美的有机整体。李渔说:“词曲佳而搬演不得其人,歌童好而教率不得其法,皆是暴殄天物”,有了好的剧本,还必须有好的演员。戏剧艺术正是要在导演的统一指挥下,以演员的表演为中心手段,并且在服装、化妆、道具、音乐、效果(在现代戏剧中还要加上灯光、布景)等等艺术工作者的协作之下,创造出完美的整体的舞台形象。关于李渔对导演和表演艺术的有关论述,我们将在《李渔论戏剧导演》中详细介绍,兹不赘述。
戏剧作为一种审美活动,从艺术欣赏的角度看,既涉及审美欣赏对象(戏剧意境、戏剧形象),又涉及审美欣赏主体(读者和观众);还涉及审美欣赏对象和审美欣赏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艺术创造的角度看,既涉及审美创造的对象(现实生活),又涉及审美创造的主体(作家、演员);同时涉及创造对象与创造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等等。上面我们花了大量篇幅,着重考察了李渔怎样从戏剧作品的角度来看待戏剧的审美特性,具体地说,也就是李渔怎样从戏剧作品、舞台形象作为剧作家和演员的创作结果,同时作为观众和读者的欣赏对象的角度来把握戏剧的审美特性,以及戏剧的审美作用的发生及其特点。其实,李渔并没有把眼光局限于此。他同时也注意了审美创造主体本身--戏剧家的创作活动的某些特点(如想象、天才、灵感等)及其对戏剧审美活动的影响,还注意了戏剧家与观众在审美活动中相互关系的特殊规律。
戏剧家的写戏与道学家的写文章,在思维方式上是很不相同的。道学家的文章充满着“道学气”,说明他们是以抽象的推理的方式进行说教,他们要“劝善戒恶”,便要讲一篇“善”与“恶”的大道理,其中充满着“善”、“恶”等等抽象概念;戏剧家则不同,他们不是干巴巴地讲道理,而是借优人现身说法,谓善者如此收场,不善者如此结果,使人知所趋避,就是说,用具体可感的形象的方式,用潜移默化的情感传染的方式达到劝善戒恶的目的。戏剧家当然也要进行思维,但他们不是通过思维制造概念,而是通过思维来编织浸透着情感的形象。因此,这是另一种思维。我国古代的艺术理论家们,包括李渔,自然对艺术思维的性质和特点,还没有今天我们这样清楚的、自觉的认识;但是他们毕竟不同程度地接触到了艺术创作中思维活动的某些特点,例如,关于艺术创作中的想象问题,我国古典美学中就讲得很多,陆机、刘勰等人都早已有了专门论述。李渔对此也有相当深入的认识。他在好几个地方对戏剧家如何进行想象活动,作了生动的描述和说明。关于这一点,我们在《李渔论戏剧真实》中已经作了介绍,这里就不再重复。我现在只想强调指出下面一点,即李渔论述戏剧家想象活动的时候,特别注意了戏剧艺术本身的特点--戏剧要借优人在舞台上的表演,塑造人物性格。这是与诗、词不同的。因此,李渔特别注意戏剧家为了塑造舞台上的人物性格而进行想象活动的情况。他指出,戏剧家为了塑造出鲜明、生动、逼真的戏剧舞台的艺术形象,就必须做到“手则握笔,口却登场”,“既以口代优人,复以耳当听者”,处处考虑到舞台艺术的特殊性;在这样的前提下,展开想象的翅膀,写什么人,就要设身处地、身临其境,把自己想象成什么人,揣摩人物的心理状态,设想自己处在他那样的环境和他那样的地位,会怎样想、怎样说、怎样做,会有什么样的思想感情,只有这样,才能把人物写得惟妙惟肖。三百年前的李渔关于戏剧家想象活动的问题能作出这样的论述,确实是很高明的。
在阐述想象问题的同时,李渔还涉及到戏剧创作中作家主观活动的另外的一些现象,如今天我们常说的艺术天才和灵感等问题。关于灵感以及天才问题,我国古代美学家们也早有论述。例如陆机《文赋》中就描绘了创作中的那种“来不可遏,去不可止,藏若景灭,行犹响起”的灵感状态,说灵感来时,如风发泉涌,去时又如枯木涸流。然而他又“未识夫开塞之所由”。关于“才”,那就讲得更多了。例如,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多次讲到“才气”、“才性”、“才力”等概念,并且把“才”、“气”、“学”、“习”四者联系在一起,说“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郑”,并说“才有天资,学慎始习”。明代戏剧理论家王骥德在《曲律》中谈到天才问题时说:“天之生一曲才,与生一曲喉,一也。天苟不赋,即毕世拈弄,终日咿呀,拙者仍拙,求一语之似,不可几而及也。”并且认为,“大匠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也。其所能者,人也;所不能者,天也。”这种认为天才就是天赋之才的观点,当然并不正确。历代的艺术理论家,几乎没有不涉及灵感和天才问题的。李渔对戏剧家的灵感和天才问题,也阐述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天才就是天生的“异才”,犹如造物之生灵芝。灵芝无根,其生也,莫其然而然。有人说,人的天才虽无根,但“有茎”(即谓通过诵读可得)。李渔认为不然。“才犹禾苗,诗书犹粪壤,……才之种子不与焉,无才而诵读,读之既成,亦不过章句儒生而已矣”。天才,从根本上说,不能从后天得到,而是“填词种子,要在性中带来。性中无此,做杀不佳”,“强而后能者,毕竟是半路出家,止可冒斋饭吃,不能成佛作祖也”。李渔对天才的上述看法,当然是先验的唯心的;但是,考察他关于戏剧创作问题的全部理论,可以发现他也并不否认后天的培养、锻炼可以形成戏剧家的才能。他的《闲情偶寄》的《词曲部》和《演习部》的整个论述,就是向戏剧作家和演员讲述戏剧艺术的各种规律,并认为这些规律是可以通过学习、通过训练掌握的。李渔说:“山民善跋,水民善涉,术疏则巧者亦拙,业久则粗者亦精,填过数十种新词,悉付优人,听其歌演,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况为朱墨所从出者乎?”他以自己的切身体会,说明可以通过后天的实践、学习,培养戏剧艺术的才能:“语云:‘耕当问奴,织当访婢。’予虽不敏,亦曲中之老奴,歌中之黠婢也。”
关于灵感问题,李渔也多有论及。譬如,他认为戏剧创作,有时开手顺利,有时开手不顺利,其原因是所谓“机”与“兴”之有无。他是这样说的:“有养机使动之法在。如入手艰涩,姑置勿填,以避烦苦之势。自寻乐境,养动生机,俟襟怀略展之后,仍复拈毫。有兴即填,否则又置。如是者数四,未有不忽撞天机者。”这里说的“机”与“兴”,即是灵感。但灵感的出现,似乎全凭运气,你能“忽撞天机”,就能获得成功;但是能不能“撞”上“天机”,却没有准儿。在另一个地方,李渔谈到戏剧家在创作时,“有出于有心,有不必尽出于有心”,“心之所至,笔亦至焉,是人之所能为也。若夫笔之所至,心亦至焉,则人不能尽主之矣。且有心不欲然,而笔使之然,若有鬼物主持其间者,此等文字,尚可谓之有意乎哉。文章一道,实实通神,非欺人语。千古奇文,非人为之,神为之、鬼为之也。人则鬼、神所附者耳。”李渔的“鬼神所附”的话,很像柏拉图--这个古希腊的美学家认为,在艺术创造时,神灵凭附到艺术家身上,使他得到灵感,处于迷狂状态,写出优美的作品。此外,李渔在上述那段话里,实际上还论述了艺术创作中的“下意识”问题:笔先至,心后至;甚至心不欲然,而笔使之然。这不就是今天有些人所说的“下意识”或“潜意识”吗?这种现象存在不存在呢?当然存在。艺术创作中确实有作家自己还没有从理性上深刻把握的东西被写出来。但是切不可把艺术创作中的“无意识”或“潜意识”现象过分夸大。如果对这种现象进行深入考察,就会发现那所谓“下意识”,实际上常常是以平时的大量体验和思考为基础的。艺术家、戏曲家在创作中可能有某个时候、某种程度的“下意识”或“潜意识”,但从总体上看,他必须有清醒的理智和意识;倘若总是“下意识”、“潜意识”,那就同精神病无异,是无法进行艺术创作的。李渔当然不可能如我们今天这样对这种现象作出科学解释。他得出的结论是:文章通神,鬼神为之,人则鬼、神所附者耳。这就把问题变得神秘莫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