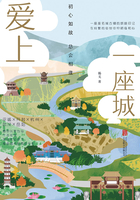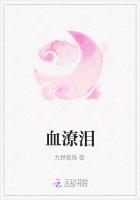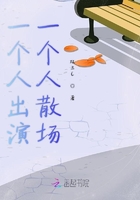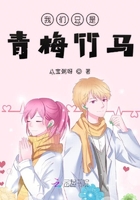我不知道如何形容我的心情,说悲痛罢,我的确还没有达到那样的程度,我不过是朱先生的一个普通的学生,普通到先生即使当面见到我,不管是在当年还是后来,都不可能认得。我没有那种朱先生在一群学生中一眼就认得出来的荣幸。
在五十年代中期,我对他所讲授的现代汉语没有多少兴趣。同学之中,醉心于文学的是绝大多数。在三年级分专门化课程时。志愿学语文的才只有百分之27。
然而我对于朱先生的现代汉语语法课程却十分欣赏。从欣赏到赞赏,以致于日后,不知不觉地产生了一种崇拜的感觉。这在当年像我这样多少有点狂傲的青年来说,是很稀罕的。
朱先生能把语言课上得那么出神入化,在中国大学中文系如果不是惟一的,至少也是少见的。哲学楼可以容纳二百多人的大教室,座位总是挤得满满的。我们年级文学班和语言班加起来才一百人。那些多出来的人,不是从哪里钻出来的。过道上,暖气管上挤满了人。每次上课都要提前去,否则就有站着听课的危险。
其实朱先生的课上得很朴素。
他没有王瑶先生那样风趣,那样博闻强记,也不像王力先生那样气魄宏大的理论构架,更没有系主任杨晦先生那样独创到不合时宜的程度。当然,他也没有何其芳、蔡仪先生那样大的名声。说起来,在那五十年代中期,北大中文系学术自由的风气还是十分浓郁的。杨晦先生在世界和平理事会宣布关汉卿为世界文化名人,全国大加纪念的年头,居然在论文中说,关汉卿并不像田汉在剧本中所写的那样充满革命热情,而是一个浪荡文人,可以说是在乌七八糟的环境中的一头猪。这引起了戴不凡先生的怒火,说是对关汉卿的污蔑。他轻描淡定地笑了笑,说我污蔑他干什么,他如果不是猪,在那种年代,他就没法活下去。
杨先生顺便谈到了夏衍把茅盾的《林家铺子》都给改坏了。本来是表现日本经济和军事侵略的,给他加上了一个资本家大鱼吃小鱼,就走了样。甚至连巴金,他也不以为然,说是他的作品不过是像中学生一样写得比较热情一点而已。我提出《家春秋》还是不错的。他说,如果把这三部删改成一部就好了。
在这样星光灿烂的学术巨星之中,朱先生无疑是一个后辈。他不以惊人之语见长,他的魅力不在片言只语之间,而在他的雄辩。
他上课不像游国恩先生那样发讲义,也不要求大家记笔记。每堂课只发一张油印的例句。他的观点,就从例句中分析出来,往往从第一个例句刚分析出一个观点,到第二个例句中,就变得行不通了,于是他就发展自己的观点,使之能够包容更广泛的客观事实。他不断平静地用最平常的语言材料揭露现有结论的不足,然后寻找新的解释,建构新的理论。
经过几个层次的曲折反复以后,他终于带领我们到了他自己相当独到的结论了。然而,忽然他又提出一个新例句,是和这个结论矛盾的,大家不禁愕然,他却坦然说,如果不用这个观点,而用别的学者的说法,可以避免这样的矛盾,但是他随手举出一连串的例句来,是其它学者的结论,不但不能解决,而且相形之下,那些结论显得十分荒谬。
只有在这时,屏声静息的课堂才开始轻松起来,一些语言班的同学禁不住点头赞叹,而我们文学班的同学也往往相视一笑,表示一种满足。
我虽然极端害怕语言课程,但朱先生的课却例外,每一堂课,我都觉得是一种享受。我逐渐被他迷住了。但我的被迷,并不像他的一些得意门生(如北大教授陆俭明)连走路都学他,我仍然对语言学课程敬而远之,但我却不知不觉被他研究问题的方法所黛陶,受到感染。这是我当时所没有意识到的。
直到许多年以后,我在编选自己的论文选集时,我突然意识到,我那些写得最好的论文,所用的方法,很大程度上,就是朱先生上课所用的。我逐渐发现,我写的最好的论文的思路,都是朱德熙式的,也就是类似剥笋壳的方式,层层自我非难,层层转折逼近的方法。
我觉得朱先生在某种意义上,用他的方法塑造了我(当然,除了了朱先生以外,还有普列汉诺夫)。
不仅在论文的写作方法上,而且我的讲课方式也深受影响。我本来是个矛盾的人,一方面心雄万夫,极望有所成就,一方面又十分自卑,特别是在六十年代,左得可怕的氛围中,我平均每二点九年就挨一次批判,当时,最大的愿望就是结束挨整的命运,因而对自己有什么优点,竟茫然不觉。
直到八十年代中期,由于广泛被邀请到各省大学讲课,我才知道,我讲课的效果还是挺不错的。意识到这一点之后,我不无认真地分析了一下自己的讲授方法,居然又发现了朱先生的剥笋壳的方法,层层转进的方法,自我非难的方法,是我讲授方法中比较突出的。
这就使我深深地怀念起朱先生来。
有时甚至想写一封信给他。
然而,又觉得也许是十分唐突的,朱先生不可能记得我这样一个学生。
92年在美国,误认为朱先生在华盛顿州立大学作研究,得了肺癌,西亚图又离我所在大学英语系不远。因而极想找到朱先生的电话号码,打一电话表示情意。一个朋友到西亚图去演讲,答应帮忙,然而不知怎么的,他没有弄到电话号码,而这时,香港文化教育出版社总编辑田小琳,她也是朱先生五十年代的学生来信嘱我慰问朱先生,我答应努力接着就是学期结束考试,考试后和我合作的教授夫妇请我吃饭,在另一个班上课的教授的丈夫告诉我,美国大学生对我的课评价十分高,有一个学生对他说,这个中国人是百分之二百的教授。他劝我说,你是一个很好的教授,我建议你不要抽烟。我告诉他我不抽烟。他抱歉他说,在他印象中,中国人抽烟的太多了。
由抽烟我又想起了朱先生的肺癌,不知朱先生抽不抽烟。田小琳那里,我还没有回信,朱先生在哥伦比亚大学医院逝世的消息却登在报纸上了。
受伤的蒲公英
——吴组缃的比喻
五十年代,在北大教授中,吴组缃先生的讲课是很叫座的。他是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一席之地的着名作家,和身为诗人的林庚先生一样有着精致的艺术感觉,但是不像林庚先生那样以诗人的潇洒的感性,对司空见惯的语言现象,作纯艺术的阐释。他的长处是警策,常常显出小说家对于生活的深思熟虑的洞察。他的精彩的论述往往并不限于艺术的理解,同时也饱含着对于生活的体验。可是他讲课的姿态说来很有一点冒险,手执一卷讲义,和当时最不受欢迎的念讲稿方式差不多。那薄薄的稿子,有时就是一篇并不太长的论文。但是他的所创造的奇迹是:薄薄的十几张纸,居然念到一学期还没有念完。
他每念完一段,就从容不迫地即兴发挥起来。讲稿上的,是书面语言的严谨的结论,而他所发挥的,则是他艺术创作和人生体验的结晶。
记得在讲到《红楼梦》中那些人物年纪都在十五岁上下,竟然发生了那么多刻骨铭心的爱情,连像茗烟那样的小孩子也发生了一些苟且之事。他先作了一个比喻说:你看,那路旁的一株蒲公英,如果它经过路人的践踏,就会提前开放出畸形的花朵来。这些个丫头、小厮,一个个被压抑、被摧残,结果是他们的生命在垂危之际,情感就畸形地开放了。正是因为这样,也就特别地凄丽动人。
吴先生的讲授,不但渗透着艺术鉴赏力,而且贯穿着生活的洞察力。从这一点来说,他比之任何其它教授都略胜一筹。也只有这样的双重的睿智,才能有吴组缃式的深遂和无畏。有一次,他给我们开了一个讲座。题目是关于茅盾的《春蚕》。当时众口一词地认为,《春蚕》中的老通宝是一个成功的保守的老农民的形象。他却认为,茅盾善于写城市生活,从根本上来说,不善于写农民。他笔下的老通宝就是一个分裂的角色。一方面,对于新鲜事物,新的科学技术,他是保守的,对于洋货他是敌对的。但是,在决策加大投人,借贷买桑叶时,又是非常冒险的。这种冒险性,事实上是吴荪甫式的,而不该是老通宝式的。他说,每一个作家事实上都有一个自己的模式,这种模式的力量相当强大,往往在不知不觉之中主宰着他,几乎是鬼使神差地让他往他自己的陷井中陷下去,最可怕的是,作家自己对此一无所知,当他跌下去的时候,他是面带笑容的,舒舒服服的。
正当我们被他的阐释迷住了的时候,吴先生却仍然从容地把手圈成一个空拳,举到嘴边,习惯性咳嗽几声,又继续他沉稳的讲授了。他在学生中有相当多崇拜者,每逢他上课,连向来懒散的,善于在课堂上瞌睡的宰予们一个个都正襟危坐。他的分析方式,不知影响了多少人,就连他的圈着手咳嗽的习惯后来影响到他的一个门生,等到他能够在北大讲台上讲课时,也常常情不自禁地作吴组缃式的咳嗽,不过他不仅仅是在课堂上,而且也在书斋里。虽然他这样做也许是不由自主的,但是却给人以假冒伪劣的感觉。
调戏谢冕教授
谢冕教授和我是老同学。年青时,一起浪漫,一起读诗,写诗,一起以发不正统的歪论为乐,还一起骂人,不过他骂得比较文雅,而我骂得比较恶毒。例如对那些思想比较僵化的同学,他最多说那些社会主义清教徒,而我就不过瘾,一定要接着说:什么清教徒,混教徒还差不多,一个个地瓜脑袋,只配到伪满洲国去当国民。
眼睛一眨,老母鸡变鸭,他成了诗坛权威了,又是北京大学的博士生导师,桃李满天下,有一次我在美国大学里遇到一个系主任,一个老美,好斗的女权主义者,泼辣(aggressive)得很,可以说辣气逼人,居然是他的学生,还对他敬礼有加。
他为人、做事、做学问都热情。六十岁不改当年的诗人气质。对诗的迷恋使得他比较天真。连到一个不起眼的地方去旅游都兴致勃勃,令人想到小女子散文家。
一帮子很有才华的戴着博士帽的门徒簇拥着他,用崇敬的目光织成光环的网络围困着他。虽然,我知道那些狡猾甚于聪明的博士们的真诚,是要打折扣的,但是,谢冕以大度雍容服众,如孔夫子一般,垂拱而治。开学术会议,有谢冕在场,气氛是自由的,但是又多了一份肃穆,没有什么人敢于像日常生活中那样以胡言乱语为荣,博士生们的黄色幽默笑话一概暂时储入内存。
进人谢冕的家就等于进人了诗的境界,博士生们情不自禁地把脚尖提起来。唯一敢于大大咧咧、嘻嘻哈哈、咋咋唬唬的,就是鄙人。只有我敢于告诉他,人家背后称他为文坛儿童团长。
适逢他主编的十本一套的百年中国文学思潮出版。第一本就是他自己写的。关于1907年中国文学的,这是一本相当学术化的书。比起他过去以才情取胜的书,这本带着更强的学术意味。其中有许多第一手鲜为人知的学术信息,书中有抒情地描述他在空旷无人的图书馆中读《清议报》的情景,尤其动人。在这套书出版的讨论会上,我说,此乃谢冕从以才华取胜转化为以学问取胜的里程碑。
他把才拿到的泛着油墨清香的样书展示在我面前;先不翻开内页,而是把封套里面的相片供我欣赏。说是比之书他更为满意的就是这张相片。得意之色溢于言表。我觉得,这的确是谢冕最好的一张相片。但是,我不想过分奉承他。我故意作异常认真的样子,把眼镜拿下来,端详了一番,点了点头。
他说,不错吧?
我又点了点头,说:端的不差。
他说:好在有思想深度,是吧?
我说:言之有理。这张相片有点像严复,又有点像郭沫若。但是,严复有思想而没有浪漫情调,郭沫若有浪漫情调而缺乏思谢冕满脸发出青春的光彩,期待我说出他二美兼备的话来。我让他等了一分钟,才说,你呀,既没有思想,又没有浪漫情调。
谢冕大笑。
性的高论:孙绍振比之谢冕更育诗人的激情。
谢冕很谦虚,说:我不是诗人,孙绍振才是。
我听了连忙走了过去,扶着他的肩膀说:谢冕什么都比我强,就是有四点不如我。
这一下子大家,包括谢冕,都感到兴趣了。
我清理了一下喉咙,慢条丝理地说:第一,吹牛。
满座欢笑。
人问,这第二呢?
我清理了两下喉咙:慢条丝理地说:放炮。
又是欢声四起,问第三是什么。
我更加从容地说:这第三嘛,就是骂人。
在欢笑声中,连谢冕也表示,在这方面他的确自愧不如。大家催我讲最一条。
我十分爽快地说:第四就是:造——谣。
全场热烈鼓掌。
我做了一个手势,请大家雅静,说,我什么都比谢冕强,就是一点不如他。
人问:什么?
我说,这方面的差距是十万八千里。
众人催:快!
我说:艳遇。
所有的人都热烈鼓掌。背朝着谢冕的都转过身来。
谢冕也鼓掌,说:这个猴子。
饭后,会还没有完,我有事,要先走。
北大洪子诚教授,也是我们老同学,对我说,你这一走,我们的会就只能光开会,而不能开心了。
我说,要开心也容易,只要像我一样敢于调戏调戏谢冕。
谢冤的书斋和童话
谢冕教授家的书迅猛地膨胀。当我来到他那显得窒息的书房的时候,不由得笑了起来。向来号称整饬的谢冕连过道里都罗着高及胸口的杂志,而他那书房则成了书堆的峡谷,我只能像海底的鱼一样侧着身子进去。
就在前不久,我听说,他宣布拒绝买书了。这究竟是幽默还是愤激,我没有细想。
倒是想起来他在香港的报纸上的文章,说是他需要一个书斋。当时我正在香港。觉得很是奇怪。内地的教授固然比较贫寒,但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教授多多少少有一点例外。因为他们得天独厚地可以轮流到日本或者澳门大学讲学。只要出去一两年,就有足够钱买下一套比较像样的房子。又听说,有一次,北大中文系已经安排他去澳门大学当系主任了。可是人们说,谢冕觉得这么长的时间,离开内地的诗坛,是不负责任的。那时,正好他的弟于张颖武先生在我那里,我就对他说,这个人真是个书呆子。一边叫着要一个书斋,一边又不肯出访。张颖武先生说:为这个事,谢老师还认真考虑了两天两夜。我说:活该,谁让他傻呼呼!
这次要到北京参加一个博士论文的答辩会,顺便就去谢冕家里去玩玩。看到他那越发变得狭小的书房,不由得嘲笑他的糊涂。既然要书房,就该去日本或者澳门一行。考虑什么在国内的影响,又不是毛泽东,当年他组织别人去法国勤工俭学,他自己却不去,说是中国的事情还没有弄清楚,暂时不去外国。
他哈哈大笑,说谢冕真是太重要了,中国简直一天都离不开他。听这口气我才感到传言有误。便把张颖武先生如何说的,告诉了他。他更是大笑不已。说,:这简直是一个童话,绝妙的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