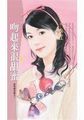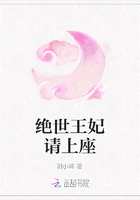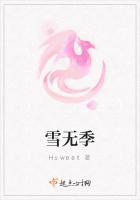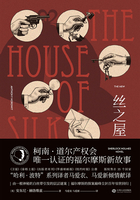史苇湘
我乘坐的破卡车离开兰州继续西行,地势越走越高,天空也越来越湛蓝明净,黄土愈多,青山绿树逐渐稀少,天与地似乎离得很近,离开一个一个绿洲城镇,连接它们的就是望不到边的戈壁滩,不但渺无人烟,也难见到有生命的一草一木,我们的卡车就像一叶小舟,漂浮在茫茫的砂碛里,我才真正体会到唐代诗人岑参所吟咏的“过碛觉天低”。兰新公路逶迤向西,仿佛没有尽头,过了嘉峪关,我已走了近四十天,和青山碧流,人烟稠密的巴山蜀水相比,完全是另一个境界了。
1948年9月24日,我终于到了敦煌县城,两条十字交叉的小街道,只有三五家底矮的小店铺开着门,街西有一座衰朽的同治年间的木构节孝牌坊,伴着几棵老榆树,树荫下有一个卖瓜的地摊,一个衣服褴褛、疲倦不堪的老年人躺在芦席上吸着烟,等待顾客。
太阳偏西不久,瓜摊、店铺就收业闭门了。到了下午9点,天还不黑,血红的太阳,像一个醉酒汉在天边摇摇晃晃不肯沉落。晚风骤起,一街尘土,几只野狗在空荡的街上窜来窜去,狺狺吠叫,打破了这荒城的静寂。
当晚,我和敦煌艺术研究所的一位会计住在一家商店里,半夜,突然街上喧嚷嚎哭,人喊狗叫,店主人说:“没事没事,外面抓兵。”虽然疲乏不堪,却不能入睡,我回想了四十多天的旅程,三千余公里,景物全异,惟有这“有吏夜捉人”的景象处处相同。
第二天我乘一辆去莫高窟的卡车,在没有路的戈壁滩上颠簸了两个多小时,终于到了目的地。一进窟区仿佛到了一个清凉世界,乔木高耸,浓荫蔽日。森严的岩壁、密集的洞窟给我的第一印象:这是一个庄严、静寂的小绿洲。
我被安置在一间小土屋里,和沿途住过的河西走廊的旅舍非常相似,屋里是土坑,土桌子、土壁橱、土书架,除了一个可以挪动的木凳,所有家具全是用土坯垒起来的,上面用草泥、石灰一抹,也居然光洁平滑、不潮、不塌,非常适用,当时我竟产生了《西游记》里水帘洞中的石桌、石椅、石案、石床的联想,我意识到将要过另一种有点神秘味道的生活,心里充满了新奇感。事务员老范(和我们一起生活了四十多年的范华同志)给我送来一盏铜质煤油灯,向我说这排房子是原来寺院的马房,是每年庙会群众拴牲口的地方,三年前才改造成职工的宿舍。
由于长途劳顿,好奇心与新鲜感终于敌不过三千公里和四十天旅途积累的疲乏,不到十点,我就在新铺的土坑上睡熟了。半夜醒来,皓月满窗,铃声大作,引起我一阵惊恐,原来是九层楼(第96窟)檐角上的铁马——风铃,每当夜深人静,从鸣沙山上滑下来的晚风就要将它“演奏”一番,后来,渐渐习惯,四十年来虽然它夜夜鸣奏依旧,我却早已忘却它的存在了。
当时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办公室设在中寺,一幢低矮的四合院中有两棵枝柯交错、浓绿满庭的老榆树,每株有两人合抱的围径,向西的门楼上横着一块乾隆四十五年立的“雷音禅林”的木雕匾额,证明中寺就是清初雷音寺,寺外有一片小场地,沿着场地就是南北延伸的围墙,保护着半截埋在沙里的窟区。要进入洞窟,首先要经过题有“西域胜积”的栅门。后来我才知道当时征调民工修筑的围墙还不到三年,就像在河西走廊上所见的古长城一样,已经断墙处处,残破不堪。
当时敦煌艺术研究所负责管理窟区,共有二十多个工作人员,流沙簌簌在危崖上漂流,像瀑布一样,窟前沙丘起伏,长着一丛一丛的骆驼刺和红柳,下层洞窟多半被沙淹埋,危岩残壁上栈道早毁,上层洞窟大部分要从清末王道士雇人毁壁凿成的洞穴穿过,好奇的是尽管这些破洞残壁如此褴褛,其中壁画与彩塑却处处神采奕奕放射着诱人的艺术魅力,诱惑着我要急切地去认识这个被人类历史遗忘了的艺术世界。
当段文杰、范文藻、孙儒、欧阳琳这些老同志领我第一次进入石窟时,我被这些古老瑰丽的壁画和彩塑惊吓的发呆了,假若说人间确曾有过什么“威慑力量”,在我充满三灾八难的一生中,还没有一次可以与初见莫高窟时,心灵上受到的震撼与冲击可以比拟。当时,我很快就回忆起1943年在成都为张大千先生的“抚临敦煌壁画”展览会上服务时,见到的那些大幅壁画摹本,如何使我动心,大千先生为我解说敦煌壁画时说的“要做一个中国画家,一定要到敦煌去”的谆谆教导,5年以后的1948年秋天,我终于进入了莫高窟,才发现展览会上我见到的不过是千分之一、万分之一而已,而且那些精湛的临本,是张大千先生以他精深、睿智的艺术慧眼理解研究过的艺术,今天这些壁画海洋的原貌就在我的眼前,陆离斑驳,五光十色,处处有人类历史的足迹,也有人间的幻梦……
当时,我刚从艺术专科学校毕业,五年中学到的绘画基本技法和一些初步的装饰画原理,以及一点西洋美术史知识、美识常识,就要来换取进入敦煌艺术殿堂的“门票”,显然是太自不量力了。
但,作为一个风尘千里的朝圣者,我终于踏进这座圣殿的门槛了。
初到莫高窟,我是处在一种持续的兴奋之中,既忘却了远别家乡离愁,也没有被天天上洞上窟的奔波所苦,仿佛每天都在享用无尽丰美的绮筵盛宴,白天看到一顶又一顶华丽的藻井,一壁又一壁宏丽的经变,一身又一身的生动的彩塑,晚上往往不能入睡,在煤油灯下翻捡笔记本,核对了窟号与壁位,生怕以后再找不着它们,同时又悬念着,明天又会看见一些什么使我激动的形象呢?会不会有更为生动的飞天?更为优美的菩萨,更为富丽的图案?……我初到莫高窟的一个月,天天晚上都是在这种为艺术幻梦的悬想中进入梦乡。
后来,看的洞窟越多,我越迷惘,越不知所措,宝贵的东西太多了,几乎每个窟都有可取之处,一些著名的代表洞更是美不胜收。巡礼一月,我渐渐感觉自己有所偏爱,由于在学校里最后两年,十分着迷印象绘画,那个授课的欧洲教师特别注意训练我们的色彩感觉,启发我们在外光里组合色彩,而敦煌壁画对比强烈,鲜明艳丽的色彩经验,历时千载,尚如此惊心夺目,更不用说五至六世纪那些虽已变色却古朴典雅的色彩处理十分接近现代艺术某些表现手法……
绘画的另一重要特征,就是用笔墨色彩表达对美的感受,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莫高窟几乎无处不在作这样的追求,那些流畅明快的线条,所表现的夺壁欲出形象:沉思庄严的佛陀,雍容妙曼的菩萨,谨淳忠厚的佛弟子,威武雄壮的天王……还有那些壮丽的楼阁,活泼跃动的飞禽奔兽,透明的水池,娇艳的莲花……每一个洞多像我小时候玩过的“万花筒”,决不重复地变换着场景,虽然我也意识到,这些形象不仅有它外在的美,一定还蕴含着一个又一个故事与史实,但,我对它们还一无所知。
如饥似渴的参观,仿佛着了魔,甚至那些破墙残壁上的两块颜色,三五条线描,都会使我一顾三盼,流连忘返。
当时我只有二十四岁,在四川虽然看到过许多画展和少数几个博物馆,相比之下,还没有一处比得上初到莫高窟,见到敦煌壁画时令我如此些激动,如此新鲜。
当时生活非常严峻,这里的一群知识分子却能埋头专心工作,一日两餐白水煮面条和清汤白菜、萝卜,维持着生命的最低要求,但是在精神上都非常富有,上洞下洞,孜孜不倦,天天如此,毫无怠意。很容易就接受了这种精神的感染,谈石窟里的事情就成为生活中的重要内容。
在尝试临摹之前,我先去当见习学生,参观段文杰、范文藻诸位先生临画。在粗糙的白麻纸上,段先生正在用自制的红土挥毫勾勒,描绘北魏下层的“金刚力士”刚劲的线描,画出了一群力士在山峦间奔驰跳跃的情景,背景是大片脱色的土墙,涂上去的颜色竟和剥落的墙壁颜色完全一样,我好奇地问他:“这是一种什么颜色?”他幽默地说:“遍地都是。”原来他们用的就是窟前由大泉河水冲积的细泥,澄去沉沙,漂出细泥,加胶水磨制而成。不用调和,自然就和一千四百年前的墙泥一样。难怪每天晚饭后聊天时,都是人手一钵,在研制第二天上洞时用的颜色,这些颜色是刷墙的红土、医药用的锌白,当地画工画神像用的“鬼子蓝”、“鬼子绿”,经过他们仔细加工,适当地运用,竟能临摹出十分上乘的临摹本,当时材料奇缺,许多颜色、纸张多是就地取材的代用品。董希文先生临摹的428窟的《须达拏太子本生》,甚至使用的是最劣等的染料。
至今还清晰地记得,我学习临摹的第一个洞就是著名的第285窟。当时我并不理解西魏大统四年——五年铭文的时代意义,只是热爱这个洞形象生动,线描与色彩完整,特别是窟顶“天体”奔驰的动物,翱翔的飞天形成的飞动感和绕窟顶一周的禅僧们,他们用周围的山林泉水和各类动物所表现的自然意趣,令人十分着迷,画了一个礼拜,临摹出好几幅小品,当时还有点“自我感觉良好”,谁知比我先到此两年的老同学范文藻君,怕影响我的情绪,背着我向欧阳说:“老史用的西风画线描。”我知道这些评论之后,才从唯形象美是崇的艺术激情中冷静了一点,反思了我的基础。
面对如此博大精深的遗产认真地作一次自我反省,是在莫高窟工作之前必要的思想清理,当时还不懂得总结二字的意义,现在回忆起来很有味道,进入莫高窟就像步入一个琳琅豪华的粮果店。主观上多么想什么都尝一尝,对北魏、西魏、隋、唐、宋、元各代壁画都想临摹一番,去探究它们是怎样画的,可是,我的味觉有多少品尝能力?我的技法有多少表达能力?我的肠胃有多少消化能力?
事先我思想上毫无准备,仅凭那一点艺术热情,仿佛自己什么都能干,及至一接触实践,才发现自己与敦煌艺术还有相当距离,要真正入门,还须作长期艰苦的努力和漫长的跋涉。
当然,在学校里我还自命是一个勤奋的学生,读完了中国通史和外国史,加上幼年的古文经文训练,具备了一些阅读能力和写作技术,临到毕业,我的油画制作是以一幅用调色刀刮抹出来的《灌县风景》而得过奖,到艺专的第十学期,才学完西洋美术史:从文艺复兴到印象派。幸运的是上了两年美学课,一位老师讲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一位老师讲蔡仪先生的《新美学》,当时学生社团聘请一些校外学者来校讲学,1947年,我还听过洪毅然先生的美学讲座,加上自学的哲学、文艺理论,也埋头于各类时评政论,地下放着各种刊物……像一个杂货铺。临到要到敦煌之前我才经老师介绍,在四川省立图书馆选了向达先生翻译的《斯坦因西域考古记》中一些有关敦煌的章节。
来到莫高窟,面对如此巨大的艺术宝库,我当然会感到瞠目不知所对。主观上认为临摹工作似乎容易一些,听了同事们的议论,我才感到在这里要进入“角色”,需要一切从头开始,重新建立自己的学习秩序和认识方法。然而要认识它,又谈何容易,例如1948年深秋,我在285窟,南壁禅窟之间的一组人物,只觉得它形象优美,色线鲜明,内容是什么?我一无所知。要到十五年以后的1962年春天,我才读懂了它,给他命名为《沙弥守戒自杀缘品》。
当时的莫高窟,千疮百孔,荒凉破败,尽管经过几年的抢险、补危,有如杯水车薪,由于经费、人力、交通、物资样样奇缺,好心的愿望只能写在纸上。眼看风沙、阳光年年岁岁剥蚀着座座宝库,冬天的积雪,秋天的暴雨,夏天的骄阳,春天的狂风威胁着每一个洞的通道、窟门和下层洞窟,不知有几千平方米的宝贵壁画被大自然吞噬,身临其境的人除了着急,只有摇头叹息,束手无策。
许多下层洞窟被积沙壅到窟口,三四米高的大窟门被填得只剩下一条十公分的缝隙。至为宝贵的藏经洞就是被这不知多少岁月的风沙雨雪逐渐撬开的,王道士所谓“发现”,只不过是一个偶然的原因,我望着16窟甬道壁画上一条又一条风沙雨雪留下的啮痕,仿佛是垂危的民族文化老人额上数不清的皱纹,一种沉重的压力落在我的心上,感到无限的凄楚与恐惧,这时候我对敦煌与莫高窟知之甚少,从一个年青的美术学徒的感性上,已经意识到它是我们民族的骄傲,到莫高窟才一个多月,我就受到了先行者们的感染,生活虽然艰苦,以段文杰为首的一群年青人,情绪总是那么乐观、饱满,在常书鸿先生的领导下,能够在这里坚持下去,我逐步理解他们甘心投身在这片戈壁滩上,行为就是无限悲壮的誓词,因为莫高窟并不能任凭风吹雪打,任凭虎去狼来,虽然这群人在当时尚无回天之力来救它,却不能让它自生自灭。
我的同学孙儒同志,早我一年来到莫高窟,这位从建筑专业毕业,本应和钢筋水泥、现代建筑打交道的人,丢掉当时无处施展才能的内地,来到敦煌搞文物保护,和技工窦占彪、木工周德信,以土坯、草泥、木材为原料,土法上马,搞设计施工,这里支根杉木,那里修座便桥,这里砌几级台阶,那里加一段栏杆,因陋就简,就地取材,在当时也可谓尽力而为了。
窟外的修修补补,只解决了部分交通问题,千疮百孔的洞内,壁画将要脱落,彩塑已经倾斜,早年被破坏的残塑、残肢、断头到处都有,还有那些悬空突出的古代木构窟檐,其危险程度,令人望而生畏,说它岌岌可危,还不如说是在那里苟延残喘,不知道哪天一阵狂风,就会使它飘然而下粉身碎骨……特别是那些题记清晰、彩绘鲜明的北宋窟檐,每一座都是无价之宝,还能承受多久风沙雨雪的摧残?灾难逆料,回想到当时是在危难中如何认识它们的价值,又如何在认识中不断增加着越来越沉重的忧虑,当时国民党政府把大量的社会财富投入反人民的内战,何曾想到这些石窟的安危?仅凭少数几个先知先觉的文化人的呼吁,又能起多大作用?想到这些国宝家珍的命运,只有不寒而栗。
当时这批食不果腹的年青美术工作者,孜孜不倦的临摹工作,目的就是通过将来的展览用敦煌艺术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向社会呼吁,像张大千、王子云、常书鸿诸位先生所做的那样。但,当时一些有重要的壁画的洞窟大多道路不通,孤悬在崖壁上,敦煌遗书所说“悉有虚栏通达”的栈道,早被焚毁,只剩下崖壁上的梁孔、椽孔证实确有过栈道存在。要临摹一幅壁画,是一次艰苦的体力奋斗。我到莫高窟不久,就参加了搬蜈蚣梯的活动。我们一群男女青年,为了送一个同志到没有通路的高处洞窟里去工作,大家齐心协力,搬运一根五米多长的独木梯,粗壮的圆木上,钻有距离相等的圆孔,插入一根根短圆木,像一条百脚蜈蚣。先将这种梯子放进洞口,上去一个人,并用绳子把画板、画架、颜色箱水瓶、水罐,一一吊上去,这在当时是一件很有趣的集体活动。为了竖起笨重的梯子,大家吵吵嚷嚷,喊着号子,有说有笑,打破了石窟的静寂。只有到了敦煌,亲身实践,才懂得古代画工的辛苦,要征服一面又一面20~30平方米的壁画没有摩顶放踵的吃苦精神,俯仰伸屈的艰苦劳作是画不出来的。虽然也是绘画,决没有什么“明窗净几”、“逸笔草草”、抒胸中之逸气的潇洒感。
当时生活的困难,已到了最低点,几个月发不出工资,仅有的一点经费养活不了一辆破卡车,留在这里的人,也没有经济能力“逃回”内地。难怪在我之前已经来过多少青年画家和学人,都由于这个难熬的生活环境和种种原因先后离去,临到1948年冬天,莫高窟就只剩下常书鸿先生和我们七个年轻的业务员。这里与外面的世界完全是封闭的,听不见新闻,看不见内地的新书杂志,仅有的一份兰州出版的《和平日报》要半个月到20天才能到达莫高窟,看病购物要骑毛驴进城,从城上回来的人才讲一点在县城里道听途说的“新闻”。更为可怜的是这个“研究所”当时只有一部残缺不全的聚珍本“二十四史”,被尘封在柜子里,很少有人去用它,只有进洞临摹壁画是唯一的乐趣和最大的慰藉,有时互相去看看临摹品,交换一下技法上的经验,请早来两年的段文杰先生做一些指导,除此,天外的世界是个什么样子就无法知道了。
十月的晚秋季节,莫高窟的树叶在一片一片地飘落,几天前还是一片赭黄色的丛林,逐渐变成一片灰褐色,银白杨的树干和枝条完全裸露出来了,衬着湛蓝的天空,在太阳光下格外耀眼,河谷的秋风虽然已有寒意,窟内却十分暖和,罐子里的水还没有结冰,颜色在纸上还可以铺平,这时候临摹工作还在进行。
一场初雪之后,大泉河结了一层薄冰,后来冰河越来越宽,我们一群男女青年,头戴皮帽、棉帽、头巾,穿着七长八短的棉袄、皮裘,脚上穿着笨重的毡靴,抱着他们的画板、颜色箱、画架、测量仪、皮卷尺,从洞窟里撤下来了,在落叶满地的沙路上吃力迈进着,远远望去,像一群逃荒的流民,但是他(她)们仍然有说有笑,在萧瑟的寒风中也没有忘记幽默。他们从石窟上撤下来,准备在一间狭窄的装有铁皮炉子的工作室里窝冬。
就在这一年的12月,一辆美国军用吉普车,越过冻结的冰河,送来一对年轻的美国考古学者温生特夫妇,他们裹着毛毯,疲惫不堪,十分狼狈,大概没有料想中国西北的严冬竟是这样寒冷,陪他们来的是有名的考古学家陈梦家先生。在莫高窟工作了几天之后,来到我们唯一装有铁皮大炉子的工作室,炉子里燃烧着潮湿的红柳与梭梭柴,一端吱吱淌水,另一头着火喷烟,熏得满室烟气呛人,他们看了表示惊讶,急切地说:“在这样艰苦的环境里你们还能坚持临摹与研究工作,你们的政府(国民党政府)一定会给你们很高的报酬吧!”我们听了哄然大笑,由于我们笑得很爽朗,很感染人,使一到莫高窟就不断叹息,十分同情我们所处困境的陈梦家先生也破颜苦笑了。
实际情况,当时的研究所已断绝经费数月之久,职工们早已借粮而炊。
这两个年轻的美国人是以美元帝国的价值标准来衡量世界上的一切。他们不能理解,莫高窟对于中国人的价值,不是任何物质财富可以衡量的。
回首往事,四十二个春秋已经匆匆过去了,初到莫高窟的第一印象在逐渐褪淡,也许将会泯灭,可是我和敦煌艺术初相见时的心灵碰撞却至今难忘。也许正是那点初相见时的狂热,就注定了未来漫长岁月中的锲而难舍,从佛教的姻缘观来解释,似乎与你有缘,这种关系,真有点既在意料之中,又有点相见恨晚,作为代表民族文化的实体,你是一代又一代有血有肉,有创造力和想象力的先民们制作出来的,你不应该被后人遗忘,而让外国人来主宰你的命运。……也许就是这一点“一见钟情”与“一往情深”造成了这四十多年我与敦煌石窟的欲罢难休。
我也曾短暂地离开过你,无论从下放地——古效谷城所在地黄渠荒原回来,还是从繁华的巴黎、热闹的东京回来,我总要沿着走廊、上下磴道去看你,一个窟一个窟重新检点那些我早已熟悉的壁画的塑像,对你作一番重新认识,多么像诗人杜甫于七世纪时在四川所写的“山城多变态,一上一回新。”每次远别重逢,我总会在窟内发现新问题,看到一些新现象,估量出一些新价值,其实石窟艺术没有变,只不过是我在比较中多了一点认识你的能力。宋人诗中曾经自诩“云水光中洗眼来”,的确,我是在辛劳的汗水中,喧嚣的现代文明中和远被东海、地中海、阿拉伯海的波光雾影中一次又一次洗了眼,不断看到你崇高的意义和不断增长的价值。是的,每次暂别归来,我心里总是要为莫高窟上一次“尊号”。
大概由于年久月深,对莫高窟的“底细”知道得比较多了一些,四十年前初相见时那种仅仅从视角上见到的艺术魅力,所引起的激情逐步冷静了。纵览历史,横观世界,我对莫高窟的理解与联想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广阔和深远,也许由于各种价值观念在我的心上积压得越来越沉重,深深感到思维反映有些迟钝,语言开始晦涩,很难全面而概括地表达出我对莫高窟的情怀,我也深悉现状,我是在衰老,而伟大的敦煌艺术却青春永在,魅力长存,将会一代又一代激励着后来的献身者,他们会在你伟大怀抱里继续发掘我们民族无穷的智慧。
*原载《敦煌研究》199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