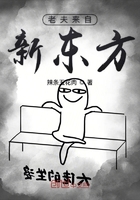满是淤泥的黄河河滩上,一队队骨瘦如柴的河工正吃力的劳作着。
放眼望去,蚂蚁一样聚集的河工将这一段百余里长的黄河都裹得严严实实。
而在骄阳之下,一群大元的低级武官此时正聚在河堤上指指点点嘻嘻哈哈。
“想不到朝中大人恁大闲心,居然管这些南人的死活。要我说,这黄河开也就开了,管他作甚,河滩上长的了草,就养的了牛羊,何必费这白花花的银钱。”
“哼!这可是脱脱老大人的主意,他是咱蒙古人有名的贤相,看的自然比我们长久些。”
“脱脱虽是素来贤明,可今次恐怕是有些痴傻。这修黄河的银子虽然不少,但拨下来由老爷们层层经手,现如今别说这三十万河工的吃用,就是咱们这些兄弟都有些看不上眼。”
“你、你怎么敢说脱脱老大人的坏话!”
蒙古人本就烈性,一群武官说着说着就要打起来。
好在有和事老赶紧止住双方,压低声音往后一瞥,“崽子们不要命了,这般喧嚷?若惊扰了国师,人人死不足惜。”
这么一说,众人一时都噤若寒蝉,把敬畏的目光投往不远处的大柳树下。
那里正有一位宝相庄严,穿着金色僧袍的喇嘛凝视着那些蝼蚁一样的河工。这喇嘛身上流传着说不尽的吉祥宝光,大柳树下只静静一坐,也像是在尘世之外的一片小天地看这芸芸众生。
这人正是大元朝的国师,活佛八思巴。
众多武官不知这位活佛怎么忽然来了兴致要看黄河,但见他在这柳树下满脸凝重的一坐就是十日。
武官们都震惊不已。
这世上竟然还有能让八思巴活佛脸上失色的事情!
正想着,下面的河工忽然喧闹成一团,越来越多的河工正向一处聚集!这样不同寻常的动静,很快让其他不知情的河工也躁动起来。
“怎么回事?!”
很快就有监工飞驰下河堤,挥舞着鞭子冲入人群。
众武官正纳闷着,已有监工将消息回报,“好像挖出了什么东西。”
“哦?莫不是什么宝贝?”武官们相互看看满脸喜意,一个个翘首等着。
不一会儿,一个监工用马鞭拨开众人骂骂咧咧的走了出来。后面则跟了两个苦力,脚步沉重的将一个物事抬上河堤来。
武官们都拿架等着,有眼尖的早看清了苦力们抬着的那物事。
那是一个半人大小的石头人,只是不知经过多少岁月,青苔浸染的已经满是幽绿幽绿的光泽。石头人的四肢尽皆断折,就连脑袋上也有一道重重的刀伤,只留下一只完好的眼珠。猛一看上去,只觉得分外狰狞。
苦力们将石人抬到近前,众人看个了分明,当即都有些失望,“嗨!以为挖到了什么宝,只是个破石偶,还是个一只眼的货色!”
武官们正耍闹,那个面目狰狞不堪的石人身上忽然渗出血迹,一字一字血红浮出来。
“莫、道、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
“啊呀呀呀!”
蒙古人崇信鬼神,看到这样惊悚的一幕,武官们头皮一乍当即吓得哇哇大叫起来。
随即一道冲天戾气忽然从石人身上激发。
宛如白虹贯日!
那些长期受到压迫的民夫只刹那间都觉得一腔郁郁之气在心中愤懑难安。
忽一人大叫“反了!”
转瞬间三十万人齐声大叫,“反了!反了!”
河工们的齐声大喝恍如密雷一样滚滚的在黄河两岸回响,那些正要冲过去镇压的监工都面如土色的停下脚步一步步后退。
活佛八思巴凝重的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谜团揭开,他却没有大欢喜。
一身金光闪耀宝相庄严的活佛沉默的站起身来,招招手唤来跟随的小沙弥回了大都。
旬日之间,天下大乱!
————————————————
大明朝正德年间时候,东南诸省已经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经过几代人的休养生息,市民黎庶都渐渐尝到了太平安乐的滋味。
正值踏春的时节,金华城外更是游人如织欢声笑语。
不过却有一行人行色匆匆,有些格格不入。
领头那人三十多岁,中等身材,身穿宝蓝色棉罩甲,头戴圆顶幞头,脚踏粉底皂靴,手中握着一把煞气森然的绣春刀。面相虽然方正威严,脸色却阴沉的可怕。他身后跟着的一众力士也是各个风尘仆仆煞气森然。
那些游玩百姓有些见识的,认得正是锦衣卫武官的打扮,都变了脸色纷纷走散。
自从天子重开锦衣卫以来,这些杀人不眨眼的恶棍,都被百姓们视为灭门灾星唯恐避之不及。
被这些锦衣卫围在中间的是一个脸颊枯瘦、邋遢不羁的中年文士,旁边鞍前马后伺候着的还有两个二十来岁的年轻学子。
脸颊枯瘦的中年文士叫做王守仁,去年冬天的时候因为宦官刘瑾擅政,逮捕南京给事中御史戴铣等二十余人。王守仁上疏论政,却不料触怒了刘瑾,被施廷杖四十,谪贬至荒蛮的贵州龙场当龙场驿驿丞。
他的两个弟子不忍恩师遭难,决定一路随行。长的温文世故些的学子叫做王艮,另一个身材粗壮有些跋扈骄傲的则叫做聂豹。
兴许是赶路太急,几人脸上都露着疲惫倦色。
只有最后那个一路东张西望的年轻和尚,披着一件颇显妖异的大红袈裟,左手托着一个乌黑的钵盂神色悠然。
这和尚二十七八岁摸样,面颊方正柔和,眉目明朗,颇有几分儒生像。
他背上背了一个帛卷,里面似乎缠着一卷画轴,负在身上看上去有些不伦不类。
这一行押解本来顺风顺水,谁知道司礼监掌印太监刘瑾竟然睚眦必报,一路派出多股人马追杀。
好在护送王守仁的锦衣卫百户崔伯候武艺高强心狠手辣,再加上王守仁的弟子聂豹又是个有大本事的浑人,这一路押送,崔伯候手下的锦衣力士折损了不少,王守仁倒没伤到分毫。
但谁知,随着追杀的继续,竟陆陆续续出现了不少的左道妖人!
崔伯候和聂豹虽然武艺绝伦,但是对上那些旁门左道不但占不到什么便宜反倒吃了几个大亏。一时间,竟是人心惶惶,忧虑不安。
前些日子路过一个县城的时候,正好遇到一个在为大户人家做法事的和尚,因此在王艮的一力坚持下,由他自掏腰包求了这和尚同行。如今已经有七八日了。
带队的锦衣卫武官崔伯候抬眼瞅瞅将落的日头,眼光闪烁,只一犹豫,低喝一声,“这边走!”
说着引着众人偏离了官道,只管往道旁幽深荒僻的林中钻去。
“嗯?”
似乎察觉到什么,那悠然徐行的和尚忽然一顿停住了脚步。
温文学子王艮见状,忙笑着向他解释,“法师,现在满朝文武都惧怕讨好那阉贼,若再一路走官道,只怕沿途官员拿捏我等,不如且从小路绕行。”
年轻和尚点点头,认真道,“老板不要叫我什么法师,我也只不过是把别的和尚撸管的时间拿来多读了几本经书罢了。”
口中虽然谦逊,脸上却带了几分自豪。
王艮脸上一僵,眼神有些直,“老、老板?”
“是啊。”
王艮脸色震惊有些不能接受,“不是应该叫施主的吗?”
“可我没有白拿你的钱,我是做工了的。我既然堂堂正正的靠自己的汗水赚钱,当然应该叫你老板。”
“是、是这样吗?”王艮不停地擦汗。
旁边的聂豹闻言冷哼一声,满脸暴躁。
在聂豹看来这和尚如此年轻,怎么能有那降妖伏魔的神通。而且每天的要价竟有四钱银子,十足是个黑心宰人的主儿。
聂豹平日对这些欺骗愚夫愚妇的僧道最是不耻,忍不住暴喝一声:“呔!臭和尚,你整日价哄俺师兄的银钱,这一路哪见你降过半个妖人!”
和尚闻言不慌不忙,“你且让妖人来见我。”
这几日许是运气好,倒真没有妖孽作祟。
和尚滑头的回答让聂豹气往上冲,忍不住就要拔拳相向。
这几日二人争吵非止一次,王艮早有经验,赶忙上前架住他的师弟,“不可对法师无礼。”
正吵闹间,一个锦衣校尉皱眉看看崔伯候选的那条小路,回忆了半天,凑上前去对崔伯候耳语了几声。
崔伯候有些吃惊的和他对答两句,接着眉头紧锁。
旋即心中一动,向那年轻和尚走来。
崔伯候仔细端详着那和尚,说话自然而然的带了几分官威,“那和尚,这几日相处,本官还不曾问你姓名。”
那年轻和尚见官爷问话不敢怠慢,“大人叫我韩穿便是。”
那官爷顿时有些惊奇,“怎么,和尚仍用俗家名字?难道尊师没有赐下法号,你身上可有度牒?”
韩穿暗道不妙,不愧是官府中人,一问就问到了紧要处。
像他这样的野和尚,身上哪来的度牒?!
不过他也不慌不忙,随口就是胡言乱语。
“大人想来不知,出家人又分为方外之人与方内之人。方外之人拜佛,方内之人度众生。贫僧是方内之人,修的是红尘法门。若真要拘泥,你称我心魔和尚便是了。”
众人听了,尚未细思,就有一锦衣小校张嘴就骂,“笑话!你是心魔和尚,老子还是无生老母呢!”
崔伯候一怔,忙看那小校。
小校哼一声,向崔伯侯道,“大哥,我来东城司之前是替镇抚司管来往文书,那心魔和尚的缉捕文告都悬了百余年了,今日倒让我见到冒认的了。”
崔伯候经他提醒这才模模糊糊的记起来,当年辅弼洪武帝大破蒙元的皇觉寺八部众中的确有一个叫做心魔和尚。
只是后来靖难之役,人人谣传建文帝朱允炆是化装成和尚潜出皇城,因此嫌疑最大的皇觉寺僧众立刻成了永乐皇帝朱棣的眼中钉肉中刺。
随后不知为何皇觉寺一夜间分崩离析,八部众流散江湖,到如今已经不知过去了多少岁月。
这世上欺世盗名之辈颇多,崔伯候也懒得计较这些。
他从差役捕手做起,到了今日地位,思虑自然老辣,当即不理这个话茬不动声色的问道,“拜佛我等晓得,却不知方内人要如何渡众生?”
韩穿眼睛一亮放言道,“自然是做法事了。只需要全心全意的做个道场,自然消灾解忧,遇难成祥。”
听到这个有些坑爹的答案,崔伯候脸色阴沉。
当即他冷冰冰道,“和尚,实不相瞒,刚才我手下的小旗张邦给我说,前面的小路虽然近些,也避人烟,不过途中经过一处兰若寺极是险恶,常有人被树精女鬼所困不得好死。如果你没有什么降妖伏魔的本领,我们何苦去白送性命。”
王艮听了心中一紧,脸上就带了几分忧色。
这和尚是他一力坚持要邀请的,虽说不知道他有多大能耐,但是队伍中有个高人心中多少踏实些。他颇有家财,也不在乎那点小钱。只是既然前途险恶,说不得要问清楚,免得被这厮坑死。
王艮当即逼问道,“法师,你怎么说?”
王艮怕和尚胡乱夸口,又道,“倘若法师不能降妖伏魔,也请照实说,不要白送了彼此性命。之前付给法师的银钱也无需退还。”
韩穿诧异的瞥他一眼,一脸的自信,“老板多虑了,小僧自幼修行袈裟伏魔功。这功法既然有伏魔二字,岂能辜负了我十余年寒暑?!”
众人听得一呆,脸色都渐渐难看。
他们都不是什么门外汉,就连不太懂武功的王艮也隐约听说过袈裟伏魔功,这只是一门比较高深的武学而已,和真正的伏魔扯不上半点关系。
聂豹最是耿直,劈手抓住韩穿衣襟就打,“贼和尚,你好大胆子!骗到老子头上!”
韩穿见他翻脸,略感讶然,却也并不惧怕,大喝一声,“慢来!”当即侧身一躲一拳迎出。这一拳势大力沉,虎虎生风,刚猛处就连聂豹也不敢争锋。
众人都有些意外,这和尚手底下倒有些功底。
不过在崔伯候、聂豹这样的行家眼中,这样九分力足的招式虽然吓人却无甚精妙。聂豹人粗夯些,武技上却颇有心得,见韩穿是刚猛地路子,振奋精神化解了这一拳,接着不动声色的改用了小巧借力手段“扑”的一声将他掀翻在地。
和尚冷不防跌这一跤,正有些吃惊,谁想聂豹闪身到他背后,双臂立刻锁住了他的关节。
韩穿大意失手手脚受制,他也不挣扎,回头无奈道,“喂,别闹了”。
聂豹微微冷笑,手上加了几分力气,趁机去他袈裟袖中摸那被骗去的银子。
谁知那袖中颇宽大,一摸之下竟没摸到底,只抓出一把符篆和一个青绿色的葫芦。
聂豹瞥一眼随手扔掉,用力将和尚胳膊拧过来,大手将那袈裟袖一撩底朝天倒个通透。
只听一阵叮当乱响地上竟掉了三四尺高的零碎物事。
这一大堆东西都是佛道两门零碎的法器,多是符篆、净瓶、葫芦、铜印、铜镜、铜壶、桃木小剑、九截木鞭,还有一些道袍袈裟,替换下的破衣烂衫之类日常用品。那些法器除了拳头大的十七八枚铜印在阳光照耀下闪闪的耀眼,其他都看上去都低劣不堪。
但东西一多就滥,那铜印想来也不是什么宝贵的物事。
众锦衣力士看着看着都忍不住咋舌嚷嚷起来,“好家伙!这和尚一人便做得个道场!”
聂豹定睛一看,没找到那些散碎银子,这才惊觉有异。凭这条衣袖怎能藏下恁多的物事?!
和尚见有机会,趁聂豹怔愣一脚将他蹬开,接着爬将起来往树林中走。
那一大堆零碎物事忽然像是醒过来的生灵一样,稀里哗啦,拖拖拉拉叮当响着追了过去。
那年轻和尚大袖一抖回头大叫一声,“看我的袈裟功!”
大红的袈裟袍袖倏地绽开,像是一个大红色怪物张开大口,囫囵一裹将东西收个罄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