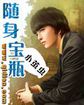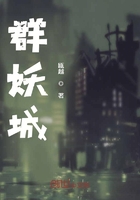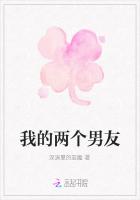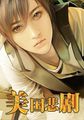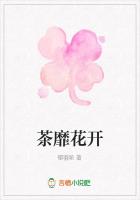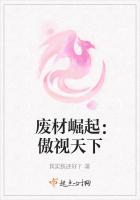茅盾一开始以“时代女性”作为小说人物,对他的文学生涯来说,是一个幸运而高明的选择。在前两章所勾画的20年代文学背景中,可见他的独特之处:不像蒋光慈、胡也频等人从意识形态出发去塑造“无产阶级”新英雄,也未着意于男性形象,却用心刻画了“几个特异的女子”。她们的“模特儿”来自都市“新女性”,已常见于当时流行的恋爱小说中,而所谓“特异”,乃在于给她们套上了“时代性”的笼辔,其中包含进步史观与小说形式上的考量。在三部曲中她们不拘一格,风情万种,或纯真、或放浪、或颓废,之所以得到如此的艺术表现,还得归因于其时作者对于“革命”含义的不确定把握,表现为一种对未来朦胧许诺的乌托邦空间,混杂着苏维埃想象、无政府主义、女“性”解放、欧洲现代主义文学,甚至包括“小资产阶级”的习性。
复杂性还涉及茅盾早期小说与都市的关系,对此学者间莫衷一是。一般认为现代“都市文学”至30年代趋于成熟,而《子夜》开场一段上海“外白渡桥”的夜景,几被视作标志性描写。许道明指出《子夜》的那种“把握上海这座现代化城市的气魄”在其处女作《蚀》中已见端倪。尤其是章秋柳“特见上海精神”。 而吴福辉在其文采斐然的《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一书中未提茅盾,大概是觉得他的“革命”身份与“海派”南辕北辙之故。在一本谈论北京的书中,赵园偶提一笔茅盾,却有惊人之论。她认为三部曲中《幻灭》,尤其是《追求》,已是“更成熟更有功力的城市文学作品”,其“由人性深度到达的都会文化深度,是穆时英(1912—1940)辈无力企及的”。之所以如此看高茅盾,固然是他的小说“以西欧某种 ‘文学城市’ 为参照”,但我想还是不能低估他的“革命”性。就那些“时代女性”而言,她们游走于革命与都市之间,一方面处处是上海市景:南京路、法国公园、电影院、跳舞场、酒楼、旅馆、石库门弄堂、亭子间,另一方面她们与现实的资本主义机制貌合神离,如来自乌托邦的幽灵。有时革命与都市的界线不甚分明,但即使“颓废”如章秋柳,在德意志“表现主义”的投影中象征着“激情的迸发”,在灵肉一致方面变得更为圣洁。事实上在女性身体暴露方面含有诉诸窥视的“诱惑”(seduction),但仍有伦理的尺度,其商业性不像张资平、叶灵凤等人走得那么远。
这些“时代女性”标志着他的文学“现代性”追求,同“美人香草”、“红颜知己”这类传统美学的决裂,也显示了他所受到的欧洲现代主义文学的影响,尽管在他整个的创作生涯中仅是昙花一现。这一选择也有政治因素在内,因为无形之中忽视了男性。茅盾后来谈到《蚀》三部曲“没有出现肯定的正面人物”,这当然是指“李克”式的男性革命者。从实际的政治考虑,尽管他亲身经历大革命的“大漩涡”、“大洪炉”,与“革命运动的领导核心有相当多的接触”,又“经常能和基层组织与群众发生关系”,他却不能直接写这样的“大革命”历史。这要涉及具体的人和事,以及国共两党之间的是非曲直,这就不是茅盾所能盖棺论定,另一方面大约他实在看不出有什么“正面人物”是值得作艺术表现的吧。有的学者指出,三部曲里真正的历史推动力是缺席的,如王德威指出,在三部曲中并未体现历史的推动力,仅反复表现了这些女性的革命热情与失望。这就和“正面人物”的缺席有关。
当时批评三部曲最尖锐的来自太阳社的“革命文学”理论家钱杏邨。他指出茅盾的作品没有成为“大勇者,真正革命者”的“代言人”,而是做了“幻灭动摇没落人物”的“代言人”。“所谓 ‘大勇者,真正革命者’ 代表着什么呢? 他们是必然的代表时代的进展,必然的是代表着有着前途,有着希望的向上的人类,他们是创造着新的时代的脚色。”从这样的高调里,我们已经可以听到那种无可抗拒的“必然”——来自“世界革命”的“宏大叙事”的神圣召唤。即使在二三十年代的欧洲,世界革命的历史叙事也已经四分五裂,卢卡奇力图构筑所谓“无产阶级革命”叙事的新模式。而茅盾所能提供的最初契机却是一部混合着杂音的交响曲。从五四以来那种线性的进化历史观在中国知识分子脑中已经生了根,但在20年代末,至少在左翼文人那里,这一现代时间意识更以一种机械的理解与马克思的历史分期观念相结合。这不仅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及其权力运作直接关联,而处于劣势的无产阶级更需要普世性的理论作后盾。在这样的背景下,茅盾早期小说中以“时代性”为主题,并对时间意识作探索并非偶然,而钱杏邨的批评焦点也集中在所谓茅盾的“创作哲学”——即时间意识上。从《蚀》三部曲开始,通过“时代女性”而表现“过去”、“现在”与“将来”之间的关系,也是一个逐渐展开而凸显的现象。三部曲将近尾声时,出现了所谓“北欧神话”的时间的象征框架,也就是茅盾在1928年秋《从牯岭到东京》一文中声称“现在是北欧的勇敢的命运女神做我精神上的前导”。一年之后茅盾在《读〈倪焕之〉》一文中明确提出“时代性”和“意识形态”作为他文学创作的追求目标,这“时代性”一词也多半从当时批评三部曲的文章里借来。 而在“意识形态”方面更受到“革命文学”论争的触发。因此这时间意识的不断加深的过程,在象征以至概念的层面给作品中女性形象的塑造发生不同程度的作用,而作者将主观的时间框架强加于想象世界时,将自己的狂想投射到富于“肉感”的女性身体上,其间必然出现主观意图与语言表现之间的矛盾、错置或自我消解等实际效果。
这些早期小说里的女主角,茅盾自己说表现了一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革命运动中的“精神状态”,和他自己后来所说的“时代性”增大了距离。其实在他的作品里,问题不那么简单:这样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表现如何在“女性”、“人性”、“民族性”以及“阶级性”的斑斓色谱中定位? 如果某种线性描述仍是作家研究的重要依据,我们不难发现这些女性形象——《蚀》三部曲中的静女士、方太太、孙舞阳、章秋柳、《野蔷薇》里的娴娴,以《虹》的梅女士为终结——从各篇小说创作的先后时序来看,她们呈现某种曲线的运动,向“时代性”的创作准则越靠越近。换言之,随着作者描写技术的改进,她们在思想气质上更具时代性或社会性,她们的主体意识表达得更具革命性。更主要的是,叙述者运用“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时间框架,直接或间接地在她们身上体现这种时间意识。理想地说,她们应当被表现为处身在历史的变动中,能够正视现实,抓住现实,既不留恋、伤感于过去,也不幻想将来。在清醒地认识现实的基础上进入将来。这些人物不一定被表现为领导革命运动的“大勇的真正革命者”,但像梅女士那样,在“时代”这一“学校”的熏陶中成长,遂向往革命,不折不挠,跟上历史的进程,掌握了自己的命运。更带暗示意义的是,这样的“时代性”蕴含某种原始的激情冲动,冲向一个有待重新整合和开展的革命目标。
茅盾写小说含有存在意义上的紧迫性,不仅与生存问题纠缠在一起,更重要的是,小说也是他探索、求证革命信仰的方式。在不可能为历史提供具体的解决方案时,更为有效的是把革命再现为一个有关存在价值的比喻,仿佛是一面镜子,反映当下展开的人生舞台,其中戏剧性地展开“真与伪,善与恶,美与丑”的互相激战,并卷入读者的思绪与感受。时间意识常常出现在一些严重的人生关口,主人公面临存在和选择时,凸现了生存的价值与当下的意义;当欲望与责任冲突之际,革命——作为集体狂欢的节日,或血腥淋漓的事件——成为价值衡量的标尺,警醒自我的鞭策,也是一种方向的暗示,未来的许诺。然而,在小说里,这一“时间框架”作为历史叙述的载体,却也成为作者的主观欲望的空间构筑,与女性形象的构造、与作者自己的存在及身份认同的危机,互相穿插在一起,呈现出极其复杂的图像。
王德威精辟地指出普实克仅注意茅盾小说里特别注重“现在”,而没有注意到其中所含的“将来”时态,更具意识形态的复杂性:
茅盾所刻意经营的是,历史小说应当设定一种目标,能在回顾与展望两者之间左右逢源。他对当下瞬息即逝的那种紧张不安的凝视,或显示一种促进历史过程的姿态,并赋之于一个神秘的“历史”的框架。开展中的事件深受注意,不仅因为它们的重要意义,并且因为它们构成一个过渡阶段,一段序曲,导向最后的革命的历史形式。这一展望的时态,即将当下置于过去时的括号中,是茅盾作品的关键。
我想说明的是,这一“过去”与“未来”互相纠缠的“关键”,贯穿于茅盾的女性形象塑造过程中,也是理解所谓他“从左拉到更近于托尔斯泰”的枢纽。茅盾在《幻灭》之后就考虑这部小说的革命含意与整体框架,考虑到如何结束,遂意识到他的历史叙述不可能放弃作品的价值和作家的责任。在“客观”描写历史的同时,如何渗入作家的“主观”,向读者传达希望的信息,将读者负载到未来、融汇到革命的巨流里,成为茅盾讲究形式的中心课题。然而茅盾在处理“现在”——我认为这一“关键”中的“关键”时,却出现了深刻的危机,集中体现了客观/主观、自然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现代性/革命文学、享乐原则/自由意志之间的激烈冲突。这些冲突之所以激烈,正因为他把女性看作同“革命”自然疏离的力量,这也与他受到“自然主义”的所谓“兽性”哲学的深刻影响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