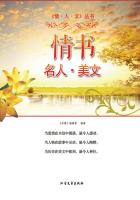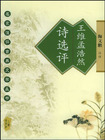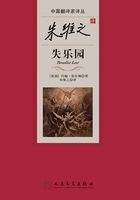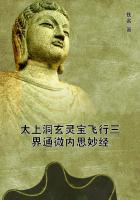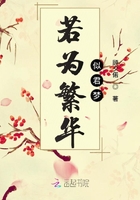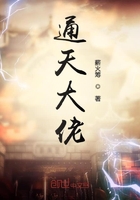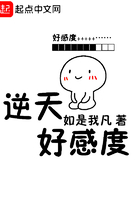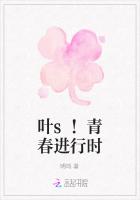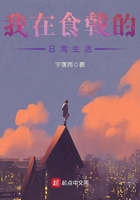在《虹》里梅女士“主体”的“意识形态”的构筑,标志着茅盾小说创作的跃进,某种意义上在形式上确立了“现实主义”的范式。我们习惯上在“现实主义”的框架中理解这一中国现代小说的形成,然而在当时语境中就茅盾的个案而言,他一向热衷于鼓吹形形式式的“主义”,但在“革命文学”的过渡中,看上去倾向于某种“新写实主义”,但也是不确定的。在《从牯岭到东京》中有一大段谈到“有人在提倡新写实主义”,他说起俄国有一种“新写实主义”,产生于内战之后的困难时期,形式上“短小精悍,紧张”,被戏称为“电报体”。他说:
所以新写实主义不是偶然发生的,也不是要对无产阶级说法,所以要简练些。然而文艺技巧上的一种新型,却是确定了的。我们现在移植过来,怎样呢? 这是个待试验的问题。
茅盾提出要改造“文艺的技术”,即“不要太欧化,不要多用新术语,不要太多了象征色彩,不要从正面说教似的宣传新思想”。这些主张应当是向“无产阶级文学”开放的。但他当时写三部曲,鼓吹为城市小资产阶级服务,又说:“所以为要使我们的新文艺走到小资产阶级市民的队伍去,我们的描写技术不得不有一度改造,而是否即是 ‘向新写实主义的路’,则尚待多方的试验。”
我们不妨从另一角度来看“现实主义”,即小说形式的现代性问题。在《从牯岭到东京》里茅盾自述其小说创作的转型,被广为引述:
有一位英国批评家说过这样的话:左拉因为要做小说,才去经验人生;托尔斯泰则是经验了人生以后才来做小说。这两位大师的出发点何其不同,然而他们的作品却同样的震动了一世了! 左拉对于人生的态度至少可说是“冷观的”,和托尔斯泰那样的热爱人生,显然又是正相反;然而他们的作品却又同样是现实人生的批评和反映。我爱左拉,我亦爱托尔斯泰;我曾经热心地——虽然无效地而且很受误会和反对,鼓吹过左拉的自然主义,可是到我自己来试作小说的时候,我却更近于托尔斯泰了。
从定义上考察,茅盾的“自然主义”也有问题。学者们指出他对“自然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提法有抵牾之处,其实不光是定义,他的文学主张的表述常前后不一,这恐怕是中国式“拿来主义”的特性所决定的。当他援引左拉和托尔斯泰作为他的文学创作楷模时,似乎怠慢了不久前经他大力推奖的无产阶级文学泰斗高尔基,而且在这篇《从牯岭到东京》和稍后的《读〈倪焕之〉》中,干脆表示“要使新文艺走进小资产阶级市民的队伍”,他不但不再重弹“无产阶级文学”观,甚至批评那种“为劳苦群众而作”的新文学是无的放矢,“它的文坛上没有表现小资产阶级的作品,这不能不说是怪现象吧! 这仿佛证明了我们的作家一向只忙于追逐世界文艺的新潮,几乎成为东施效颦。”这些言论表明,同他前一阵激进文学立场相比较,出现即使不算倒退,也是与革命离心的倾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 是因为派性作怪? 因为当时“创造社”成员在标榜“无产阶级”的“革命文学”,他故意要对着干? 还是因为他的小说被批评为“小资产阶级”的,就干脆为自己辩护? 不无反讽的是,似乎要弥补这一“断裂”,就在1929年底,茅盾为《中学生》创刊号写《高尔基》一文,后来回忆道:“我这篇文章是 ‘有意为之’ 的,因为创造社、太阳社的朋友们说我是提倡小资产阶级文学,我就偏来宣传无产阶级文学的创始者和代言人高尔基。同时也为了指明,真正的普罗文学应该像高尔基的作品那样有血有肉,而不是革命口号的图解。”突出这些“断裂”,有利于我们对茅盾的文学思想有一种更为合乎历史实际的把握。
茅盾学习与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碎片性和断裂性对于五四知识分子来说具普遍意义。要弄清他如何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情况,即使抓住主要的思想线索,爬梳材料,其结果也很可能是一头雾水。尽管他在20年代初介绍过“共产主义”学说,也翻译过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但并没有因此作深入研究。更多的时候与其说是阅读原著,不如说是受间接影响,不无以讹传讹的成分。郭沫若的情况有相似处。他最初接触马克思主义,是20年代初在日本通过李闪亭这位“中国马克思”,了解了有关“唯物史观的公式”、“资本主义的必然的崩溃”以及“无产阶级专政”的道理,还是似懂非懂。后来翻译了日本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遂自认为在思想上“形成了一个转换期”。但后来在创造社新秀们的眼中,郭的马克思主义差不多已经需要加以修理了。
什么是左拉? 什么是托尔斯泰? 并非一两语能讲清。略可参照的是,卢卡奇在著名论文《是描写还是叙述?》里,以左拉的《娜娜》和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中的“赛马”情节为例,比较他们之间艺术手法的不同,认为前者注重客观“描写”,生活细节无论巨细,都得到精确的刻画,而作者的纯熟技巧将事件和场面表现得有声有色,但情节与情节之间缺乏有机的联系。如果说左拉的描写以其精细的观察为根据,而托尔斯泰的“叙述”则出之于经验的感受。托氏讲究整体的布局,情节的展开带着情感的韵律。如写到渥伦斯基从马上摔下时,对安娜的情绪反应所作的精心刻画,成为整个小说情节转折的关键,与前后的事件互相关联,直至最后将读者的情绪引向其所期许的高潮。
左拉和托尔斯泰之间的区别,在茅盾的语境里,或可简捷地翻译成客观和主观的区别。茅盾原先信奉的左拉相当于一种镜子反映论,到此时他转向托尔斯泰,乃明确到他的小说不仅应当反映现实,更应当有一种方向,即进而通过“意识形态”的中介“辩证法”地表现“历史的必然”。本来文学研究会提倡“为人生的艺术”,不光含有功利性,在再现理论上要求文学忠实反映现实生活,同时反对那些纯粹主观的非具象的艺术表现。且看郑振铎(1898—1958)1924年在《小说月报》上的一段“卷头语”:
文艺作品之所以能感动读者,完全在他的叙写的真实。但所谓“真实”,并非谓文艺如人间史迹的记述,所述的事迹必须是真实的,乃谓所叙写的事迹,不妨为想象的、幻想的、神奇的,而他的叙写却非真实的不可。如安徒生的童话,虽叙写小绿虫、蝴蝶,以及其他动物世界的事,而他的叙述却极为真实,能使读者能如身历其境,这就是所谓“叙写的真实”。至于那种写未读过书的农夫的说话,而却用典故与“雅词”,写中国的事,而使人觉得“非中国的”,则即使其所写的事迹完全是真实的,也非所谓文艺上的“真实”,决不能感动读者。
这篇“卷头语”在表达文学研究会的主张颇有代表性,犹如一个标准的缩本。所谓“叙写的真实”有两层意思。允许“不妨为想象的、幻想的、神奇的”,如安徒生的童话世界,此亦即“文艺上的真实”。但另一方面写“中国的事”,不能使人觉得“非中国的”,或写“未读过书的农夫”,就不能用“典故与雅词”,换言之应当酷肖其形其声,不能脱离“真实”的农夫。总之,“真实”是铁律,“艺术的真实”必须以现实世界为基础。这种理论体现了“现实主义”的“反映”论的基本信条,虽然与“照相现实主义”有别。这里的核心课题是“真实”,仍含有某种抽象性,尚未涉及到底什么才是“真实”,由谁决定“真实”等“主体”性问题。
茅盾在20年代初宣扬“自然主义”,强调对现象世界“客观、科学”的“观察”,也正合乎文学研究会的宗旨。但是正如其自述,当他开始写小说时,就从左拉移向托尔斯泰,即抱有伦理的道义感和政治的方向感,确定了“革命”的“主体”。不久在与“革命文学”论争的互动中,他的创作方向进一步得到马克思主义的武装,更自觉地以表现阶级的“意识形态”为“真实”,同时也以改造自身的“意识形态”为己任。上文说过茅盾在《读〈倪焕之〉》和《〈野蔷薇〉序》中表示要力求表现小说人物的阶级“意识形态”及体现“历史必然”的“时代性”,虽然他的文学实践还有待开展,但我们看《野蔷薇》里的几个短篇,那些女主角大多属于小资产阶级,作品着重她们的心理刻画。“时代性”是有关历史精神,那么“意识形态”是有关人物的意识及其背后的东西。这两个概念的提出,标志着茅盾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思想的进一步深化,使他的小说创作更受到理论的指导,也更党性化。但这样给自己的创作带来另一种不确定性,由于“意识形态”这一观念本身具有马克思主义的党性,服从阶级斗争的权力秩序,如他所主张表现的“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即遭到革命阵营内部的批判,并影响到他日后的创作。事实上随着“革命文学”运动的开展,茅盾的写作已不由自主的纳入“革命”的进程,作家代“宏大历史”立言,在表现“历史的必然”时,既必须表现自身对历史必然的热情体认,同时必须听从代表这一历史必然的“革命”权威的指令。
当他的小说文本既融入革命文本而随之浮沉,在文学再现的过程中既要求客观反映现实,同时也强调这一客观反映乃取决于作家的主观,受制于无产阶级权力的操控。茅盾在早期小说创作中这一转变尚未为学者所注意。如普实克出色论述了茅盾善于通过人物心理和感受来反映外在世界,从而体现了描写上的“客观性”。他认为:“茅盾自觉追求的就是这样一个目标:客观地叙述,反映现实的真相,不作主观的描写。”这样片面强调“客观性”,就忽视了复杂的“主观”问题。同样的安敏成对茅盾早期小说的解读精义纷呈,但欠于将他的创作中所表现的“道德阻碍”同“革命文学”之争“语境化”(contextulization),因此也难以深入探讨“现实主义”的主体转变。同样难免的,在将《蚀》三部曲同《子夜》放在同一平面上分析时,也看不出《虹》的重要性。
围绕“时代性”、“意识形态”这些新概念,茅盾的小说世界图像变得更为复杂,给他的创作带来新的矛盾,某种意义上变得更不透明,遂使他的“现实主义”风格——即使并不成熟——达到一个新的阶段,至于这是否意味着具有更高的艺术造诣,乃属于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尤其是《虹》,更有趣地处于过渡阶段的交汇点,凸显了作品的寓言性,如梅女士既具人性又具神性,不仅夏志清将这部小说读作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寓言”,也如安敏成所说,对这样的“现实主义”作品,读者需要一种“寓言”性的读解方式。任何现实主义叙事模式本来就不等于镜子般反映现实 (即使是镜子里所呈现的,亦是现实的映射,而非现实本身),而在受到“意识形态”理论干预的现实主义叙事模式里,渗透着马克思主义对于历史与意识关系的诠释与幻象;如茅盾所声称的“凝视现实,分析现实,揭破现实”含有新的意义,即作家不仅自信获得代言“真理”的权威,而且获得再现“现实”的辩证方法。所谓“意识形态”也指文化符码的系统性及其生产过程,因此在现实主义叙事里,历史或个人作为革命运动的“机制”,各自受到语言的符码系统的控辖;这两者成为互相关照、互相作用的“中介”,由此它们的文学再现不仅与语言之间造成张力,也都与现实之间加深裂痕,且更带有作家的自觉意识。历史与个人之间的辩证互动及其所展现的自由意志构成了小说叙述展开的基本动力,而作家的艺术想象与再现技能表现在如何创造和操纵这两者各自所具的运动逻辑及其相互间的关系。
这样的“现实主义”叙述模式的形成与“意识形态”观念的确立,都与作家对于“真理”的主体意识有关,在这样的语境里,作家需要更为明确地解决所谓写作的主客观问题。在1923年《文学与人生》一文中,他接受文学即“反映”论:“人们怎样生活,社会怎样情形,文学就把那种种反映出来。譬如人生是个杯子,文学就是杯子在镜子里的影子。”后来20年代中期在《文学的新使命》中认为“文学决不可仅仅是一面镜子,应该是一个指南针”。 在写《幻灭》与《动摇》时,他已经“时时注意不要离开了题旨,时时顾到要使篇中每一动作都朝着一个方向,都为促成这总目的之有机的结构”。 而在1929年底,即在完成《虹》与《野蔷薇》后不久,在《西洋文学通论》一书中说:“文艺之必须表现人间的现实,是无可疑议的;但自然主义者只抓住眼前的现实,以文艺为照相机,而忽略了文艺创造生活的使命,又是无疑的大缺点。文艺不是镜子,而是斧头;不应该只限于反映,而应该创造的!”另在《关于高尔基》一文中说:“文艺作品不但须尽了镜子的反映作用,并且还须尽了斧子的砍削的功能;砍削人生使合于正轨。”虽然这些说法总的精神是一致的,但“斧子”的比喻表示作者对于文学中主观干预的加强及其自信,其底层蕴含着对于“真理”的认识的自信。所谓“砍削人生使合于正轨”,则意味着给文学的道德责任感加上了强制的成分。
茅盾对“意识形态”的把握,不仅要求表现小说人物的阶级意识,而且要求揭示某种“背后”的东西。这“意识形态”似乎表明他的思想转型扮演了一个关键角色,并为他的写作困境提供了某种解决的方式。这也直接影响到他后来的小说,如果说更展现了千姿百态的社会面相,塑造了各种阶级或阶层的人物形象,那么“意识形态”的概念有助于分析、区别不同人物的阶级属性,从文学再现的角度说,也为语言的文学再现及其生产规定了某种秩序,使“现实主义”文学更朝理性化的方向移动。前面提到20年代中期以来由于阶级斗争的激化,茅盾、郭沫若等都认为这时代已产生新的意识危机,更呼吁心灵的眼睛来看透“真实”。如果从更为深广的思想脉络来看,中国现代意识本来就是在危机中寻求突进而得到发展的,事实上自清末以来,随着西洋现代科技和学术文化的输入,中国人不断在改变对世界的看法,而现在这几位思想界代言人不约而同地强调“看”这一文化行为时,反映的是要求看到事物的“背后”的焦虑,亦涉及语言再现与意识之间的危机。因此随着“意识形态”及其思想模式的传播和接受,思想界的主流却趋向平静。从茅盾的例子看,当他声称文学不仅应当是“镜子”而应当是“斧子”时,他显得不再那么焦虑了。
这或许有助于讨论茅盾在早期创作中的所谓从左拉到托尔斯泰的转变问题。关于他的主客观之间的关系,只有放到“意识形态”与权力写作的机制中观察,才能见到其中更为微妙的层面。一方面这样的“现实主义”是更客观的,它根植于现实生活,排斥现代主义的个性表现,与种种超现实的象征主义、神秘主义、唯美主义等绝缘。如梅女士这个“人物性格有发展,而且最合乎生活规律的有阶段的逐渐的发展而不是跳跃式的发展”,这种生活常态的描写也较为贴近生活的日常性,像梅女士这样能够不断从所谓“现实的学校”里接受教育,又能够“因时制变”地“适应新的世界”,也确实体现了“时代性”。客观性还在于排除那种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因此也就排除了“自我表现”的可能,而且由于作者自信所描写的一切都是无可怀疑的普遍真理,因此不必使读者感到叙述者的存在,语言与现实再现之间越没有间隔、越透明,就越容易将读者带进小说世界,与人物发生共鸣。
另一方面,作家主观的运作表现在材料的选择、处理,情节的安排、组织以及语言风格方面。但在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结构里,主观与客观的关系纠结在一起。马克思主义本身属于世界观的一种,像茅盾那样的与之认同是一种主观信仰的选择。同时马克思主义以人类“解放”为目标,要求认识客观世界,在某种程度上也能达到对客观世界的认知,作家的主观在追求客观的同时,也要求去除自己的主观性。而对“真理”的追求,则需要一种超凡的主体意识,像梅女士那种“意识”的构筑是被强化了的、也是更复杂的。尽管主体意识加强,包括革命的道德激情,它要求呈现为一种客观的形式,必定被“历史”客体化。正如茅盾的例子,当他成为“历史”的“机制”,所谓“斧砍”的动作乃受到历史的指令。因此作家既是启蒙民众的导师,也是历史和民众的学生,即如茅盾说梅女士的“思想改造过程”,是“长期的,学到老,改造到老”,这何尝不是茅盾的自我写照?
总之,应当作区别的是作家主观的不同表现方式,在茅盾的“客观”描述中不应忽视其叙述主体与“历史”这一主使者之间的意识形态及政治权力关系:在“客观”反映现实生活的同时,这一叙述主体更强调自身的“观点”或“世界观”的构成。他必须时时把握和强调历史“方向”,作为其“正确”视角的依据;这一叙述主体也常常缺乏自信,因其必须得到“历史”力量的首肯才能获得其法定性。
从《蚀》三部曲到《虹》,茅盾逐渐完成了将小说转化为革命的寓言形式,他构筑了“历史”的谜,作为“革命”的火药库,也是期待权力填充的真空。尽管茅盾已经将写作自觉地臣服于“历史”的权威,但由于实际“革命”权力的缺席,他的写作仍免受那种主宰后来革命文学的“面对面”的政治干预,因此他所创造的小说人物及形式是开放型的,为“现实主义”模式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复杂性与可能性。正如安敏成所认为的在革命的“缝隙”中现实主义展示其美学形式的探索,他认为在20年代末“现实主义”不能适应蔚成燎原之势的革命群众运动,因此凸显了那种从西方借来的现实主义的“局限”。这结论大致不错,但像《虹》这部小说,已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由于作者的主观与历史之间的某种不确定、不和谐,使梅女士这一人物形象仍混杂着多种色彩与声音,在“真理”尚缺乏权威保证的情况下,作品仍讲究修辞。但另一方面,《虹》已经在叙述形式上赋予历史运动的自主性,而梅女士的形象塑造已经具备对革命环境适应性格,遂打破了倪焕之那种内向、极端的类型。换言之,这样的“写实主义”叙述模式已经具备了再现更大规模的革命运动的条件。
对于这时期茅盾在左拉与托尔斯泰之间他更倾心于后者的自白,得到学者们普遍的重视,但如果我们能将他关于高尔基的“文学是斧子”的话一起考虑,在诠释上或能引向更为深刻的历史与意识形态的层面,揭示出文学现代性开展过程中的问题。普实克认为,茅盾与托尔斯泰的相似之处,在于小说的“史诗”特征及其在艺术上是“描绘”而非“叙述”的特征。 关于托尔斯泰的这两个特征,前面说过卢卡奇曾有专论。可惜的是,普实克对于茅盾的分析,未能像卢卡奇那样揭示出托尔斯泰的宗教背景及其文化前设所含的内在吊诡。他指出托氏小说的史诗特质根植于他的乌托邦灵魂与世俗世界之间的断痕,因而要求小说形式超越因循的再现模式。他的宗教也即“自然”,那种乌托邦式的叙事开展,如心灵的牧歌,四季的循环,使人际关系的和谐表现与个体精神的内在自足展现出丰富的层面。而不无揶揄的是,托尔斯泰所崇尚的“自然”恰恰属于“文化”的范畴,换言之,托氏不可能弃绝文明的赐予,他所强调的爱情与热情在小说里则集中体现为“婚姻”,亦即文化的形式。卢卡奇说:“然而爱情作为纯粹的自然力量,作为激情,并不属于托尔斯泰的自然的世界;热烈的爱情过于受到人际关系的束缚,因此也过于疏离,以至含而不露,或横生枝节;总之这是过于文化的。”
这样的批评也大致合乎茅盾的《虹》,问题不仅在于作家写什么,也在于作家选择的条件。茅盾在“自然”与“文化”之间的选择,似乎更受到中国传统伦理的符码的制约,其间的差异和对照比托尔斯泰更为泾渭分明。如果说茅盾在塑造梅女士这一形象上大匠运“斧”,那么对她的自然激情的开展,为的是砍除她的“女性”和“母性”,而“历史”也被构成“新文化”之迷思,被构成一座“意识形态”的迷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