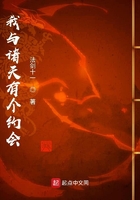吃过晚饭,王宾问起来绢画。凌霜把绢画铺到桌子上,用手指着,道:“这十六个字是‘雷打朱白,禹王冰绡,金街银雨,玉椟在天。’书逸先生说这十六个字是楚国的文字,比李斯是虫鸟篆还要老。”
王宾点了点头,道:“难怪我们都不认得。那个书逸先生还说什么了?”
项承志道:“没有了。”
王宾想着,说:“也许这就是太阿宝剑隐藏之处。”
项继先无奈地道:“可是我们不知道在哪啊?”
傲霜扑哧一笑,立刻发现自己不应该笑,连忙掩住。
凌霜愠道:“你笑什么?”
傲霜尽力憋住,才道:“我想说,我们明天去找那个算命先生去算一卦。”
凌霜又想气。又想笑,道;“胡闹。”
王宾一愣,道:“什么算命先生?”
凌霜道:“王伯伯不要听她胡说。”
傲霜不服气,道:“他本来就是一个算命先生嘛。我们在飞英寺看到一回,接着在集市上又看到了。这不,我们才回到镇上,就又碰到了他。”哦,王宾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第二天,项继先早早起来,陪着哥哥到后面的竹林里弹琴,练习吐纳。在哥哥悠扬的琴声中,山林间钟灵毓秀的气息在经脉里缓缓游动,如同山间潺潺涌动的溪流。端木豪夫妇曾经说过,法无定式,制敌为先。招式要练,但是不能被招式束缚。所谓的功夫,其实就是练气。悠长的气息,可以在对阵时有绵绵不绝的后劲。胜负之间,生死之时,不过是吸呼之间。项承志在拨动琴弦之时,控制自己的气息,运用到指尖,借着琴声发出去。项继先则借着琴声练气,一来可以熟悉琴韵,免受其害,二来也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回来时时候,凌霜和傲霜已经准备好了饭菜。在龙家每一顿都是有酒有肉,一时间,吃到积翠庵里简单粗陋的蔬食,竟有一种清新的口感,较之飞英寺的细腻,别有一种滋味。
项继先吃着十分顺口,笑着道:“如果一辈子都能吃到这样的饭菜,夫复何求?”
傲霜的嘴一撇,道:“这不过是姐姐的牛刀小试而已。”
项承志目光一转,道:“王伯伯呢?去那面了吗?”
凌霜一点头,道:“嗯,菜也送过了。放心吧,继先哥哥。”傲霜道:“炒了满满的一盆,只盛出这么一点,全送过去了。”
凌霜夹了一箸放到她的碗里,道:“够吃就行了。”
傲霜道:“我是怕不够继先哥哥吃。他练剑挺累的。”说着,夹了一大箸送到项继先的碗里。项继先一愣。傲霜的这一箸差一点加来一半,夹回去又不好,不由得停住筷子。
项承志一笑,道:“还不赶紧吃,一会儿还得练功呢?要不王伯伯又要骂了。”
项承志已经看出姐妹俩的心思都在弟弟一个人身上。一个沉静,一个爽快。沉静的温柔细腻,善解人意。爽快的快人快语,解忧散愁。自幼兄弟的心眼就比自己多两个,调皮捣蛋的事没少干,当然,也少不了父亲的责骂。还有几回被父亲冤枉,替自己背了黑锅。这个不知道被父亲怒斥为“朽木不可雕也”的弟弟就同时为姐妹俩相中,既高兴,又羡慕。其实,龙静雪也不错,叽叽喳喳,就象翠林间的一只百灵鸟,活泼,快乐。
不过,他们的快乐在夜幕再一次降临的时候,就被王宾浓重的阴郁所打破。究竟出了什么事?四个人面面相觑。直到三更鼓将尽,王宾的房里还传出沉重的叹息,一下子加重了几个人的忧虑,都感觉到了一种无形的压力。
这种令人窒息的阴郁持续了两天,四个人被王宾引到了对面的院子。这还是第二次到这个院子里来。上一次还是兄弟俩重逢的时候,到现在已经半年有余。
昏黄的灯光摇曳出一丛一丛的暗影。年轻的和尚坐在上首的蒲团上。手里不停地捻着一挂紫红色的念珠。那是一挂金丝楠木的念珠。现在,四个人已经知道这个年轻的和尚就是逊国建文帝朱允炆。不过,他现在的法名叫应文。
在他的两旁,是一直随侍左右的应贤和应能。应文一直称两个人为师兄。哪一个敢做皇帝的师兄?只能恭恭敬敬地听着。再往下就是溥源大师,叶希贤,牛景先。
进来后,王宾侧过身,道:“你们赶紧见过圣驾。”
建文帝举起一只手,道:“不必了。我也不是什么皇帝了。”四个人规规矩矩地跪下,行了三拜九叩的大礼。然后垂首站到一旁。
建文帝叹了一口气,道:“左拾遗戴德彝,兵部尚书铁铉。能见到他们的后人,余心亦安矣。”话虽然这样说,语气依然有些沉重。其实,这是他第二次见到四个人,只是上一次只是闷闷地吃了一顿饭。以后就再也没有见面。停了一下,向叶希贤道:“应贤师兄,你们这两天你们又在计议什么,连几个孩子都搬出来了?”
叶希贤的法名叫应贤,所以,建文皇帝叫他师兄。叶希贤起身上前拜了一拜,道:“回陛下,燕逆的探子已经到了藏书镇。”
建文帝苦笑了一下,道:“伯夷和叔齐不食周粟,采薇首阳山。天地悠悠,你我又将安身何处?”
叶希贤道:“回陛下,孩子们在‘越绝书’里找到了太阿宝剑的藏宝图。”
建文帝一愣,道:“就是嬴政的那把太阿剑吗?”
叶希贤道:“正是。”
建文帝皱了一下眉,道:“你们想干什么?”
叶希贤道:“昔日,欧冶子干将两大铸剑师为楚王铸造了太阿宝剑。晋王欲得之,发兵围楚。晋强楚弱,楚王绝望之际,城头仗剑一劈,剑气磅礴,楚军伏尸二十万,反败为胜。”
建文帝淡淡地道:“那又如何?”
叶希贤道:“回陛下,楚也。燕王,晋也。太祖皇帝洪福齐天,让陛下得到了宝图。得此剑,陛下就可以反败为胜,扭转乾坤。”
哦,建文帝点了点头,道:“知道藏在哪吗?”
叶希贤面露难色,道:“现在还不知道。”
建文帝轻叹一声,道:“那你们打算怎么办啊?”
叶希贤道:“既然燕逆的探子已经来了,三十六计走为上。一边走,一边找。”
建文帝笑了,道:“明明是流落番邦,偏偏要说去打猎。你们啊!”建文帝是在借北宋徽钦二帝来比喻眼前的事。他的目光中每一个人的脸上走过,才道:“你说我们还朝哪走啊?”
沉默了一下,叶希贤道:“善攻者,攻于九天之上;善藏者,藏于九地之下。”
建文帝还是一脸的苦笑,道:“攻,就凭你们这几个老弱病残吗?将铁公与戴公这一点点血脉也送入燕王咻咻巨口吗?算了吧。”建文皇帝连连摇头。
项继先上前一步,跪倒,道:“陛下,他们不认识我们,擒贼先擒王,我们进宫行刺,也好一报杀父之仇。”
建文帝又开始摇头,道:“傻孩子,你当太祖皇帝的皇城是湖州城吗?只怕你们行刺不成,锦衣卫马上就会开始行刺,那可是他们的拿手好戏啊。”
这话一出口,所有人都激灵灵打了一个冷战。行刺,暗杀,侦听,满朝的文武大臣尽在锦衣卫的掌控之下。现在他们是不知道建文帝躲在这里,眨眼之时,积翠庵就会灰飞烟灭,不复存在。
既然不能攻,那就只有藏了。可是,没有人知道哪里才是最安全的,应该向哪里走,怎么走。一阵难言的沉默之后,傲霜小声咕哝了一句。声音很低,谁也没有听清。
凌霜狠狠地盯了她一眼,责备她不要乱说话。王宾就坐在傲霜的旁边,问道:“丫头,你说不如什么?”
凌霜轻声道:“不要听她乱说,王伯伯。”
“我怎么乱说了!”傲霜不但没有闭嘴,反倒放大了声音,“我不就是说实在没有招,不如卜一卦吗?”
卜一卦?这是什么招啊?众人正在摇头,建文帝微笑道:“这也是一个办法。”说着,站起来,双手和什,向溥源大师深深一躬,道:“烦请溥源师兄为贫僧卜一卦吧。”
溥源大师哪里敢接受他这一躬!连忙站起避开,深深一拜,道:“折杀贫僧!但有吩咐,尽力便是。”
次日,兄弟俩上前面抬回一只崭新的木桶。建文帝沐浴后,换上了干净僧袍,披好崭新的袈裟。独自一个人坐在静室里。眉垂目合,手捻佛珠,默诵经文。
真正占卜是一件很庄重的事。斋戒,沐浴,更衣,都是必不可少的。身处庙宇,斋戒倒是顺势而为,不用费事。
刚刚用过斋饭,戒空小和尚气喘吁吁地跑过来,道:“你们今天千万不要到前面去。更不要弹琴。我走了。”说完,又急匆匆地跑了回去。这是干嘛呀?匆匆而来,匆匆而去,把几个人扔到五里云雾之中。
记得年前苏州知府来到时候也没有这样,这回来的莫不是什么大人物?
项承志回到房里,抱起遏云行,向后门走去。他是要到箬帽峰下去练琴。那里的空气清新,是练琴的好地方。
看着项承志走出后门,傲霜眨了眨眼道:“我们也去吗?”
凌霜面露诧异。道:“你又想干什么?”这个妹妹从小到大就爱调皮捣蛋,为了这,没少挨父亲的骂,甚至被母亲打过两回。傲霜虽然稍有收敛,不过还是管不住自己,还是经常悄悄干一些出格的事。但是,她知道妹妹的这句话是向项继先说的。她也向项继先看去。
项继先想了一下,用手指了一下后门,划了一个圈,又指了一下前面,然后点了一下头。凌霜心里一个劲的叹息:这两个人,可咋办啊。她心里想着,项继先和傲霜已经到了后门。看到姐姐还站着没动,傲霜小声招呼:”姐姐,快点啊。”说完就消失在门后边。
哎,你们等等我啊。来不及细想,就跟着跑出去。
积翠庵只是一座不大的寺庙,前后只有三进进院子。三个人很快就从墙外绕到了前面的山门。不过,立刻就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说句心里话,积翠庵的香火实在是不敢恭维,经常十天半月也不见一个烧香礼佛的。但是,只要来一个就是一个大施主,比如年前的苏州知府。不过,现在的这个施主似乎来头更大。山门两旁各站着两个全副武装的军士。头戴尖帽,褐色的飞鱼服,腰下悬挂着绣春刀,脚蹬白皮靴。手按刀柄,不可一世。这是锦衣卫啊。当初被抄家,就是这帮人如狼似虎闯进家门抓走了家里所有的人。那景象,一辈子也不会忘记。项继先的拳头不由自主攥紧了,发出格格的响声。
噗,一粒小石子打在了肩头。谁?项继先一惊。一回头,只见哥哥正向自己挥手,示意过去。三个人只好悄悄地退回树林,走到项承志面前。项承志的脸一直向着天,好一会儿才叹了一口气,道:“我们在这里待不几天了,就不要给溥源大师找麻烦了。”三个人的心头都是一震。也许在自己会出了心头的一口恶气,却会给溥源大师留下麻烦,甚至彻底断了积翠庵几十个和尚的衣食父母。
咬了咬牙,看了一眼山门两边的四个锦衣卫,低低地道:“哥哥,我们在这里看一看究竟是谁行不行?”
项承志犹豫了好一会儿,道:“好吧。”
大约过了一个时辰,从山门里走出一群人。走在最前面的两个人一个就是溥源大师。另一个身形有些微胖,面皮白白净净。这不是一个太监吗?不过,从身上的服饰可以看出来,这可不是一个以前在家里看到的传旨太监,而是一个品级非常高的太监。这种品级的太监一出去,十有八九就是代表着皇帝。
他来这里干什么?在几个人都惊惑中,溥源大师送出来山门四五十步以后停住了脚步。太监恭恭敬敬向溥源大师拜了一拜,才带着人下山而去。
看着太监一行人转过山弯,溥源大师抬起头,长长吁了一口气,道:“出来吧,孩子们。”
几个人都是一愣,溥源大师不会功夫啊,怎么知道我们躲在这里。站起来,问道:“大师,您怎么知道我们在这里?”
溥源大师轻轻摇摇头,道:“你们当锦衣卫都是吃白饭的吗?要不是人家手下留情,你们几个不死也会被关到锦衣卫的诏狱。赶紧回去吧。”诏狱!几个人不禁打了一个寒噤。
夜幕降临,一个落魄的中年文士到积翠庵投宿。一身有些破蔽的儒衫,张口就是诗词歌赋,和溥源大师相谈甚欢。
明天就是占卜的日子了。
吃过了晚饭。兄弟俩把两个院子里的大缸全部挑满。
噗噗,兄弟俩刚刚躺下,有人弹窗纸。谁?项继先一把抓起秋水寒。项承志夹起遏云行。一前一后跳到院子里。院子里静悄悄的,一个人影也没有。
夜星闪烁,树影婆娑。
项承志抱琴的右手拇指向项继先的身后一挑。项继先立刻明白,人就在身后。手指上指,就是人站在墙上。手紧紧扣住剑柄,一动不敢动,三四丈的距离,对于高手来说,想取自己的性命,那可是不费吹灰之力。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以静制动,静以待变。身后传来一声轻笑,有人道:“端木豪两口子的眼光真的是不错啊。小崽子,有种的,就跟我来吧。”声音就像一缕夜风,很轻,倏忽之间就飘散无踪。
追!项继先转过身的时候,墙上已经是空荡荡的。项承志从从身边掠过,吐出来两个字:“白影。”
待他听清,项承志人已经飘过了墙头。项继先连忙一个提纵跟上去。墙外就是箬帽峰,一条白影正往上山上飘。几丈外就是哥哥。
那人似乎在等着兄弟俩,不紧不慢,就落下兄弟俩几丈远。项承志的琴技主要以内功为主,气息要比项继先的绵长。项继先加紧几步,才和项承志并肩,低声提醒道:“小心,哥。”
“嗯。”项承志只嗯了一声,一手抱琴,一手解开琴套,褪下。项继先也不敢大意,把秋水寒也握在手中。
三个人很快就到了山腰上一片树林。白影停住了身形,待兄弟俩也站住,才轻轻嘘了一口气,道:“这里不错啊!就这里吧。”
兄弟俩都是一愣,忍不住问道:“你究竟想干什么?”
“把你们埋在这里。如何?”白影一边说,一边转过身。他的声音还是很轻,甚至很悠闲。不过,在兄弟俩的耳中,无异于是一声惊雷。方才的追赶中,兄弟俩已经是有些气喘吁吁,白影却如同闲庭信步,浑若无事。
拼了!兄弟俩全神戒备,盯着眼前的白影。现在,兄弟俩知道眼前的白影就是龙王寨的四当家的白龙。龙老爷子曾经说过,龙王寨上真正主事的就是白龙。此人智勇双全,极为难缠。不少黑白两道的成名人物都是折到了他的手里。清冷的月光下,白影本来满是书卷气的脸庞,在迷蒙的月影下竟然有些狰狞。
嚓,嚓,嚓,白龙的脚步很慢,踩在去年的枯草上,每一步都听得清清楚楚。
嗡,嗡,嗡,项承志猛地一拨琴弦。大敌当前,项承志一出手,就是“霹雳惊弦”。而且每一次都拼尽了全力,每发一次,心血就是一阵沸腾。
琴声一起,白龙堆脚步陡然停下,脸上露出一丝惊愕。这么猛烈的指法,普通的琴弦早就寸断了。真不知道莫心柔从哪里找来的琴弦。此琴志在必得!心念一动,左臂一探,骤然欺进,来抓项承志的遏云行。
好厉害!项承志尽力向后一撤,几乎成了金刚铁板桥。白龙这一抓倒是没又想过会一击奏效,刚要变式,一道寒光直奔咽喉而来。忙止住进势,生生将上身向后挪了半尺,让开剑锋,两指一错,在剑脊弹了一下,锵然一声龙吟,秋水寒被斜斜弹开。
白龙年近四旬,在武功上的浸淫已经超过了二十年,多年在江湖上的拼杀,积累了无数杀敌制胜的经验。而项承志兄弟俩初出茅庐,和真正的高手对阵还是第一次。功夫可以起五更,睡半夜,但是经验不能,只能一点点的拼杀,积累。
一招过后,兄弟俩的劣势就显现出来。白龙白衣飘飘,在琴剑中挥洒自如。若不是秋水寒的锋锐无匹,若不是兄弟俩心意相通,才屡屡从白龙的手下侥幸逃脱。不过,现在就是兄弟俩想脱身都办不到,时间一久,只怕真的会葬身在这箬帽峰。
咳,咳,咳
忽然,夜风里传来了一阵咳嗽声,很苍老,也很突兀。
兄弟俩左支右绌,哪里还有心思注意这些。不过,白龙却是大大的吃了一惊,一个倒蹿,蹿出足有两三丈远,靠在一棵树上,脑袋极快地左右摆动,神色身世惊惶。兄弟俩现在连吃惊是心情都没有了,扶着一棵树,大口喘着粗气。
只听夜风里又传来一阵咳嗽,有人道:“我说白龙啊,你怎么就不长记性。我老药花子能救你的命。可现在老药花子想睡一觉,你都不让我睡安生。你这条该死的的小臭虫!”
兄弟俩这回听清了。这个声音好苍老,听得出,即便没有古稀,也得年过花甲。这样一个老人,为什么白龙会如此惧怕?
随着踢哩趿拉脚步声,一个人颤颤巍巍老头走到白龙面前。用手指着白龙的:“你个臭小子。趁着我老药花子到关外这几年,你就忘记了你自己赌的毒誓了!你给我说一遍。”老者的肩头扛着一柄锄头,不过样式和常见的不太一样,在月光下,发出乌色的亮光。
刚才还神气活现的白龙额头渗出了都打得汗珠,嘴唇抖了抖,道:“死者您的药锄之下。”
“亏得你还记得!”老药花子手指点动,“你自己说,你该死不?”
白龙的两只手抠住身后的树干,下颌不停地抖动,身体也不停地往下堆。最后,两只手按到了树下,抓住了有些糟朽的陈草。陡地,白龙的双臂在树根上一撑,双脚搅起陈草败叶泥土,卷向老药花子。同时,两条腿一个“乌龙绞柱”,直蹬老药花子的胸口。
兄弟俩的惊呼还没有来得及出口,老态龙钟的老药花子突然变得敏捷无比。白龙搅起的陈草败叶泥土刚刚扬起,人就已经跳到一边,抡起药锄,噗地一声,刨进了白龙的后心,又准又狠,毫厘不差。老药花子的一躲一刨,实在是平淡无奇,偏偏就是这平淡无奇的一击,堂堂龙王寨的四当家的就血溅荒山,一命呜呼了。
老药花子拔下药锄,噗,血溅起足有半尺多高。老药花子
拄着药锄,叹了一口气,道:“你说你,当初救了你,现在又杀了你,还得刨个坑儿埋了你。你说是不是我这个老药花子上辈子欠你的。这辈子你来讨债啊。”一边说,一边挥动药锄开始刨坑。那药锄端地锋利无比,随着嚓嚓轻响,一块一块的山岩泥土被刨下来,就像快刀切豆腐,毫不费力。
等兄弟俩的气息喘地匀乎了,老药花子的坑也刨好了,叫道:“你们两个还看什么?还不赶紧帮我把这条死虫子抬到坑里埋了?你们是不是还想报官啊?”
报官?那不是自找麻烦吗?兄弟俩放下琴剑,抬起白龙堆尸首扔到坑里。然后捧起山岩泥土往坑里扬。老药花子阻止道:“这个就不麻烦你们俩了。你们去找一些枯草败叶来。”
兄弟俩一愣,老药花子头也不抬,药锄挑开大块的山岩,发出当当响声,散碎的泥土被勾到坑里。箬帽峰到处都是去年的陈枝败叶。一转身的功夫,兄弟俩一人抱回了一抱。
坑刨得快,土培得也快。老药花子拿出一只布囊,往土上抖了一些药末子,用药锄荡平,道:“把草扬上吧。”哦,兄弟俩明白了,把陈枝败叶一把一把扬到土坑上。老药花子十分满意,看着兄弟俩扬完,道:“不想有事,就管好你们的嘴。我走了。”药锄往肩头上一扛,又颤巍巍地走进了丛林。
短短的时间里,兄弟俩从生到死,险一险两世为人。老药花子一走,两个人倒有些茫然不知所措。正站着,老药花子的声音传了过来:“赶紧回吧。再磨蹭,天就亮了。”
可不,兄弟俩恍然大悟,向林中一抱拳,道:“多谢老人家。”没有回声,大概是走远了吧。兄弟俩顾不得许多,收好琴剑,急匆匆跑下箬帽峰。悄悄地回到房里,换下被汗水浸透的衣衫。还好,白龙没有动刀剑,除了几块淤青,没有什么大碍。不过,睡意全无,瞪着眼睛躺在床上。
天刚蒙蒙亮,兄弟俩就起来,赶紧找木盆把衣服洗了。刚洗到一半,凌霜就起来烧水做饭,看到兄弟俩在洗衣服,道:“大哥,二哥起得好早啊。”啊啊。兄弟俩应着,加紧洗衣服。
兄弟俩以前早上也是洗过衣服的,凌霜倒也不觉得有什么奇怪,略微洗漱了一下,就去准备早饭。今天是占卜的日子,还有许多水要烧呢?
经过了庄重的沐浴,更衣,焚香。溥源大师捧出一只条形的锦盒放在香案上。双手和什,默诵经文。诵毕,小心翼翼启开锦盒,拿出一只红绫包裹,解开,露出一把齐齐整整的蓍草。这蓍草是溥源大师亲自到河南汤阴的文王演易台前精心采集的的蓍草,视若珍宝。
溥源大师用手一拂,摊开蓍草,随手拣起一根夹在左手的小指之间。右手一荡,蓍草一分为二,四四分数,开始起卦。
所有人都端坐在蒲团上,平心静气。
“系辞”云: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为二,以象两,挂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时,归奇於仂,以象闰,五岁再闰,故再仂而后挂。
大衍之数五十,取四十九为用。因为只有用“四十九”根蓍草,过揲的余数才能是“三十六、三十二、二十八、二十四”,以四揲之,才能够得到“九六七八”。由此推导出九为乾爻,三十六为乾策;六为坤爻,二十四为坤策。
分而为二,以象两,挂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时:分而为二者,以四十九策分置左右,两手象两者,左手象天,右手象地,是象两仪也。‘挂一’者,挂犹悬也,于左手之中取一策悬于右手小指之间。‘象三’者,所挂之策所以象人而配天地,是象三才也。‘揲之以四’者,‘揲’,数之也,谓先置右手之策于一处,而以右手四、四而数左手之策,又置左手之策于一处,而以左手四、四而数右手之策也。‘象四时’者,皆以四数,是象四时也。”
归奇於仂,以象闰,五岁再闰,故再仂而后挂:“奇”是所挂之一,仂左右手之余策。归奇於仂象征历法中的闰年;一挂两揲两仂为五,故为“五岁”。再:两。象征五年之中两次闰月。
这段周易起卦的“系辞”项承志也看过,只可惜似懂非懂,现在看着溥源大师一点一点地起数,在纸上记下爻数。
反反复复六遍,溥源大师放下蓍草,轻轻吁了一口气道:“得‘地山谦’动九三‘谦之坤’。”
建文帝没有出声。“易经”为诸经之首,他当然读过。溥源大师说出了卦名,立即想起了‘谦’卦的卦辞:亨,君子有终。谦,山在地之下,既有谦虚谦让之意,也暗含着退避退让。难道这真的是天意难为吗?想到这里,不由得暗叹一声。
叶希贤叹了一声,道:“走是一定要走的。只是不知道此一行是吉是凶?”
溥源大师道:“九三爻辞是:‘劳谦,君子有终,吉’。只怕要劳动圣驾,纵有风险,也定能逢凶化吉,遇难呈祥。”
牛景先听了这话,点了点头,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应先皱了一下眉,道:“溥源师兄,不知道卦象有没有说哪个方向才是应该去的方向?”
溥源大师提起笔画了几下,道:“动九三‘地山谦’之‘坤’。既然要动,就要在变卦里看。”建文帝默然地点了点头。
溥源大师徐徐地道:“元亨,利牝马之贞。君子有攸往,先迷后得,主利。西南得朋,东北丧朋,安贞吉。至于方向,想来圣驾心中已经明了,无须老僧赘言。牝者,雌也,也指溪谷。此一行,应多走山川溪谷,少行大路。”这话倒是不假,逃亡自然是与隐蔽越好,走大路不是自找麻烦吗?
溥源大师说到这里,沉吟了一下,脸上露出忧色。建文帝一见,和缓地道:“溥源师兄有话尽可直言。”
溥源大师看着几个人,犹豫了一下,道:“这个‘牝’字是不是说让圣驾乔装改扮才能‘安贞吉’呢?”
牛景先一愣,继而头摇得想拨浪鼓一样,道:“那怎么行?现在圣驾屈尊为僧已经够为难的了。难道还要扮成女装不成?不成,不成!”
“小不忍则乱大谋。”建文帝语气依旧和缓,“更始诛刘縯,汉光武恨之入骨,表面上佯为驯服,暗中发奋,才成就一番帝业。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在位也好,逊国也罢。建文帝依旧是众人心中的九五之尊,说的话就是金口玉言,只好默不作声。
溥源大师看建文皇帝等人没有异议,接着道:“还有,应先,应能,还有应贤几位师兄,牛老檀越,几位以前在久在朝中为官,认识几位的人不在少数。没有抓到几位,燕王殿下怎么会死心,早就发下了海捕文书,各州各县画影图形,一旦哪一个认出诸位中的哪一个,那可就大事不妙了。”此言不差啊!难道就让圣驾一个人独往天涯吗?那怎么行?
沉寂了一会儿,项承志犹疑着道:“大师是不是想让我们兄弟二人护送圣驾啊?”溥源大师微然颔首。
“我们也去!”傲霜应声道。
蓦地,建文帝发出悠悠一声长叹,一脸的萧索。
溥源大师问道:“不知圣驾还有何事忧心于怀?”
建文帝喟然道:“此一行不知止于何时何地啊?”
溥源大师端详了一会儿卦象,缓缓地道:“天遥地远,山高水长,声如奔雷,万事可解。”
别人也许没有听明白,建文帝却甚是明白。“地山谦”的变卦是“坤”,错卦是“天泽履”有走之象;互卦是是“雷水解”,有通达之意;综卦“雷地豫”.中卦辞也有“行师”二字,难不成西南真有匡扶社稷的王师不成。有没有且不去管它,现在是山穷水尽,走出去也许就是柳暗花明,海阔天空。思量着,道:“今天十七,明天十八。我们明天就走吧。”说着,叹了一口气,站起来向溥源大师合什一拜,走了出去。
占卜完结,溥源大师精心收好蓍草。画着卦象的纸也收了起来。刚刚收好,戒空小和尚跑了进来,合什道:“师傅,昨天投宿的文士不见了。”
“哦,”溥源大师捧着锦盒,“也许他去赶早去登箬帽峰去来吧。我们回去吧。”兄弟俩听了,不禁相视一笑。白龙是在箬帽峰上。不过不是今天赶早去的,而是昨天半夜去的。而且再也下不了箬帽峰了。
送走了溥源大师,叶希贤沉吟道:“圣驾已经恩准乔装改扮。但究竟如何改扮才能确保圣驾无虞却是要从长计议的。”叶希贤的话没有错,此一次西南之行前途未卜,如果不考虑周详,一旦出现个一差二错,后果不堪设想。
一阵难挨的沉默,傲霜扯了一下项继先的衣袖,小声道:“继先哥哥,你说圣驾改扮成比丘行不行啊?”她没敢说扮成女尼,婉转的说成比丘。
不过,她的话一出口,项继先就像被火烫了一下,低声呵斥道:“不许胡说。”傲霜吓了一跳,立刻低下头。
两个人的声音都很低,连坐在不远的叶希贤都没有听清,回头问道:“你们在说什么?”
“傲霜说,说让圣驾改,改扮成比丘。”项继先声音还是很低,有些吞吞吐吐。
“比丘?”叶希贤轻轻念着,思忖着,继而点点头,“好倒是好,只是也要委屈你们几个了。”
傲霜没有想到叶希贤会答应,冲口道:“委屈什么?”
“削发为尼。”项继先淡淡吐出四个字。
“我才不!”傲霜使劲的一摇头。
叶希贤呵呵一笑,道:“圣驾改扮成比丘,你们随行护驾,要是做俗家打扮,除了瞎子,只怕没有人看不露。”
傲霜偏着脑袋想了一会儿,道:“我们不削发,削了发也没有度牒。细查之下也一样会露。如果官府盘问,就说是刚收到俗家弟子,等削发以后在发度牒。”
“好吧,就这么办。”几个人都表示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