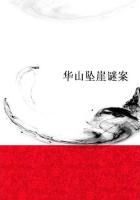“只要我身上有钱,看到这些募捐箱,就没法儿无动于衷,”他说,“今天电信的消息多好啊!那些好样的黑山人。”
“您不是说真的吧?”当公爵夫人告诉他渥伦斯基也乘这趟车走时,他大叫起来。刹那间,奥伯朗斯基的脸显得很哀伤,可没过一会儿,他就抚平络腮胡子,迈着略带弹性的步子走进了渥伦斯基所在的候车室。奥伯朗斯基巳经完全忘记了他扑在妹妹尸体上痛哭失声的样子,而只把渥伦斯基看成英雄和老朋友。
“尽管他有许多缺点,但还得替他说句公道话,”奥伯朗斯基一走,公爵夫人就对科斯尼雪夫说,“他是个地道的俄罗斯人,斯拉夫人的天性!我只是担心渥伦斯基看到他会难过。不管怎么说,这个人的遭遇让我很感动。路上和他谈谈吧。”公爵夫人说。
“好的,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向来不喜欢他。但他今天的举动弥补了很多过失。他不但自己参军,还出资带去了一个骑兵连。”
“我听说了。”
站台的铃声响了。大家都朝门口拥去。
“他在那儿!”公爵夫人指着渥伦斯基说,他穿着一件长大衣,戴着一顶黑色宽边帽,手挽着母亲从他们身边走过。奥伯朗斯基走在他旁边,兴奋地说着什么。
渥伦斯基皱着眉头,直盯着前方,似乎没听到奥伯朗斯基说些什么。
或许是奥伯朗斯基指给他看了,渥伦斯基朝科斯尼雪夫和公爵夫人站立的方向望了望,默默地举了举帽子。他饱经沧桑的脸,像化石一样漠然。
来到火车旁,渥伦斯基让母亲先走,自己默默走进一节车厢就不见了。
站台上奏起了叶上帝保佑沙皇》的音乐,然后是一片“乌拉”和“万岁”的欢呼声。一个胸部凹陷的高个儿年轻人,特别醒目地行着礼,在头上挥舞着毡帽和花束。两名军官和一位戴着油腻帽子的大胡子老者,也从年轻人身后探出头来行礼。
科斯尼雪夫同公爵夫人告辞后,和卡塔瓦索夫走进拥挤不堪的车厢。列车开动了。
列车在察里津车站受到一群齐声高唱爱国歌曲的年轻人的欢迎。志愿兵又探出脑袋来行礼,但科斯尼雪夫并不留心他们。他同他们有过很多接触,巳经熟悉他们的大体类型,没什么兴趣。但卡塔瓦索夫从事的学术工作却没有研究志愿兵的机会,因此对志愿兵很感兴趣,拉着科斯尼雪夫问这问那。
科斯尼雪夫建议他去二等车厢同那些志愿兵谈谈。到了下一站,卡塔瓦索夫就过去了。
列车一停,卡塔瓦索夫就换了车厢,去同志愿兵结识。志愿兵坐在车厢角落里大声说话,显然知道乘客们和刚进来的卡塔瓦索夫都在注意他们。那位胸部凹陷的高个儿年轻人说话声比谁都响,他显然喝醉了,在说学校里发生的什么事情。他对面坐着一位身穿奥地利近卫军服的中年军官。他微笑地听年轻人讲,想打断他的话。第三个志愿兵穿着炮兵制服,坐在他们旁边的一个箱子上。第四个志愿兵在睡觉。
卡塔瓦索夫同年轻人交谈起来,了解到他原来是位莫斯科富商,二十二岁之前就挥霍掉了一大笔财产。卡塔瓦索夫不喜欢他,因为他有股女人气,娇生惯养,身体羸弱。年轻人确信尤其是在这种喝得醉醺醺的时候自己正在实施什么英雄壮举,大煞风景地拼命自吹自擂。
第二位退役军官也给卡塔瓦索夫留下了不愉快的印象。他显然经历丰富,在铁路上供过职,当过管家,开过工厂,尽说些不必要的话,用些不恰当的术语。
但卡塔瓦索夫非常喜欢第三位炮兵。他是个谦逊沉静的人,很佩服那位退役近卫军的学识和那位商人自我牺牲的英勇行为,对自己却缄口不语。当卡塔瓦索夫问他,是什么促使他去塞尔维亚时,他谦虚地回答道:
“哦,大家都去的。应当帮帮塞尔维亚人,他们真可怜。”
“是啊,他们特别缺少炮兵。”卡塔瓦索夫说。
“不过我在炮兵连服役时间不长,也许他们会把我调到步兵连或骑兵连去。”
“他们最需要的是炮兵,为什么却要把你调到步兵连去?”卡塔瓦索夫说,根据炮兵的年龄,他推断他的军衔一·定很高。
“我在炮兵连服役时间不长,我是个退役的士官生。”他说,然后开始解释他为什么没有通过军官委任考试。
这一切都给卡塔瓦索夫留下了不太愉快的印象。当志愿兵下车到站台上喝酒时,卡塔瓦索夫想找人聊聊,证实一下自己的不愉快印象。一位身穿军大衣的老年乘客,一直在听卡塔瓦索夫和志愿兵谈话。只剩下他俩时,卡塔瓦索夫同他聊了起来。
“所有这些上那儿去的人,情况多么不同啊!”卡塔瓦索夫含含糊糊地说,既想表达自己的观点,又想引出老者的看法。
这位老兵参加过两次战役。他知道军人该是什么样子,通过那些志愿兵的外表、言谈乃至他们一路上狂喝滥饮的架势,他认为他们都是些兵痞。此外,他住在一个县城里,想说说他那里有个退役军人,是个酒鬼加小偷,由于没人肯雇佣他,他才报名参军。但他凭经验知道在当前的民意下,要表达任何与流行观点相左的看法,特别是指斥志愿兵,是很危险的事,因此他也对卡塔瓦索夫察言观色。
“嗯,那边需要人。”他笑眯眯地说。他们开始谈论最新的战争消息,彼此掩饰着心中对明天将同谁作战的疑惑,因为根据最新情报,土耳其人巳经被全线击溃。最后,他俩谁也没有表达自己的看法就分手了。
卡塔瓦索夫回到自己车厢,跟科斯尼雪夫说起他对志愿兵观察的结果时,不由得含糊其辞,好让科斯尼雪夫觉得他们都是出色的士兵。
到了一个大站,迎接志愿兵的又是一片歌声和欢呼声,又出现了拿着募捐箱的男男女女,当地的夫人们又向他们献花,陪他们走进餐厅,但所有这一切都远不如在莫斯科那样声势浩大。
列车停在省城站台时,科斯尼雪夫没去餐厅,而是在站台上来回踱步。
他第一次经过渥伦斯基车厢时,注意到百叶窗是放下来的。第二次经过时,他看到老伯爵夫人坐在窗户边上,招手让他过去。
“您瞧,我现在送他去库尔斯克。”她说。
“是啊,我听说了。”科斯尼雪夫答道,站在她的窗口朝里边张望。“他这次的举动多漂亮啊!”他发现渥伦斯基不在车厢里,又说。
“是的,可是经历过那样的不幸之后,他还能干什么呢?”
“多么可怕的事!”科斯尼雪夫说。
“咳,我遭的是哪门子罪呀!请进来吧……咳,我这是遭的哪门子罪啊!”科斯尼雪夫走进来坐在她身边时,她又说了一遍。“您想也想不到!整整一个半月他跟谁都不说话,要我求他他才肯吃东西。一秒钟都不能让他一个人待着。我们拿走了所有他可以用来自杀的东西。我们住在楼下,可谁也闹不清他会干些什么。您知道他有一回为了她开枪自杀吗?”她说,回想起这一幕,老太太紧锁眉头。“是的,她这种女人,真是死得其所。连死的方式都那么卑鄙下贱。”
“这事不应该由我们来评判,伯爵夫人,”科斯尼雪夫叹息着说,“但我能理解您有多痛苦。”
“咳,别提了!我住在我的庄园里,他也和我住在一起。有人送来一封信,他回了信,让人送去。我们都不知道她自己就在车站。晚上我刚回到自己房里,玛丽就告诉我在车站有位夫人卧轨自杀了。我觉得晴天霹雳一般!我就知道是她!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院‘别告诉他!’但他巳经知道了。他的马夫到了车站,什么都看到了。我跑到他房间,他巳经发疯了,他的样子太可怕了!他一声不吭,骑马冲到车站。我不知道在那里发生了什么情况,但他们带他回来的时候,他就跟死尸一样。我都认不出他来了。‘完全虚脱了。’医生说。然后他就语无伦次,几近疯癫。咳,真是没法说呀!”公爵夫人摆摆手说道,“可怕的时刻啊!怎么说她也是个坏女人。简直是玩命的激情!只不过证明她不太正常罢了。对,她就是证明了这一点!她毁了两个了不起的男人她丈夫和我倒霉的儿子。”
“她丈夫怎么样了?”科斯尼雪夫问。
“他带走了她的小女儿。阿列克斯起初什么都答应了。但现在他非常懊悔把自己的女儿交给了一个陌生人,可他又不能食言。卡列宁来参加葬礼了,我们尽量安排好,不让他和阿列克斯见面。这样对他和对做丈夫的来说都要好些。她使他自由了。但我可怜的儿子完全沉湎在她身上,他什么都抛弃了他的事业和我,可她还不同情他,存心想置他于死地。不管怎么说,她的死就是一个不信教的可怕女人的死法。上帝饶恕我吧!我一看到我儿子给糟蹋成那样,就免不了要恨她!”
“他现在怎么样呢?”
“老天有眼,帮助我们了。发生了塞尔维亚战争!我老了,不懂什么战争,可对他来说,这是上帝的恩赐。我是他母亲,当然会担心他,主要是彼得堡那边不太看好这件事。但没法子!这是唯一能使他振作起来的事情。他的朋友亚希文玩牌输了个精光,也要去塞尔维亚,是他来看他,说服他一起去的。现在他动心了。请您和他谈谈吧。我希望他能分分心。他太悲伤了。倒霉的是,他的牙疼病又犯了。但他见到您会很高兴的。请您和他谈谈。他在那边散步。”
科斯尼雪夫说他很乐意同他谈谈,就朝另一侧的站台走去。
在站台上堆积的麻布袋投下的斜影里,渥伦斯基穿着长大衣,帽子拉得低低的,双手插在口袋里,像笼中困兽一样走来走去,每走二十步就来个急转身。科斯尼雪夫走近的时候,觉得渥伦斯基似乎看到他了,却又假装没看见。但科斯尼雪夫不在意,他和渥伦斯基交往不再掺杂任何个人因素。
在他眼里,渥伦斯基此刻似乎是位从事伟大事业的伟大人物,科斯尼雪夫认为有责任去鼓舞他、激励他。他走到他身边。
渥伦斯基站住了,看着科斯尼雪夫,认出他来,朝前走几步迎上前去,使劲地握了握他的手。
“也许您不希望见到我,”科斯尼雪夫说,“不过我能否为您出点力啊?”
“见到您比见到别人要少些不愉快,”渥伦斯基说,“对不起。我生活当中巳经没有任何乐趣了。”
“我理解,我希望能为您效劳,”科斯尼雪夫凝视着渥伦斯基明显流露出痛苦的脸,说,“您是否需要我给李斯提奇或米兰写封信呢?”
“哦,不!”渥伦斯基答道,似乎理解起来颇费了一番工夫,“如果您不介意,我们来回走走吧。车厢里太闷了。写封信?不,谢谢。去死是不需要什么介绍信的!除非写给土耳其人!”他笑了笑又说,只有嘴唇动了动。他的眼中始终是愤怒和痛苦的神情。
“是的,但不管怎么说,和头面人物建立起关系都是必要的,也更方便些。不过,随您的便。很高兴听到您的决定。志愿兵受到了不少批评,像您这样的人可以改善舆论对他们的印象。
“我做人的特点就是不在乎生死,有足够的体能去冲锋陷阵,去拼杀,或者倒下我很确信这一点。我很高兴有些事情可以让我献出我不需要而且非常厌恶的生命!它对别人也许还有点用处。”由于牙齿剧痛不止,妨碍他表达想要表达的内容,他很不耐烦地动了动下颌。
“我敢断言,您会恢复状态的,”科斯尼雪夫感动地说,“帮助同胞兄弟从压迫中解放出来,是一个值得为之出生人死的目标。上帝赐予您战斗的胜利和内心的安宁。”他又说,把手伸出来。
渥伦斯基激动地握住他的手。
“是啊,作为工具,我或许还有点用,但作为人,我却是个废物。”他一字一顿地说。
他结实牙齿的剧烈疼痛使他满嘴都是口水,说话受到妨碍。他默不作声地望着缓慢、平稳地在铁轨上滑行而来的煤水车的车轮。
忽然,一阵奇怪的感觉不是身体的疼痛,而是内心的痛楚使他瞬间忘却了牙疼。看到煤水车和铁轨,再加上同那次灾祸后他从未见过的朋友交谈,他忽然想到了她,想到了那天他像疯子一样冲进车站时她所剩下的一切:在一张桌子上,她那残缺不全、余温仍在的尸体,恬不知耻地横陈于陌生人眼皮之下。盘着浓密发辫的完整的脑袋朝后仰着,鬓角上有几缕鬈发。红唇半开半闭,美丽的脸上凝固着一种表情嘴唇凄伧,双眼睁开,目光凝滞这骇人的表情,似乎在用语言重复着他们争吵时她对他说的那句可怕的话院你会后悔的!
他竭力回忆他们初次邂逅时她的模样也是在站台上她那么神秘、动人、美丽,自己追求欢乐,也给予他人欢乐,不像他所记得的她最后一刻留给他的残忍的报复神情。他竭力回忆他们相守的美妙时光,但这些时光被永远玷污了。他只记得她威胁他,要让他饮恨终生,如今她办到了,胜利了。他不再觉得牙疼,一阵嗫泣扭曲了他的脸。
他在麻布袋旁来回走了两遍才控制住自己的情绪,然后,他平静地对科斯尼雪夫说:
“除了昨天的电讯,您还看到过什么新的消息吗?是的,他们第三次被打败了,但明天会有一场决战。”
两个人又谈论了一番推选米兰出任国王的公告以及它可能产生的巨大效果。站台铃响第二遍后,他们回到了各自的车厢。
科斯尼雪夫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能够离开莫斯科,所以没给弟弟发电报让他来车站接他。快到中午,卡塔瓦索夫和科斯尼雪夫乘着在车站租来的四轮小马车,像阿拉伯人一样满身尘土地停在坡克罗夫斯克·列文家的大门口时,列文并不在家。凯蒂同父亲及姐姐坐在阳台上,她认出了大伯子,于是跑下去迎接他。
“您来都不通知我们一声,亏您好意思!”她说,把手伸给他,让他吻吻她的前额。
“我们一路上很好,不用麻烦你们。”科斯尼雪夫说。“我一身是灰,不敢碰您。我前一阵很忙,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可以离开。您还和从前一样,”他笑着说,“避开激流,躲在宁静的浅滩上安享您的幸福。这是我们的朋友卡塔瓦索夫,他总算来了。”
“我可不是黑人!等我洗一洗,我就有人样儿了!”卡塔瓦索夫微笑着伸出手,用他惯常的戏谑口气说。与他黑乎乎的脸盘相比,他的牙显得特别亮白。
“科斯提亚会很高兴的!他去农场了,这会儿该回来了。”
“老是忙着管理的事!”卡塔瓦索夫说,“‘躲在宁静的浅滩上’确实没说错。我们在城市里,除了塞尔维亚战争,什么也看不到!我的朋友对这场战争有什么看法?一定与众不同吧?”
“哦,没什么特别的,和大家一样,”凯蒂回答,很尴尬地看了看科斯尼雪夫,“我派人去找他。爸爸和我们在一起。他刚从国外回来不久。”
凯蒂派人去找列文,让仆人把满身风尘的两位客人分别带到列文书房和多莉以前住的房间去洗刷,又交代好给客人准备午餐,然后就敏捷地(这在怀孕期间是不允许的)跑上了露台。
“瑟吉尔斯·伊万尼其和卡塔瓦索夫教授来了。”她说。
“哦,这么热的天,他们多辛苦哇!”公爵说。
“不,爸爸,他人很好。科斯提亚很喜欢他。”凯蒂注意到爸爸脸上的讽剌神情,恳求似的笑着说。
“我无所谓。”
“您去招待他们吧,亲爱的,”凯蒂对姐姐说,“他们在车站碰到史蒂瓦,他很好。我要赶快去看看米提亚。真够戗,从早餐开始我就没喂过他了。他现在该醒了,一准在大哭特哭。”她感到奶水很胀,快步朝育儿室走去。
她猜得不错,婴儿和她之间的联系还没有割断,她从乳房发胀就能肯定孩子饿了。
她还没到育儿室就知道婴儿在哭。他确实在哭。她听到他的哭声,加快了脚步。但她走得越快,他就哭得越响,哭声响亮健康,听得出他饿得不耐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