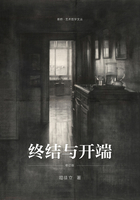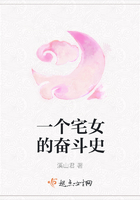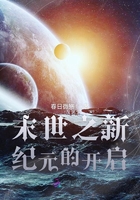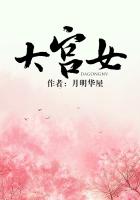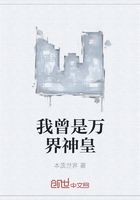发现岩画
缘分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做梦也不会想到我竟与岩画有了不解之缘。
1968年“文革”中,我参加了贺兰县潘昶公社关渠4队的“两教”(即社会主义教育和集体主义教育)试点。这里离黄河很近,是一个很穷又偏僻的小村庄。到了1969年春天,“两教”结束时,在写总结报告中,我针对过去整农村干部的那套“冷、闷、斗、踢”方法,提出了关心爱护、说服教育的方法。没料到县委很重视,不仅把我的报告印发“三干会”,而且让我同潘昶公社副社长王生兰到通义、立岗、四十里店、洪广、常信、金山几个公社去检查“两教”的进行情况。
当我们来到金山公社后,公社干部说贺兰口生产队“两教”搞得好,并建议我们到那儿去看看。于是我同王生兰社长骑着自行车直奔贺兰山。这一带的地形王社长很熟,他说他小时候在这一带放过羊。
我们沿着弯弯曲曲的小道上了山。骑自行车上山真费劲,走走停停,直喘大气,干脆把外衣脱了迎着山风蹬。骑到半山腰有一个羊圈,放羊的都出去了,王社长说:“不骑了,把车子撂到这儿吧,下山时再来骑。”我感到诧异,不打声招呼就把车子放下如果丢了怎么办?那时一辆自行车顶半个家当,可不是闹着玩的。他看出了我的心思,满有把握地说:“放心吧,丢不了。”我只好不情愿地锁好自行车跟着他走向贺兰口。
当晚我们住在小学校里,点着小油灯,生产队长、贫协主席、会计向我们汇报了“两教”和春耕情况,这里留给我的印象是山上闭塞,民风淳厚,是一方世外桃源。
第二天上午生产队干部过来又聊了聊,我整理了一下笔记也就无事可做了,难得清闲。王社长有许多亲戚要拜访,由他去了。我那时二十多岁,正是精力充沛风华正茂的年华,生性好动,来到这山清水秀之地巴不得快些去游览一番。吃过午饭,我向树多的山口走去。大山的诱惑力吸引着我来到了贺兰山口。山口两侧高山对峙,峰峦苍翠,山泉淙淙,一排柳树婀娜多姿,景色如画,秀色可餐,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当我来到南侧一块突出的巨石前,突然发现上面刻画了许多动物,除了牛、马、羊、鹿、骆驼、虎之外,还有一些长颈粗尾叫不上名字的怪兽,有的奔跑,有的站立,动静不一,姿势各异。
这块巨石当地人叫它龙口,下边浪花飞溅,上边各种动物密集。这幅美妙而又激动人心的画面深深地铭刻在我的脑海里。这时,我把自己记忆里的各种动物形象搜罗出来进行对比、分析,我甚至把过去看过的《化石》刊物上的恐龙形象也拿来和岩石上的怪兽进行对比。我深感这些石头上的画太奇妙了,过去学过的知识远远不够用了。
山石上刻的画有的清楚,有的刻槽深,有的模糊,有的甚至漫漶一片,有的石皮也剥落了。我站在旁边可以轻轻地摸,比划着看,上上下下看了个够,然后又向前走,边走边看。只见山崖上、大石头上都有画,简直走进了石刻艺术的画廊。
除了动物岩画外,最多的还是各种各样的人面像,变化多端奇形怪状,充满了神秘感,此外还带有一点恐怖感。山风呼呼叫,泉水哗哗流,使人仿佛进入了另外一番天地。一个个古怪的大脑袋似乎瞪着眼睛瞧着你,有的又没有眼睛,好像张着血盆大口要喊出什么,真是不可思议。这里的人面像不仅面部变化多样,而且发式也很特殊,有的打着髻,有的光着头,还有的似插着羽毛和牛羊角,总之比戏台上的那些脸谱有意思得多。
沿着南侧山沟看到S形山弯顶头,没有岩画了,我又从北侧沿着山石寻找岩画,北侧比南侧岩画多得多,绝大部分仍然是人面像或面具,成片成片的人面像高悬于山崖上,十分壮观。而且看到了人的实心手掌,左右手都有,我把手贴在上面比了比,同我的手一样大,令我惊喜不已。
不知不觉落日衔山临近黄昏了。
虽然走马观花粗粗地看了一遍,但让我流连忘返,回味无穷。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岩画,而那时我还不知道眼前形象各异、生动多姿的符号就是人类最早的造型艺术——岩画。
谁也说不清的石头画
晚饭时,我问村干部下午看到的那些石头画是谁搞的?是什么时候的?他们谁也说不清,只是含糊地说可能是过去人搞的吧,再就无法解释了。
为了搞清这些石头画的来历,我请小队会计领我到山脚下一位姓伏的老人家,老人是山里最年长者。
伏老八十,浓眉大眼,虽然头发雪白,但脸色红润,身体硬朗,说话底气足。老人家儿孙都单另过,老两口有3间房,外间是大间,有一盘大炕,铺毡堆被,炕对面是一排盛粮食和衣物的大木柜,里间屋放着杂七杂八的东西。老人家是位猎人,地上堆了有一米多高的青羊皮,足有几十张。老伴夸他是神枪手,打青羊一枪一个,不放空枪,脾气倔着呢,打不上青羊十天八天不回家。
坐在大炕上我们无拘无束地攀谈起来。
“沟里石崖上那些画您老记不记得是什么时候有的?”我问老人家。
“山墙(指山崖)上那些画早就有了,我小的时候就有了,我也问过我爷爷,他说他小的时候就有。”
“那时间一定很久了。”我说。
“我估摸有些年头了,我们都是路过看一眼,到底有多少年我就说不上了。”
“有没有什么传说?”我启发他。“传说是有呢,听老人们讲,山墙上的那些人头,是过去杀一个人就刻一个人头,杀的人真不少呀。”老人惋惜地说。
“还有什么传说没有?”我又问。
“别的传说没有了,听老人们说南山墙下有一幅画是画李昊王的,画得可真了,还有大旗呢。就在南山墙根,一个大石头旁。”老人笑着说。
“是哪个大石头?”
“从龙口向西50步,那个有很多人头的山墙西下角水渠边边上。”
“你知道不知道你的老祖先是当地人,还是从哪里来的?”我只得刨根问底了。“传说是从山西洪洞县大槐树迁来的。”老人说。
“这么说你们不是原住户了,这里有没有原来的老住户。”
“没有。”老人肯定地说。
再也问不出什么了。我终于明白,由于历史的变迁和战乱,原有的住户早已不知去向,后来迁移来的当然说不清原委,从此断了音信、传说,也断了文化的延续。人们一辈辈流传下来的只能是只言片语。
回到学校,王社长已经睡觉了。我躺在炕上怎么也睡不着,脑子里翻来覆去全是下午看到的那些画,令人兴奋又使人焦虑,要看出个道道来还得下番工夫。明天就要下山了,得和王社长商量商量,无论如何明天再给我半天时间,只需半天时间,让我再去看一看,得看个究竟,还得验证一下伏老所说那幅李昊王的画。
“王社长,你醒醒。”我使劲摇了摇沉睡中的王社长。
“啥事?”王社长迷迷糊糊地问。
“明天咱们下午回吧,上午我还想再去看看那些山墙上的画。不会误事,下坡路跑得快。”我把理由都抖搂出来了。
“你们这些大学生呀就是名堂多。好吧,下午回就下午回。”他满足了我的要求。
深深刻在脑海里
第二天一大早,我洗了一把脸,冒着寒气,迎着朝阳进了山。有了思想准备,也有了经验,我仍沿着老路来到龙口。
龙口上下的巨石上到处镌刻着岩画。高处的山石上有动物岩画,有各种人物形象,尤其是那些人面像,由于阳光斜射,看得特别清楚。那些山崖上的画一个一个就像精灵一样,有着无穷的生命力,有悲欢离合,也有七情六欲。这里铮铮铁骨的山石,铸造了它们豪迈的性格,清澈的泉水给了它们活泼的灵性。有些研磨的画就像薄纸一样浅;有些刻槽深的画又光又滑则似大山是块泥巴用手抠出来的,使人体味到时光的悠远,也感到岁月的沧桑。
尽管这些历史“老人们”不会说话,但它们满脸的皱纹和疤痕却告诉我,它们经历了太多的创伤。
在龙口中部的石缝右上侧和石缝中下部似禽掌又似蘑菇的右下角各有一组跳舞的人:石缝右上侧的是7人组舞,上方似有一人在领舞,其他6人手拉手在跳舞,身着长袍,舞姿婀娜,动作优美,步伐一致,既像是娱乐,又似在求偶,更像在祈求丰收。在这组舞蹈的下方约1米处,仍有一组跳舞的画面,4人组舞,身着长袍,舞姿与7人组舞相似。两组舞蹈动作一致,着装一样,只是人数不同。另外,上部7人组舞头顶有弧形波浪纹饰,琢磨象征人们在苍穹之下或帐房之内进行庆丰收或敬天地祭鬼神的活动,总之与劳动和娱乐有关。
在组舞的上部马鞍形山石的南北两侧,我发现南侧有羊的形象还有骆驼、马匹、人面的形象,在北侧的石面上又欣喜地发现两人射猎的形象,人物似着长袍,手执弓箭,而且弓箭很大。人物的装饰头部似有角形或羽形头饰,估计是一种狩猎时的伪装。在人的下部有一个长长的像尾巴一样的东西,估计也是狩猎时的伪装。
在马鞍形山石西北侧我又看到了太阳的形象,但不知为何太阳下有一条长线,是不是表示云彩?同时还看到了鸟的形象,是一只直立的鸟,有鸟冠,长尾,很美丽。这里的人面像更特殊,坐南面北的石面上有一个人面眼睛似一只睁一只闭,百思不得其解。在龙口处的下方,有双鹿造像以及大量的人面,中间是大量的各种动物群麇。
总之,龙口这儿的岩画是一处岩画的荟萃之地,有许多惊人之笔和精彩之作,异彩纷呈,鬼斧神工,艺术之光照亮了山崖,也照亮了我的心。
在龙口西大约50米的地方,有一方明代万历三十七年修筑贺兰关隘时的文告,十分清楚。在文告西侧15米一个巨石下角,我找到了那方西夏时李昊王出行的画,坐南向北,画面长约1米,高约60厘米,画着两个人物,一个骑着马,头上戴着一顶官帽,显示出一副威严神气的样子;而另一人在拉马护驾。人物身后还画了两面三角形旗,表现了人物显赫的地位和气宇轩昂的风度。整个画的制作细腻,人物五官齐全,形象逼真,人物、战马比例适中,虎虎有生气。这幅画绝对是雕刻精品,可能是描绘了当年西夏王李元昊去离宫时的情景。
这幅写实作品不同于其他岩画。史载李元昊“性雄毅,多大略,善绘画,能创制物始。圆面高准,身长五尺余。少时好衣长袖绯衣,冠墨冠,佩弓矢,从卫步卒张青盖。出乘马,以二旗引,百余骑自从。晓浮图学,通蕃汉文字”(《宋史》卷四八五)。岩画与历史记载相比较何其相似乃尔!说明此图可证史,是十分珍贵的形象资料。
如果细看,那些形形色色人面中的多种图案却表示着某种含义,我的认识终于触及到神秘所在了。在众多的人面像前,我像一个朝觐者虔诚地拜谒在这众神之下,反复观察、对比、沉思,感到与宗教的某种崇拜有关,但到底是什么?我回答不上来。在众神的考问下,我还只是一名小学生。
站在高大伟岸的山崖下,面对着连绵几百米长的数百个人面像、图画、文字,随着山风的呼啸,我仿佛听到了历史的回声,感受到了心灵的震撼,受到了某种启迪。
下山时,我一步一回头。难忘的贺兰口之行结束了,但贺兰口岩画却深深地留在了脑际。
我终于又来看你了
从山上回来不久,我被分配到金贵中学,当了三年高中语文、政治教师和班主任,并且自学了中医。1974年初我从金贵中学调到了县科技卫生局,有空我就到县科委图书馆借书,一借一大摞,医疗卫生、历史地理、文物考古,见什么借什么,唯独没有岩画方面的文章和著作。
1978年我在《科学知识》杂志上终于看到一篇盖山林介绍阴山岩画的文章,如获至宝,我反复研读和咀嚼,心头点燃了一盏明灯,贺兰口岩石上的那些画不就是岩画吗?无论内容、题材、手法与阴山岩画几乎一模一样。
光阴荏苒,岁月蹉跎,10年后的1979年深秋,有了理论的武装,我忍耐不住探求岩画的渴望,坐着我弟弟拉石头的汽车第二次来到了魂牵梦萦的贺兰口。
久违了,贺兰口岩画,我终于又来看你了。
山石依旧,柳树凋零,我踏着枯干的叶子,沿着10年前的足迹边看边拍照。
由于“农业学大寨”引水修渠,炸坏了龙口处的珍贵岩画,那幅西夏王李元昊岩画也被炸掉了,损失严重。
站在龙口的破碎岩画旁,我感到时不待人,得快些行动了。
这次来拍了两卷120胶卷,又匆匆下山去了。这点资料成了我后来研究岩画的基础材料和资本。
岁月的风尘吹去和封杀了许多美好的记忆,但贺兰口岩画却拂之不去,苦苦折磨着我。
本能的好奇心和求知的渴望,促使我一往无前地探索岩画的奥秘。
1982年我从县医院要求调到县爱卫会工作,脱下穿了不到两年的白大褂。这次抉择是痛苦的,仿佛又走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但为了搞岩画我不得不走这条路。相对讲,到了爱卫会,时间充裕,可以上山搞岩画了。
为了上山搞岩画,也为了开展农村卫生工作,我同爱卫会新分配来工作的大学生张富贵商量买一辆带拖斗的摩托车。汽车买不起,买辆摩托花钱不多,省油,方便,有拖斗,可坐人也可以拉东西,一举数得。给卫生局打了一个报告,很快就批准了。
1983年6月初,我在天津医学院的进修结束了,一回来就和小张开着长江750摩托车拉上宁夏医学院的老朋友杨文彪一道上山去看岩画。
杨文彪是我在金贵中学任教时结识的好朋友,天津南开大学生物系毕业,为人豪爽、热情。早在金贵中学时我就多次向他讲过发现贺兰口岩画一事,这次特意让他去开开眼。看过岩画他赞不绝口。我们在北侧的西夏文题记处推敲和揣摩了半天西夏字,怎么也不认识,连猜都猜不出来,只好照猫画虎地描下来请西夏专家释读了。
那一天看得尽兴,在贺兰口住了一夜,晚上又听说拜寺口也有岩画。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又赶到了拜寺口,拜寺口虽距贺兰口约10公里,山石却都是由花岗岩组成,进山仅有一条羊肠小道,行路十分不便。经过调查,在沟内5公里处的一块巨石上发现刻有大明进士侯廷凤石刻题记一方,宽2.5米,高1.3米,记述了拜寺口壮丽景色以及修路的情景。此行虽然收获有限,却也了却了一桩悬案和心事,摸清了拜寺口的家底。
第一次亲密接触
经过深入的考察我们进一步认识了岩画的巨大价值,更加坚定了我整理岩画的决心和信心。
时逢县上搞农村“改水”工作,我就把改水的点首先设在了贺兰口。我们动员群众挖沟压塑料水管,挨家挨户安装水管和水龙头。这里改水太方便了,在龙口处修了一个蓄水池,水管支在池子里,利用水的自然冲击力,水就像自来水一样会自动流向各家各户,而且饮用的是卫生健康的矿泉水。
当然这些工作由技术工人去做,我每天问问进展,帮助解决问题,大部分时间则是钻在山沟里观察岩画,然后经过测量一一进行记录、编号、拍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