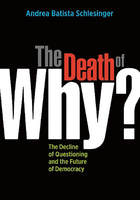三奶奶也觉得五娘闹得过分,但毕竟是自家妹子,无论如何要替她说几句好话。话到嘴边还未出口,被看破意图的太夫人瞪了一眼,意有所指地敲打她:“从前府上人少,我也由着你们瞎闹。但往后人越来越多了,该守的规矩还是得守。尤其嫡庶之别是成家立户的根本,不可不明。”
咀嚼着太夫人的话,三奶奶不由一阵心慌。往后人多,嫡庶之别,难道徐严和徐梧也得纳妾?左右有徐寒在,想来凌靖雪不会把方五娘怎样。她自身难保,不敢再插嘴,默默给方五娘递了个眼色。
好汉不吃眼前亏,方五娘咬咬唇:“妾身等了一日不见爷过来,以为出了事。下人们语焉不详,我才慌慌张张失了分寸,冲撞老太太和公主。”顿了顿,屈膝半跪下:“一切皆是妾身的过错,请老太太宽恕。”
太夫人瞟了她一眼,悠悠道:“你们二房的事,怎么问到我这里来?”
凌靖雪本还担心太夫人护着方五娘,没想到竟是一副任她发落的模样。她趁势发话,口气严厉教训方五娘道:“姨娘是驸马身边的人,就算信不过我,也不该大呼小叫让别人笑话。再说大嫂正在安胎,你这样冒冒失失闯来,万一惊了人怎么办?这几日驸马在正房休养,姨娘正可好好思过,谨言慎行。”
方五娘从小到大都被家人捧在手心里宠着,何曾受过这样的训斥?况且对方还是她最讨厌的凌靖雪。眼圈一红,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她悲悲切切地福了福身。
太夫人看着她就觉得心烦,又惦记着徐寒无人照料,忙不迭把她们打发了回去。叹了口气,不免对管妈妈感叹:“一个清高,一个柔弱,这对姐妹简直要把我气死!还好寒哥儿没娶她做正房,怎么带出去见人!”
管妈妈劝慰道:“驸马肯歇在公主房里,太夫人还有什么不放心?”
“从前我以为她心机深沉,谁知竟是个苦命孩子。”太夫人话锋一转,感叹起凌靖雪的身世来:“这样的孩子有一点好,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只盼她记得徐家的好,真心实意与寒哥儿过日子,我就安心了!”
“今儿的事,难道您就没有一点怀疑?”管妈妈小心翼翼地问。
太夫人深深望了她一眼,叹息道:“女人家的小心思,我活了六十多年还看不清楚?但寒哥儿心有多偏,五娘是个什么成色,你不是不知道。只要不太过分,我权且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由她们斗去。”
管妈妈念了句佛:“有您这样的长辈,当真是她前世修来的福分!”
徐寒病了三日,凌靖雪就在他身边照顾了三日。他醒来的一瞬间,她却无声地转开了眸子,快步走出房间,仍然听到他干哑的声音:“我在哪里?五娘呢?”
砚剑十分为难,吞吞吐吐好半天才将几日来发生的事说个大概。徐寒越听脸色越难看,最后烦躁地挥挥手:“这么说老太太还是知道了?”
失望与无奈明明白白写在他的脸上,砚剑只得含糊以对。徐寒长长叹息,垂头思索了很久,最后吐出一句话:“备车去别院。”
凌靖雪表情复杂地看着他的背影,心头说不出的滋味。墨梅怯生生道:“要不奴婢跟去瞧瞧?”她已经渐渐熟悉了偷听的工作。
“不必,让他去吧。”她抚着面庞,怔怔问出一句:“我真的比不上她么?”
几日不见,别院门庭冷落,只有徐恬的丫鬟茜儿端着一碗汤羹从院子里走过。徐寒想了想,叫住她:“方姨娘近来如何?”
茜儿因为徐恬的缘故不喜欢方五娘,趁机添油加醋地告状:“方姨娘前儿摔了三只碗,五只碟子;昨儿泼了两碗茶。今天大小姐实在看不下去,劝了好一阵子,姨娘好像听进去了,到现在只砸了一个花瓶。”
徐寒气得说不出话,特地在方五娘门前听了许久,动静慢慢停了方推门而入,沉着脸道:“我在家里养病,你就不能消停几日?”
熟悉的声音如惊雷令方五娘直直打了个激灵,根本不注意他说了什么。三步并作两步,又惊又喜扑进他的怀里,满面泪痕泣道:“寒哥,你来了!我……我好想你!”
任凭徐寒再气恼她的不懂事,听得软语温存也不由得缓和了脸色。双手紧紧揽住她的纤腰,思念如潮水奔涌而出,喃喃道:“我也想你得紧,这不来看你了么?这几****虽见不到你,但时时刻刻都梦见你。”
方五娘泣不成声:“我……我……”两人尽诉相思之情,甜甜蜜蜜用过午膳。见他神色稍和,她一扁嘴,摇着他的手臂撒娇:“你要为我做主啊!”
心头咯噔一声,他挑了挑眉,装作若无其事:“什么事?”
“公主仗着身份欺侮我,让我闭门思过!”她边擦着眼泪边控诉,面容哀伤:“她不给你请太医,我气不过才找上门去,她却拿太夫人压我。”
若非他事先问清楚了事实,几乎要被她的话蒙混过去。“是我不想打扰府里,她只不过照我的意思罢了。就算你焦急,也不该莽莽撞撞回去。”自己的苦心安排被她一手毁了,还一副恶人先告状的样子,他大失所望。
方五娘没想到他会向着凌靖雪说话,伤心、愤懑、委屈一齐涌上心头,该说不该说的喷涌而出:“你答应过我永不碰她,为什么睡在她房里?就算你生了病,也该我照顾才是,为什么是她!你以前答应过,今生今世只爱我一个!”
“昭林公主是名正言顺的徐夫人,怎能一辈子不圆房?”他完全想不起何时做过这样的承诺,觉得她简直不可理喻:“无论如何你都不该冲撞她!”
就算再宠爱方五娘,徐寒毕竟是个知书晓理的君子,深明嫡庶之分。抬为贵妾在他看来已经是做了最大程度的让步,没想到她竟贪心不足。失落的空洞在他心中越延越大,看她的眼神也从柔情渐渐变成了陌生。
她犹自不知,呜呜哭着。徐寒大病初愈被她哭得愈发头晕,忍不住喝道:“闭嘴!”
哪怕她再使小性子,徐寒从来都温声细语,舍不得呵斥她一句,而今却……她愣了好一阵子,回过神眼泪汹涌澎湃,仿佛要将他淹没其中:“你……你骂我!你从来不会骂我的!你是不是不喜欢我了?”
病中的人难免神志不清醒,徐寒情急之下冲她嚷了一嗓子,立刻就后悔了。将心比心,若换了她病在榻上,他亦急得六神无主,无怪她乱了方寸。再看她哭得肝肠寸断,他的心仿佛也揪成了一团,压抑得喘不过气。
他张臂想将她拥在怀中柔声安慰,却被她赌气地甩开了。他毫不气馁,好言好语耐心地哄着她。不知说了几大车的好话,她总算抽抽噎噎止住了哭泣,认真地望着他:“那你答应我,不许喜欢公主!”
真是孩子话!他满口应承着将她揽在怀里,刮了刮她的鼻子:“都哭成花猫了。我今晚留下来陪你好不好?往后可不能任性了。”
想起当日的丢脸事,她亦神色懊恼,乖巧地应着,撒娇道:“人家担心你,想偷偷溜进去看看,哪里知道会惊动太夫人!”
他忽然心中一动,眉头拧成一个结,端正了语气问道:“是谁给你传的信?”
方五娘对他向来知无不言,脱口而出:“书剑!”话刚出口顿时后悔,万一他不喜欢身边人通风报信,连累了书剑事小,往后还能倚靠谁?但改口已然来不及,她只好弥补道:“我逼了他半天,总算问出几句话。”
徐寒心思却在另一件事上,听闻是书剑松了口气。方五娘大闹徐府,得益的只有凌靖雪一个。倘若一切皆是她策划,蒙蔽了徐家上上下下,这个女人实在太可怕。但书剑对凌靖雪插足他与方五娘之事颇有看法,必不会听命于她。
方五娘见他不追问,悄悄把话题转开:“我闷在屋里好几天了,你陪我出去转转好不好?”仰头望着他,眼中满是求恳的神色。
几日来她大约寝食难安吧,他笑着拢了拢她的秀发,心中微歉。两人肩并肩走出院子,路过侍立一旁的书剑身边,他有意无意地瞟了几眼,若有所思。
“驸马罚了书剑半年银子,可说了原因?”墨竹急匆匆地追问。
墨梅被她惊了一跳,结结巴巴道:“我……我听他们说的。”
凌靖雪眼神示意墨竹不要慌,摆摆手道:“知道了。”
墨梅福身刚退下,墨竹便迫不及待地解释:“公主和驸马说话的时候书剑一直在门外听,我特意让人都走开,他一点都没有怀疑,怎么会……”
“你们不要乱了阵脚,就算驸马罚了书剑,也不见得怀疑我们。”凌靖雪静心细思,越想越觉得徐寒不可能发现自己的布置:“书剑忠心方姨娘,驸马却不见得喜欢他一仆侍二主,或是因为这个缘故罚了他也未可知。”
依徐寒冷漠沉稳的性子,必定不喜欢身边人多嘴多舌,她渐渐有了把握,吩咐荷澜开了箱笼:“你就说看在他侍候驸马多年的份上,私下给点银子。记得要大张旗鼓,还要嘱咐书剑不可告诉驸马。”
书剑向来花钱大手大脚,猛然没了进项,正在发愁后半年的生活。荷澜忽然雪中送炭,他感激涕零,忙不迭收了,连声道谢。这种事本来就容易成为谈资,墨竹只稍稍放了个风,满院皆称赞凌靖雪会做人,是个体恤下人的好主子。
墨竹喜滋滋地给凌靖雪转述下人的话,抿唇笑道:“这些都是二少爷院里的老人儿,只要大家众口一词,日子长了二少爷自然知道公主的好。”
凌靖雪笑笑:“难为你四处奔走,这几日好生歇歇罢。”
意外地抬了抬眼,墨竹欲言又止。凌靖雪敏锐地感觉到了,拍拍她的背:“既然跟了我,咱们便是一条船上的人,有什么话莫要藏在心里。”
“奴婢只是觉得,公主对咱们特别好……”这话大有巴结之嫌,墨竹臊得满脸通红,着急着摆手:“奴婢只是随便琢磨。”
往事历历在目,凌靖雪叹了口气,感慨颇深:“当年若没有荷澜她们一力护着,我早不知道在哪里了。”
墨竹恍然大悟,深觉自己多嘴,不知找什么话掩盖过去。恰好荷澜在这个时候进来,奇怪地看了她一眼,垂手而立。
墨竹知道他们主仆俩有话说,忙不迭退了下去。荷澜确认四下无人,方附耳道:“苏公公派人送信儿,皇上问公主的事办得怎样了。”
一听皇上两字,凌靖雪霎时面寒如霜,冷冷道:“你告诉他,这些天我忙着绣他赐的绸缎,没空调查免死金牌藏在哪里。”
凌风龙脾气暴躁,她这样明嘲暗讽,难保不会恼羞成怒。荷澜怕她吃亏,好言劝道:“公主久久没有进展,想必皇上着了急。奴婢说几句好话,先拖着也就是了。”
“难道你还看不出来?徐家对我百般不信任只因为他。”忆起徐寒的冷漠态度,她心头大恨:“自己想做出尔反尔的丢脸事,何必扯到我身上来!他不是素来当做没有我这个女儿么?现在怎么巴巴派人来问我?”
见她动了气,荷澜不敢再劝,立在一旁面有难色。过了好一阵,她略略顺过气,缓缓道:“想拿到免死金牌救子渊,非得得到徐庭仪信任不可。他若不配合我演这场戏,我一个人终究难能。”
荷澜松了口气,展颜笑道:“奴婢就怕皇上心急之下错怪了公主。如今只要向苏公公说明,皇上必能理解您的一片苦心。”
谁知她摇了摇手:“你不需告诉他,只照我的话说。”
荷澜怔了怔,但她态度坚决,唯有迟迟疑疑地去了。
凌风龙乍听之下果然气急败坏,眉宇间现出一抹厉色,冷冷道:“好好,自以为翅膀长硬了,还是以为徐庭仪能护得住她?看来朕不给几分厉害瞧瞧,连自己的女儿都敢造反!”袍袖一挥,他怒喝道:“拟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