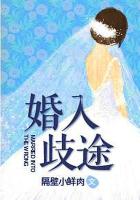下雨了。
躺在床上打吊针的明德,一个被岁月和疾病折磨得奄奄一息的打鱼佬,干瘪的鼻孔动了动,苏醒的嗅觉一把抓住这让人兴奋的气息,湿润清新渗满鱼腥味的春雨的气息,似一群鲜活的游鱼四处窜动。他从昏睡中睁开眼,床对面的窗口正划过一道道明亮的雨柱。这场期待已久的春雨,穿越了漫长的冬季,每一根雨都饱满粗壮,强劲有力,一把把飞驰的渔叉样射向大地。
想到渔叉,想到鱼,这个已卧床多日的病老头儿,感到麻木的四肢又能动了,他抬了抬腿,伸了伸手,双手一撑直起身子,把一张苍老病态的脸努力贴近窗口,手臂上的针头牵动了连着的吊针瓶,吊在楼板上的半瓶药水一阵摇晃。就是在家里打吊针,他也坚决不上医院,上了医院,就说不定等不到这场雨了。他的头尽力探向窗口,鼻孔翕动,用力吸着这鱼腥味儿的沁人肺腑的湿润气息,一阵急速地打在窗台的雨溅到了他的脸上。他张开嘴,承接着这迟到的甘霖,病态的脸如旱苗浇上了清水,鲜活,满足而陶醉。透过陈旧的木窗棂,他看见雨在地上打起了水泡,像浮着一地的鸡蛋鸭蛋,渐渐汇聚成一条长长的队伍,顺着地势的低凹处,朝院坎外流去。
他知道,这一路路浮着水泡的雨水,从山坡,从田野,从人家的院场,汇成的千万条奔跑的水流,越过河坎,哗哗地流进河流;这些从天而降的春雨们,一定会一根不少地注进行将断流的沮河。
想到河,想到即将涨溢的一河春水,这个长时间连稀粥也不想喝一口的老人突然感到肌肠咕噜了;他想吃饭;他又活过来了。只要有水,这副干瘪的老骨架也会变得生机勃勃。于是他张开了口。没有想到,声音也像是几天没吃饭了,软绵绵,像女人的裹脚布。一会儿,一个驼了背,拄着棍的老女人出现在房屋门口,同样苍老的脸努力往上抬,有些吃惊地望着已从床上坐起来的老伴儿。这个快死的老头子是又活了。
这张春雨足足下了三天,下得地上沟潦纵横,流水潺湲,下得这个病魔折磨得枯萎灰暗的打鱼佬的脸上一片灿烂。已蛰伏了的想法,已沉睡了的感觉,经这春雨一浇,像田野里苏醒过来的种子,像栅栏旁,墙根下的一些花花草草,争相撑破了泥土,扭动着勃然的芽,从泥土下钻出来了。打鱼,这伴随了他一生的劳动,曾经赖以糊口的生计,人生的艰辛和磨砺的化身,现在却成了他生命的乐趣和最后的期待了;想到打鱼,想到流淌的清冽的河流,想到在清明的河水中畅游的鱼儿,一身的老骨头已在快活地啪啪作响了。
这三天里,他吃饱喝足,还故意拄着棍子在家人的面前噔噔噔地走去走来,这是要让他们相信,自己的病完全好了,他又可以下河了。
雨停了,远处的山上,缭绕的白色雨云还没有完全收上天去,这个迫不及待的老头儿就拔了还剩半瓶药水的吊针针头,拄了一根棍子,匆匆忙忙赶扑河边。
果然,几天的春雨,干涸的河水又活过来了。完全跟自己想像的一模一样:一波一波的一河春水向前涌去,已断流的河水又接上了;河面宽了,一涌一涌的亮闪闪的波浪,直铺到岸边来了。这个望水的打鱼佬,深嵌皱纹的脸上的笑意,清水淌过石滩似的明快生动。
河流恢复了往昔的模样:卵石累累的赤裸河床全被水盖住了,水们正轰轰隆隆漫过河床,河滩一片亮光闪烁,哗啦悠扬。
天空,山脉,新发的树叶,刚生出的新草,草地里零星开放的花朵,一地金黄的油菜花,一畦葱绿的麦苗田,天地间被雨水冲洗得干干净净,鲜明艳丽,一条明净的河水就在这颜色分明的世界里流淌。这才像河,这才是记忆中的河流应有的颜容。望水的打鱼佬恍然回到了过去的岁月。他满意地仰望着天。太阳出来了,只有这一团黄亮的日头依旧年轻光鲜,又把一块块阳光撒进了河水,河面跳动着一滩阳光,似有无数的桃花鱼正急着上滩。老人的嘴角翘动,唇边的几根白须,笑得像一只弹动的河虾。
整整等了一个老冬了,以为是看不到涨水了,想到在河里滚爬了一辈子,最后是看着那一泡尿似的河水死去,心里就不甘心,就忍了脾气,伸出手去,让那挎着一个卫生箱一走一瘸的家伙,去扎一个又一个针眼。在那些卧床的日子里,在意识不很清醒的时候,一阵器械响后,那个村保健室的姓张的瘸腿医生就在抱怨说,血管老缩了,把我的针头打弯了几根了。个杂种的,老子的手上不知别弯了多少渔叉,还说你这小小的针头么!
望着哗哗闪光的河水,明德觉得所受的委屈和忍耐都值了。雨水一定是一根不少地全落进河了,才有这满河漂的水溢岸流淌。看样子河水还在上涨,因为近岸的地方时时漂来一些枯草,河水的中间还翻滚着一丛枯枝,一个树蔸。明德望着河中翻滚而过的树蔸,脸上有些凄然。是的,是看不了几回了,它在拼命涨给我看呢。
春天涨溢的河水是清亮的,不像夏天山洪暴发时一河的黄汤,流的全是泥沙。只有春雨能让这条河回到往日的样子,它年轻时的模样;春天下再大的雨河水也是澄明透亮的,如同人生的许多往事,不管经历了多长日月,回想起来也如这河水里的卵石清晰历历。
不知什么时候自己就离不开了这条河。开始是那些在河里游窜的鱼,是生活所迫。后来不须以打鱼来养活一家老小了,可是一有时间还是往河里扎,在农忙时正午休息的间歇,在日头下沉霞光漫天的傍晚。几天不下河,浑身就不自在,就有无数的蚂蚁在身上爬,人就会掉了魂儿:不到河水里泡一泡,人就像一匹干卷的叶,就像一棵枯萎的树。自己已成了这条河的一部分,或者这一条长长的河流就是已身,就在自己的身上流淌。总之,这一生都离不开这条河了。
打鱼佬明德用手里的棍子把吊在河堤的一些枯草往岸上拢了拢。再有一场雨,这些烂枝烂草就要冲进河去了。这是一条干净的河,不能弄脏了它。只要望一望这河清水,身心就同清洗过的凉爽轻快。明德贪婪地望着从眼前淌过去的河水。他咂了咂嘴,似乎在品尝河流的甘甜。一河春水荡到了河边,明德站立的坎下,开在河边的一树桃花,伸进河水的一枝花蕾被冲得一起一伏。
这才是河呀,满满荡荡,横冲直撞。这满河的春汛就像在自己血管中流淌,明德感到了往日的亢奋,衰老的气力重新回到了身上,在手背和腿脚隆起的青筋中蹿得啪啪作响。他随手一扬,拄了一冬的棍子飞了出去。
他要下河了。
从楼上板仓里提出了网。板仓装了半仓的谷,网就放在谷上面的蛇皮袋子里。网和粮食同样重要,同样要保存好。秋天是收藏粮食的季节,不用了的网呢,就用一根晾衣服的长竹杆撑开,靠在墙角的瓦檐上,撑开的湿淋淋的网像一柄长曲尺。网晾干,补好,就同谷一起放进仓里了。
吱呀呀地移开沉重的仓盖,提出蛇皮袋子,拍拍蛇皮袋子,沾着的谷一阵簌簌掉落声。解开系在蛇皮袋子颈口的布带子,黄铜色的撒网就从蛇皮袋子里盎然开放。
刚开始打鱼时,河就跟现在涨了一河春水样,一年四季清绿绿地满河漂。河面来往的,全是竖着桅杆带着黑棚子的望不到尾的船队,上下蹿着的小渔船。桅杆船是带着木材山货进宜昌入汉口或者贩来城里洋布洋货的商船。小渔船上就是站着像年轻的明德样光着上身,手里提起的篙杆带了一串白哗哗水花的打鱼人。码头总是泊了一条接一条的大商船,那时的明德就划着一条新打的散着桐油味儿的小渔船,上面横着渔叉,起片,堆着一堆提起来都是一人多高的拦网,穿行在这些商船中。要趁商船停泊的时机兜售一船的鱼。一阵吆喝过后,那边的商船舷上出现一个人头,俯下来交谈几句,这边的小渔船哐啷一声开了船头的渔仓,一阵撞得仓板咚咚响,明德就掏出几尾在手上绕去绕来的鱼,往那站在大船船头的人掷过去。
那是一段年轻而让人快活的日子。没有料到的是,河竟然也和人一样,也要老。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这话活到了现在才有体会。就这么几十年,一块宽宽大大的河缩了,窄了。天还是这个天,地还是这个地,那漫河漂的河水却不知流到什么地方去了。满眼的,不再是溢岸而去的河水,全是一河铺向前去的寂寞的卵石。只剩中间一条窄窄的水带,随便丢几个石凳,几步就能跨过去,像过一条沟。到了冬天,一条河简直就成小孩的一泡尿了。河水断流了。岸边的泥沙淤起来,带黑棚的商船早已消失,泊船的码头成了人们倒垃圾的场所;曾经一篙杆撑不到底的深潭,也成了一个长满枯草的石坑了。
和消失的商船一样,渔船,渔叉,拳头大网眼的拦网,都悄无声息地退出了打鱼的生涯。自从河里行不了船,就用起了撒网。虽然不能像以前样,上岸时,树枝扭成的串子,提了沉沉几串全是一尺多长令人羡慕的大鱼,但是一个个滩头打下来,总会有半渔篓跳去跳来的一拃多长的红翅膀,翘白,麦穗子的小渔,拿到街上也能换些油盐钱——那时河水还没有完全断流,这些以前看也懒看的,沾上了网就要抖进河里去的小鱼,在那一段时间却成了这沮河的主产品。
后来,却是连这些小鱼小虾也难见了。
水浅了,鱼小了,打鱼的网,网眼也越来越小。手上的这部撒网,还是多年前做的,那时生产队还没有解散,河面虽行不了船,但河水仍在一年四季流淌。全是抽吃饭前的一点儿时间,抓起吊在墙上的针,丝线,在中午嘶哑的蝉声里,打上几裙网。这部撒网做起后,下水的机会却是一年比一年少了,裸露的河床越来越宽,水渐渐断流,没有地方撒网了。很多打鱼佬,有的是死去了,活着的也早改行了。走遍一条河,很难碰到一个挎着渔网背着渔篓的人。河里的鱼几乎绝迹了,打鱼成了一个正在消失的古老的行当。想到这里,明德心里总有些黯然。
在这个村子里,明德是第一个关心天气的人。他为长久的晴空万里而叹息,为瞬间的乌云密布而欢呼。乌云代表着倾盆大雨,代表枯竭的河流又浪涛奔腾。他盼着下雨,盼着涨水,像孩子们盼望快乐的节日。只要一涨水,他就要下河。在这条已没有了什么鱼的河流里,人们时常在雨过天晴之后,看见一个打鱼佬的身影。
明德开了板仓,提出蛇皮袋子,手一抖,铜黄的撒网就从蛇皮袋中脱颖而出,叮当的网坠一片欢呼雀跃。蛇皮袋子蜕到了地上,露出的粗壮的网绳铜丝一样摩擦得吱吱作响,它是脱离了桎梏,在舒展筋骨,它是在做绽放前的摩拳擦掌。吊在网下的铜坠子黄光闪动,一片铿锵。这一部网被无数的枝桩,石头拉破,上面也补了一块块大小不一,颜色深浅各异的补丁,可是在明德的眼里仍是那样活泼年轻,眼中仍是久别重逢的喜悦。老伙计,只有你还不见老,还像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他仿佛看见了自己年轻时划着船桨,在河上倒腾时清寒却一身朝气的样儿,攥着似乎要脱手而去的撒网,明德微笑着的嘴角的胡须,那两只老虾又在弹动了。
那时还没有什么尼龙线,攒了鱼钱,称了二斤半麻线。先是用苦柿水泡了一个秋天,又用稠亮的桐油泡了一个冬天,麻线就变成了坚韧的铜丝了。跟人一样,苦头吃的多,就经踹,经熬,自从河里行不了船,又用了整整三十年了,现在还闪着结实的亮光,攥在手里还能感受到甸甸的分量。自己也在河里泡了一辈子了,就是木头也泡成钢筋铁骨了。村里活到自己这个数岁的,已经没有了。这全是河水浸泡的结果,也是河的功劳啊。明德挽着有些倨骜不驯的网。
被河水泡过的,还有这些铜坠子。明德挽到网脚,摸着吊在网脚下的一个个的摆动的铜坠子,冰亮,坚硬,锋利般的滑爽。别人做网坠子用锡,他却要用铜。铜的虽沉,用起来却顺手,不像锡的,提起来轻飘飘的;又抢水,只要撒出去,那鱼就跑不脱。他喜欢结实厚重的东西,日子才过得稳重。在于旁人,这部网就显得老式笨重。早些年,也喜欢下河整水的大女婿,想在丈人面前露一手,拉开架式撒了几网,脸上就显出了不胜其力的赧颜。像时代久远的剑或者弓,旁人是用不了它的,它只听命它的主人,只有属于那个时代的人,才配使用它。
老人想起这些往事,感到了自豪。可是当他把网从楼上板仓里提出来,顺着楼梯提下楼时,突然感到这部曾经使起来易如反掌的铜坠的撒网,有些沉手了。还是老了。在这个世界上,人就是比东西老得快;河流不是东西,它是人。因此,它才会比人老得更快。
年青时就没有这种感觉。像用不完的青春日子一样,哗哗流淌的河水仿佛永远也淌不完,浅水的,深水里的鱼也永远打不尽。打开船舱,提着大串大串卷去摆来的鱼,绾着两只裤腿一脚跳上岸,赤脚在干燥的地上踩出湿漉漉的脚印时,两旁那些羡慕苍老的目光就像只是别人的事,从没有想到自己的好时光会像那波光闪动的河水一样悄然断流,衰老也会降临自己的身上。
只有拨着指头可数的几次春汛,河流才恍然回到青春的时光。河面铺展,河水潺湲。天地间的一条河流,流得明明净净;河有多宽,投在河水里的倒影就伸了多长,河水就像在岸边的树木房子,在白云,在天上人间融为一体的澄明的世界里穿行,流淌,满眼的明亮洁净,让人感到活着的幸福安祥。
见了这一河明净的水,这人就不由得想跳进去。清凉的河水在两腿间激荡,柔顺又坚硬的河水就会从腿杆,从脚掌流进人的身心,人就成了河流流动的一部分。
何况那河水里,还藏了许多灵动的鱼。人与鱼的追逐就像一场游戏,这游戏让单调短暂的人生多了许多的乐趣。
明德整理着网,似乎找到了自己为什么痴迷打鱼的原因。他把网扣带在手腕上,扯着网绳,黄色的网线从枯槁的手掌中滑过,又盘成了了一圈,他就像握着一条跃跃欲试的蟒龙。
你这才好一点儿!
听见声音,明德抬起头。责备的是老伴儿。驼了背的女人拄着棍子,伸着头望老头子抖弄着不会再产生任何效益的网,不满让一脸的皱纹更弯更深了。
打鱼回来,女人就要忙着揭开冒着几丝热气的锅盖,饭菜端上桌,接着就要拿着一杆秤砣碰得秤盘当当响的还是十六两的旧式杆秤,提了一篓子白花花的鱼,颤巍着一双小脚,牵着孩子去午后空旷的街上满街叫卖。
女人的叫卖声还在苍白寂静的街道上回响呢,河水就消失了,女人也老了。明德在满怀的感慨里把曾经让女人卖过无数回鱼的网紧挽在手上。渔篓就挂在大门背后的墙上,走过去取下来,吹去上面的灰,往身上一背,不管身后老伴儿的唠叨,像多年前下河样,赤着脚,卷着裤腿出门了。
刚出门,门口的鸡一阵惊叫,低斜着身子跑远去。明德扭过脸,一阵痛心的抽搐。门口阶沿上的,船上盖的高粱杆被趴掉了一地。杂种的,一条船成了鸡窝了!
每到冬天,船就会起岸,放两条板凳,翻扣着。一阵当当叮叮,船重新维修一遍,换了腐烂的船帮,加了几抓铁钉,刮上了新鲜的泥子,里里外外刷了几道桐油,在太阳下晒得黄亮亮的,满院是桐油和木头的香味儿;这船只等春天一到,又下河去。
不知是在哪一年,河水跌落,露出了搁浅的河床。从此,起岸的船再没有下河。
那些年头,怎么也不相信这河水会突然消失,河水重新从河床上漫过的希望波浪一样时时在心头涌动。在等待的哪几年,每到冬天,都不惜花上一大笔钱,买来一大桶桐油,照例请来木匠,将风吹日晒奓裂干翘的船又维修一遍。可是春天到来的河面仍在一年比一年窄。一河苍白无奈的卵石一年比一年宽。等待了多年准备下河的船,最终像一条被希望风干的鱼,侧扣在屋檐下了。这一扣就是几十年。几个堰塘养鱼的,来看了好几回了,家人都同意卖掉,可是明德脖子一昂,粗着几条青筋说,除非老子死了。他留着这条船,就像留着河流碧波荡漾的希望,曾经有过的乘风破浪的年轻岁月。
船侧扣在屋檐下,免不了日晒风吹,雨雪侵凌。就用高粱杆盖着。可是夜来的风,可恶的鸡,把盖在上面的高粱杆掀下来。病了一段时间,无人照管,这鸡竟大着胆子在上面做窝了。出门来的明德有些恼火,就提着网,弯下腰去,一手把掉下来的一截高粱杆捡起来,狠狠朝还在逡巡的鸡抛去。
多年没有下河,船板早干枯了,也裂了缝。如同枯萎的手,干缩的腿。小心捂盖被子似的,明德又拿来一捆吱吱作响的高粱杆,给自己的老伙计盖好。
此生再无缘下水的,还有拦网,还有起片,还有渔叉,还有篙杆和船桨,全是伴随了他少年青年壮年打鱼生涯的忠诚勤劳的老伙计。
深潭不怕,一人多高的拦网下下去,撑着船来回地拍打着水面,水花下面的鱼惊惶得乱蹿,一蹿就撞上网了;鱼落了窝扎了洞也不怕,站在船头,一丈多长的起片就像自己伸出的细长的手,钻进岩缝,掏几掏,一拨出水面,就会带出一条比筷子还长的大滑鱼。
老人抬头望去,剩下的最后一部拦网,挂在菜园里,做了拦鸡的栅栏了。没有鸡来,它就拦着进出菜园的风,和园边杏树上飘落下的杏花,还像往日漂在潭水中似的,在空气中晃晃荡荡;而那一条一丈八尺长的起片,也还放在了屋檐下的檩木上,从墙的这一头伸到了另一头,如同一条爬过屋檐的蟒蛇。——知道我要下河了么,看你高兴得!老人仰望着放在檐上的篾起片,听见它在春风中兴奋地发出金属般的颤哨声。
杂种的,不言不语的,原来都在看着呀。好,今天让我好好地撒几网你们看。老人突然觉得自己有了劲了,迈出去的脚步甚至感觉到消失了多年的弹性。
河流像一根青藤,从很远的地方伸来,又扭动远去。它结出的果子和长着的树叶,就是两岸的房子,田地和生活在里面的人们。
河流长出的果子和叶子越来越多了,可是这一条青藤却要枯萎了。这让挎着撒网走在街上的明德有些伤心。他望着热闹却混乱的街道,络绎的商贩,琳琅的摊点,繁闹中给人乱糟糟的感觉。房子多了,气派了也俗气了,人多了,阔气了也退化了。他熟悉这条街在前清和民国的样子,知道每一扇铺面每一幢房子的历史。如今,所谓的兴旺只不过是过去的事情改头换面的重现。流转的世事使很多逝去的事情再次重现,可是,这个小镇曾经繁华的水运,竖着高高的桅杆,盖着乌棚的帆船,朝雾渔船游弋,晚霞撒网打鱼的情景,让人无限怀念的生活却是像水一样流走了就不再回来了!
老人挎着一部叮当做响的撒网走过街头,招来不少的目光。
哟,您老还能打鱼啊?好啦?——那是熟人。
这河里还有鱼?——那是有些无知的年轻人。唉,正是因为他们无知,才做贱这条河啊。明德为河流抱不平。
一群小孩,见了这妆扮得有些奇特的老人,从大人的嘴里知道了他将从事的事情,就围过来蹦蹦跳跳:哦哦,看打鱼哟——看打鱼哟——激动的神情不亚于街上出现了一个耍把戏的。
被小孩子们簇拥着,老人来到街道口,踏着昔日码头的石阶下河。堆积如山的垃圾蔓延到石阶上来了,宽广的石阶被逼得难于下脚。过去这是一条干干净净的石阶,青石砌坎,条石护栏,石坎儿被上下河的脚磨成了一条槽,乌黑光亮。现在却满是污垢。他把脚插进一块石坎,四周一望,全是花花绿绿的垃圾;不远处还有一条下水道,冲出一股黑水,绕过一片树林,流进了河,风送来刺鼻的嗅味儿。这个码头,一张雨后,现在更是污浊丑陋。明德突然有些气愤,一抬脚,踢飞了一个易拉罐,当当滚下坎去。
没有料到,身后的孩子也学着踢一些瓶子,一些垃圾。这让老人有些发愣。他下了河坎,弯下腰去,把滚到河边的易拉罐捡起来,一扬手,脏瘪的易拉罐又回到了垃圾堆上。孩子们觉得好玩,于是无数的易拉罐,瓶子,一些硬质的脏东西飞上了码头。
几十年前,这么大的孩子正是玩水的年龄。一个个脱得精光,站在码头上,眼前白光一闪,又一个孩子纵身跳进水去,码头冲起了一柱浪花。可是现在,深不见底的码头已成了一个旱包,一个人们堆放垃圾的场所,一些条石也被谁撬去做了自家的墙脚了。听见几声磕得铣铁撮子响,明德昂起头,又有人在上面倒垃圾,一些脏东西正从垃圾堆上滚下来。
明德的心中是无奈和遗憾。他们是没有见过这条河年轻时的样子啊。他望着那一条白亮的水,继续挎着网往前走。他知道,只要脚一踩进河水,所有的不快就会被清亮的河水冲走。
河水闪着亮光,一晃一晃,叮叮当当漫过石滩。明德的脚一落进水,那些漫过石滩的水们便一涌而来,围着这两条久违的腿打转。明德突然感到眼中有些发涩。这条河,这些水,还没有忘记我这个打鱼佬。伙计们,我还以为见不到你们了。明德提起脚在河水里摆了摆,像是要洗去那些垃圾的污垢,又像在抚摩一群围过来的撒欢的猫狗。水们拥着他摆动的脚,荡起水花。
这双脚熟悉这条河的每一寸地方。即使闭着眼,脚一踩,也能知道到了什么河段。在那些没有星光没有月光,听着河水的流动声,一人挎着一部网,一夜打遍沮河上下的日子里,靠的就是这一双脚。这是伸在水底的两盏探灯,再走多远就是滩,水有多深,哪里有几个石头,石缝可以伸进多长的起片,里头藏什么样的鱼,河底的事务他都一清二楚。
明德的两条腿站在水中,就像两根吸管,将河水的甘露,河流的生气立刻嗞嗞地导遍了他的全身。即将枯萎的朽木,悠然青葱,碍事的手脚,一下灵活了。他的脸上水流过一样,又漫着一层清朗的喜悦。回过头来,望着跟在身后的一群小蛆,见他们个个双手提着鞋子,小鸭子似地伸张着手,踩跷似的身子一走一软。他笑了。河下得少,这些石子就得硌你!时间长了,脚下的石子就软了,就变成一群听话的鱼了,大大小小的,鱼嘴一样啃着脚掌,啃得人心发痒,熨帖舒坦。
没有时间去看那群小蛆,明德拉开架式,要撒网了。拎着网绳在河水抖几抖,扭去扭来的网就在水中发出一阵舒畅的声响。
桃花一开,各色的鱼就会上滩。有白条子,有红翅膀,有马口,有棒槌,还有大的如猪崽的草鱼。小鱼上滩时,河水如同开锅似的,一片水花,如果是一大阵红翅膀,就像倒了一河五颜六色的染料,又像是水底冒出了无数朵桃花杏花;如果是大鱼上滩,就有一行行水柱逆流冲撞。男女老幼,扑腾着一河人。着急的女人们,也会拿着洗衣棒追赶着上滩的大鱼。孩子们也跑去跑来,提箩筐篓子。箩筐篓子也装不下,就脱下衣服,裤腿,袖筒全扎起来,也装满了鼓鼓囊囊的鱼。平日里鱼也多啊。一到日头下山,霞光从山顶上投下来,河面上群鱼跃动,像密集的雨点打出无数的金色的圆圈儿。
明德咂了一下嘴,不知是不是对往事的回味。他拐起左肘,分开了渔网。仍是往年打鱼的把式,用一种古老的一陈不变的姿态,重复着人类的劳动,可是每一次简单的重复都会有不同的收获。现在,明德弯下腰去,悄然向前几步,脚从河水里轻手轻脚地提起来,又悄无声息地插进水去。那是怕惊跑了在水里游动的鱼。突然身一直,手里的网张开大口扑了出去。铜质的网坠,在太阳下闪着亮光,像是一簇呼哨的箭头,嗖嗖嗖射下水去。
身后的孩子们一阵小跑,踩得水花四溅。
鱼!鱼!鱼!
明德扯着网绳收网。网眼闪着无数的亮光,似无数的鱼在跳动。然而只有明德知道,那只是太阳的反光,不是鱼。有无鱼不是用眼看的,是在手上的感觉。紧捏在手里的网绳突然带了电似的颤动不止,那就是有戏了。然而手里的网绳十分安静,只传来水流颤悠的律动。
孩子们很失望。又望着他撒。收拢网来,卡着网蔸如同拿着一朵成开的花,抖几抖,铜坠翻动。鱼!一个孩子惊呼着。可是翻过来,只是一个白色的卵石。
卟嗵一声,网蔸里的卵石连同孩子们的失望掉进水去。明德又饶有兴趣地撒网,可是如是几次,让孩子们终于明白,这个老头跟他们一样,不是在打什么鱼,而是跟他们一样,在玩一种游戏;不解的是,这个游戏如此单调又费力,可是这个老头儿却玩得那样投入,玩得那样高兴。孩子们望着老头儿独自快乐的脸,感到了无聊;他们要去捡石子儿玩了。
如果是以前,孩子们跟得如此近,明德就会喝斥。鱼很灵敏,听见一点儿响动,一群鱼就四散了。现在,不用他喝斥,他甚至想让孩子们留下来分享他“打鱼”的快乐,可是孩子们却主动离去了。正在享受快乐的明德突然感到了孤独。
前头深水里有鱼。
你骗人。
孩子们骨碌着一双双眼睛,望望他手里的网,又望望前面的深水。前面的水深,水面是澄绿的。
他没有骗他们。去年下河,总共打的一只虾子,三只螃蟹,还有两条小鱼——比火柴盒还长的一个硬棒槌,比分子钱大的一个屎黄皮,就是在对岸深绿色的水里打的;那两条小鱼送给了用罐头瓶盛水玩的孩子。
一片柳树下的绿色水面,曾是一个深潭,两部一人多高的拦网结在一起,才能沉底。那一年下了三条船,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那一条一百多斤的鱼弄上船,压得船一晃一晃的,船舷都漫进水了。后来水跌了,几个石头还能扎沤。砍一些柳树枝,扛两捆稻草往石头周围一丢,到过年时,还能起一澡盆的鱼。现在,那几个大石头也被淤死了,只露一个脑壳了。
河底的卵石闪动着一片条条白光。多希望那不是太阳光线的折射,是游动在河底的鱼啊。明德鼓起劲儿,在孩子们的面前撒了一网又一网,可是每一网都只有跳跃的阳光,几个湿漉漉的鹅卵石。最终是他的努力没有挽留住孩子们,他们转身走了,去捡那些毫无用处的石子了;手里的网也显出无精打采了,再撒出去就瘪了,就没有劲了。
可是明德像是在和谁拗劲儿,仍是一网一网努力地撒。他撒了一生的网,现在是撒一网少一网了。他知道,他的生命已经不多了,这给他带来欢乐和痛苦的人生的行当即将离他而去了。于是张肘,分网,弯腰,起步,出网,收网——每一个动作都做得一丝不苟,出网前蹑手蹑脚,出网时猛如脱兔,仿佛河水中真有一群鱼在游动。可是每一网收拢来,网眼里都只有跳跃的太阳的碎光,几个卡在网兜的卵石。
那些网眼上的碎光一次比一次跳得晃眼。这不是日光,是一网活蹦乱跳的鱼,是让人眼花缭乱的鱼,只不过是自己不去捉它罢了。明德这样想着,心里就对孩子们说,是鱼,都是鱼啊,孩子们,你们为什么不来看啊。几个孩子在远处的浅水里,正兴致勃勃地低头寻石子儿搬螃蟹,全然无心思注意这已走向了深水里的老头儿,只有背后的渔篓听见了老伙计心里说的话,当撒网再次抛出去的时候,这个已经陈旧的渔篓兴奋地挤到前面来。
天空很蓝。一只白鹭在上空盘旋。身子一斜,飞得比两岸的山岗还低,接着落在河滩上,一只长腿钉在水中,另一只弯曲着。明德知道,那是准备见了鱼,要随时伸出去捕抓。杂种的,也想到涨了水,要来捕鱼么。
仿佛是为了与捕鱼的鹭鸶比个高低,明德提了网朝滩上面更深的水走去。脚从水里提起来,都提起一串白哗哗的水花,像两根从水里提起来的篙杆。明德在水里走着,就像踩着两行水花移动。
可是除了网几个石头,连虾也没有网到一只。网越撒越瘪,落下水去的越来越瘪的网圈,一次比一次离自己近。唉,是老了。网提在手里越来越沉,手,腿,都有些发颤了。突然胸口刀刺似的十分难受——病又犯了。河水,天空,似在旋转。在水中站了好一会儿,屏了好几次气,明德才让不住颤抖的身子稳住了,又接着撒网。但是那撒出去的网,竟带得自己在水中踉跄了几步。真是臊人啊。明德喘着气,有些羞愧地偷偷望过去。还好,孩子们并没有这撒得像一根绳子的网,只有站在水滩的白鹭,朝这边了望。要是河里没有鱼了,连一只虾也打不到了,这条河,就要彻底被人遗忘了。
那怎么行啊。明德感到胸口又一阵疼痛,像码头上滚下一路肮的垃圾让人难受。来吧,哪怕是一只螃蟹,是一只小虾。明德颤动着手臂,再次把网张开。不能让伙计们失望啊,那躺靠在檐下的船,探着头发出颤音的檐檩上的起片,落拓成了护园的栅栏,仍然不忘如同在水中漂动着的拦网——
不会有太多的机会了。靠近岸的白色卵石滩,已湿湿地黑着一条边了。春汛在跌了。要不了一两天,河水又会缩得像一条绳子;要不了几年,这青藤一样结出了村庄,房子和人的河流,就要干枯了。
伤感的明德越走越深。河水漫过了他的膝盖,他的大腿。那些在水底闪动的,不是卵石,不是阳光的影子,是鱼,是藏在深水的一河的鱼啊。看,那晃动的幽暗的脊背,时时闪来的一片片白白的肚皮。撒啊!腰后的渔篓憋不住了,为了帮老伙计使劲儿,飞到前面来了。
明德在沉向水底的一瞬间,望见了无数的鱼,摆动着明亮的身影朝他涌来。
远远地听见扑通一声,几个在浅石滩玩耍的孩子抬起头来,看见的只有静得有些寂寞的流潺着的河面,河面上一只孤独的盘旋着的雪白的鹭鸶。
就在这一个春天,在一张春雨之后,许多干涸的河流又淌起了河水,流得全是明亮亮的,映着岸边新发的草,新开的花,枯树上新抽的绿叶,过几天就又会消失的春水。在一条名叫沮河的河水中,春水流过卵石的浅滩,速度就快了,一河的春水被凸起的卵石撕碎,像流了一河叮当作响的阳光。
鱼!鱼!鱼!不知谁喊了一声,低头玩耍的孩子们抬起头来。
一片耀眼的光亮碎片里,似有一尾硕大的鱼,正一冲一冲地蹿游着。捉鱼啊!孩子们撒腿欢跑,踩起了一河喧嚣的水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