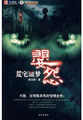又是一个大晴天。
田保站在稻场,仰望着东方的天空。露出脸儿来的日头,就像一枚刚打的蛋黄。入了秋,这日头也和那地上的草一样,沾上了一层露水,有些稠,有些潮,把田野、稻草、房子、院场全打湿了,就像涂上了一层湿漉漉的蛋清。
田保拿起了竖在墙檐下的扫帚。稻场上很干净,但是田保还想扫一遍;不扫,就像对不住谁似的。扫帚一下挨一下地扫着,不像在扫,像在刷。不一会儿,一块晒地刷出了一条条清晰的扫痕,整洁、干净而又清新。夜风吹来了几片露水打湿的树叶,野猫踩落的两块瓦砾,全被扫到了稻场边上。清扫出来的晒床,就像水清洗过一样。
他是要晒最后的一床稻谷。
再过两天,田保就要走了,就要离开这个家,离开这块院场,出门打工了。栏里的一只羊,老妈去世时办了丧事;笼里的几只鸡,卖给了鸡贩子;门口的两块田,租给了别人种。剩下的事儿,就是处理堆放在堂屋的几袋谷了。
那是今年收的最后一批粮食。如果是以往,就要晒了装进板仓。那平着仓沿的一仓谷,是到明年收割前,一家人,还有那羊啊鸡的口粮。可是现在,妈去世了,孩子上了大学,自己出门打工,一去就是一年,这些粮食,这些金灿灿的东西,总不能喂了老鼠啊。
以往,要待在家照顾老妈,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别人去打工,去挣钱,心头急得猫爪儿抓的一样。现在,老妈不在了,可以放心大胆地出门了。可是一想到真的要离开这个家,这片田园,这幢土房,想到自己一走,这幢房子就要永久地锁着了,就要和许多出门打工的人家一样,门口都要长草了,又觉得难受,心里头还是一只猫爪儿抓着。可是一想到儿子上学借的一大笔学费,他的心就硬了,就不能管什么猫爪儿狗爪儿了。
扫完了地的田保,坐在了门坎儿上抽烟。地上还有些潮,要等日头跨过了屋后的山冈,将地晒干了,晒热了,才能铺上谷。
越过山冈的朝阳,照在门前的那一片田地里,那些刚刚收割,露着稻草茬儿,堆着稻草垛儿的水田上。田保知道,他一出门,做的活儿就和种田无关了。他已熟悉了耕田,拉耙、栽秧、割谷,还有晒谷车谷的这些农活儿;他已习惯了秧苗儿、稻草、谷子的味道。一想到自己要到一个陌生的环境,从事一些陌生的工作,再难嗅到让他安心的田地和农作物的气味儿,他的心就空了,就像什么也没有了,轻飘飘的,如一片被露水打湿了趴在地上的树叶儿。
堆在堂屋里的几袋谷,早就该卖了。那开着拖拉机,开着农用车下乡来收谷的贩子,不止一次上门来,可是最后,他都没让他们拖走。谷在屋里放着、堆着,就像将他即将飘走的心压着。这谷一搬走,他的心就会飘起来,飘荡在无所依傍的天空了。出门的日子是一拖再拖,一起相约去打工的同伴,已不止一次地催促,可他总是面有难色地说:“我还有一屋的谷。”同伴大惑不解,接着眼光像是看傻子似的说:“卖呀!”
他当然知道卖。这些谷子已经晒了好几天,又用风戽过了一遍,要卖随时可以出门;可是只要这些谷一出门,他田保,就不再是乡下的田保了,他就会变成另外一个人,变成高房林立、机器轰鸣中的一个匆忙的身影。他种了大半辈子的田,谁不说他是个过细人,是个种田的好把势。他的田耙得撒得过河,他的秧栽得像一根线。他的田不管什么时候看,都整整齐齐,像一块块刀切的豆腐。有事无事的,他总爱在自家的田地里留恋、逡巡,这里挖一下,那里修一下,像看不尽的风光似的。映在他眼里的每一片庄稼、每一块田地,都让他充满了爱恋和自豪。在这即将出门的时候,他想把那几袋谷子再好好整晒一番,再拿去卖。也许,这一生的农活儿,就只有这一回了。他这一生,是最后一次卖谷了!
上门来的贩子,抓起一把谷子,又让它从手掌流下来,拍了拍手说,保证按国家粮站一级谷的价格收,不让他吃亏,还不用他自己拖来拖去的麻烦,上车就走!可他最后还是选择了国家的粮站。这倒不是因为他有多高的觉悟,也不是因为多少年来交粮交成了习惯,他知道那“国家”两个字包括的广阔的范围。国家,该是多么大啊,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不管你是到哪里打工,都在国家这个范围里。说不定哪一天,自己在外打工的时候,吃的饭就是自己卖给粮站的谷。这些谷流转到自己打工的工地,就像见到了亲人一样。想到这里,他既兴奋又欣慰,迟疑的心就像有了安全的归宿。
当阳光铺满稻场的时候,一袋袋的谷子也从那低矮的土房里抱出来了。谷都装在蛇皮袋子里,那是装过化肥的大塑料袋,田保抱着一袋谷就像抱着一个睡眠中的孩子,显得小心翼翼。他腰弯着,赤着的脚快速移动,新扫出的场地上全是一个个清晰的脚印。田保把他的“孩子”全抱到稻场上,然后解开系着蛇皮袋子的麻绳,用一只膀子抬着,另一只手把蛇皮袋子的底部一角抓起来,那袋子里的谷就醒了似的哗啦啦流出来。
在秋天清冷的晨气里,一种熟悉的香味儿荡漾开来。这是田野泥土的气息,是干爽的稻草香味,是谷子散发的清香。这扑鼻的气息让田保浑身一震,如同打蔫的禾苗浇下一瓢清水,悠然又青葱了。被即将离乡的伤感和无奈炙烤得垂头怏怏的汉子,眼中又放出快活的光来,凝滞了的血液又汩汩地在身上流淌。他的胳膊青筋突露,那是一个健壮的庄稼汉子全身心地投入劳动的征兆;他的脚步变得轻快有力;他的神情变得专心又庄重。那是农活儿又唤醒了一颗疲惫的心。在稻谷的香味儿里,这个汉子忘记了离愁,忘记了伤感,又和那田野、大地、阳光交融一体。
不一会儿,田保就把一袋袋的谷从袋子里倒了出来,一堆堆谷像一座座小山。田保倒拿着蛇皮袋子的两角像晾晒衣服似的抖了两抖,里面的谷就倒了出来。不知是谁家的鸡,嗅着了稻谷的香味儿,早跑来稻场边上,围着那满地的金黄逡巡。见几束金光四射,几粒谷落下了坎儿,就低了头伸着脖子去抢啄。田保呼的一声从坎上跳下来,像滚下来的一块巨石,吓得鸡魂飞魄散,拍打着翅膀咯咯地叫着逃去。田保赶走了鸡,蹲下身来,扒开草,寻找蹦落在草丛的谷。那谷子躺在草蔸下,田保用两个手指拈起来,对着太阳一看,仍是金黄,只是上面沾了露水和泥土。田保吹一吹谷子上的灰土,放到手掌心里,像托着什么贵重的东西。场坎边一阵微风吹来,田保赶紧合紧了手掌,怕手里的谷吹走了。往日晒谷的时候,田保不是这般的小气,看鸡在稻场边伸着脖子徘徊,他也会把还带着草屑的谷抓一把撒过去,那群鸡就会跃起来,欢叫着去迎接那盛开在空中的丰收的花朵。但是今天,田保却舍不得一粒,他对鸡不明事理的窥视产生了愤怒,他握着谷站在稻场上,又望着鸡威慑地踹一脚,那还在留恋的鸡就彻底打消了觊觎的念头,远远地跑开了。
用一个木耙,把那一座座山似的谷扒开来晒。谷堆倒下来,田保听见一阵金属般的摩擦声。只有坚硬的谷子才能发出这种声响,只有他田保才能种出这样饱满的果实。田保自豪地把谷子推平,平展展地铺了一晒场。见到阳光,那谷就睁开眼了,尖尖的谷子嘴上全是闪亮的光点,仿佛在兴奋地唼喋。推开谷堆,见里面夹着一片稻草的叶子,田保弯下腰去,把那叶子捡起来,见半截还隐隐地透着青色,就送到了嘴里。田保一边推晒着谷子,一边咀嚼着稻草叶,一股稻田的清香就顺着喉咙流进了胸田,他的心中又翻滚着一田田的稻浪。
谷黄的时候,那稻苗的叶子也黄了,鲜润茁壮地在风中摇曳。那个时候,风吹拂着稻田,稻田翻滚着浪涛,浪涛中的田保,正拖着一口割谷的板仓,就像在金黄的浪涛中拖着一条船,金黄的浪涛划开了一条波浪。田保把一捆捆稻禾举起来,奋力在板仓上摔打,谷子就如同雨点儿打落在板仓里。时而几粒弹起来,弹打在田保的脸上、脖子上、裸露的胸脯上,一阵儿酥痒,一阵儿生痛。望着眼前遍地的金色波澜,摔打着谷子的田保,脸上充满了笑意。几年前,女人得病去世了,就只有他田保一人拖着一口板仓,在那片金黄的稻浪里收割。风在稻草叶儿上打着旋儿,嘭嘭嘭的板谷的声音传得沉闷又悠远,单调又寂寞。可是今天回想起来,那是多么让人舒贴的声音啊,它让人的心头饱满而又踏实。
谷推平了,接下来是要用齿耙耙出一行行谷沟,像田垅似的,这样会让更多的谷接触到阳光。可是田保,这个种田的汉子,却扔去了手中的齿耙。他习惯用自己的脚代替齿耙,代替那些生硬的、会碰痛那些谷子的铁齿。他的两片脚掌像犁似的嵌进谷堆里,贴着地面拖着往前去,那些谷子就浪花儿似的在他的脚背上翻涌。
当田保回过头来,那一稻场的谷一沟沟地起伏着,像织出的一块金毯,又像盖上了一片金瓦,流淌着太阳的光辉。树上的蝉,仿佛也为这一片金黄所鼓舞,吐着亮闪闪的金线似的蝉鸣,欢快又嘹亮。
骄阳下,戴着一顶草帽,光着黝黑的脊背,卷着裤腿的汉子,低头在谷子里来来回回一趟又一趟地走着。远处的人见了,以为这个汉子低着头在谷堆里翻找着什么东西呢。而那晒谷场边儿上的大柳树上的蝉,也像凑热闹似的,拉长了抑扬顿挫的嗓子,不停地问:“找到了吗?找到了吗……”
不知从谁家的院子里飞来一群麻雀。这一团灰色的小家伙儿,团绵而又轻盈,在上空飞来飞去。它们落到稻场边上的那棵大柳树上,霎时大柳树像长出了无数片的叶子,在风中不停地抖动。麻雀在大柳树上叽叽喳喳地商量着,然后派几只前哨飞下树来试探,一跳一跳地向那场里的谷子靠拢去。跳一跳停一停,跳一跳停一停,来试探的麻雀竖着的尾巴一跳一摇,像是在向身后的伙伴招手,要它们放心跟上。那金黄饱满的谷粒就在嘴边了,突然那一直低头耙谷的人长了后眼似的一下转过身来,吓得地上的鸟儿惊散而起。田保在场坎边拾起一块石子儿,朝唧喳着的树一扬手,鸟群便像一阵风吹的落叶,飞离树枝,又团绵着成了一块纱布,飘上空中而去。
晒谷的时候,最担心的不是偷食的鸡,也不是偷食的鸟,而是怕老天爷的脸。危机的出现往往是在正午,是在大家进门去吃午饭的时候。那时,太阳还像一团火在天上烧着,也没有丝毫变脸的征兆。吃了饭,田保一时觉得很疲惫。那群鸟儿也不知躲到什么地方去了,树上的叶子静静的,一动不动像睡着了,于是田保就把一把椅子转过来,反坐在椅子上,胳膊搭着椅背。开始的时候,两眼还瞅望着院场上的谷,渐渐地两个眼皮就不知什么时候合在了一起。天阴了不知道,凉凉地刮起了风也不知道,突然从天空劈下的一个炸雷,才将田保从昏睡中惊醒。田保赶忙跑到稻场仰头一望,只见一片乌云像从西边的山上跑来的一群牛马,将天空挤满了,把日头也遮没了。赶快收谷!又是推,又是扫,手忙脚乱,谷还没有收拢,一片雨早射了下来。好不容易将摊晒的谷收拢,用塑料布盖上,雨却停了,一片野兽似的云早跑得不见了踪影,鲜艳的日头露出来,不知躲到何处去的蝉,这时又在树上叫了起来。一天的谷算是白晒了。田保会毫无目的地骂一句,把那些淋湿的谷子推开来,一切的活儿又要从头开始。
田保仰头望天,天上空荡荡的,像没有一丝波纹的深潭。远处的山顶上只有几朵白云,如浮在水面的几团棉花。望着无雨的天空,田保有些失落。原来自己心里竟是盼望着下一场暴雨,再体验一回那手忙脚乱,那汗流浃背。午饭时,突然听见从空中传来的几声炸响,打雷了!田保放下手中的饭碗,兴奋地跑出门来,又站在稻场上仰头望天,天上仍明晃晃地悬着个刺眼的大日头,到处是白亮亮的一片。远处的天边似飘来一丝乌云,近了,才发现是一群大雁。那大雁飞过田保的上空,“啊啊”地叫了两声,又飞走了,消失在远方的深潭里。田保这才想起,那几声炸雷似的声音,是修公路的放炮声。田保垂下头来,望着地上的谷,他在心里对那些谷子说:“看来,我是一天也留不住你们啦!”
虽然已经用风戽车了一遍,但是他还是把檐下的风戽又扛到了稻场,一撮箕一撮箕地把那些谷子送上了风戽。风戽已经用了多年了,去年还上过一回桐油,太阳一晒,还发出桐油的味道。站在稻场上的风戽,就像一只忠实的老牲口,听任主人摆布。田保一手搅着风戽的风轮,一手控制着出谷的栓口。这只牲口就卖力地发出哐啷声,织布一样,从风戽的肚里源源不断地纺出谷子来。看着这道金色瀑流,听着风戽的车轮发出悦耳的声音,车谷汉子又是一脸陶醉的模样。当最后几粒谷子从风戽的漏斗口流出来,他脸上的陶醉也像流完了。田保上下搅动了几下栓子,转着风轮,吹干净了里面的灰尘与草茬,拍了拍和自己一样高的风戽说:“伙计,恐怕以后再也没有谷车了!”他见过许多出门打工的空无一人的家门,都是一个风戽拦在紧闭的大门口,那是预防什么动物撞开门钻进去。本是车谷的农具,从此就像一只看家狗一样,一年四季地站守在大门前了。
车好了谷,田保两手垂着,从杂屋里提出板车轮子,放到屋檐下的板车架下。粮店在街上,卖粮都用板车。放下了板车架,田保把板车扫了又扫。其实那板车两旁的板子磨得光亮亮的,露出洁净的黄亮色泽,但是田保还是认认真真清扫了一遍。这卖粮的每一道程序,他都要一丝不苟地重复一遍。发现了几块夹在板缝中的草,田保也一根根地抽出来剔净了。
装谷的蛇皮袋子田保也是挑了又挑,选出的都是一般大小的新塑料袋,装上车的谷醒目又齐整。临出门,田保又从箱子里翻出一套衬衣长裤。那灰色的衬衣已经洗得发白;一条长裤也磨了一个破洞,还没来得及补,可是很干净。他用一根绳子把裤子系在腰里,在肚脐处打了一个活结,像挂在肚子上的两只耳环。儿子给过他一根旧皮带,可是他觉得还是绳子用起来顺手,就像捆油菜、捆稻草、捆柴火一样。光着腿来光着腿去的田保已习惯了卷着裤腿,于是他又把那长裤腿卷起来。那卷着的裤腿也像是掉在他腿上的两个环儿。收拾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的田保不像是去卖谷,而像去走亲访友,去参加一个什么隆重的仪式。是的,这是他最后一次卖谷。
田保拖着一板车谷,到了粮站,见场子里停的全是装着谷子的板车、拖拉机,地上还晒着一摊摊的谷,还有人在忙着车谷。从风戽口里车出的灰尘、杂物像冒着的轻烟,又像出笼的蚊虫,哄哄地迎着太阳的光漫天翻飞。那是因为没有晒干,或杂质多,没有验收上,都在这粮站里返工。
田保望着那些一脸焦虑返工的人们,想到自己干干净净的谷,心中坦然又骄傲。他像一个胸有成竹的人,拉着一板车的谷进了粮站大门。等候卖粮的人们,见田保拉着谷子进院来,熟悉的向他打着招呼,不熟悉的也在两旁指指点点,不用看也明白,那是一片羡慕的眼神。他知道,这不是在说他田保种田种得如何好,而是在羡慕他田保养了一个会读书的儿子。这么多年来,全村就只有他一家出了一个名牌大学生。田保一想到这份荣耀,儿子那无限灿烂的前程,所有的不快就烟消云散了。
验收粮食的人,一手拿着一个小本儿,一手拿着一柄长长的尖刀,被一群人簇拥着。那人到哪里,那一群人就如河水中的一团浪花儿荡到哪里。人人都想卖个好价,都想抢在别人前头卖了好回家。围着收粮人转的,无一不手上伸着一支香烟,小心又恭敬的样子。但是收粮人并不把围着的人放在眼里,按着他自己定的收谷顺序验收,一刀子朝要验收的谷袋戳去,然后拔出刀来,刀槽里就有一槽的谷。他捏一捏,看一看,或者放在嘴里嚼一嚼,在那小本儿上龙飞凤舞地画上一等、二等、三等的等级,然后撕下来交给卖粮的人去过秤。收粮人要不就把手里的一把谷顺着风一扬,说:“再车!再晒!”他就是爷,就是金口玉言,你不返工就只有拖回家去。田保是老卖粮的了,不急不躁地等着,时而也和人们搭着闲话,他倒希望那验收粮的,最后一个来到他的面前。
可是那被围着的收粮人,还是朝他走来了。望着那明晃晃的三角刀,田保心里缩了一下,忙弯着腰,掏出半包香烟,抽出一根恭恭敬敬地双手递上去。那人看也不看,一把扯过来,朝上衣口袋里一塞,眼睛早已瞄准一袋谷,用手摸一摸,似乎在找一个软肋,然后一刀捅了进去。田保在一旁看得身上一惊一悚的,仿佛那一刀是扎在自己身上。这个收粮的检验员抽出刀来,瞄了一眼那刀槽里的谷子说:“二级!”田保心里一凉,自己的谷不说是个特级,也应是个一级啊。田保忙解开扎袋口的绳子,抓了一把伸在那人的面前:“同志您再看看,我的谷这么干净……”那人却不理他,狗撒尿似的抬起一条大腿,就着自己的腿当写字的凳儿,画了一张票撕下来“卖就拿去过秤”!
田保接过那张盖了大红印、潦潦草草写着“二级”的谷票,呆呆地坐在那里。这么好的谷,晒了三道,车了三道,比哪一年都整得干净,都晒得干爽,可怎么会是个二级?田保呆望着袋子上被验粮人戳的那个洞,就像戳在自己的腰上,还在隐隐作痛。几颗谷从刀划的洞口挤了出来,仿佛还在不服气,田保就轻抚着,把挤出来的谷摁进去,像安慰着受委屈的孩子。如果是以往,田保转身拖起谷就往家走,不卖了!可是这次,他耍不成脾气了。同伴们说不能再等他了!
“今年真是邪门了,最好的就只是个二级!”有人见他还在迟疑,就对他说。
那人他并不认识,正在返工,就着风戽车谷。他就想,为什么这么多人宁愿返工也还要将谷卖给粮店,不给贩子呢?
仓库门前,卖谷的板车都停满了,一袋袋的谷正从板车上搬下来,被人低头弯腰扛进仓库,就像一路路的螺蛳,慢慢地爬进仓门。看不见移动着的螺蛳的脸,只能看见那形形色色螺蛳样的壳,和那螺蛳壳一样的各式各样的塑料谷袋下,一双双形形色色的脚。
仓库全是用石头砌的,长长的一幢房子,从墙角到屋顶,冷冰冰的全是清一色的石头,用水泥勾着缝。门上画着一个像刚从坟里挖出来的骷髅,下面支着两根骨头,一股森冷威严的气息从这门口吹出来,让田保更觉得自己是把谷子送到了另一个世界,一去永不回了。
进了仓库,谷子堆成了山。就像进了一个大山洞,站在里面仰望仓顶,冷幽幽的,很大很高。一溜儿“之”字形的木板,从下面接到那谷山的顶去,是搭的一道桥,人扛着一袋袋的谷顺着木板桥一直走上顶去,也像一路螺蛳在那里攀爬。田保扛着一包谷爬到了山顶,站在谷堆的顶端,松开手里抓着的袋子口,那袋子里的谷就擦着自己的脸颊从肩上滑进谷堆了。田保张开鼻翼,嗅着自家谷子熟悉的香味儿,看见亲手种的谷像熔炉中流出的金晃晃的熔浆,顺着谷坡往下流,流了一截就停住了,仿佛已凝固到那山坡样的谷堆上。当他拿着空袋子顺着那条木板桥走到谷堆下面,回过头来看时,后面上去的人,正站在谷堆顶上,从他肩上流下来的谷又将自己的谷覆盖了。一缕缕阳光从仓库的窗口射进来,像一排探照灯,照着这一屋耀眼的金黄。
卖了谷的田保并没有急着回家,独自坐在堆着几条空谷袋的板车上抽烟。一些人手里数着钞票,嘴里念着“一、二、三……”匆匆地从他的面前走过。那是卖完了粮急着回家的,家里还有很多的事儿等着。可是田保,他是没有事儿了,什么事儿也不会再有了。卖完了粮,明天一出门,两扇门一锁,他就彻彻底底不再是种田的田保了。也许,他会在厂房里穿着千人一面的灰色的制服,成那流水线上的一员;也许,他会在耸着高高的脚手架的工地上,戴顶安全帽,忙碌地撮着水泥浆。戴顶草帽,卷着裤腿,扛着农具的田保就永远离农田而去了!田保独自坐在板车上,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地上是一地的烟灰,如同他黯淡忧伤的情绪。一个戴着红袖标的人走过来,严厉地说道:“你没有看见墙上的字吗?严禁烟火!”田保惊慌地站起来,把半截烟头扔在地上,又用脚摁熄了,脸上是让人不忍再发脾气的忠厚的笑。那粮店值勤人缓和了态度,“还在这里做什么,都要关门了!”田保这才注意到,热闹的粮站已没有什么人了,仓库的屋顶上已是一片晚霞的金黄,只有那大树上的蝉仍在叫着,粮站的工作人员正把那台称谷的台秤轰隆隆推进仓库的大门。
田保推着空荡荡的板车出了粮站,又回头望了望那关着自己谷的仓库,那被霞光映红屋顶的一幢长长的石头房子。说不定哪一天,这些国库里的粮食流转到了全国各地,流转到自己打工的工地,打开饭盒,看着这白花花的米饭,嗅着这香喷喷的味儿,就知道是自己田里的谷子了。“到那时,人还能知道这米饭就是我种下的谷打出的米吗?能,当然能!”拖着板车回家的田保,自己对自己说。他有一个窍门儿,他能知道是不是自己的谷打出的米,而且谁也不知道!想到这里,田保就有些得意地笑了。
拖着哐啷响的空板车,走在田野的小道上,田保显得轻松而又愉快。黄昏已经来临,天上的星星越来越明亮,在田保看来,那满天的星星都是无数的闪着金光的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