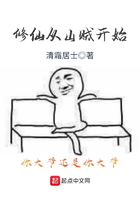李信上半身附在桌上,一处一处地指着,抬头问道:“也就是说只要杜游击所部渡过太子河,这一部东江就安全了?”
“边墙一线由北至南分别是一堵墙堡,碱场堡,禅山堡,我军现在位于濮阳堡附近。”陈睿见李信不解,继续道:“据卑职所知,这几处堡垒皆是东江军经营多年之根基,所以照理来说,只要杜游击渡过太子河应该就是安全的。”
李信揉了揉太阳穴,暗自嘀咕道:“照理来说?那应该就是万无一失了!”
“等等!”
金信直瞧着地图插嘴道,将算盘放到一边,神色也郑重起来,瞧着地图说道:“国轩说的只是大概,某不这么认为。”
“哦?”
陈睿诧异地看着金信直,李信疑惑地问道:“端言可有什么想法?”
金信直走到陈睿身边,低头望边墙一线,说道:“诸位莫不是忘了今天正月旅顺大败?”
众人被金信直这么一说,纷纷在脑海中寻起这段记忆,天启五年正月,后金突破东江防线,直逼旅顺,大战过后,东江军在辽南门户被横扫一空,东江将领张盘等皆战死。
见众人还没明白,金信直的表情更加严肃,低沉着声音向陈睿说道:“国轩,照理来说,东江军在辽南经营多年,以何为界?”
陈睿思虑了一番,疑惑地回道:“大致是以北汛口至大长山岛一线。”
“你是说?”陈睿脑中灵光一闪,像是抓住了什么,大声道:“东江军的防线难以保障吾等的安全?”
“某想说的就是这些。”金信直叹了口气。“吾家世代军户,深知鞑子与我大明想法并不一致,对我明军来说,实筑堡垒,就是我明军范围,但是鞑子却不这么想。”
“端言说的对。”沈贺年粗声附和道:“某在关宁亦是呆了几年,鞑子来去匆匆,从不把我大明所标地界当回事。”
“按你们的意思,也就是说无论杜游击是否渡过太子河,都难保安全?”李信扫视着地图,顺着众人的话茬继续说下去。
“恐怕大人言中了。”陈睿用手拧着下巴,说道:“但某恐怕东江军不是这么想的,因为宽甸一线的东江部队向来攻多余守。”
“可不管鞑子是否会攻击宽甸,但这一战,吾等却不能不打。”李信无奈地叹口气,抑制住心里的疑惑,大声道:“将多余的粮草全都收拾好,留下一百辅兵看守粮草,其余人等轻装皆骑马,支援杜游击!”
“大人!”众人正战兵接令,陈睿赶紧打断道:“如今情况不明,我等都是第一次上阵,是否应该暂缓两天?”
李信记起了那三千刚刚离去不远的步卒,被陈睿这么一说,既然有人去前方探路那倒可以慢上几天,不过心中却有些惭愧,若是真的有事,那三千人命也与自己有些关系,改口说道:“那就休息一日,等明日再动身。”
沈贺年,金信直,柳国忠见李信和陈睿面色不定,不知道陈睿为何打断李信的部署,不过既然李信已经下了命令,都点头称是,陈睿听李信改变了想法,终于送了一口气,几人见话说的都差不多了,相继告退。
“死道友莫死贫道。”李信望着地图暗自说道:“几位千总如果遇到了女真人,只能怪你们运气太糟了。”
一直到了第二天中午,李信才留下了两百人看着粮草,其余的骑营士兵都骑上了马匹,跟着李信一行人以常速进军太子河,既然不能肯定自己的安全,陈睿以三人为一组,又将所有骑兵化为三轮,疯狂地向队伍前方派出大批斥候,并且专门准备了三队斥候,随时跟前方步卒保持联系。
太子河北岸。
连绵地脚步声紧凑地让人喘不过气来,两岸的山林中,数百军士正在拼命地砍伐着木材,而等候在一旁的军士则赶忙将这些木材送到河边,等待许久的人群迅速在岸边搭建起浮桥,建筑的大军沿着太子河北岸相互推耸着,不时有人落入冰凉的河水中,溅起一朵朵发白的水花,引得岸上的人群赶忙救援。
在大军的后方,杜建德望着河滩上拥挤的人群,眉头紧凑,沙哑着声音问道:“还需多久方能将浮桥搭好?”
“禀大人,大概还需一个时辰。”
得到属下的汇报后,杜建德没有在看搭建中的浮桥,转身望向身后,漫漫地丘陵都被茂密的苍木所覆盖,一切事物都被掩盖其中,除了军士们砍伐时喊出的号子声和巨木的倒地声外,一切都平凡无奇。
“只要渡过了太子河,我们就安全了。”杜建德暗暗送了一口气,疲惫不堪的身体也振作了一下,轻轻笑道:“总算可以回家了。”
“可以回家了!”杜建德身旁的一名亲兵掩饰不住疲惫偷偷地掐了自己大腿一下,疼痛一番后脸上挂上了欣喜的笑容,紧绷的眼角间带上了一丝柔和,望着缓缓的太子河水,言道:“大人所言甚是,只要渡过了太子河,就是我东江的地盘,道时候就不必再担心奴兵的追击了。”
杜建德盯着这名亲兵,拍了下脑袋,像是想起什么似的,哈哈一笑,对着这名亲兵打趣道:“这次回去,你小子就攒够钱娶亲了,到时候本将一定要去你那喝几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