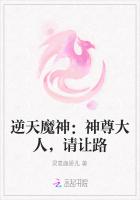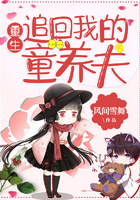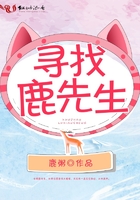后文中的讨论将对把背景设置在20世纪70年代小城市的故事予以更仔细的审视,并考虑到上述这一切。影片《孔雀》(2004)由顾长卫执导,改编自李樯的中篇小说。《孔雀》的叙事是片断的、插曲式的,用多个简短的、有所省略的时刻追忆了20世纪70年代末期的生活。这一手法意味着放弃了《霸王别姬》和《活着》所采用的对于历史的完整阐释。《孔雀》作为北京电影学院1982级摄影专业毕业生顾长卫40多岁时的导演处女作,和一位30多岁的小说作家李樯的编剧处女作,对于工人家庭出身的三兄妹的叙事发生在河南省安阳地区一个偏僻的小城鹤阳。而影片的拍摄则是在一个同样不起眼的小镇——隶属于同一地区的水治。吸收了新生代的手法,影片的人物由籍籍无名的新演员说着河南方言出演。顾长卫本人与第五代的密切联系来自他掌镜的作品,其中有几部是以寓言形式拍摄的:张艺谋的《红高粱》和《菊豆》,陈凯歌的《孩子王》、《命若琴弦》(又译《边走边唱》)和《霸王别姬》。他还拍摄了姜文的《阳光灿烂的日子》、《鬼子来了》,并在美国拍摄了罗伯特·奥尔特曼(RobertAltman)的《迷色布局》(TheGingerbreadMan)。顾长卫参演的作品有《孩子王》(饰吴秘书)。《孔雀》是由私人投资的,投资额大约1600万人民币。影片的宣传将其定位为艺术片的“优质电影”,寄望于本片导演作为摄影师所享有的世界声誉和影片作为2005年柏林电影节银熊奖得主的成就。影院发行的票房回报迄今并不见佳,影片对于在一种常见的不利环境背景下满足生活愿望的复杂性有着沉闷的,甚至可以说是压抑的描述,也许这正是票房失利的原因。中国评论家承认影片的人道主义特质,包括其前所未有的对复杂的心理现实主义的探索。胡克:《电影叙事观念的拓展与游移:2004年国产电影剧作艺术评析》,载《当代电影》2005年第2期,页6—10。这部影片的特点似乎无法归入代际差别中的任何一方。影片中的小城背景下成长故事的主观叙述接近王爱华的民俗志,它关注的是地域和主体经验,同时又与其他电影进行了对话。
三《孔雀》及其多重设置
《孔雀》设置的历史背景是20世纪70年代末期,而情感与精神的内在世界的象征是河南省一个小城的地域文化背景。恰如导演所言,它是一次对普通人的愿望的致敬。同时,本片也是对于那些描述普通人(没有实现的)愿望与梦想的影片的致敬和对话。它以沉郁的调子,纵深长镜头的手法,讲述相连的三个(或曰两个半)人的成长故事,与台湾20世纪80年代的“新电影”相近。后者讲的是在台北飞速发展成为移民城市的年代里,那些被剥夺的机会和未实现的梦想的童年记忆。例子是侯孝贤的《风柜来的人》(1983)、《恋恋风尘》(1986)和杨德昌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1991)。把个人生活设置在具有历史意义的艰难时世的手法,在20世纪90年代已形成了潮流,著名的例子有史蒂文·斯皮尔伯格的《辛德勒名单》(1993)和罗贝尔托·贝尼尼的《美丽人生》(1997)等个人化的反映纳粹屠杀犹太人的影片。托马斯·艾尔萨埃瑟(ThomasElsaesser):《主体位置、言说位置:从〈浩劫〉、〈我们的希特勒〉、〈家园〉到〈毁灭〉和〈辛德勒名单〉》,载维维安·索布切克主编:《历史在持续:电影、电视和现代大事》,劳特里奇出版社,1996年,页146—183。《孔雀》中的人物不是死亡集中营里的囚犯,而是无形的枷锁下拥有创造力的灵魂。在其音乐设计上,《孔雀》背离了运用当地戏曲或民间音乐的常规,反而使用大量的静默和环境音效(特别是火车的汽笛声)来制作音乐和音响,间杂着特意创作的并不多愁善感但是动人心弦的(有时是浪漫的)音乐。尽管有所不同,这仍能使人联想起波兰作曲家茨比格涅夫·普莱兹纳为他长期的合作者波兰导演克日什托夫·基耶斯洛夫斯基的《三色:蓝色》(1993)所创作的音乐,及其视觉—音乐概念。导演顾长卫在一次访谈中提到了他最喜爱的导演小津安二郎。小津安二郎创作了许多表现最普通的家庭生活的影片,然而传达出的内涵却绝不普通。见夏雨对顾长卫的采访:《又是一个中国年?》,载《南方周末》,2005年2月24日,D25。应该把这些与其他影片的“对话”视为非共时性的不谋而合,而非仅仅是“派生话语”(derivativediscourse)。不同影片中因使用一种特定的“现象学”手法而在密切地彼此回应。这是克日什托夫·基耶斯洛夫斯基的一个有关创作过程的重要观点,出自《蓝色》DVD版本中的访谈。他反驳了线性等级的观点,即任何出现时间较晚的东西都必然是对先前出现的东西的模仿,并且陈述了非共时性创作实践的抽象趋同。
(一)日常空间中的历史设置
“动乱年代不再简单地作为施暴和受虐的演武场,家庭里、亲人间的相互嫌隙和无情解体,更深刻地映衬着时代的悲凉。”郑洞天:《老鼠对大米的感觉——2004年的电影》,载《当代电影》2005年第2期,页5—6。
《孔雀》的开场含义丰富。两个成人和三个孩子围着一张放在普通的阳台角落的小桌子吃饭。锣鼓声从不远处响起,说明街上有不花钱的热闹可看,最小的男孩热切地站起来,打算冲下楼去。他立刻被父亲制止了,父亲要他坐下,把饭吃完。而另两个孩子从桌子旁跑过去。显然是下楼了。观众可以体验到严厉的父亲和好奇的儿子之间的紧张关系,因为他们同样被这声音撩拨着,期望看到某种热闹,以满足窥视欲望,看看可能比普通家庭用餐更令人激动的场景。但是影片在下一刻仍是跟总体为蓝灰色的画面并无二致的内容,因为它没有切到那个让观众随着孩子激动的脚步目睹戏剧性的活动影像。恰恰相反,我们的目光被父亲强硬而粗暴的命令控制住了,实际上是被摄影机停留在日常空间里的长镜头控制住了。凝固在这一刻中的是行动与不得行动、日常的景象和可能的热闹、父与子之间的张力。切换过后,依然是长镜头。
谢晋那一部出色的《天云山传奇》(1980)树立了一种普遍的电影观念,即认可受难的目击者成为关于历史的拥有权威与道德的代言人。而后,20世纪90年代初期对于这一段历史的史诗性再现的叙事中,家庭成员们经历了漫长的多重的痛苦,因而作为整个民族历史的道德见证人的权威性,也是毋庸置疑的。在谢晋的政治情节剧中适应性很强的个人和张艺谋的相应影片(《活着》)中那对饱受创伤并且逆来顺受的夫妻,作为人,既有道德上的正直又有尊严。因此,值得指出的是,近期中国电影对于历史代言人的塑造方式,并不是政府的主旋律影片对于非官方的普通观点的阐释,虽说这种阐释借鉴自政治情节剧中构建日常生活的认同机制。相反,是这一历史见证人向非道德和不道德的变更,所伴随着的是将舞台转向先前被视为琐碎无关的日常空间。
评论家胡克曾指出“人性本善的观念在21世纪初叶的影片中已黯然失色。
自现在起,对人性邪恶一面的表现会加强”,特别是要抛弃此前的作品中那些“掩饰黑暗灵魂的玫瑰色外壳”。胡克:《电影叙事观念的拓展与游移:2004年国产电影剧作艺术评析》,载《当代电影》2005年第2期,页6—10。道德优越感被弃置一旁,而个人主义和多种彼此竞争的主张之间的激烈冲突被推到前台。不再有对牺牲者、从犯、好心人、大人物的认同,反而是非道德的(“邪恶的”)历史代言人能够成为集体无意识中的一个人物。如果“革命文学和电影”的一个关键性悖论是,“人民”作为模范革命公民来加以表现,对于他们媒体并没有任何从他们本身角度出发而进行的塑造,更不用提凸显其人性弱点了;因此后毛泽东时代的影片中则发生了被压抑者的回归热潮。这些作品不仅仅呈现为风格各异的形式,而且在不同程度上背离了再现的中性意义,在更近的几年中,它们有意识地塑造自私自利的非道德化的人物。在《孔雀》中,人物是操纵型的,他们在内心深处怀有对彼此的深深的憎恶。
正如卫红对一个陌生人所承认的:“我不喜欢我的家人,他们也不喜欢我。”她划伤了自己的手腕来争取他的同情和友好的关注,却不曾付出任何情感上的回馈。
后来,她和她的弟弟试图毒死父母最关心的大哥。作为负面感情的中心,每个人对他人而言都是潜在的伤害。在《孔雀》中,是这些情感纠葛,而不是被视为宏大历史事件的东西,成为日常痛苦的根源。而这个年代,原本通常是被归入“十年动乱”的叙述中的。这类叛逆的而且有着潜在的伤害力的代言人,其破坏力出现在历史事件的中央舞台之外。其他几部近期的影片也持有类似的观点,包括《美人草》(2004)中丑陋的谎言,以及《茉莉花开》(2004)中杀死丈夫和家人的冲动。
在史铁生的早期作品中,他曾写道:“历史不是过去的历史,而是现世与心灵的历史。”叙事中的过去对应着个体生存的内在真实。因此,历史循环论的读解可以应用一种迥然不同的叙事主体,既可以表现物质生存条件的全面改善而继续存在精神真空这一普遍看法,也可以揭示一种接近于原始资本主义的残忍阶段的内心状态,对于救世理想的不信任更强化了原始资本主义的冷酷本质。后者的表象是:不仅是历史,而且人性也无法给人以安慰,正如《孔雀》和其他真切地感受到这种状态的当代影片所给出的例证。尽管在下文中我们将要讨论到,《孔雀》依然期待着给希望以一席之地,尽管这希望稍纵即逝,支离破碎。
作为叙事策略,此前与邪恶人物相关联的不受欢迎的特质返回到了无害的普通人身上,而这种策略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可以说是一种成规,在有些影片中邪恶由阶级敌人和特务来代表,在另一些影片中则是腐败的官僚,还有一些影片中则是貌似无害的普通人。正如人们所知,只要道德模式依然能够取悦观众的审判观念,并赋予一种获得历史真理、获得回报的潜在允诺,比如动人心弦的温柔场景,在叙事结束前及时地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样就不会有所进步。而某些影片却冒险取消了这种审判观念,把每个人都牵涉为历史苦难的从犯,留给观众没有结局的失落状态。大胆进入这些令人痛楚的领域是中国现代主义的任务,第五代早期的某些影片曾通过暧昧的叙事些微涉足这一领域,或者以此来抑制认同感。比如《黄土地》中的某些场景就含混暧昧,依然有待读解。在这一方面,《孔雀》也没有建立道德模式,没有给予审判结局。不仅是个别场景对于自己意图展现的内容态度暧昧,而且动作简单而清晰的场景和片段也贯穿着一种晦涩感,因为紧随其后的场景或者相距久远的场景会使之发生逆转或予以修正。影片清楚地告诉观众什么正在发生,观众可能对于这究竟意味着什么会形成自己的结论,但由于许多场景和片段暗示出此前的结论可能有误,因此观众不得不转变自己的观念,这样的处理方式同批判现实主义在20世纪30年代的手法也有所不同。比如,有两个极其残酷的场景,一个是大哥遭到无情少年们的毒打,另一个是母亲施虐式地把毒药喂给了家里养的鹅,随后的场景却展现出,大哥奇迹般地获得了平衡感,弟弟妹妹们也有了和解的愿望,脆弱然而生机勃勃的生活状态就这样安然度过了充斥着彼此间酷烈的精神伤害的总体背景。电影里的几头鹅扮演了有关生命和死亡的本质的角色,从侧面衬托出一家人不同的生命的本能冲动。关于鸡、鸭、鹅,一个在孩提时曾仔细观察过它们的作家写道:“它们微不足道的活动在我面前流露着友情、礼貌、幽默、上进和尊严。它们的本能冲动,如此复杂,如此深不可测,预示出了某些人彻底投入生命的本性,这的确令我惊讶。”当他在杀掉它们以供食用之前用双膝夹住它们温暖的身体时,“它们教会了我什么是死亡,以及为什么说生命是借来的,是债务”。参见让·勒·穆瓦涅:《趋同》,多伦多:莱俄森出版社,页9。在成长故事的结尾,那种对于一个多少有些可怜的人物的怜悯变得多余,因为大哥卫国凭借其不受任何敌意影响的强烈的自我意识,成为一家兴旺的小店铺的主人,也就成为市场经济中的新兴主体。对于貌似值得羡慕的任何嫉妒和对于无法达到的生活的幻想,事实证明是不必要的,因为家庭杂务是一个了不起的平衡器,在相当程度上让那对伞兵夫妇也落到了同样凡俗的地步;而此时卫红为了逃离工厂而接受的第一次婚姻虽已失败,她的幻想能力却并未消减。在个别场景和整体构思中,《孔雀》这种逆转性的叙事策略(不管是简单的还是累积的)有效地悬置了任何通常被电影和情节剧所采用的持续一致的审判观念。逐渐揭示生活真相却又悬置审判结局,这一叙事策略暴露出人物、情况和事件的两面性或多面性。
在招兵人员带着大队新兵乘卡车离去之前,年轻伞兵在镜子前短暂地沉醉于自豪的军礼,这一镜头是很能说明问题的。他的自豪来自于他被人羡慕的军装,他的北京口音,这些均暗示着他拥有与这个小城居民截然不同的未来。一旦脱掉伞兵服及其附属的一切(正如他后来那样),英雄主义就变成了忧伤的幻梦,或者不如说是充满想象力的年轻男女试图逃离痛苦生活的幻梦;在这种生活中,他们苦于缺乏资源、缺乏机会和缺乏有益的鼓励。再深入一步,可以说,在特定的日常背景下,宏大历史经过适度的时间磨蚀之后必将展露其平凡的世俗的一面。就在历史的日常观念中,一个一直以自我为中心的人物的脚踏实地的态度变得越来越倾向于务实地争取立足于这个世界。毫无疑问,起初卫国得到了父母的鼓励,在他练习骑自行车时,他们帮他推着自行车以保持平衡,当他不可避免地摔倒在地上时,他们教导他,给他擦汗,让他喝水。但他站了起来,而且,当自行车开始向一边倾斜的时候,他赶快伸手扶住旁边的墙壁。然而,那个让他和妻子不得不整日埋头苦干的流动餐馆生意上的成功却毫无魅力可言。不过,卫国与卫红两兄妹的差别在影片一开始就设置好了:卫红在家中拉手风琴演奏着朝鲜舞曲,身后炉子上烧的水已经开了。她宁可继续演奏自己的乐曲也不愿费心管一下炉子上的水壶。这位孤独而且感性的理想主义者的充沛精力,简直可以与沸腾的水的热量相媲美,正是这种力量使她坚持到底,即使在似乎任何事都出了岔子的时候也一如既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