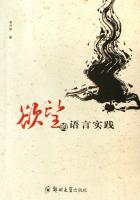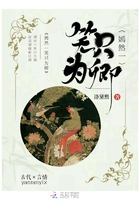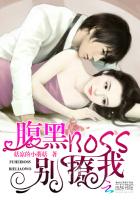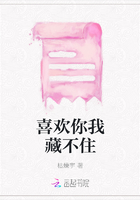正如人世间对万事万物的好恶有所不同一样,批评家对作家作品也有各自不同的喜好和不同的审美标准。尽管“天地间自有一杆秤”,文学亦有相对的评判尺度,但不同的文学观念、不同的审美要求,仍会造成不同的批评效果,有时甚至是真知灼见与偏颇之见交织在一起。香港学者司马长风的《中国新文学史》中关于曹禺的批评,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司马长风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史》是一部颇具特色的文学史著。该书以活泼多姿的行文风格和重本体研究的批评特色见长,书中不乏作者的真知灼见,但值得商榷之处也不少。本文仅就其曹禺批评,对《雷两》“写作上的投机心理”、蘩漪形象的刻画缺乏民族性格依据以及曹禺对西方名剧的“窃取”等问题试与司马先生商榷。
细读司马先生在史著中对曹禺的全部批评(包括二十四章、二十九章),他对曹禺在中国话剧史上的贡献及地位是充分肯定的。他认为,自《雷雨》、《日出》问世,曹禺便“从此奠定在戏剧创作首席地位,更到今天,仍无人能够超过”。他还集中概括了《雷雨》的杰出之处:
第一,从《雷雨》开始,话剧在广大的社会中,才成为引人入胜的戏剧,它为话剧树立了里程碑。
第二,它使舶来的话剧,成为纯熟的本地风光的话剧,夸张一点说,为话剧建立了民族风格。
第三,在穿插紧凑,对话生动,剧中人个性的突出各点上,都超越他的前辈,迄今仍无后来者。
他甚至认为,“《雷雨》一经面世”,包括洪深、田汉、欧阳予倩在内的所有前辈剧作家“便立刻黯然无光了”。
然而,也许是应了“笼统地肯定,具体地否定”的一句老话吧,对曹禺作了如此高度肯定的司马先生,并不以曹禺的贡献为然,在同两章里,他对曹禺还做了不少不客气的批评。这些批评,有的是极中肯綮,富于见地的,有的却带有一定的偏见成分,或者比较简单化地加以否定。笔者愿意就后者涉及的几个小问题与司马先生商榷。
一、关于《雷雨》“写作上的投机心理”问题
这本是一个不值得讨论的话题,但关系到主要人物形象的真实性问题,故无法避开。
司马先生关于《雷雨》“写作上的投机心理”主要有如下意见:
曹禺出身清华……本可以归属为京派作家,换言之应是谨守文学本业的作家,可是他太聪明,有如一个透明的水晶球,站在那里两只眼睛向四面八方打招呼,博取喝彩。他一方面在艺术深度上下工夫,一方面在政治上花枝招展:一方面要表现温良的人性,一方面又突出无情的阶级意识;可以说《雷雨》是一部多面投机的作品。
在他心中第一个权威是观众,必须使观众感兴趣他才能成名……第二他要敷衍的是当道者,当时实行“先安内后攘外”的政府;第三他要应对的是弥漫上海文坛、号召阶级斗争的左派势力。
撇开其言词中作为一个严肃的批评家不应出现的挖苦和许多不负责任的议论不提,应当肯定,司马先生的批评并未完全脱离曹禺创作的实际。因为正像不少优秀的剧作家一样,曹禺的确是以观众的需求为第一权威的,他“成功的基础”就在于他“非常懂得、了解、适应观众的审美心理和欣赏情趣”。与此同时,他又是一个真诚而执著地感受着时代生活的作家,无论他自觉与否,在他的剧作中,一定的阶级意识是客观存在的。问题在于,司马先生将一个二十岁出头的青年学生描绘得如此工于心计、四方讨好、八面玲珑,而且添加了许多完全可以说是批评家主观性的不负责的议论。这样做,不仅令人感到司马先生作为一个批评家对于研究对象缺乏应有的宽容和体贴,而且表现了司马先生有意与各种政治拉开距离的某种偏见。而正是这种偏见,影响了司马先生作为一个严肃的批评家对于作家作品的合理判断。
尤其是对于周朴园形象塑造的不正确的评判。在司马先生看来,周朴园是一个典型的“为多面投机”而创造出来的人物形象。他认为,曹禺“把剧中的反派主角周朴园,也写得深情款款,写他对侍萍始乱终弃之后,30年来受良心的惩罚。客厅里摆着30年前的旧家具……都表现了不平凡的人情人性,显出了这个富豪之家的阎王、丑恶的大资本家,有它崇高庄严的一面”。这样做,并不是因为作者“有什么人道观念,伦理深情”,而是为了“迎合国人传统观念(也连带敷衍南京政府)满足观众趣味”。此外,曹禺为了“迎合左派势力”,还“突出矿工鲁大海,及揭露周朴园的凶恶,但突出得都很失败”。失败的原因就在于鲁大海对周朴园的揭露“太概念化,缺乏说服力”,而且“违反常识”,缺乏真实生活为依据。“因为近代的资本家全凭企业的圆滑进行,资本迅速周转来获取利润;绝不肯造成死伤数千人的事故来赚钱……江水不深,怎能同时淹死两千二百人?”
鲁大海形象的成败已有公论,这里说说周朴园的形象刻画。
我们都知道,周朴园形象的塑造,无论是其“凶残”的一面还是“温良”一面的刻画,都不是作者有意迎合哪一种政治势力的产物。它是“人类行为的必然性”的艺术表现,是作家对生活本来面目高度概括的结果。《雷雨》之所以被广大观众认可,被人们广为赞誉,其原因之一就在于作家能够遵循生活本来的逻辑,写出了周朴园作为一个具有董事长地位同时也兼有封建家长身份的男人,在面对不同的境况和不同的对象时,其可能会有的不同的作为和不同的情感反应。这些作为和反应,包括了周朴园心灵孤寂需要情感安慰时,自然萌发的对侍萍的怀念和内疚之情,也包括了当他发现这种感情将要危及其名誉、地位时,完全出自本能地对侍萍的软硬兼施,以及后来自以为真相败露,让周萍跪下认了生母等。这种种表现周朴园复杂心态的似假又真,是真亦假的情感和作为,不仅充分说明了周朴园形象的切近生活、真实可信,说明了“深情款款”、“崇高庄严”与丑恶残忍有同时存在于周朴园身上的可能性,同时也说明了所谓“迎合观众”和“敷衍南京政府”的子虚乌有。
至于对周朴园凶残一面的揭露有无“违反常识”,他是否“造成死伤数千人的事故来赚钱”,江水是否“同时淹死两千二百人”,似乎更是不成为问题的问题。文学理论的ABC告诉我们,现实主义作家描绘的是生活中可能会有的事情,艺术的真实本来就并不能等同于生活的真实。而资本在原始积累阶段大多都不择手段,这应是一个人所共知的常识。只要生活中存在这种现象,周朴园性格中“凶残”一面的揭露就能找到合理的解释。曹禺将出事地点确定在哈尔滨也许有失考虑,但类似的事故在偌大的中国并非没有发生的可能。它与“迎合左派势力”之说显然是风马牛不相及。
二、关于蘩漪形象的“中国风”问题
司马先生对蘩漪形象的分析是与周朴园形象的分析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他对曹禺“对近代西方人正面肯定的肉欲性爱则给予很高的评价”和对于曹禺“特别喜爱那个为了性爱扔弃母爱的蘩漪”表示大为不解。他以近乎大男子主义的调侃语气议论道:“一个女人渴望性的满足,原不是什么罪恶,但也绝不是可歌颂的德行。她反抗年长20岁的周朴园,可以欣赏;但是霸占比她年轻8岁的周萍,则未免太缺乏同情。周朴园霸占她是罪行,她霸占周萍同样是罪恶。这样一个平凡的女性,曹禺对她竟这样一往情深,大值得注意。”
注意什么呢?第一,注意曹禺“写作上的投机心理”。第二,注意蘩漪形象的刻画缺乏民族性格为依据。
关于第二点,司马先生在同一章的《李健吾》一节中说得更清楚,他说:“剧中(指李健吾剧作)的每一角色,每一言一动,都是纯中国风的,不像曹禺的《雷雨》,最花心血描写的蘩漪,竟为了性和爱发狂,弃母爱如粪土,那是中国罕见,西方才有的女性。”
事实上,为了性和爱发狂的女性,在中国的古代的确少有记载。我们从古代文学中所能见到的,大多都是为了爱而抑郁终生的女性形象。但这并不等于说,中国没有为了性和爱而发狂的女性。爱,毕竟是人的本能,更是女人的天性,只是传统的伦理道德使史家不屑于也不能够留下有关的记载。即使有也是作为反面的形象出现。
何况,“中国风”本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因为“民族性格是一个历史范畴,随着社会生活的改变而改变”。虽说在我们原来的民族性格中,恪守妇道、忠贞守节为表现之一,但随着门户打开、西风东渐,原有的“中国风”已起变化。《雷雨》描绘的正是这种已不同以往的“本地风光”。
《雷雨》所讲的是20世纪30年代的故事。这时候,已是“五四”狂飙运动过去了十几年。像司马先生所指责的“他对近代西方人正面肯定的肉欲性爱则给予很高的评价”虽表达不够准确,但在当时,提倡个性解放、婚姻自由,的确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这时候,在中国的大地上出现像蘩漪这样既保留着旧式女人的性格,又为个人的性和爱而抛弃了妇道的女性,大概不能算是什么罕见的事情。
就蘩漪而言,她35岁的年纪,想来“五四”时期应在新式学堂受过个性解放思想的洗礼。在嫁入周家前,她的心灵应早已埋下对爱的憧憬。对于她,“热情原是一片浇不息的水”,偏偏命运把她安排到一个极其特殊的生活环境中。因此,正常的心灵渴求被压抑,对爱的向往变为极端的行动,最终为爱陷入了疯狂。
至此,蘩漪形象有无“中国风”,有无坚实的民族性格为依据,应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
然而,司马先生花费许多的文字,目的只是说说蘩漪性格刻画的“中国风”问题而已么?不!他想印证的依然是曹禺的“写作上的投机心理”。
司马先生的逻辑是这样推理的:违逆伦常的蘩漪形象的塑造,说明曹禺“对伦常的毁灭不但丝毫无动于衷,并有窃窃快意之感”。而毫无伦常观念的曹禺表现周朴园的人性人情,并不是因为作者“有什么人道观念,伦理深情”,而分明是要“迎合观众”,并“敷衍南京政府”,可见曹禺写作上的确有投机心理。
这样的逻辑果真能够成立吗?
三、关于曹禺对西方名剧的“窃取”问题
在外来影响问题上,司马先生对曹禺也表示不能满意。他说:
除了写作上的投机心理,《雷雨》以及初期另外两个剧本《日出》和《原野》,都有人指出是窃取西方剧作名著。例如:《雷雨》一剧,完全以易卜生的《群鬼》为蓝本,再加上俄国奥斯绰夫斯基的《大雷雨》的一点情节……《日出》一剧始脱于法国小仲马的《茶花女》。陈白露相当于玛格丽特,方达生相当于阿芒……《原野》一剧,很显然的是受了美国欧尼尔的《琼斯皇帝》的启示而写成,只是作者加强了农民如何向土豪乡绅复仇的描写。
他在“李健吾”一节将李与曹作了比较后又说:
曹禺的每一部作品,几乎都可以找出袭取的蛛丝马迹。
很显然,在外来影响问题上,司马先生与国内学者有着很大的分歧,与海外学者的看法也并不一致。
一般来说,国内学者强调的是曹禺对西方戏剧的学习、借鉴以及在此基础上的融化和创造;“海外学者多注意曹禺对西洋戏剧的模仿”,司马先生则认为曹禺有“窃取”、“袭取”西方名剧之嫌。
笔者认为,曹禺对西方戏剧的学习、借鉴是有创造性的,他是中国戏剧史上的一座丰碑,但其早期剧作的确存在着对西方名剧的一定程度的模仿现象。陈平原先生也认为:“海外学者多注意曹禺对西洋戏剧的模仿,这无疑是有一定道理的,曹禺确实是易卜生、奥尼尔、契诃夫等牵上路的。”而我们在阅读曹禺早期剧作《雷雨》、《日出》时,可以明显感觉出来的与《群鬼》、《大雷雨》等西方名剧在某些人物关系的设置或某些场景、氛围以及台词、细节上的似曾相识,就是作者早期模仿的证明。
也许有人认为,这是曹禺受西方戏剧影响的表现,不能说是模仿。其实,影响与模仿虽有很大的区别,但二者有时是不能截然分开的。只要在接受外来影响时,对外来的东西还“化”得有痕迹,甚至能“对号入座”,就不能否认其出现过这种模仿。
模仿作为人类的一种本能,它是人类学习必经的一个阶段,更是作家成长过程中一个重要的阶段。对于青年曹禺而言,尽管他的处女作一炮打响,而后的几部剧作也是佳构,但他对西方话剧的学习和借鉴显然也经过了有意无意的模仿阶段。当然,更多的是无意的模仿。我们可以想见,当年轻而尚缺创作经验的曹禺在阅读过许多令他着迷的西方名剧后,出于由衷地喜爱,其中许多片断、场景、台词等已经被他揣摩再三并且在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于是,当他被创作的欲望之火熊熊燃烧着时,这些人物、场景、片断、细节甚至氛围、道具很可能与现实生活一起袭来,不断地冲击着他的笔端,令他无法分清哪些是实有的生活,哪些是自己的虚构,而哪些又是别人已有过的文学创作。曹禺自己所讲的“尽管我用了力量来思索,我追忆不出哪一点是在故意模拟谁。也许在所谓‘潜意识’的下层,我自己欺骗了自己:我是一忘恩的仆隶,一缕一缕地抽取人家的金丝,织好了自己丑陋的衣服,而否认这些褪了色(因为到了我手里)的金丝也还是主人家的”,大概也是这个意思。
当然,这里所讲的模仿,主要是指对西方名剧的某些已有的艺术表现如细节、场景等的模仿,它与作者对西方戏剧的技巧和手法的学习是不能混淆的。现在的一些论著,往往将作家对西方名剧的模仿,与曹禺对西方戏剧手法、技巧的学习借鉴混为一谈,这是不够恰当的。在中国,话剧为舶来的艺术品种,人们在舶来其基本形式时一般也会将其结构、手法一道舶来。剧作家可以在借用时出奇出新,但不会有太大的变化,因为那毕竟是千百年来西方许多民族对这一艺术品种所投注的美学理想的凝结。因而,当作家借用其形式、手法、技巧来表现民族的生活,比如曹禺借用“锁闭式结构”来演绎周鲁两家三十年的恩怨,他学习索福克勒斯的“发现”手法来推动情节的发展等,我们就不能责之为“模仿”。这就像旧诗词中的五言、七言等格式及重复、顶针等修辞手法一样,哪一作家都可以运用,不同的只是这些格式、韵律、手法所表达的情感以及表达的角度不同而已。李渔所讲的“新也者,天下事物之美称也。而文章一道,较之他物,尤加倍焉”,其中的“新”,当指艺术表现方面的新。而我们称之为“模仿”或“窃取”的对象,主要就是指一些表现了作家艺术创造性的新的东西。
不过,尽管对象相同,但“模仿”和“窃取”却是性质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我们都清楚“窃取”一词的含义,司马先生引文中列举的关于曹禺剧作的种种所谓“窃取”的事例,也清楚地告诉了我们什么是对西方名剧的“窃取”。然而笔者认为那是不实的夸大其词,司马先生的“窃取”论是一个根本不能成立的观点。
不错,曹禺早期剧作是经常可以见到一定的对西方名剧的模仿,然而这种模仿,只是对某一场景、某一意念、某一氛围或某一细节的移植式模仿,它已经过了作家的改造。它与司马先生所提到的“完全以易卜生《群鬼》为蓝本”;“始脱于……《茶花女》”;“只是加强了农民如何向土豪乡绅复仇的描写”等近乎整体意味的“窃取”,可说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种行为。前者是指自觉不自觉地个别或细部地学习模仿别人的长处;后者是指几乎整体地有意地照搬照套别人已有的成果。前者对作家能够起到一种良善的作用,但在创作中起决定作用的依然是创作主体的创造能力;后者却是作家创作能力低劣的表现。而曹禺高超的戏剧艺术造诣连司马先生也不得不感叹“世间确有天才”。可见,“窃取”论对于曹禺确是一个极不恰当的批评。
与此同时,笔者也不能完全同意国内个别学者关于“曹禺已将外国的东西不露痕迹地‘化’到民族的东西之中’”的提法。从曹禺整个创作活动看,可以这么说,但对其早期创作而言,提法却不合适。尽管“曹禺上路后不大遵守先师的遗训,而是返身到这古老的文化传统中吸取养分,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生根开花结果”,尽管曹禺对西方戏剧的民族化已经取得了优异的成绩,我们也不能因此讳言曹禺早期曾有过模仿的现象,毕竟曹禺最有影响力的作品是他早期的《雷雨》,而恰恰是这部剧作有模仿《群鬼》、《大雷雨》等西方名剧的痕迹。我们指出这种现象,并不等于要否定曹禺,而只是要客观地、全面地探索一个伟大的剧作家真实的创作历程,还这一作家在接受外来影响问题上的本来面目,避免文学批评上的绝对化倾向。此外,我们坦言曹禺早期的模仿现象,目的也是在理论上将“模仿”与“窃取”划分清楚,避免理论上的模糊性所带来的负面效应。
作为批评家,司马先生的意愿也许是良好的。他希望能在总体肯定的前提下对曹禺剧作及其接受影响等问题再作探索,他的确也以他独具个性的批评引起了同行的关注,他的见解我们不时可以从国内外的曹禺研究论著中见到。而且,自从他的《中国新文学史》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出版(国内一般80年代才见到),他遍布字里行间的真知灼见以及活泼多姿的批评方式,对于海内外尤其是国内当时的现代文学研究,对于当时充斥着绝对化之风的批评界都起到了一种强大的冲击作用。只是由于审美标准、文学观念等缘故,其批评中也存在偏颇之处,其对曹禺的批评正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