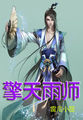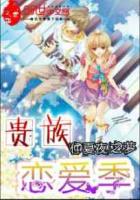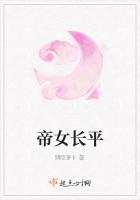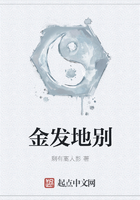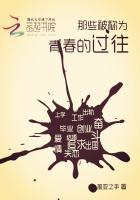(2002年1月)
四十多年前,毛主席发动“大跃进”运动,本来是想打破常规,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尽快改变我国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结果却事与愿违,经过三年紧紧张张的努力,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从总体上说我国经济建设的困难越来越大,甚至连正常的生产和人民生活都不能保证了,从1961年开始对国民经济进行了伤筋动骨的调整。我当时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参与了国民经济调整的一些工作,这一段工作中有许多值得回忆的事情。
一、国民经济调整方针的提出
国民经济调整方针是在严重的经济困难形势下提出的。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左”倾错误的日趋严重,特别是“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瞎指挥风和干部特殊化风等“五风”的泛滥,严重挫伤了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加上从1959年起我国连续三年遭受了比较严重的自然灾害,农业生产急剧减产。粮食产量1959年降到3400亿斤(当时估产5100亿斤),1960年又降到2870亿斤(当时估产3700亿斤),跌到了1951年的水平。棉花、油料、肉类生产也普遍大幅度减产。加之高估产、高征购,留给农民群众的口粮远远不够维持他们日常生活的需要。城市居民的粮食供应也异常紧张,出现了全国性的粮食恐慌和危机,许多人由于营养不良得了浮肿病,很多地方出现了饿死人的现象。工业由于大炼钢铁,致使比例关系严重失调,企业管理混乱,也陷入了越来越大的困境。
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决定从1961年开始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早在1960年6月上海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主席在讲了反“左”倾、反右倾的历史经验后,承认我们在一定程度上犯了错误,指出我国的建设路线也要随时总结经验,缩短弯路。他还提出计划少提一点,实际工作努力增加,留有余地。这都说明党中央和毛主席已经感觉到由于指标过高造成的工作被动,准备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1960年8月,李富春同志主持国家计委研究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时,提出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工作的方针应以整顿、巩固、提高为主。国务院在审议这个计划安排时,周恩来总理说:对方针的提法,与其讲整顿,不如讲调整,并建议加上“充实”二字。于是形成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9月底中央批准了国家计委的报告,实际上肯定了“八字方针”。12月中旬,周总理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对“八字方针”作了这样的解释:“‘调整’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扩大再生产;‘巩固’是为了再前进;‘充实’是为了搞好配套,使生产能力得到充分发挥。”1961年1月,党的八届九中全会正式通过了这个“八字方针”。1961年3月,毛主席在广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过去两次决定(指两次郑州会议的决定)没有认真地贯彻执行,我们吃了很大亏,我也有责任。他一再强调要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并说我们的问题是情况不明、决心不大、方法不对。他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这标志着毛主席和党中央又回过头来,继续开展被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中断了的纠“左”工作,又回到实事求是的路线上来。
二、调整就是要“退够站稳”
李富春同志受周总理委托,主持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他同薄一波同志一起“压缩空气”。当时还有一种说法是“消肿”,说我国国民经济基础较小,“大跃进”搞成了个“虚胖子”,人们形象地说是患了“浮肿病”,调整就是要“消肿”。1961年1月中央决定成立六个中央局,恢复了10人小组,把原来收上来的企业再次下放给地方,发挥各地方的作用,渡过难关。富春同志认为,根本问题是需求与供给失去平衡,供不应求。怎么办?无非是一方面扩大供给,一方面控制需求。当时,扩大供给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的家底子都折腾得差不多了,只能控制需求。
调整并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情,从提出调整到真正落实,前后经历了差不多一年时间,经历了从不愿退到退够的过程。这本身也是个调查研究、不断总结的过程。调整必须首先控制需求,控制需求首先要压缩基本建设投资规模。基建投资一压缩,社会对钢铁的需求量大大下降,钢材没有人要了。回过来不得不压缩生产,许多工业企业开工不足,生产能力不能发挥。由于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突出表现在工农业之间比例严重失调,农业和农村经济发生严重危机,所以必须调整工农业之间的比例关系,要使工业生产规模与农业生产提供的剩余产品尽可能相适应。因此,工业生产指标必须下降,退够才能调整,这是一个严峻的现实。在调整中最难的部分就是钢铁生产指标。2月1日,冶金部向周总理汇报,说煤炭供应非常困难,大高炉已经停了5座,平炉保温14座(鞍钢有5座,武钢有6座,包钢有3座)。炼钢炉停了再开动损失较小,炼铁炉停了再开动损失就大了。但是,钢铁工业必须压缩,不停炉又没有办法。
党的八届九中全会通过的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中提出,1961年钢产量指标是1900万吨,与1960年大致持平,稍有提高。当时的想法还是想在维持已有生产水平的基础上进行调整。但是,由于三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对生产力的破坏,企业管理混乱,生产设备失修,煤矿采掘比例严重失调,加上市场供应紧张,职工生产积极性严重受挫,组织生产非常困难,第一季度钢铁生产大幅度下降。当时流传着这样一个说法:“积极分子不声不响,中间分子懒气洋洋,落后分子消极抵抗。”3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曾提出1961年不搞一年计划,搞两年计划,即1961、1962年两年共生产3690万吨钢,各年分别生产1800多万吨,可见这时仍不想退。主席还提出能否搞8年计划,即1963—1970年的计划,同时提出工业要整风,要解决思想问题,大厂要设政治处,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3月28日,邓小平同志提出马上组织工业调查,他说1961—1963年这三年,主要搞填平补齐,每年钢搞1300~2000万吨就了不起。实际上后来也没有能生产那么多。
5、6月间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对确定调整的目标具有重要意义。李富春同志根据国家计委的预测提出:铁1500万吨,钢1050万吨。他说,工业指标下降是个惩罚,工业发展过快,工业战线拉得过长,城市人口增加过多,这些他都负有主要责任。毛主席插话说:好,不怕外国人骂。我们本不行,人家说行,自己也说行,不好。我们未学会,至少还要学11年。毛主席还说:认识客观世界是逐步认识、逐步深入的,没有例外,我也在内。他说:上半年把农业问题搞通、搞好,下半年搞城市问题、工业问题。他要求各省、区、市开完三级干部会后,农村工作交给二、三把手搞,第一把手集中力量搞城市工作,7月到8月中旬可以作些调查研究。中央工商务部也要下去调查研究,工业部长不要老坐在家里,一个半月后上山开会。在会议上,陈云、富春同志提出来“要退够站稳,按比例前进”。这是第一次提出“退够站稳”,过去谁敢讲“退够”!不要说“退够”,说“退”就是个问题。这时正式提出来“退够”,这就把有计划按比例提了出来。
当时大家都问什么叫“够”?富春同志回答,所谓退够就是退到满足农业和市场之后。他提出要抓三件事,第一是缩短战线,第二是要减人,第三是要搞工业若干条。5月31日,陈云同志正式提出来,要解决粮食问题,城市要减少人口。小平同志具体地讲,看起来要从城市里减少2000万人。他说:钢能搞多少搞多少,今年可能搞1400万吨。少奇同志讲,现在看起来,矛盾集中到粮食,我们的错误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少奇同志在这次会议上第一次提出这种评价。6月12日,毛主席提出三个第一:农业第一,市场第一,出口第一。他说,过去陈云同志曾经讲过,现在看起来,这三个第一是不能推翻的。各个部门要去调查研究,用调查研究的材料来教育我们的干部。
1961年究竟能搞多少万吨钢铁?这成了党中央与经济部门领导人关注的重要问题。6月15日,薄一波同志在经委党组会议上讲,能够搞到1000万吨就可以了,不要勉强了。6月27日,国家计委综合局提出要调整钢计划指标,预计1961年1000万吨,1962年1200万吨,1963年1400万吨。这一年的钢铁生产仍然很艰难,就是这些降下来的指标后来也大大压缩了。经过大量调查研究,到7、8月间国家计委估计,1961年钢产量至多能完成850万吨。中央书记处讨论工业问题时,周总理说:看起来不退够,形势稳不住,不好调整,哪有部队打仗在火线上调整的?必须撤到后方进行调整。几十年过去了,现在回想起来,对“大跃进”也要进行一分为二的分析。“大跃进”时期钢铁工业铺的许多摊子,现在有相当一部分是我们发展工业的基础。例如,当时的安阳钢铁厂、邯郸钢铁厂、济南钢铁厂等几个北方的钢铁企业,现在都是年产上百万吨钢的大中型钢铁企业。在“大跃进”时期,济南钢铁厂只能生产铁,不能生产钢。安阳钢铁厂和邯郸钢铁厂当时产量都很少,也就是年产十万吨左右钢的水平,现在这些企业都发展起来了。当然,有这样的发展是经过了后来的扩建和技术改造的。
8月23日至9月16日在庐山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主要讨论工业问题,讨论修改党中央关于工业指示的文件。在会议讨论中,小平同志说:1967年前都贯彻“八字方针”,在最近两三年内主要是调整,后几年着重在充实、巩固、提高。究竟退到哪一条线?是个很重要的问题。究竟是退到长江、淮河,还是黄河,退到庐山为止,不能再退了。工业调整是为了前进,退够是为了有利于调整,有利于前进。毛主席说:认识一致下决心调整,三年“大跃进”走了些弯路,现在认识了客观规律,就是大收获,现在到山沟了,指标退够了,该上山了。
经过讨论,党中央发了《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指示》指出:我们已经丧失了一年的时机,现在再不能犹豫了,必须当机立断,该退的坚决退下来,把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的指标降到确实可靠、留有余地的水平上。在今后三年内,必须以调整为中心,如果不下这个决心,仍坚持那些不切实际的指标,既不能上,又不愿下,我们的工业以至整个国民经济就会陷入更被动、更严重的局面。会后,经党中央批准,国家计委对计划指标作了较大的调整,基本建设投资由167亿元降为87亿元,钢产量降为850万吨,粮食产量由4100亿斤降为2700亿斤。这样,才确保了对国民经济调整的有效进行。
用现在的话讲,1961年开始的调整,不是“软着陆”,是“硬着陆”,就像天空中的飞行物,一下子撞到地面上一样。经过“大跃进”这一仗的挫折和损失,退却下来,头脑比较冷静了,这一系列的调整方针和措施才形成。
三、对弓长岭矿山和鞍山钢铁公司的调查
在毛主席倡导全党开展调查研究后,1961年从中央到地方都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毛主席认为在“大跃进”中反映和暴露出来的这些矛盾,譬如浮夸风、“共产风”等,都是没有认真地对实际进行调查研究。在九中全会上,毛主席作了自我批评,还点名批评了一些省委书记,他号召大家再回过头来到实际中去作调查研究,到群众中去作调查研究,深入基层去作调查研究,各个省市的负责同志、各个部门的负责同志也都下去作调查研究。邓小平同志在书记处会议上反复强调要进行调查研究。这一年,毛主席、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都亲自下去作调查研究。上半年重点解决了农村人民公社的体制和政策问题,下半年着重解决城市和工业问题。根据党中央和周恩来总理的部署,国务院各部委领导也开始到基层进行调查研究。
1961年下去搞调查研究非常重要。“大跃进”的三年,大家头脑发热,不能冷静地思考问题,决策脱离实际,造成了那么大的损失。我在这一年主要是受中央和国家经委委托,配合贯彻执行中央已经确定的“八字方针”进行企业调研。周总理指定我带领一批人去作矿山和鞍钢的调查研究,我和国家经委生产办公室及物资局的同志一起去作了一番调查研究。我主持起草了两个报送国务院的调查报告:一个是弓长岭矿山的调查报告,一个是鞍山钢铁公司的调查报告,报告对矿山和鞍钢以后的恢复与发展提出了建议。这一番调查研究非常重要,没有这一番调查研究,就不能够下决心进行国民经济的调整;没有这一番调查研究,也拿不出切合实际的、有效的调整国民经济的措施来。特别是经过这一番调查研究,大家认真地总结了“大跃进”的经验教训。
我于1961年4月17日至5月21日带队到辽宁省的弓长岭铁矿进行调查。对矿山进行调查,是周总理亲自布置的。当时受“大跃进”运动破坏最严重的是冶金工业,冶金工业中最关键的是矿山问题,薄一波同志找我商量,让我带一个调查组到矿山去。选择什么矿山呢?当时我们仔细地商量了一番,就选择了鞍山弓长岭矿山。
弓长岭矿山是个老矿,是主要供应鞍钢平炉富矿的基地,对于鞍钢的生产关系十分重要。那次与我一起去的调查组成员有十几个人,经委各个局都派人去了,主要是经委生产办公室的同志。那时矿山的生活供应非常困难,工作组的同志基本上吃不到青菜,一天到晚吃干菜,好一点的可以吃到点木耳、黄花,有的同志因为每天吃这种菜,脸都浮肿了。在弓长岭进行调查的时候,工作组分成了几个小组深入到整个生产过程中,选一些有代表性的车间、班组,进行深入调查。弓长岭矿山有上万工人,我们进行调查就是要总结“大跃进”的经验教训。因为类似弓长岭矿山的问题,在全国有普遍性,周总理要我们进行矿山调查就是这个意思。调查了几个矿山之后,使我们真正体会到基层干部做工作的难处,与我们坐在机关里感到的完全是两回事。我们在机关里工作还可以务点虚,他们在基层的工作全是务实的事,都有时间性,一步不到都不行。
那次调查,大家真是深入下去了。我们真实地了解了“大跃进”对矿山生产秩序和设备的破坏,以及运动之后矿山生产恢复与发展的情况。“大跃进”对矿山的影响的确是很大的,矿山不顾采掘计划,不顾采掘比例关系,造成了极大的损失和浪费。突出的问题是干群失和、设备失修、采掘失调。干群失和,就是干部群众都有怨气,上下不和;设备失修,因为弓长岭不是个露天矿,而是个井下矿,设备失修非常严重,有些已经开不起来了;采掘失调,光采不掘了,它力量有限,尽量多生产富矿,掘进没有跟上。用当时矿山职工群众的话讲是“上级压下级,干部压工人,工人压机器,机器生了气”。那次调查对我们大家印象最深的就是:违反客观规律早晚是要受到惩罚的。
那时候弓长岭矿山领导整天愁眉不展,压力相当大,虽然计划调整了,任务指标压缩了,但是要恢复矿山的正常生产,工作量仍然是相当大的。弓长岭是富矿,鞍钢的平炉靠的就是弓长岭矿山提供的矿石。其他矿山都是露天工作,工作条件和环境要好一点;弓长岭是坑采,工作条件和环境则要艰苦得多。职工的生活也比较困难,在我们的调查报告中专门附了一个对矿工家庭的调查。在我们进行矿山调查期间,矿山领导经常来找我们诉苦,几乎看不到他们有笑脸。此外,他们对我们工作组也是心存戒备呀,他们搞不清楚你来是要干什么的。因为1957年反右派,1959年反右倾,1961年你又来了,隔两年一次,你来干什么?所以矿山领导对我们是心存戒备的。通过调查,我们是更深刻地体会到了“大跃进”的教训和所造成的一些恶果,“大跃进”的负面影响非常严重。调整期间许多生产企业已经没有“大跃进”时期那种不顾一切的劲头了,人们已经冷静下来了。
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查研究,我们收获很大。回来以后,我们把弓长岭矿山的情况给薄一波同志汇报了,一波很重视,要我们马上写个报告。究竟怎么来写这个报告,大家讨论了不知多少次。有的同志问我:哪些话该说?哪些话不该说?我说:该说不该说,是实在事就得说,不说也不行,捂也捂不住。进行调查,就是了解真实情况,总得反映真实情况。5月20日,我们向经委提交了《对改进弓长岭矿山工作的意见》的调查报告。对于这份调查报告,一波很重视,并立即把这份报告送到国务院。
报告针对“大跃进”中受到严重冲击的弓长岭矿山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整顿的建议。这些建议虽然是从弓长岭矿山的实际出发而提出来的,但它对许多在“大跃进”中遭受同样冲击的企业来说,确实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我们对弓长岭矿山提出的整顿建议有七条,主要内容是:
第一,坚持中型机械化开采的方针。坚持这一方针有利设备的合理使用,除新建矿区外,都应坚持这个方针。贯彻执行这一开采方针,在全国矿山中也有普遍意义。必须改变干部中贪大图新的思想,改变在设备的配套上,搞所谓“大勺子、小碗、细脖子”(即大电铲、小矿车和土洋结合的漏斗)的不合理状态。为此,应调走“大勺子”换“小勺”,使其配套,以凿岩台车(三角架)代替穿孔机,加强各个薄弱环节(如经常铺好轨道、修好漏斗)。同时,要建立各项生产技术管理制度,加强各个环节的工作,以适应生产的需要。
第二,稳定和充实矿山基层干部,提高基层干部的政治水平和组织机械化生产的业务水平。在这次整顿中,应该特别注意稳定基层干部的工作岗位,这是建立责任制的前提。除个别需要调整的人员外,一般不宜作大的调动,使其安心工作,在工作中提高自己。职工队伍也要稳定,尤其配套工种,如机械操纵手等更要稳定,防止乱调。针对工段党政领导干部大多都是老工人或老技术出身的人员,为适应新技术,应从矿山或采区科室中抽调政治强、懂得技术、有组织能力的知识分子充实领导或担当一部分具体工作(如技术员、党委干事等),帮助老工人出身的干部提高管理水平。在提高基层干部工作水平上,有关领导机关要给予条件,其中最主要的是要少开会,开短会,开有准备的会,把工段党政干部到上面开会时间多的情况改变过来,保证基层干部有足够的时间在自己的岗位上研究和处理本企业问题,有足够的时间学政治、学业务、学技术。同时举办一些适合基层干部需要的科学技术报告会和短期学习班(一次学几天,过两三个月再学几天)。组织干部经常学习时事和政治,工段至少要有一份报纸、一份《时事手册》之类的通俗刊物。基层干部也必须坚持参加定期的体力劳动和跟班制度。对工人要大力开展技术培训工作,举办各种专业的短期训练班,帮助工人特别是老工人掌握新技术,提高操作水平。
第三,要给矿山基层党支部书记更多一点时间抓思想政治工作。在今后一两年内,矿山党组织要把组织学习党的基础知识放在一个重要地位,要有计划地举办党训班,轮训干部和党员,结合具体事例,全面地、系统地进行党的基础知识的教育。应先分批轮训基层支部书记,帮助他们学会怎样做好支部工作。要坚持党的会议制度。每个月至少有一次会议研究和分析本工段的生产形势与职工思想动态;每个党员都要做群众工作,每人至少交一两个知心朋友,及时表扬联系群众好的模范党员。
第四,进一步做好设备维护管理工作。应广泛开展爱护设备工具的群众运动,把设备的维护保养提到首要地位。要向一切不按操作规程办事的现象开展斗争,一是党员和干部要以自我批评的精神,认真检查和克服乱干、蛮干的现象。二是要建立和健全各项规章制度,认真贯彻责任制,特别是岗位责任制。三是建立和健全设备的维护与检修制度,做到有计划地检修,克服过去“不坏不修”的做法。工段必须有一定的独立维修能力,才能做好日常维护工作。
第五,认真执行规章制度。矿山的问题主要是对已有操作规程和规章制度的贯彻执行问题。矿山一些工人对其所使用的设备性能及操作规程不熟悉、不习惯。因此,干部和党员除必须模范地遵守规程,按规程指挥生产外,还必须加强对工人执行规章制度的说服教育工作,开展群众性的技术监督。在举办技术培训时,应把工人的岗位操作规程列为主要课题,并经常按照操作规程测定岗位工人的操作水平。
第六,适当解决工人的升级问题。对于那些经过考试或评比,技术水平确实已经提高的,要适当给以晋级。奖金的分配要克服平均主义的现象,奖励条件要具体,经济指标要全面,使奖励制度起到促进生产的积极作用。对工人中提拔的干部,原则上应根据他们从事管理工作后的思想和工作表现,按照干部的工资标准进行适当调整。
第七,进一步安排职工生活。在矿山,首先要加强对集体宿舍的管理,改善单身工人的居住条件,火炕要热,要减少室内潮湿,要增添报纸、杂志和必要的文娱用品(如扑克、象棋、乒乓球等)。食堂管理工作也要进一步改善,必须保证给足分量,热饭热菜,减少排队,改进服务态度,提高饭菜质量。对矿区副食品和日用品供应,要加以改进,商业部门应增设商业供应点,增加适合矿区用的商品,有些凭票供应的商品(如呢绒制品、自行车、手表等),可以组织就地凭票供应。同时要增设一般服务修理行业,如修鞋、缝补衣服、拆洗被服以及其他修理业等。搞好卫生,增强工人身心健康,要主要抓好公共食堂和宿舍的卫生,职工居住区,必须增设厕所,改善环境卫生。同时也要增添必要的文娱活动场所,如电影院、篮球场等,以活跃职工的业余生活。从矿山的条件看,实现上述要求并不是很困难的,但做好了这些工作,对工人的生产积极性会有很大的促进。
这些建议有些虽然十分具体,但是对矿山整顿,恢复和发展生产起了很大的作用。
这一年7月21日至8月28日,我又带领同一个工作组到鞍钢进行调查。由于有了弓长岭调查的经验,鞍钢调查就进行得比较顺利。所以,很快就把资料整理出来,找出来它存在的主要矛盾,加以分析,提出建议。鞍钢是“大跃进”中的重灾户啊,由于高指标的压力,鞍钢被迫走上了“大风高温、多装快炼”的不顾实际可能的路子。高炉出铁质量不好,平炉炼钢时间又要缩短,难度相当大。那个时候炼钢厂的厂长就对我讲这样干不行!当时平炉装铁水,装到什么样程度呢?装到风口了,就是往里面喷吹煤气的喷吹口。炉门都得拿耐火材料给它堵上,就是拿镁砂一层一层把它堵上,把这个炉门坎给堵得很高。门很小,门下边堵得很高,尽量让它多装铁水。炼钢非常困难,不光多装,还要快炼,还要缩短时间。鞍钢的损失相当巨大,就像打了一场烂仗一样,我们到鞍钢时,它还处于在那儿打扫战场的过程中。
所以,我们这时到鞍钢调查,看到的情况的确令我们伤心,车间里生产秩序还没有完全恢复。在“大跃进”中,鞍钢把所有的规章制度都给烧掉了。1958年底,中央工业工作部部长李雪峰得到一个报告,说鞍钢正在破掉规章制度,把规章制度都给烧了。李雪峰马上告诉王鹤寿,王鹤寿同志就派我立即去鞍钢制止这种做法,我赶到之前,辽宁省委书记处书记喻屏同志已经赶去纠正了这个错误。当时有个技术人员桌子里边还藏了一本规章制度没烧,有人揭发他,他也只好交出来。最可气的就是,因为把操作规程都给烧了,大石桥镁矿厂配烧镁砂的炉子要开炉却开不起来,因为不知道该怎么开。所以在逐步恢复规章制度时,大家还不放心呢,不知道什么时候你又来批我了。企业生产要有个规障制度,可是又不敢公开拿出来这个规章制度执行,这对我们来说确实是上了深刻的一课。
在鞍钢调查期间,接触面要比弓长岭矿山广一些,我们分成几个组深入下去“解剖麻雀”。鞍钢是个庞然大物,解剖它也不那么容易。鞍钢的运输十分复杂,密如蛛网,经常发生事故,不是汽车把木头栏杆撞断了,就是汽车撞上火车了,鞍钢当时运输的混乱状况就到了这种程度。这两次调查研究,对我们当时国家经委和物资总局的同志来说是非常必要的。调查结束后,我们写出了关于鞍钢的调查报告,总结出鞍钢在生产上存在的四条短腿,即辅助部门制约着鞍钢生产的发展。这四条短腿,一是矿山,二是耐火材料焦化等辅助部门,三是机械维修,四是运输包括厂内运输。这些短腿严重阻碍着鞍钢的生产和发展,也是鞍钢进行整顿的主要工作内容,因此,我们在调查报告中提出了鞍钢整顿的“填平补齐”方案。
对于“大跃进”造成的损失,人们的说法不一,我看按当时价格算有几百亿元。还有几千万人上山,劳动力的损失有多大啊!
四、继续进行调整的决策
1962年1月17日到2月7日,在北京召开了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七千人大会”是国民经济调整的一个动员大会,目的就是要统一思想。刘少奇同志在会议上的工作报告,根据毛主席的意见事先发给大家进行讨论。在讨论少奇同志这个报告的时候,大家几乎没有提什么不同意见。少奇同志在会议上作报告的时候,离开他已准备好的稿子,提出来“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个讲话使与会同志深有感触。在“大跃进”中农村盛行的浮夸风,确实到了让人难以置信的程度。例如,报纸上登出来天津小站稻田里边密密匝匝稻子想歪都歪不下来,一个小孩坐在稻子上边,这实在是令人难以置信的。1959年庐山会议后再一次开始反右倾,又来了个“左”倾思想抬头,这在政治上对大家影响很大,好多省都挖出所谓“反党集团”,这样一来就没有人敢讲不同意见了,这在政治上损失太大。所以,农村中“共产风”、浮夸风等“五风”愈演愈烈;工厂里、机关里也反右倾,国家经委受到了批判。这时对敢说话的人、对不同意见施加了政治压力,造成了极坏的恶果。从那以后,听不到不同声音了。“七千人大会”改变了这种空气。我们国家经委的几个负责同志参加了工业部门组的讨论,工业部门在“大跃进”中教训最深刻,所以对刘少奇同志的报告表示完全赞成。这一次会议和过去的会议不同,过去开会是先报告、后讨论,这次会议是先讨论、后报告。参加这次会议时,我们大家都感觉心情舒畅,就是毛主席讲的“白天出气,晚上不看戏”。
2月19日、3月16日、3月17日,彭真同志主持召开了三次矿山工作汇报会,就是抓调整,抓落实。2月22、23日,少奇同志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是在西楼会议室召开的,后来被叫成“西楼会议”。我参加了这次会议,并作了详细的记录。在这次会议上,少奇、小平、陈云、富春、彭真、先念同志都讲了话,他们都是敞开讲的,讲得很好,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少奇同志在这次会议上指出,我们现在处在“非常时期”,国民经济到了这么样的程度,在国外总统就要宣布废除宪法所赋予的权利。他建议恢复中央财经小组,由陈云同志主持财经小组的工作,先念、富春同志帮助陈云同志,把薛暮桥同志调回来做财经小组的秘书长。2月26日,陈云、富春、先念同志在怀仁堂召开各部门党组成员参加的国务院扩大会议,传达西楼会议精神,主要是陈云同志讲,富春、先念同志也讲了话。陈云同志作了《关于目前财政经济的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的讲话,陈云同志的讲话影响是比较大的,他分析了当时的经济形势,指出经济困难的主要表现:一是农业在近几年有很大的减产,要恢复过来,大约需要三年到五年的时间。工作的基点应该是争取快,准备慢。二是已经摆开的基本建设规模,超过了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性,同工农业生产水平不相适应,不仅农业负担不了,工业也负担不了。陈云同志提出了六条措施:一是把今后十年经济规划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恢复阶段,后一阶段是发展阶段,恢复阶段照少奇的说法类似非常时期,要有更多的集中统一,一切步骤要稳扎稳打;二是减少城市人口,“精兵简政”,这是克服困难的一项根本性措施;三是采取一切办法制止通货膨胀;四是尽力保证城市居民的最低生活需要;五是把一切可能的力量用于农业增产;六是计划机关的主要注意力,应转移到农业增产和制止通货膨胀方面来。3月12、13日,在西楼又开了一次会议。少奇同志在会议上讲,今后十年分成两段,前一段调整,后一段发展,争取快,准备慢。后来给毛主席汇报,主席同意少奇的意见,稍作修改,提出调整以恢复为主,这就更明确了。
国民经济调整从根本上讲,就是缩短战线。主要表现在这三个方面:第一个是生产指标要下来,第二个是基本建设战线要缩短,第三个是要减人。此外,就是整顿生产和经济秩序,包括整顿企业管理、搞“工业70条”,使管理制度化、规范化。
5月7—11日,中央召开工作会议,总结经验教训。据当时统计,1961年的农业生产比1957年下降了26%,农业水平实际只相当于1951年的水平。虽然重工业有很大发展,可是没有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大办钢铁时,光炼铁点就搞了1300个,力量分散,没有形成一个拳头。毛主席讲,在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就是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取得了战争的胜利。我们国民经济的发展,特别是重工业的发展,这么一个“大仗”,我们没有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很典型的是1300个炼铁点一起上马,结果像武钢、包钢这样的重点单位、重点项目,该快的反而慢了。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正式决定城市减少职工2000万人,就是2000万人下乡。陈云同志提出开设高级馆子,给市民供应2两豆子和尼龙袜子。5月18日,在西楼开会专门讨论物价问题,针对物价上涨较快,提出关键是控制自由市场的价格,但实际上是控制不住的。因为我们的主渠道没有东西,允许开放自由市场,但价格又不能不控制。5月19日到6月5日,中央财经小组连续召开会议,讨论采取措施来扭转国民经济的被动局面。生活在今天的人们对那时我国的困难局面是难以想象的。陈云同志为了保护干部,给干部补助一些副食品,司局长以上干部每月2斤肉、2斤鸡蛋、1斤白糖,一般干部每月1斤白糖、每天2两豆子,被叫作“肉蛋干部”、“糖豆干部”。可见陈云同志保护干部用心之苦啊!
8月3—24日,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我参加了这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形势发展了变化,开始批判邓子恢同志。邓老主张在农村搞承包,毛主席则反对在农村搞承包制,主席在会上讲形势、矛盾、阶级斗争三个问题。我进会场看到,邓老的脸色煞白,一句话也不说,他这个人原来是谈笑风生的。陈云同志当时对农业的形势估计得比较严重,所以北戴河会议上,主席批邓老,里边就有这么几句话:有些人对农村形势估计得那么严重,实际是不是那么回事?那是指陈云同志。陈云、一波同志身体不好,住在北戴河休息,谷牧同志和我去看望他们,给他们汇报了会议的情况,讲主席批邓老了,他们都没有表态。薄一波同志给中办打电话说他可以参加会议,陈云同志一直没有参加会议。
8月27日—9月4日国家经委召开经委主任会议,传达北戴河会议精神。10月22日,少奇同志在西楼召开会议,会议提出要提高技术水平和技术装备水平,少奇说,能不能考虑从日本买一些关键的技术装备、关键的技术。后来,为落实这一精神,从奥地利进口了吹氧炼钢的技术。
五、进一步整顿和加强企业管理
“大跃进”时期的“左”倾错误,在宏观上造成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在微观上破坏了企业的正常生产秩序。企业管理混乱,生产指挥系统失灵。在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中,国家一方面从宏观上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同时在微观上也进一步对企业进行整顿,加强企业管理。在整顿企业和加强企业管理方面,国家经委做了许多工作,主要是抓了以下四项工作:
第一项工作,制定和贯彻执行《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即“工业70条”)。“工业70条”是在总结了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和“大跃进”时期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制定的,它是在薄一波同志亲自领导下,由国家经委副主任饶斌同志具体负责和协助拟定的。参加起草工作的还有马洪、梅行、廖季立、董峰、张沛、赵荫华等同志。“工业70条”是深入调查研究、反复讨论的产物。早在1960年底,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就开始组织一些同志下厂调查。毛主席提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以后,又组织调查组分头下厂进行企业调整。饶斌同志曾到东北,深入工厂调查研究,跟同志们一起讨论。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薄一波同志于1961年6月亲自带领一个起草文件的班子到沈阳,边调查、边讨论、边起草。我当时正在沈阳调查,也参加了这次讨论。在沈阳起草了企业管理工作条例的草稿。然后,薄一波同志带着写出的草稿,赴哈尔滨、长春等地征求地方和企业的意见,经过多次修改,最终形成《国营工业企业管理工作条例(草案)》。8月,在邓小平同志主持下,中央书记处在北戴河连续举行四天会议,逐条进行讨论、修改,最后将文件定为70条。后来又经过在庐山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讨论、修改。9月17日,毛主席和周总理审阅时,不约而同地将《条例》题目中“管理”二字删掉了,最后定名为《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工业70条”是我国第一部关于国营工业企业管理的章程,成为整个调整时期整顿工业企业、加强企业管理的一个重要文件。
“工业70条”的贯彻执行过程,采取面上普遍传达,能改的马上改;点上分批试行,一个企业一个企业地进行整顿的方式。“工业70条”受到广大职工的欢迎,到1962年第一季度检查时,第一批试点的3000个工业企业都在不同程度上理顺了企业内部的关系,企业管理都有所加强和改善,生产也逐步好转。由于工业调整与企业整顿同时进行,到1965年,“大跃进”中受到破坏的国营工业企业大部分都恢复了元气,各项工作都有很大进步。如果按“工业70条”的路子走下去,工业企业管理肯定会打下良好的基础。可惜的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它被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诬蔑为“复辟资本主义的黑纲领”,中断了这个良好的开端与发展势头。
第二项工作,试办托拉斯,以经济方法管理经济。在“一五”计划建设过程中,当发现由中央各部集中管理的体制统得过死,不利于发挥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时,党中央和毛主席从1956年就开始考虑改进我国经济管理体制。1958年4月,党中央和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工业企业下放的几项规定》,除了一些主要的、特殊的以及“试验田”性质的企业仍由中央继续管理以外,其余企业原则上一律下放,归地方管理。但是,由于在实施中采取“一阵风”的做法,企业下放过快过猛,加上“大跃进”运动,打乱了企业之间原有的生产协作关系,各地方大上基本建设项目,大量增加在职职工人数,平调国营企业的设备、材料等,计划调给中央的物资调不上来,导致计划失控,工业生产秩序混乱。面对出现的混乱局面,1959年3月又将大中型企业收上来归中央管理。这就是:一放就乱,一乱就收。这样收收放放,放放收收,都没有解决条块分割、协作很差的问题。其原因主要是不论是集中管理还是分散管理,都是采用行政管理方法,而不是经济方法。
因此,60年代初,毛主席、刘少奇、周总理和邓小平同志已开始考虑借鉴西方工业发达国家管理企业的方法,即组织托拉斯。毛主席说,我们工业建设可以走托拉斯的道路,托拉斯是工业发达国家找到的比较进步的组织管理形式。1963年我国经济形势明显好转后,党中央和毛主席就决定对工业管理体制进行改革,设想逐步减少行政管理办法,增加经济管理办法,在工业、交通部门组织专业公司,试办托拉斯。1963年10月,当薄一波同志向中央汇报工业工作问题时,刘少奇同志说:“体制问题要好好研究。资本主义管理企业的经验,特别是搞垄断企业的经验要学习。”“托拉斯、辛迪加、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等等,列宁不是早就讲过了吗?如何管理好企业,无非是有组织、有计划、避免和减少官僚主义。组织企业性质的公司管,可能比行政机构管得好一些,官僚主义可能少一点。考虑把各部的管理局改成公司,不是行政机关,而是经济组织,这样可以进一步接近生产,接近企业。”这说明,当时中央领导已在考虑用经济办法代替行政办法。
试办托拉斯是国家经委承担的一件大事。在薄一波同志领导下,试办托拉斯工作由国家经委副主任饶斌同志、经委委员吴亮平同志具体负责。他们首先组织工作组进行调查研究,然后会同工业、交通各部研究试办托拉斯的具体方案。国家经委于1964年6月拟出《关于试办工业、交通托拉斯的意见报告》,提交中央书记处讨论。党中央、国务院于8月批转各中央局、省、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和国务院各部委党组参照执行。
推行托拉斯试点,第一批在全国共试办了12个托拉斯。其中,全国性的托拉斯有9个,它们是烟草公司、医药公司、地质机械仪器公司、盐业公司、汽车公司、橡胶公司、拖拉机内燃机配件公司、纺织机械公司、制铝工业公司;地方性的托拉斯有3个,它们是华东煤炭工业公司、京津唐电力公司、长江航运公司。试办托拉斯是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探索。从试办情况看,虽然时间很短,都收到一定好的效果,当然也出现了一些矛盾。但是,如果坚持试验下去,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不断改进,也许可以逐步走出一条用经济办法管理经济的路子来。可惜的是“文化大革命”破坏了这一重要探索。
第三项工作,抓机械工业专业化协作。这是国家经委副主任叶林同志负责的。“一五”时期和“大跃进”时期搞了许多“大而全”、“小而全”的企业。本来在一个城市建设一个铸造中心,就可以满足一大批机械工厂的需要。可是由于条块分割,每个机械厂都要建一个铸造车间,造成重复建设,浪费了机器设备,浪费了人力和财力。国家经委抓这项工作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第四项工作,抓增加品种,提高质量。早在1958年12月武昌会议时,毛主席就讲:铁要好铁,钢要好钢。1960年6月上海会议时,毛主席明确提出生产、基建都要把质量放在第一位。1960年11月,还专门召开了特殊钢会议,讨论以合金钢为中心的优质钢及八大品种的安排。但在“大跃进”时期,由于钢铁指标过高,为完成产量计划疲于奔命,品种、质量问题始终没有解决。进入调整时期后,数量指标降下来了,国家经委狠狠地抓了几年增加品质、提高质量的工作。
在调整时期,国家经委还抓了其他许多工作,如贯彻执行“鞍钢宪法”、学习解放军政治工作经验、工业学大庆等。特别是经过前两年的调整,到1963年就想做点建设性的工作。国家经委就研究决定筹备召开三个会议:一是政治工作会议,抓思想;一是经济工作会议,抓效益;一是技术工作会议,抓技术水平的提高。三个会议都经过长时间的准备,这三个会议不仅开得适时,而且确实有效果。国家经委这时召开三个会议,是在“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基础上,想进一步总结经验,在这个基础上要发展了。
5月召开技术工作会议,会议是我主持的。会议讨论了如何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赶上世界60年代的先进技术水平和有关的技术政策问题;讨论了如何加强技术责任制,开展技术革新、技术革命的群众运动,增加产品品种和提高产品质量,培养技术力量等问题。那个时候技术问题一开始还没为大家所重视,人们主要是谈经济问题,所以技术会议的影响不算大。当时只有一条,就是企业要进行技术改造,为此国家经委专门成立了技术推广局,目的就是提高大家对技术工作的认识。我们在“大跃进”期间建立起来的一批工业企业,都需要进行技术改造。在技术工作会议上,李富春、聂荣臻同志讲了话,薄一波同志作了总结讲话,各个省、市主管技术的经委副主任都参加了。会议形成了《国家经委关于进一步开展群众性技术革新运动的几点意见》。
6月召开经济工作会议,会议是宋养初同志主持。对经济工作会议大家都比较重视,因为“大跃进”对经济造成这么大损失,要医治“大跃进”的创伤,应该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我们发展国民经济,要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勤俭节约还是我们的传家宝。大家都非常欣赏潞安矿务局石硌节矿勤俭办企业的精神。会上表彰了六个企业,包括兰州炼油厂、长治潞安矿石硌节矿、襄樊纺织厂等。会议期间,周总理亲自接见了先进企业的代表。这个会议影响比较大。
政治工作会议是在这年底举行的,目的就是想总结“大跃进”时期的经验教训。林彪提出来突出政治,会议对突出政治讨论十分热烈,关于突出政治落实到哪儿,大家在讨论中意见就不一致了,你说你的,我说我的,薄一波同志只有把邓小平同志请到会议上来。邓小平讲了一句话:突出政治,落实在三大革命运动上。三大革命运动包括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小平同志的这个回答十分巧妙,突出政治既包括阶级斗争,也包括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给与会同志留下很深印象。
经过几年的艰苦整顿,在宏观经济方面压缩需求,控制总量平衡;在微观经济方面,进行企业整顿,加强企业管理。同时随着农村形势的好转,工业生产也逐渐走上了稳定发展的道路。1961年产钢870.3万吨,1962年产钢667.2万吨,1963年产钢761.9万吨,1964年产钢964.3万吨,1965年产钢1233万吨,1966年产钢1532.4万吨。到1965年、1966年,钢铁生产各项技术经济指标大多数已恢复到历史最好水平,有的还超过了历史最好水平。其他主要工农业产品的产量也达到和超过历史最好水平。如果不是十年“文革”动乱的破坏,我国整个工业、包括钢铁工业会稳步发展,我们的工业基础就大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