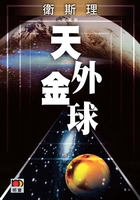因了那棵大树的掩护,六叔和五叔他们的阵地始终没有失陷。而栖宿在树上的迷生和那只大鸟却没有能逃过这场劫难。那一天,当第一排子弹呼啸着向大树飞来时,树上的那些鸟雀便惊叫着张开它们的翅膀向大河的那面飞去了。和迷生相依为伴的那只大鸟先时也是飞走了的,飞走了却又不肯远去,只是在河上来来回回地徘徊着,凄凄艾艾地鸣叫着,那声音分明是一种急切的呼唤,可迷生没有翅膀,又怎能和它一同离开那片灾难之地呢。
那时刻,六叔感觉到有一种奇异的水滴从树上落下来,就洒落在他的脖子里,那水滴热热的粘粘的,还有一股新鲜的腥味儿。六叔用手抹了一把看时,竟是一手的血,鲜红的血。六叔愣住了,抬头往树上看时,就看到了那只巨大的鸟巢,那血就是从那鸟巢里洒落下来的。六叔想到了他的那个迷生儿子,就由不得站起了身子,这时一颗子弹从远处飞来,击中了他的头部,只见他痛彻心髓地大叫一声,便栽倒在地再也没有起来。
我的那位迷生堂弟终于死了,他是带着一个谜而来的,又带着一个谜而去了。从此,大河沿是再也没有一天安宁的日子了。
13.迷失了自己生存历史的人们
我们村子旁边的那座山名叫香山。香山也算是一座大山,连绵数百里不绝。据说八百年前这里森林茂密,水草丰美,自然环境十分地好。后来由于蒙古大军追剿逃亡的西夏遗民,放火烧山,使得这片土地最终成了一片赤白之地。如今的香山是很少有树了,有的地方甚至连草都不长,果真是一个苦焦的地方了。
八百年前的那场战争是罕见的,战争之后,在长达数十年的斩草除根的屠杀中,一个有着八十万平方公里辽阔疆域的王国,一个有着近百万人口的民族,在那场战争之后,终于在历史上消失了,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以致于让后来的研究家们费尽了心思,也没有能够找到这个民族劫后余生的蛛丝马迹。这个曾经强盛一时的民族连同这个民族所创立的辉煌的文化,是彻底的被掩埋到了历史的深处去了。现如今,当人们站在那一座座被称为东方金字塔的西夏王陵的废墟前时,面对着那片虽历经风雨而风貌尚存的神秘丘陵,无不扼腕叹息。
我是在游览西夏王陵时认识范教授的,那时我正在省城的一家报社当记者,算起来,我离开大河沿已经有十几个年头了。
范教授是研究西夏史的专家,也是国内唯一的一位能破译西夏文字的人。我和范教授很投缘,在那样的一个时间,在那样的一个地方,我们相遇了,不知道这是一种偶然呢还是一种必然。我们一见如故,尽管那时的范教授已近花甲,而我则刚过而立之年,按年龄来说我们是两代人呢,但这种年龄的差异并没有影响我们友谊的交往。
在范教授的家里,我看到了这老头儿新近所著的一部书稿,在这本书里,我也是第一次看到了手书的西夏文字。那一时,我是吃惊地跳了起来的,我发现范教授所书写的这些西夏文字,竟然和我的那位迷生堂弟所画出的咒符般的东西是一样的啊。于是,我向范教授讲了我的家乡大河沿以及迷生的许多怪诞的故事。
这老头儿,在听了有关迷生的故事以后,竟然惊愕得半天没有喘过气来,他用一双金鱼般的眼睛直瞪瞪地盯着我,那稀疏宽阔的脑门儿上沁出了一层细微的汗珠。他几乎是呓语般地说,这是不可能的,这是不可能的一个刚入世的儿童,怎么就会书写西夏文字的呢,你要知道,西夏文字的结构及书写,比汉文字要难得多啊。怪事,这真是一件天大的怪事。如果说那孩子所书写的是西夏文字的话,那他所说的那些奇怪的语言也应该是西夏语了。要知道这是失传了八百多年的语言文字啊!
范教授的话猛然提醒了我,让我又一次想起我的那位迷生堂弟活着时的许多怪异之处,动物学里有一种返祖现象,如果能用返祖现象来解释迷生的话,那么迷生的降生和我们世代生活的大河沿以及我们的家族是否有着一种必然的联系呢。我记得小时候听我大伯说过,无论是上河沿还是下河沿,都不应该闹是非的,因为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祖地的啊。我问大伯说,我们的祖地在哪里呢?大伯摇了摇头说,时间久了,他也不知道了并不是大伯不知道,而实际情况是,我们的祖宗在长时期的生存历史中给他们的后代所传授的是土地稼穑庄户牛羊,是那条千古不息的大河,却有意地把一个民族的历史给隐去了。
范教授对我们的大河沿和迷生的故事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他想让我陪同他到大河沿走一趟,他要到大河沿去做一番实地考察,老头儿想通过这次考察,企图为他的研究成果再添上神奇的一笔。我知道老头儿的心事就愉快地答应了他。我已经有多年没有回大河沿了,也正想回去看一看呢那里毕竟是我的生身之地啊,在那片美丽神秘的河谷里,有我的根呢。 14.重回大河沿
我们是在傍晚时分到达县城的,下了汽车,来迎接我们的是建社。建社是我们大河沿最有出息的人,他现在是我们这个县的县长了,事业干得呼隆隆地响哩。
建社把我们安排在他的县政府招待所里,并设了晚宴为我们接风,席间他说他明天要陪同我们一起回大河沿的。我跟他开玩笑地说,你现在是一县之长,身子重哩,怕不敢劳你的大驾吧?
建社也笑了,说,你们一个是著名专家,一个是省报记者,都是金身贵体,我又怎么敢怠慢得了嘛。
第二天一大早,建社果真就带了一辆崭新的切诺基来了,这种车的越野性能极好,人坐在里面多感舒适。我想这种车大概就是专门为建社他们这一类的县官们打造的,以便让他们在下乡视察民情时不至于太辛苦。
汽车在一条简易公路上颠簸了三个多小时,在临近中午的时候,便进入了大夏河谷,迎面扑来的风带着很浓的水汽,似乎有一种腥甜的味儿。我闻得出,这正是我那久违了的大夏河的气息啊。
沿河的一侧是壁立的悬崖,在悬崖与河水之间有一条路,路不宽,刚能过得一辆车去。在我的记忆里,这条路原本是没有这么高也没有这么宽的,还是一条过水路呢。所谓过水路,就是说这条路常是在水中隐着的,天旱的时候,河水落下去,路就显现了出来。夏天里雨水一多,河水涨起来,就把路面全淹过了。河水再大些时,就使得大河沿与外界完全断绝了联系,从而使得山外面的人,把大河沿看得越发神秘起来。
我问坐在前排座上的建社,这条路是不是你利用县长的职权重修过的?建社则回过头来说,这是灵生的功劳,咱这位小兄弟眼下是大河沿的村长,前年冬天,他领着大河沿的父老乡亲苦干了一个冬天,这山崖被他们炸掉了一层皮,人也都累脱了一层皮,这才把这条路修得像个样了。要不然的话,咱们今天还得坐毛驴车回去。
我们回到大河沿的时候村人们正在吃中饭,听到汽车声,他们都从屋里跑出来,他们有的手里拿了馍馍有的手里端了饭碗,一面吃着一边说着围过来看热闹,尤其是那些孩子们,看到汽车就像看到什么稀罕动物一样叽叽喳喳叫个不停。
在那群村人里面,数我们这个家族里的人显得最为活跃,那一种自豪与喜悦是不言而喻的。毕竟在大河沿千百户人家里,也只有我们这个家族的人才出了两个为官家做事的人啊。
灵生以村长和亲族的身份接待了我们,这个年轻剽悍的汉子,多年不见,他出落得高大魁梧,方脸隆鼻,长鬓阔眉,从敞开的胸襟那儿,微微露出些黑中泛黄的锦毛,这是典型的大河沿成熟男人的标志。
我向范教授介绍说,这是我的堂弟灵生,就是迷生的兄弟。那一时范教授就瞪大了眼睛,当他和灵生握手的时候,终又发现灵生的手指根处也是生有一层细毛的。老头儿惊奇不已,似乎真的就从眼前的这个人的身上看到了那个消失了多年的迷生的形象,从而也看到了一个消亡了的民族的影子。
这一顿饭自然是在灵生家吃的,吃饭的时候,我们这个家族的人都来了,就是四叔没来,自从那次武斗以后,四叔已多年不和家族其他人来往了。亲人团聚,那欢天喜地的情景自不必细述了。饭后,建社说他明天还要到地区开一个会的,所以必须在今天赶回县里。族人们都知道建社是官家身子,自然是由不得自己的,也就不便于再说什么了。建社临走的时候丢下话说,三天后他再来接我们回去。他还再三叮嘱我和灵生,一定要照顾好范教授,如果范教授此次考察成功的话,那对我们大河沿将是一个大贡献哩。
15.为大河沿人假想一个历史故事。
我们在大河沿待了三天,范教授的考察却没有取得多大的进展。首先是生活在大河沿这地方的人既没有出生入世的家谱,也没有一个族谱,甚至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他们的祖先是谁。五代以上的事,因没有文字记录便说不出来了。
范教授走访了大河沿一带所有上了年纪的老人,这其中就包括了我的大伯和二伯,当然还有上河沿的阴天士。只见他们瞪着一双双昏花的老眼望着大夏河对面的那一望无际的大漠以及和大漠连成一体的昏黄的天际,呓语般地说,不知道了,族上没有传下来,我们是不知道的。
对于这样的采访,范教授深感失望,但他又从这些生性淳朴爽直彪悍的大河沿人的身上,似乎探摸到了一种隐含在他们心灵深处的一种深层次的东西。老头儿一连声地叹息着说,这是一群迷失了自己生存历史的人啊。
接下来范教授就开始搜寻有关迷生的事,可整个大河沿人所提供的故事加起来也没有我向老头儿讲说的更确切更详细的了。对于迷生,我的故事是最有权威性的,连灵生都不行,灵生那时还小,不大记事的。灵生所能记得的唯一的一件事就是他曾经被迷生弄到那棵大树上去,在那只奇妙的鸟巢里呆了大半天的时间。因为迷生是偷着把灵生弄到树上去的,六叔和六婶并不知道,村人们也不知道。灵生的失踪惊动了整个大河沿,人们或上山或下河地到处寻找起来。正当大河沿被折腾得沸沸扬扬的时候,不知道啥时候,迷生又把灵生送回家去了。
现在回忆起那件事来,灵生便动了感情地说,他的那位哥哥把他弄到树上去,绝不是一种恶作剧,而完全是他的哥哥很喜欢他的缘故。那一天,小哥俩在那个鸟巢里玩得愉快极了,许多鸟儿在他们的头顶上跳跃着鸣叫着,鸟儿的叫声很好听。竟有一只胆大的鸟儿飞进他们的窝里来,用一只黄黄的小嘴啄弄着灵生的头发,就啄出了小哥俩的一串串愉快的笑声。后来的事就可想而知了,先是六叔拿了斧子吼着要砍掉那棵大树,树没有砍成,打那以后他就再也不许迷生接近灵生了。连自己的亲兄弟都不能再一起玩了,迷生便愈加感到孤独起来。
范教授问灵生说,你见过你的那位哥哥写过的那种奇妙的文字了吗?灵生回答说是见过的。范教授又问灵生,现在还能找到那些文字吗?灵生说找不到了。
自从迷生在那次枪战中被打死之后,紧接着大夏河发了一次大水,河水漫过堤,把大河沿淹成了一片水泽。水灾过后,大河沿的房屋基本上全毁了,眼前的这些房屋都是大水过后重新盖起来的。或许是一种天意,让那场灾难把一个秘密永远地封存起来了,以至于连一点儿痕迹也没有留下。
三十年过去了,大河沿的变化是巨大的。大河沿之所以没有被那场大水冲走,大河沿的人自然是相信了那块镇基石的巨大作用的。我大伯曾说大河沿是一只大船,而这只船就是拴在那尊石柱上的,只要那石柱不倒大河沿就永远也不会消失的。
在大河沿的最后一天,我和范教授爬到香山顶上去了,站在山上俯瞰大河沿,这时我才惊奇地发现,这片依山傍水绿色葱茏的土地,果真就像一条大船了呢。而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大夏河从远方汹涌而来,在这里拐了一个大弯儿,它用一种神秘的力量,不断地冲刷着河那边的堤岸,而把对岸的土又不停地悄无声息地搬运到了我们大河沿这边来,从而使我们大河沿的土地竟能像神话里的那片熙攘一样不停地生长扩大。尽管大河沿在许多年里人口不断地增多,而大河沿的人从来也没有因土地发愁过。大河沿的人都知道,大夏河会给我们送土地来的。
这时正是农历四月,田里的麦子正在抽穗,是那绿油油的一片。田边地头上的豌豆花儿星星点点地开着,河边上的那两架老水车正吱吱哑哑地转动着,把河水从河里车上来,当那清凉凉的河水流向土地的时候,那一串串欢快的笑声,让人愉悦极了。
望着大河沿这片肥沃美丽的土地,范教授一连声地赞叹了它的神奇美妙。老头儿灵感所至,竟然就构思了一篇石破天惊的故事,一向治学严谨的他,竟以虚构假想的手法,揭示出了大河沿的一个千古之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