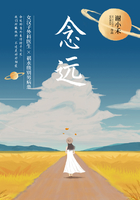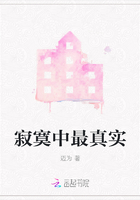王璞
我哒哒的马蹄是个美丽的错误
我不是归人,是个过客
——郑愁予
1989年7月18日,我提着一个人造革小包,包里装着我的香港出生纸,从深圳罗湖过关,移居香港。我年近不惑,不但家庭崩离,事业无成,还欠债四千。不过,小包里装着我刚写好的两篇小说,另外还有朋友铁夫给我的一个香港电话号码。他说这位杨先生曾将他两篇小说发到了港台刊物,
也许有在香港投稿的途径,你可去找找他。
杨先生是新移民,70年代末从福建移民香港,在老家他是中学语文教师。香港不承认内地学历和内地教师资格,所以他来港后一直在工厂打工。业余时间他依然关注文学。尤为奇特的是,他自己虽不写作,但热切关心大陆港台三地的文学杂志和三地作家作品的沟通。铁夫的小说就是他在内地一本杂志上看到的。因喜欢,便自告奋勇,将那篇小说投到香港一家杂志发表。与铁夫联系上之后,又将其另一篇小说寄去台湾一份报纸发表了。所以我到了香港,第一件事就是找到杨先生家,把我那两篇小说拿给他看。
那天的场景历历如在眼前:我坐在杨先生那间位于香港北角的斗室,屋子里很暗,白天也得开灯,我和这位刚结识的文学发烧友对坐在一张小方桌旁,他生就一副笑弥勒似的慈眉善目,开口便带三分笑,令有社交恐惧症的我,冒昧上门的忐忑之感顿消。杨先生一听我说明来意,二话不说,戴上副老花眼镜便凑到台灯下看我的小说,我则宾至如归般安坐在他对面,浏览着茶几上的书报杂志,默默等待。
“写得不错。”他终于抬起头来,对我道,“我给你拿去《明报月刊》发表吧。”
听上去就好像他是《明报月刊》老板似的,其实他与该刊的关系也就是他家住在其编辑部所在大厦的附近而已。不过他的“拿去”倒真的是立即落实。当下他就将那两篇稿装入一个信封,收信人处写上“编辑先生收”,寄信人处写上他自己的家庭住址和姓名,拿上它走到对面那座大厦,请传达室阿伯交给《明报月刊》的编辑先生。
大约一星期后,我接到杨先生的电话,“《明报月刊》一位黄编辑来电话了,说这期先发那篇《过客》,另外一篇留用。”
“哦,谢谢你!”我道。口气与杨先生无独有偶,如此的平静淡定,好像我早已是名作家,在任何报刊发表作品皆乃寻常事耳。而事实却是,我直到今天也还是默默无闻的一名作者,往很多报刊投稿仍只能写“编辑先生收”。在当时,更属无名小卒,发表的作品总共不到二十篇,还得把那些报屁股文章也算上。
《过客》在我的小说中从来没人注意,但我私心总对它有一份特别的情感,大约因为它是我在香港发表的第一篇小说,而它前面的那句题诗,好像是我与香港这个城市之间关系的写照。还有,那笔五百二十元的稿费,是我在香港的第一份收入。平均每千字八十元,比内地当时文学刊物的稿费多出了好几倍。我那尸骨流落在大兴安岭的奶奶说得对,香港真好!
我奶奶一向不正眼看我,她认为家中所有灾难都是我八字不好所致,可1959年初她临终前的一天,把我叫到了跟前说话。那是大兴安岭严冬中最冷的一天,外面的气温零下四十度。家中火炕怎么烧也烧不热。印象中,自从我们从北京到了大兴安岭,奶奶就一直躺在这张炕上。这天,我却看见她坐了起来朝我招呼。
“来……来……”她颤巍巍地唤道。
我吓呆了。这不仅因为我向来怕奶奶,主要是因为,她那张骤然呈现在炕头的面孔惨白如鬼。
“妈!妈!”我四下张望着叫道,这才发现屋子里只有我一个人。奶奶那双呆滞的老眼望定的就是我,她的确在对住我一个人说话。
“来,来!”她道。
我别无选择,只有上前去扶住她那摇摇欲倒的身子。这时我才发现,奶奶的目光并没对准我,而是越过我的肩头,对着那扇冰封雪冻的窗户,那双被皱纹挤逼得缩成一条缝的眼睛,此时闪闪发光。
“奶奶你看什么呐!”
“树,树,香……香港……多……”她说。
奶奶还说了一些话,那些话断断续续颠三倒四,我都忘了,我只记住了这几个字眼。所以后来母亲问我奶奶跟我说了什么,我讷讷地说不清楚。处于弥留状态的奶奶,真的说出“香港”这两个字了吗?我自己也怀疑起来。我甚至怀疑,奶奶的这句话,是否出自我的想象呢?我是自小就有将想象与现实混为一谈的毛病的。
不过我清楚地记得,父亲被打成右派,我们一家老小跟随他流放到大兴安岭之后,奶奶的确常把香港挂在嘴上:
“香港多好,从来不用穿棉袄。”
“香港天天有面包吃。”
“在香港你爸一个月赚七百块钱呢!”
对比我们眼下住在这冰天雪地中一破屋、天天吃苞米子、父亲月薪五十多元的现实生活,香港的确是个引起美好想象的地方。所以我才执着地相信,奶奶临终前念叨的不是她的老家安徽,而是她只做了两年过客的香港吧。
1972年,我和父亲曾去那个名叫西尼气的大兴安岭林区小镇寻找奶奶的坟。父亲说,如果找到了,就把奶奶的遗骨带回安徽老家。
“那还不如带去香港呢。”我心里想。
想当初,奶奶当着我们怀念香港时,父亲总是保持沉默,他一定把奶奶的话当作对他的责难了。父亲和母亲,往往会在奶奶对香港的怀恋声中吵起来:
“都是你,”母亲说,“人家都往外面跑你往里面跑,好像人家缺你一粒豆豉就打不成汤似的。现在可好,给弄到这鬼不生蛋的地方来了。”
“事后诸葛亮。”父亲反唇相讥,“那时候不是你一天到晚老念叨上海好香港不好吗?”
“我念叨的不是上海,是工作。我在上海那工作多好,我以为回来了就可以重新参加工作。哪里晓得会这样……”
“好了好了。”父亲息事宁人道,一边朝装有夹层玻璃的窗户猛眨眼,神色诡异。这一招挺有效,脾气火暴的母亲见到他这副神色,便立即收住话头,偃旗息鼓。
起初,我是在褪色的家庭照片中认识香港的。那些照片都是父亲用老式相机拍下的黑白照。父亲摄影技术实在无法恭维,那些相片,不是因曝光不足而太黑,就是曝光过度而泛白。有些还因焦距没对准而模模糊糊。好在每张照片下面都有父亲用钢笔字标写的说明,例如:
大妹三个月沙田刘家大屋门前
大妹与刘姥姥孙儿秋仔
大妹一岁筲箕湾家中
二妹两个月,沙田。
大妹是我姐姐,二妹即是我。我被母亲允许翻看这些相片时,还不到上学年龄,不识字,母亲在旁边为我念照片说明,并做一些补充讲解。那时我们还住在北京,母亲的讲解客观而含蓄,只是告诉我们沙田那房子是租的,门前菜园是房东刘家的,沙田在香港的郊区新界;而筲箕湾房子则是他们自己买下来的,在港岛市区,等等。奶奶去世以后,在窗外呼啸的北风声中,她对相片做讲解时的口气,便有奶奶之风了:
“沙田空气多好,房子多大!”
“刘姥姥人真好,哪里像个房东!到底是吃斋的人。”
“你爸爸那时是《星岛日报》记者,首席记者咧,回大陆的那年,工资涨到了八百块。”
“那他干吗回来?”我问。
“因为爱国啰。”
“哦,香港是外国。”
“不是,不是。”
“那是中国啰?”
“也不……”母亲焦躁地摆摆手,“哎呀,跟你们小孩子说不清楚。”
1995年,我申请父亲来香港探亲,住在我位于北角的出租屋里。一天他突然说:“我带你们去沙田看看。”
“你?带我们?”我与十三岁的儿子面面相觑。那时我都定居香港六年了,儿子也来了四年多,他每天换三次巴士从北角去赤柱上学,我们对香港的交通怎么着也比离开香港四十多年的父亲熟悉。还用得着他带?
父亲当年的沙田,只不过是个郊野小村,据说只有一条小巴线路可达,而且只有白天才开。
“做报馆的人老是上夜班,”母亲曾告诉我,“你爸爸下班时小巴早没有了,要坐出租车回家。”
而现在,沙田是香港最繁华的新市镇之一,各种公共交通工具皆可到达。我建议先坐巴士到红墈,然后换乘东铁。父亲却说,他已打听到香港仔有一路巴士可直达沙田新城市广场。
“那不好,两程都是巴士,慢极了。”我道。
但父亲坚持,“坐巴士可以看风景。”
我们只好先乘巴士到香港仔,再从那里转去沙田的巴士。历时几达三小时。但父亲一路上始终兴致勃勃。我们坐的是上层第一排座位,在摇晃的巴士上我最易打盹,便嘱咐儿子:“快到了叫我。”父亲却道:“放心,我叫你。”
那天我在巴士上梦见了奶奶没有?是否我与她临终前那番对话便是在巴士游的梦境里看到的?我无法断言。活到我今天这把年纪,许多往事都无法断言了,真情往往与梦境混杂在一起,但父亲那天一直对住前方窗外凝望的侧影,却是印在我心底里的一个定格,磨灭不了。而他与儿子的对话却像是怀旧影片里的画外音,幽远绵长:
“看那里!”
“什么?”
“那里!”
“哪里?”
兴奋的苍老声音与慵懒的童稚声音,对我来说,皆有振聋发聩之效。可睁开眼睛一看,看到的却都是寻常风景:车水马龙的街道,五颜六色的店铺招牌,熙来攘往的行人,层层叠叠的高楼广厦,香港人管它们叫“石屎森林”,我却觉得它们像一道道刀山,直刺天宇。想到自己也存活于其中的某一格,那种感觉,绝非三言两语了得。
我们终于站到了地面,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巨型公交总站,眼前车道如织,川流着密密麻麻的巴士和人,在轰隆隆不绝于耳的车喧人闹声中,我听见父亲的叹息:
“全变了,全变了。”
我们在道风山下那片村屋中转来转去,父亲一马当先,我和儿子趿拉着脚步跟在后面,我不断地吁请父亲别转了别转了,到新城市广场找间食肆吃饭为要。
“麦当劳都可以啦。”儿子亦对我的提案表示着支持。
但父亲不理不睬,一直走一直走。
“难道你想找到刘姥姥?”我的话语中带几分挖苦了。
谁知父亲眼睛一亮,道:
“对了!刘姥姥的女儿若还在,一定会认得我的!她岁数跟我差不多,那时候老是往我们家跑,带着她那个女儿,名字叫秋仔。秋仔跟你姐姐一般大。”
我们当然没找到我们四十四年前曾经住过的老屋,其实父亲也明知不可能找到。他好像耽迷于这种知其寻不到而寻之的游戏:一去大兴安岭就要去寻找奶奶的坟,一到了香港就要来沙田寻找老屋。在父亲去世以后,我从他的日记里得知,我们那次的寻找老屋之行,之前他至少已经搞过两次了。1985年他第一次重返香港,便邀集了四五位老友来沙田踏访。1987年又带着刚刚定居香港的姐姐来过一次。关于第一次踏访,他日记上只有两行字:
仍识车站旧地及车站对面山坡上的旧居园地,惟已是高楼拔地而起,完全无从寻旧迹了。
那么,他后来又一次次地来到这里,是想要找见些什么呢?
当我和儿子终于把他拉到一间食肆坐定,我曾半玩笑半认真地问他:“后悔了吧?”
“后悔什么?”
“不该回去啰。”
“谁说的?”父亲正色道,“此一时也彼一时也,那时有那时的想法。”
记忆所及,他从来没对自己当年的决定表示懊悔,就连在日记里提及此事,用的也是标准新闻记者式语言,这些日记从1973年开始,断断续续记到他去世的1996年,记在一些劣质笔记本甚至没封皮的手工装订草纸上,以下这一段是记在几张叠在一起的纸片上的:
四九年六月应上海《解放日报》社长范长江邀请率全家乘英轮离港。
四九年七月因英轮在台湾海峡受阻,中途返港,继续供职于《星岛日报》。
五年十月二十三日广州解放,率全家老小五口经深广赴上海应聘。
五年十一月八日接范长江自北京来电话,嘱即赴北京工作。
十一月十八日在《人民日报》社会晤范长江谈工作。
十二月一日长江同志介绍我与《人民日报》社资料室主任胡仲持等人到抗美援朝总会工作,任总会宣传部秘书。会长郭沫若,秘书长刘宁一、刘贯一。宣传部长罗隆基、廖盖隆。
这段经历在母亲充满个人感情色彩的表述里,却是这样的:
那年你爸刚刚加了工资,我们刚刚把筲箕湾的房子顶下来(即现在的按揭),多好的房子!有一天,他就喜事一样跑回来说什么解放啦有个朋友叫他回国。我说人家老早就是共产党员了,现在当上了大官,当然说国内好啦,你连民主党派都不是,跑回去鬼理你。还是再看看吧。你爸哪里肯听,非说什么中国好不容易和平了,搞建设了,需要我们知识分子。他傻里吧叽连忙跑去报社辞了工,房子嘛三钱不值两钱转顶给了一个朋友——那人现在发达了——我们扶着你奶奶抱着你姐姐——那时还没有你——上了回国的船。谁知船开到半路不开了,说是国民党在前面的海里放了鱼雷。这不正好!我们又回了香港。《星岛日报》老板真是好人,明知你爸爸是亲共分子,还让你爸原职原薪回来工作。不过我们的房子收不回来了,只好在沙田租房子住。那房子远是远一点,空气多好,又便宜。要是我们安分守己在那里住下来,以后的罪也就不会遭了。你爸的朋友老宋,当时也是租屋住,现在都当编辑了,在九龙买了豪宅,四个孩子都在美国拿了博士。他家老二还是跟你同年同月同日生在那打素医院的,现在在加拿大开公司。找了个丈夫也是吃了海水的博士。人家多么有眼光,你爸多没脑子!一次回不成还回第二次。水路走不成了走旱路。我们从罗湖过关时我已经觉得不对头:怎么这边过去的人这么少?那边过来的人这么多?唉,可惜已经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