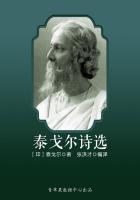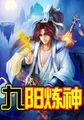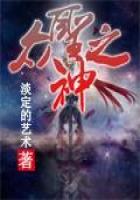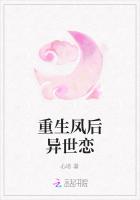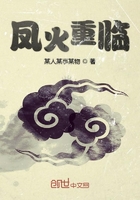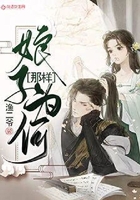编辑部组成·六人复刊第三个《收获》·从《收获》走出的作家
蔡:我们就从你到《收获》编辑部工作说起吧。
孔:那是“四人帮”粉碎以后,一九七七、一九七八年的时候,当时作家协会、文联不是被砸烂了嘛,房子被《海港》样板戏的人住了,“四人帮”一粉碎就还给作协跟文联了,那时候作协跟文联在一起办公,要重新搭架子。“四人帮”时期没有作协、没有文联,只有一个文艺刊物,就是《朝霞》。大概是一九六九年还是一九七〇年办的,那是造反派办的革命文学刊物,欧阳文彬他们办的吧。后来“四人帮”粉碎,《朝霞》当然也就没有了,停刊了。房子就还给作协、文联。文联的房子原来在延安路那边,那时还没有交还,就都在巨鹿路办公。文联在二楼,作协在三楼。这个时候作家协会搭架子,钟望阳在那里负责。原来的市委宣传部长是洪泽,他委派钟望阳来搭文联跟作家协会的架子。搭了架子以后就想先把一个刊物搞起来,叫《上海文艺》,它是《上海文学》的前身。那时候有茹志鹃、赵自、唐铁海、彭新琪,他们都开始搞《上海文艺》。那时候我也去了,大概是一九七七年底。粉碎“四人帮”的时候我还在工厂劳动呢,就是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当时洪泽部长要我到作协去,钟望阳叫我到《上海文艺》去。那时候李小林还在杭州(她的爸爸巴金被打成黑老K,她被下放到杭州去了),她就调回来了,也到《上海文艺》。没几天,上面就决定要《收获》复刊。
蔡:《收获》在前面已经两起两落了,这是第三次办起来的。
孔:开始是巴金、靳以办起来的,后来是叶以群、魏金枝负责的。一九七八年后半年,我一个,小林一个,萧岱一个,我们三个人就过来,开始筹备复刊。我们还缺一个搞编务的,就把邬锡康从文联办公室调过来。他本来下放到向阳(?)中学当老师的。后来“四人帮”一粉碎,他也回到文联来了。四个人就搞起来。一九七九年就出第一期。办起来大概过了一段时间,郭卓也过来了(她刚开始还在南京)。当时吴强也还没有解决问题(“四人帮”时期他被审查,这时候还没有彻底解放),跑来跑去的,经常到作协跟钟望阳谈,搞清楚了之后也到《收获》来,那时大概是一九七九年下半年,他不算我们的编制。他原来不是作协的副主席吗,报上先作为我们《收获》的负责人。上面市委没批准,那时候什么都不批的,他就先干着。他跟郭卓比较熟,和萧岱研究,就叫郭卓来了,郭卓本来是下放的,从南京回到上海之后,就调过来了。我们已经六个人了。到了大概是一九七九年底还是一九八〇年,又来了盛毓安,负责封面、插图、题图等美编工作。我们七个人也不分谁是头谁是编辑,不分谁看什么稿子,打通仗。只有盛毓安是美编,比较明确,不搞文字工作。再一个就是邬锡康,负责编辑部大大小小的事务工作,比如清理来稿、跟作者通信、寄刊物、发稿费、处理账目。到后来,他有空了也看稿子。这样干了十年啊。我那时候主要和李小林坐在一起,我们两个合作得比较好。她有什么稿子给我看,我有什么稿子给她看。她脑子比较敏捷,对作品构思、情节安排、人物刻画理解比较透彻,想象力比较丰富。我是历史方面、古典文学方面、文字方面搞的时间比较长,所以较为熟悉。萧岱是和郭卓合作得比较多,郭卓看了给萧岱看,萧岱看了给郭卓看。
蔡:看来你们当初两两合作得比较顺手。
孔:我看过了,给小林,觉得可以发,萧岱基本上没有意见。他们看了,有时候也跟我们商量,有时候他们觉得不好,就干脆退掉了。比如南京作者的《内奸》,我们就没有发表,后来它在南京的《钟山》发了,还得了奖。
蔡:它是被《北京文艺》登出来的。这篇稿子为什么没发?
孔:我跟李小林回忆了一下,我们没有看过这篇稿子。大概是萧岱跟吴强两个人看的。可能他们觉得不好,具体我也记不清楚了。
蔡:这篇稿子是自由来稿还是吴强与方之比较熟悉由吴强带过来的?
孔:这我不太清楚。我们《收获》有个传统,就是坚持在质量上要把好关,坚持兼容并蓄、百花齐放,国外的新潮流,比如荒诞派、黑色幽默,我们不排斥;老的传统的,如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浪漫主义,我们也坚持。再一点就是推新人,尽量发现新人新作。前面的两个《收获》是这样的,我们再复刊的也还坚持。只要是好作品,不管你是怎么样写法,是什么流派,受什么思潮影响,只要艺术性比较强,我们就发,胆子比较大。像《大墙下的红玉兰》,这个作品反映监狱生活,当时北京的刊物不敢发,我们就发。对作家的文学创作有激励作用,对他在社会上有影响,对他以后的整个地位也有很大的影响。这种情况不只他一个,还有《犯人李铜钟的故事》的河南作者张一弓,《祸起萧墙》的湖南作者水运宪,他们过去都没发过什么作品。张一弓在“四人帮”时期写过一些东西,河南对他有些看法,而我们认为他的作品还是可以发的,这对他本人在当地的处境也有一定的帮助和促进。谌容最初在北京投稿,没有人给她发,她有一篇《永远是春天》。
蔡:谌容倒是早在“文革”时期就发过东西,还出版过长篇小说。但刚粉碎“四人帮”之后,那些东西就成了忌讳的东西,刊物有意对她疏远。
孔:结果她就把自己的稿子拿到上海来,我跟李小林就说:“给她发。我们不怕。”我们就发了她的作品,而且还请她过来,在上海为她的作品举行座谈会。她当时住在上影厂招待所。我跟李小林去找她,就给她出主意,下一个写《人到中年》。这样,她才回到北京,下生活,写出《人到中年》。这样的事好多,我们推出的现在都是著名作家,像冯骥才,他的《铺花的歧路》,是我给他发的。像张抗抗,虽然“文化大革命”期间也写过,在文艺出版社出过作品,但是影响不大。“文革”后她重新拿起笔,第一篇《爱的权力》就是我跟李小林给她发的,绝大多数都是我跟李小林给她发出来的。还比如陆星儿、张辛欣、张贤亮,包括张洁、万方、王安忆,都在我们刊物上发过作品。《收获》有一点好,在别的刊物上发,作者的影响起不来,在我们刊物上一发,作者的影响就扩大了。当代有不少作家都从我们这里出来的,这一点,我们还是觉得问心无愧的。特别是徐兴业,他的遭遇挺难的,他的夫人是个画家,“四人帮”时期受不了,跑到法国巴黎去,不回来。他一个人在上海,挺苦恼的,他写了一个什么……
蔡:《金瓯缺》。
孔:对,那是后来的。他先写了《金瓯缺》的一章,写了宋徽宗和李师师的事,拿给我看。我觉得不错,有新意,有新见解,文字很典雅的。我主张发。李小林看了,也同意了。但编辑部有人说:“老孔,这个文章你要是发了,人家打上门来兴师问罪,由你挡着。这个写妓女的,写皇帝和妓女谈恋爱,这怎么能行?题材有问题。”后来吴强插话了,说:“老孔说好发就发。”萧岱也就同意了,说:“试试看。”发了之后影响很大。而且,文章一发,还救了他一家。本来他和老婆断了联系,结果他老婆在巴黎也看到了发表出来的作品,就主动跟他联系。他们两个就恢复了关系,蛮融洽的。徐兴业非常高兴,对我们很感谢。就是这篇作品发了之后,福建的出版社才要他的全稿,他才出了《金瓯缺》,三大本的长篇历史小说。要不是我们发现的,在《收获》发表出来,他的小说出不来。他的家庭也不能破镜重圆。编辑工作虽然比较辛苦,但更有乐趣。还有现在很红的,写了《苍天在上》、《大雪无痕》的陆天明。他是陆星儿的哥哥。他最初写的东西给我们,不大行。有一个中篇,我们叫他改了八次,才给他发。现在当然不同了。十多年过去了,他锻炼出来了,写作技巧有提高,文字能力也大大提高,这与他后来锲而不舍的努力有很大关系。但是最初我们《收获》对他有一定帮助。我们怎么和他交谈,叫他怎么修改,等等。和作者谈话一般是李小林和我,有关历史方面我单独和作者谈;关于作品的构思技巧、故事情节,有时候小林和他们谈,有时候拉我一道。谈过三次、四次都有的,谈了再写,写了拿来看看,再谈,再改,也蛮费工夫的。现在这些人有的都开花、结果了,成名成家了,出国啦,当校长、当教授啦,都有,蛮风光的。我们还是做了很多工作的,起码浇水、培土,我们是做过的。“文革”后最初影响较大的有四个刊物,《收获》、《十月》、《当代》、《花城》,被称为“四大名旦”。老旦是《收获》,因为资格最老;《当代》是青衣,正旦;《十月》是刀马旦;《花城》是花旦。
蔡:后来好像稍微有点变化。江苏的《钟山》上来,有顶替《十月》并取而代之的架势,被归入“四大名旦”。
人员流动·李小林扶植了大批作者·关键看作品
蔡:你在《收获》一直工作到什么时候?
孔:到一九八八年离休。
蔡:《收获》编辑部在前一阶段人员的变动我们梳理得比较清楚。那么到你离休之前,还有哪些人的进出?
孔:现在的程永新、肖元敏、钟红明,他们进来,我是晓得的。因为后来我们的来稿太多了,堆积如山,靠我们这么几个人,包括邬锡康,都一块看稿,还是来不及,工作量太大了。我们就想办法,每年或者每个学期到复旦大学招几个毕业班的学生来帮我们看稿,一次来两个人,来了好几茬。
蔡:都来过哪些人?
孔:有李小林的弟弟李晓棠。唐代凌先在我们这里看来稿,毕业之后分配到高教系统,我们想办法把他挖过来了。后来,在同学卢新华的帮助下他到美国去了。他在编辑部待了大概两年,担任过编辑部主任。后来我跟郭卓都要退休了,萧岱、吴强年龄也大了。再后来萧岱患肝癌去世了,吴强多活了两年得了脑癌也去世了,编辑部就由李小林负责着。
蔡:那你就谈谈李小林吧,看她在《收获》发挥怎样的作用。
孔:李小林思想很活跃,基础也不错,家学渊源影响嘛,《收获》有些什么问题,或者遇到疑难稿子,她可以就近向她爸爸请教。那时候我们《收获》搞活动,组织作家到莫干山修养、避暑。巴老、李小林都和我们一道去。作家有谌容,还有其他人。李小林从杭州调回来之后,从《收获》准备复刊一直到现在实际上都起着重要作用。萧岱基本上都听李小林的意见。李小林组稿很积极,对稿子的看法,给作者提意见很具体,作者都挺服气的。当时吴强就跟我说:“你们给作者提意见不要强加于人,人家作者自己这样构思的,你们说要这样那样。”我说:“我们没有强加于作者,只是提建议。我们觉得这样子比较好。他要是实在不愿改,不能发的就不发了,如果能发的,我们还是尊重他们的意见的。”其实李小林提具体意见还是到点子上的,不是乱提。当然个人有个人主观的看法。比如一个人物的塑造、某个情节的构思,可能同意我们编辑的意见,也可能会有他们自己的看法,没关系的,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见,这都是可以的。但就是这样,她扶植了一大批作者,她有头脑,能根据作者的思路、意向给他们补充点什么。她还很虚心,尽管谈起来她也很严格,但她有什么事情也总跟我商量,征求我的看法,不懂的词语、典故,她都会虚心请教人。后来,她有些根据自己的爱好出发,比如对年轻人比较放手,对程永新比较欣赏。她跟我说光靠她一个人不行,得发动他们的积极性,让年轻人也挑挑担子,我表示可以理解。
蔡:一九七九年复刊以来,有一阵子《收获》发了不少好作品,你觉得和李小林发挥的作用有没有关系?
孔:有一定的关系。当然,整个《收获》的成绩是集体的,是大家共同努力所取得的。但其中李小林的作用还是蛮大的。比方有的稿子,萧岱和郭卓,甚至吴强都觉得不好,不发,我跟李小林的意见常常一致,我们两个人认为就该登,就要发。后来萧岱想想,就让步了。比方什么稿子发第一篇,什么稿子发第二篇,这里也有争论。我们让步的也有。让步的主要是发头条的作品。《人到中年》好像就没有发头条。谁的发头条,我们有点意见,就算了。基本上大家还是融洽的。个别稿件有点出入。
蔡:萧岱当时主要做了哪些工作。
孔:萧岱当时比较忙。八十年代初期,他基本上没有看什么稿子。他继续担当文联的秘书长。有找他平反的,有老干部、老会员找他写证明的、谈话的。他一直在上海,原来是地下党的,还当过乐团的负责人,所以文艺界认识的人比较多。
蔡:当时吴强也是《收获》的负责人,他做了哪些工作?
孔:吴强基本上不看稿子,他组的稿子才看。吴强的作品,我们说不发也就不发。他的稿子多半先交给我,我看了之后才交给李小林看。我们《收获》还有个特点:不畏强暴,不看上头脸色。像有位领导,老想在《收获》上发,他写过好几部诗、散文,我们都坚持不发他的作品。为什么不发呢?因为他的作品不符合我们《收获》的标准。我们退了他好几次稿子,叫邬锡康送还他。他气得要死,说:“我就不能在你们《收获》上发作品?”每次写来都退,大为光火。吴强态度倒是挺好的,他说:“你们看不能发,就算了。”写《李自成》的姚雪垠,我们给他发了《李自成》第三部的一部分,还可以。后来他寄来好多诗,有二十几首。拿给我看,写得不行,没有诗意,韵律不合,就没有发。后来他捡了七八首在《花城》上发。我们就是这样,不管你是名家,还是领导,关键看作品。只要写得好,不管你是不是新人,名不见经传也好,默默无闻也好,只要作品有可取之处,我们也会挑上的。历史在前进,不同时期反映社会生活的角度不同,我们也认为应该有人去表现。只要作者敢写,即使冒点风险,我们也敢发,挨骂我们也不怕。像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有人认为写了性。本来它不叫这个名字的,叫个《××树》,和原来的《绿化树》一个系列的。他的书掌握在新华书店的人手里,出版社把选题给书店的人看,人家还以为是写什么植物的,认为这书看书名发行量肯定不行。后来拿给我们《收获》,索性就不用《××树》,改成《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这是市场效应,但我们也是把握分寸的,不能过头。
向前走·不理财务·巴金的名头和潜在作用·人格和风骨
蔡:你觉得现在的《收获》和你们当时的《收获》有什么不同吗?
孔:现在新的编辑跟我们老的还有点差距。我们当时是坚持艺术质量,坚持百花齐放、兼容并蓄,但是还是以现实主义手法为主,对西方新潮的、前卫的也吸收、也不排斥,但分量不是很大,不是一边倒,还是不放弃原来的。但现在新的编辑对西方的比较感兴趣,后来有人反映作品看不懂。看来稿子的倾向性有所不同了,口味两样。我们也不是不喜欢,在观念上可能有点保守。
蔡:《收获》有所变化,我认为不是什么坏事。只要它不是轻易地降低自己的格调,不是去迎合世俗、迎合时尚,而是在探索一条适应今天的读者及文学发展的新路,应该给予鼓励和支持。《收获》这样的大刊物应该走在变革的前头,不应该等待读者提出新的需求,更不要等到读者厌倦、流失还无动于衷。以往的《收获》倒是以沉稳取胜,没有什么大一点的动作,一直比较平静地发展着。《收获》正在求生存的过程中寻求拓展,也许有成功,也许有失败。但是,如果一成不变,恐怕就不是简单的成功或失败的问题,而是可能会落伍,或者更不妙。我不希望这样,热爱《收获》的读者也不愿意看到这种局面出现。
孔:《收获》要生存,而且它也要发展,要向前走,这是可以理解的。八十年代的时候,纯文学的刊物还是比较占上风的,还没有出现市场经济。
蔡:当时读者对精神食粮的渴望十分迫切,有点饥不择食的架势。
孔:我们《收获》最高发行量达到一百二十万册,八十年代我在的时候还控制在七十几万,再后来就跌到十几万了。但是我们没有赚到钱。问题在哪里呢?当时几个老的,钟望阳、吴强、萧岱他们都还在。他们都比我大十来岁。我那会算年轻的,六十岁不到。他们几个老人主要害怕承担责任,不懂财务,不大愿意管财务,知识分子的特点嘛,把出版权给了文艺出版社。我们只负责编,把编好的稿子给他们出。出版了我们只拿一点编辑费。他们赚了多少钞票,我们不管。发行到一百二十万,八九十万的时候,钱还是赚了不少,完全归文艺出版社。我们没有拿到什么好处,每期只给我们一点编辑费。
蔡:编辑费给你们多少?
孔:很少。一部分存起来,以备不时之需;一部分像奖金似的,发给大家一点,几十块,百十块的。他们那会儿不敢拿回来办。后来我们一离开,李小林魄力比较大,决定不给文艺出版社搞,我们自己发行,就拿回来自己办了。但拿回来以后,行情不对了,市面上纯文学刊物下跌了,跌到现在的情况。《收获》还算好的了,在全国大型文学刊物里发行量还算站得住脚的,大概十几万,还可以自给自足,稍有盈余,但和以前不同了。
蔡:是你离休之后才拿回来自己办的吗?
孔:好像是我快离休了,还是离休了之后,我也记不太清楚了,反正就在一九八八年前后吧。
蔡:我们谈谈巴金对《收获》杂志的贡献,他发挥怎样的作用,做了哪些事情?
孔:创刊《收获》是巴金和靳以,原来是属于中国作家协会,是中宣部管的,后来才属于上海作家协会,归上海宣传部管的,走了一个从中央到地方的过程。巴金是创始人,“文革”之前,他都要干预的,有些重要事情或稿子,他都要关心的。“文革”之后,身体还好的时候,他还去日本、去法国,虽然不来办公室,但他名誉上还是愿意担任《收获》主编的,上海作家协会主席、上海文联主席,他都推掉了,现在只保留了中国作家协会主席的名义,还有一个就是《收获》的主编。他对这个杂志还是有感情的,一直比较有感情。病不重的时候,李小林、萧岱都还请教他一些稿子的事情。有时候,我们去看他的时候,他也跟我们谈谈他的意见,也通过李小林把他的看法转达给我们。那时他还干预一些事情,出出主意。后来身体不行了,那就完全由李小林来做主了。现在还要靠他的影响,宣传部也是这个意思,巴老一直搞这个刊物,还是挂他这个主编。他有作用。全国有多少作家,有名的、没名的,都是看着巴金这个名头,想跟《收获》挂挂钩,把作品投给上海、投给《收获》,让《收获》给他们发稿。巴金的影响还是在着的,潜在的作用还是有的。当然,我也听说西南有人在网站上对巴金有些微词,这也是难免的。
蔡:我也得到过这方面的信息,你谈谈对这件事情的看法。
孔:他们一方面不了解具体情况,乱猜;另一方面他们也有些看法,不一定客观,带着主观的感情在里边。我也不大同意他们的观点,根本不是实际情况。不是巴金自己提名叫他女儿李小林当这个副主编的,是宣传部征求他的意见,他就说要一个比较熟悉业务的人,后来作协的负责人看我们这些人都走了,年龄大了,李小林的编辑业务、年龄都蛮适合的,而且一时也找不到更恰当的人。后来李小林又带了两个副主编干起来了。
蔡:那时候提李小林担任副主编,还有没有其他候选人?
孔:没有其他人选。大概是作协党组跟他们宣传部的人商量了之后决定的。那时候面临着后继无人的问题。我那时候已经六十五六了。郭卓跟我也差不多一般大。我们都要走了。就是不走,年纪也大了,应该让给年轻的。小林那时只有四十来岁,正当年。除了小林,编辑业务去找哪个人呢?其他的人,赵长天现在是搞《萌芽》了,那时候他刚来作协做党组委员,是成员之一。叶辛还没有从贵阳调回来。他最初的作品在《儿童文学》上发,没什么影响。也是我们《收获》连续发了他几个长篇作品才把他推出去的。他以后才要求调回上海。茹志鹃已经是作协的党组书记了。赵自、唐铁海都在《上海文学》,不能离开的。有的人是搞理论的。没有什么人能搞这样的大型刊物,以小说为主的刊物。当然我们也没有到外面去广泛地招兵买马,就是上海宣传部和作协商量的结果。
蔡:你们都退了、老了,李小林就成了编辑部资历最老的了,况且她已经组来许多有影响的稿子,各方面能力都是挺强的,自然地提升为副主编也是理所应当的。这里恐怕也不排除你所说的巴老在背后的潜在作用。李小林当副主编,毕竟会有不少便利因素,碰到微妙时期还有巴老这棵大树遮挡着,等等,有些条件是先在存在的。
孔:把唐代凌从高教局挖到《收获》编辑部,就是巴老说的话。当时巴老住在医院里,宣传部的领导去看他,巴老就说把唐代凌放给《收获》吧,才办成的。
蔡:除了我们已经说过的,你认为《收获》办得比较成功的因素还有哪些?
孔:《收获》的传统就是把好艺术关,只有达到一定的艺术高度,才能发表。不以作者的地位为转移,不看权势,不论名气。兼容并蓄、百花齐放,既坚持现实主义、浪漫主义手法,也吸收西方各种流派的表现手法。它既不哗众取宠,也不凝固僵化。它不断地吸收新的东西,充实到原来的、旧的框架之中,把新的、老的结合到一起,不排斥不符合自己观点的作品。推出新人新作,不光发老作家的作品,要尽量挖掘新人新作。不怕压力,不管作者本人有什么问题,或者作品本身反映的角度有什么问题,只要有发表的道理,应该反映的,应该支持作者站立起来的,我们还是会发的。我们刊物基本上是以小说为主,散文为辅。小说当中以中、长篇为主,短篇为次。一般不发诗歌,因为现在诗歌弄不准。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后,很难把握。坚持这样的格局。我们还坚持不在刊物上登广告,本来我们想登一点文化方面的广告,后来也没有,保持它的清纯的形象。这样都有助于奠定刊物一定的风格,一定的品味。还有它历史比较长,在群众中间、在读者当中的影响有一定的基础。特别是推出新人新作,很受欢迎。不但是爱好文学的青年作者欢迎,而且也受到群众的欢迎。有新鲜感,可以嗅到新鲜的气息、味道。而且写法有不同,这篇这样写,那篇那样写。有古有今,有中有西。版面比较丰富,读者可以各取所好,有助于《收获》的知名度的确立。
蔡:正是《收获》不断地推陈出新,不断地向前探求,才确定了它今天在文坛上的地位。在文学期刊中的领头位置,在广大爱好文学的读者心目中神圣的形象,它甚至成了文学抗击商品大潮、抵御物质引诱的最后一片净土,成了文学不死的象征。它衔接了“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对民主、正义和良知的人文精神追求,渗透着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抵抗俗世和权势的人格力量,使它能够立足于一个比较高拔、超脱的基点。这使得它不仅赢得知识分子的喜爱,而且也赢得热爱文学的一代又一代读者的欢迎。希望《收获》承前启后,新人辈出,越办越好。
孔:这不仅仅是刊物的风格、品味,而且也体现了办刊物的一代又一代的编辑的思想,代表了中国知识分子的风骨,不卑不亢,不谄上,不媚俗,这是《收获》几代编辑的主体精神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