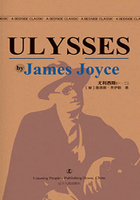自从我译的第一部外国文学作品——匈牙利剧本《战斗的洗礼》1954年在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我在文学翻译这条颇不平坦的道路上已经颠踬了整整三十年了。三十年来,在教学的本职工作之外,利用节假日和业余时间,孜孜矻矻,倒也陆续译出了三四百万字东西来。但如果问我从事这么多年翻译,有什么体会,恐怕仍是我在1979年写的一篇文章中概括的一句话:“一路颠顿竭蹶,风险频遇。”而且年纪愈是增长,愈感到捉襟见肘,笔不从心。近年来有时为年轻人看稿,往往一眼就看出译稿中的败笔,但如何改好,却常常踌躇终日,不敢落笔。总之,随着年轻时锐气的丧失,才愈感译事之难。1983年应《翻译通讯》编者的敦促,写了一篇供青年文学翻译工作者参考的文章,提出有关翻译的几个问题。虽然内容大都是老生常谈,却先后接到一些读者来信,对其中一些提法和我进行探讨。现在结合这篇回溯自己翻译活动的文章,稍许举几个实例,再进行一些阐述。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可以算对一些与我通信的年轻翻译工作者的答复。
我在给《翻译通讯》写的那篇文章中曾谈道:“……在任何学科上想要自学成材,主要靠的是个人刻苦努力,需要一点儿锲而不舍的精神,另一方面,也要有合适的土壤,也需要灌溉和施肥。”我自己谈不上多么刻苦,更缺乏锲而不舍的精神,但之所以能够踏进翻译的门槛,却多亏了几位良师益友的提携和帮助。另外,自然也由于我所处的环境给我提供了机会与方便。
从50年代初,我就担任了教外国人汉语的工作,使我不得不对汉语和两三种外语下了一点工夫。50年代正是中国同苏联及东欧国家交往频繁的时期,在外国文学方面,国内除了译介大量俄罗斯和苏联文学外,也陆续翻译出版了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家的作品。1951年在清华大学成立了外国留学生班,最早来我国学习汉语的就是上述几个国家的学生。在我教的匈牙利留学生中,有一位中国名字叫高恩德的讲师,对文学颇有修养。1952年夏高等院系调整,留学生班并入北京大学,高恩德协助我国老翻译家孙用增订补充了孙用早已翻译出版的《裴多菲诗四十首》。另一本匈牙利著名革命诗人尤若夫的《诗选》,就是我和高恩德译出初稿,再经孙用同志修改润色后出版的。高恩德精通德语,我在大学期间也学过一点德语。我们两人用德语交谈,没有什么语言隔阂。对尤若夫的诗作常常经过反复讨论,才用文字写出。孙用同志早年刻苦自学,踏上文学翻译的道路,对年轻人始终抱着诲人不倦的态度。他修改我和高恩德的译稿总是反复推敲,一字不苟。直到1964年我为上海新文艺出版社翻译德国19世纪革命诗歌二十首,孙用同志仍为我仔细润色译稿(此书后因“文化大革命”干扰未能出版)。我之能在翻译上迈出步子来,不能不归功于良师和益友(除了国际友人高恩德外,还有不少朋友给了我宝贵的帮助)。前文提到的匈牙利剧本《战斗的洗礼》,就是高恩德极力劝我把它译出来的。我不懂匈牙利文,但侥幸搞到了一个俄文译本。每译出一个段落,都经高恩德根据原文校对。其后我又陆续译了一部匈牙利剧本,一部匈牙利轻歌剧脚本(《小花牛》,1956年曾由中央实验歌剧院在北京演出)及若干短篇,都是从英语和德语转译的。
虽然翻译了几部作品,但是深深感到自己的缺陷。除了语言的障碍外,另外一个隔阂就是与中华民族文化迥异的另外一个民族的文化背景。以《战斗的洗礼》为例,书中有不少涉及天主教的文字,虽然勉强译出,但谬误甚多。剧本出版后,我的一个对天主教素有研究的老同学曾为我再次审阅,提出二十几条不合天主教习惯的词语。如“忏悔”应作“告解”,“节日”应作“瞻礼”,“圣女”应做“童贞女”,“作完礼拜”应作“望完弥撒”,“圣日”应作“主日”,等等。《战斗的洗礼》后来由作家出版社重版,我根据这位朋友的意见作了若干修改。这虽然只是个别词语的翻译,但如果不准确,就损害了原作的气氛。“翻译家必须是杂家”,这个口号吕叔湘先生在50年代初就提出过,早已引起翻译工作者的共鸣。但如何丰富知识,却是每一个搞翻译的人要为之奋斗终生的。通过第一个阶段的翻译实践,我的另一个体会是,由另外一种语言转译(或由精通原文的人口述翻译),不可避免地会使原著精粹的语言风格受到损伤,译者也常常会有“隔靴搔痒”之感。1956年我为了从德文译本转译一部波兰长篇小说(《一个人的道路》,1957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曾发奋突击了一阵子波兰文,基本上达到了借助词典能看懂原文的程度。1957年以后决心专门致力于德国文学的翻译,学到的一点波兰语、匈牙利语就开始荒废了。我深深认识到自己的愚鲁,一门外语尚学不到家,所以也没有什么可惜的。
从“反右”直到“文化大革命”,我曾无尽无休地受到批判,原因就在于从1957年起,我开始认真地译了几部德国文学作品。托马斯·曼的《布登勃洛克一家》是在“大跃进”前后和“反右倾”运动间隙中偷时间译出的(1962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亨利希·曼的《臣仆》着手翻译不久就赶上“阶级斗争月月讲、天天讲”的年月,完成时“文革”的暴风骤雨已快临头,稿子一直在出版社搁置了十余年才见到天日。在政治运动一浪高过一浪的年月中,要认真译一点东西(特别是长篇的)可真不容易,只能在风浪的间歇中偷一点时间。另一方面又惧于舆论的压力,只好采取瞒天过海的手段。我把要译的书籍拆散,夹在经典著作和笔记本里,在开不完的大小会和学习中间,偷偷觑一眼犯禁的东西,思索这个词,那个句子该如何处理。《臣仆》的大部分,《丹东之死》和两个德语中篇都是这样的违禁产物。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来了,一切事情都出了轨,我的小小的翻译事业自然也翻了车。一搁笔就是十年,等到再拿起笔来的时候,受到环境及条件的影响,我的翻译活动在方向和内容上也发生了变化,应该说这是我从事翻译的第三个时期了。
虽然我在“文革”前就被调到英语专业任教,但直到“四人帮”倒台以后,才获得重上讲台的权利。1978年第一次为学生开设英译汉翻译课,迫使我临阵磨枪,匆匆翻阅一些介绍翻译理论和技巧的材料。又由于英语荒疏多年,除了给自己补课,尽可能阅读一些英文书外,还不得不自己动手译一点东西。既然要给学生讲授翻译知识,就不能不提供一些实例,而最好的例子莫过于亲自体验过的文字。
接受系领导分配给我的开翻译课的任务,我是多少有一点违心去做的。最主要的原因是,我认为培养翻译能力决不是依靠在课堂上听老师讲一些条条道道所能做到的。只有通过大量实践,通过亲身体验,才能摸索出一条路子来(当然,这并不排除有经验的人加以指点)。其次,翻译活动是建筑在对两种语言的深厚的基础上的(且不谈还需要其他方面的素养),而多数学生在大学期间恐怕主要停留在语言学习的阶段。其结果,翻译课即使包含了一部分实践,也常常流于为学生讲解观点和修改不通顺的句子。如何改进翻译课,真正担负起培养翻译能力的任务,既不是这篇文章所能概括,也不是这里要讨论的内容。我之所以发了一些感慨,只不过想说明,自从当了翻译教师以后,我才逐渐注意到帮助年青一代走上文学翻译道路的问题。从1978年起翻译界前辈冯亦代先生为广东主编现代外国文学译丛,我也有幸参加这一工作。除了协助选定一些英国文学选题以外,还陆续校改了一部分译稿。后来我自己也先后编了几本选集,并为几个年轻人审校了若干长短译稿。工作倒也做了一些,但最深刻的体会是:自己才疏力薄,难以胜任。按道理讲,这些稿件应该已经初步达到出版的水平;对英文理解的错误只是个别的,译文通顺可读,只需要略微加工润色。但正是这一最后工序才是整个翻译过程最吃重的工作。如何把一篇已经明白通顺的译文再提高一步,尽量体现原著的风格,这需要极高的手笔。说老实话,有时我宁愿另起炉灶,自己重新译过,而不愿意在原有的基础上修修补补。翻译并不是演算数学题,只有一个正确答案。有时一个词、一个句子会在译者脑子里引出几种可能的对应语。给别人看稿,我总是认为译者提出的不是最佳的选择,需要改稿的人挖空心思,代为寻找。如果说我在翻译的道路上早走了几年,辨识力稍微高一点儿,那我也不幸害了这类人易犯的通病——眼高手低,看别人的译稿不满意,而自己又无力为之改好。本来没有资格为人师,而职业上却逼得自己走上这条路,真是苦不堪言。
目前就在为一位年轻人看一部译稿,伊夫林·沃(Evelyn?Waugh)的《Decline?and?Fall》(因为尚未最后确定书名,暂时只写英文名字)。这是我向某个出版社推荐的作品,而且前几年还自己动手译了几个章节,现在由某君译完,自然义不容辞,要给全书定稿。应该说,这位年轻译者的中外文水平都已达到一定标准,但是我不得不向他指出,要成为一个有独立工作能力的文学翻译者,仍需要刻苦努力。在审校他的译稿时,我首先发现一点背离原文的,便是译文未能忠实体现不同人物的身份地位。小说的第一部背景是一所英国私立学校。人物有博士校长,有三个教师,一个是从牛津大学被斥退的大学生(书中主角),一个原来是牧师,另一个人是经历复杂、参加过战争的退役上尉;此外,还有一个当了管家的走江湖的骗子。显然,这些形形色色的人物的对话是不能用同一语体翻译的。此外,学校里的小学生语汇,开运动会时一位美国黑人来宾满嘴的美国英语,也各有特色。我们当然不能希望译者(更不要说年轻译者)一切都处理得很好,但起码他应该锻炼出辨识不同语域、语类的“慧眼”。讲到译稿中的错误,确实不多,主要仍是一些牵涉到文化背景知识的问题:兰纳巴城堡是一个millowner(不是磨坊主,而是纱厂老板)在英国发生cotton?famine(不是棉花歉收,而是由于美国爆发内战、棉花无法出口,英国纺织厂产生了原料危机)时期,利用廉价劳动力修建的,校长穿了一件价值高昂的charvat(不是沙瓦式样,而是沙瓦服装店的)睡衣,一个女孩子正在留声机上放Gilbert?and?Sullivan(不是两个歌唱家,而是一个歌剧剧本作家、一个作曲家,两人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写了不少风靡一时的音乐喜剧)的唱片,桌子上摆着champagne-cups(不是香槟酒杯子,而是一种香槟汽水)……这些问题有的多查几本辞书即可解决,有的却就连说本族语的英国人也不太清楚。譬如说,前边提到的那位上尉(姓格莱姆)因为在前线酗酒触犯了军法,幸而来审判他的人是个熟人,那人一见面就说:“God?bless?my?soul,if?it?isn’t?Grime?of?Podgers!”(“真见鬼啦,这不是波杰的格莱姆吗?”)Podger究竟是地名还是人名?如果是人名,他同格莱姆又有什么关系?必须了解一点英国学校的情况才知道底细。原来在英国某些寄宿学校(多半是public?schools)里,男孩子分属于不同的houses(可勉强译作寄宿舍),每个house有一位house-master(也可勉强译作舍监、宿舍长),而Podger正是一位舍监的名字。弄清楚原文词语的正确含义巳不容易,如何把它译成汉语有时更困难。由于两国文化背景不同,一个国家的一些特殊事物在另一个国家是没有对应语的。更要注意的是某些词的内涵意义(Connotative?meaning),或者说,不同文化背景赋予一些词的特殊含义。也是在前文提到的那部译稿里,美国黑人的女友评论他说:It’s?only?when?he’s?on?his?best?behaviour?that?he’s?so?class-conscious,难道能从英汉词典硬搬,把class-conscious译作“有阶级觉悟”吗?我的年轻译者在这里又犯了个错误,正像我过去指出的另一个笑话:无所不知先生(Mr。Know-All)在轮船上帮助船员打扫卫生。这些都是把国内情况及用语硬搬到外国人头上。
以上举的一些译例牵涉到词语对译、译文风格、两种文化差异等问题,实际上这些问题近年来已经引起不少翻译工作者注意,许多刊物都发表了探索的文章。这不只对中青年翻译工作者很有帮助,就是对一些较有经验的译者也有启迪作用。由于我们的外语知识不是在使用该语言的自然环境中掌握的,普遍的缺陷是缺乏语感,即在辨识外语的感情色彩、社会文化含义和语言风格上“眼力”还不够。对原文“吃不透”,自然要影响译文的质量。提高外语理解能力要下真功夫,途径也决非只有一个,根据我个人的经验,除了大量阅读原著外,学习一点儿语言学,从理性上提高我们对语言的认识,对翻译工作是很有好处的。语言学是一门内容非常庞杂的学科,探讨的领域极其广阔。我个人认为,与文学翻译关系比较密切的是语言风格学、语义学和社会语言学三门学科。这里不需要也不可能对这三门学科进行详细介绍,只就它们探讨的广阔领域中几个与文学翻译有关的问题,谈一下我的看法。
1.词义问题。凡是从事翻译的人都承认理解(原文)是翻译的基础,语义学研究的对象是语言的意义,提出不少分析、理解语义——特别是词义——的理论和方法,开阔了我们的眼界。奈达的翻译理论就采用(并发挥)了语义学提出的词义成分分析法、语义场、语义层次等理论。在任何一种语言的全部词汇中都有一部分词具有两重意义:所指意义(referential?meaning)与内涵意义(connotative?meaning),这也是语义学着重研究的一个内容。“内涵意义”并不是一个恰当的译语,所谓connotative?meaning除了指词的感情色彩(最简单的是褒义和贬义)外,也应该包含词的社会、文化含义。许国璋先生曾在《现代外语》(1981年)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Culturally?Loaded?Words,列举了modern、bourgeois、criticism、labour、propaganda、metaphysics等一系列英语词,阐述说英语的本民族人与说汉语的人对这些词的理解并不相同,或者说大相径庭。我觉得Culturally?Loaded?Words这个词选得很好。王佐良先生在一次翻译座谈会上举出“江南”“塞北”两个词作例子,提出某些词对说本民族语的人具有丰富的含义,会引起种种联想,而另一民族的人却只能干巴巴地理解它们的“所指意义”(表层的字面意义),除非他长期沉浸在这一文化中。这些可能是一些极端的例子,也都是一些“大词”,但就是一些日常生活使用的“小词”,又何尝不然?breakfast、lunch、supper这三个人人每天要说的词在翻译中惹了多少麻烦,引起多少误解?(参见陈忠诚著《词语翻译丛谈》中若干章节)这种例子不胜枚举,每个从事翻译的人在处理单词时都会遇到“词汇冲突”和“词汇空缺”的现象。一个年轻人在翻译中遇到这样一个英文句子:I’ll?alway?remember?him?as?a?sportsman。是查一下英汉词典(或者连查都不用查)简单地把sportsman译成“运动员”呢,还是往深里思索一下,译为“讲义气的人”或“高尚的人”呢?还是王佐良先生在《翻译中的文化比较》一文中说的,“不了解语言当中的社会文化,谁也无法真正掌握语言”。语义学,虽然不是解决翻译单词的百宝书,但至少教会我们更加重视词语的含义,更加重视词的格调,有些词文雅,有些词俚俗,有些词委婉,有些词诙谐,有的陈旧过时,有的触犯禁忌……尽管找出一个个适当的对应词还需要译者自己绞脑汁,但可能少犯些错误,可能在忠实于原文这一点上庶几近矣。
2.称谓问题。一篇探讨称呼问题的社会语言学的文章一开始就转引了一个美国警察和一个黑人医生在街头的四句对话:
“What's?your?name,boy?”the?police?man?asked……
“Dr?Poussaint。I?m?a?physician……”
“What's?your?first?name,boy……”
“Alvin。”
波森医生追叙他当时的感受时说:“我的心怦怦乱跳,我在奇耻大辱中喃喃自语……当时,我的尊严被剥夺殆尽……”不熟悉美国的一套关于称呼的社会语言学规则,就不能理解波森医生的气愤来自警察通过对他的“称呼”进行了两次侮辱。第一次,警察使用了“体现种族的社会选择法”,叫他boy;第二次,警察不顾波森医生提供的头衔和姓(医生对警察也不够恭敬——没有按警察称呼规则的要求提供自己名字),又一次叫他boy,进行侮辱。
这一个小小的例子使我们知道“称呼”是一个多么复杂的问题,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长期形成的一套“礼规”。搞翻译的人常常会被种种奇怪的称谓语弄得晕头转向,只以带old一词的称谓语为例,A?Concise?Dictionary?of?English?Slang?and?Colloquialisms(B。A。Phythian编,1979年英国Hodder?and?Stough?ton出版)就收集了十三个:old?boy,old?girl,old?chap,old?dear,old?fruit,old?lad,old?man,old?woman,old?thing,old?sport,old?son,old?bean,old-and-bitter。使这一问题更加复杂化的是一个称呼语可以用于不同的被称呼的对象。old?girl一般用于丈夫叫妻子,但我在Brighton?Rock一书中还发现这个词可以用来代替“妈妈”(……the?old?girl?might?have?a?word?for?him。)。old?chap一般用于称呼老朋友,但我在阅读中也发现父亲用以叫儿子的例子。这些称谓语如何译成汉语,实在大伤脑筋。但反过来一想,汉语中还不是同样存在种种稀奇古怪的叫法吗?丈夫如何叫自己配偶(或对第三者谈及自己的配偶)就是一件令人头疼的事:“我的爱人”“我的老伴”……几十年前倒有不少解决的办法,从“贱内”到“孩子他妈”,或“喂”到“内掌柜的”,有大量用语可以选择。但是随着社会的变化,很多词已经从语汇中消失了。学习外语又何尝不然?
包括在称呼这一研究项目中还有亲属的名称(有哪个英语翻译工作者不为cousin一字为难?)和存在于不少语言中的成对的单数第二人称代词(一个表示尊敬,一个表示亲昵如德语的Sie-du,法语的Vous-tu,意大利语的Lei-tu,俄语的Vy-ty等等)。初学翻译的人常常会不假思索地把表示尊敬的代词译为“您”,另一个译为“你”,但是问题绝不这么简单。社会语言学对这一对代词——从历史发展到各个民族的使用惯例——进行了研究,有助于我们如何选择汉语的译词。
社会语言学研讨的领域远远不止一个称呼问题,它研究社会(社会发展)与语言(语言发展)的关系,研究语言由于社会环境不同、由于说话人的社会地位不同而产生的种种差异。有人开玩笑地说,社会语言学研究的只是一句话:Who?speaks?what?language?to?whom?and?on?what?occasion?倒也不无道理。社会语言学叫我们注意到不同身份地位,不同文化程度(尽管是同一民族)的人使用的言语不同,而且就是同一个人在不同场合(对上级、对朋友、对妻子、对儿女)言语也有差别。翻译工作者有必要注意语言的这些变体。但这一点,我个人认为,也可以归在下面谈的语言风格一项去。
3.风格问题。同语义学及社会语言学相比,风格学是一门古老的科学。欧洲风格学虽然建立于18世纪,但早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就写过《修辞学》,有人认为风格学就是从修辞学发展而来的。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出版了一本不太引人注意的小册子《文学风格论》(印数四万二千册,并不算少),收了歌德等四篇文章,据译者王元化谈,这是他从库柏编译的一本英语《文学风格论》中摘译的。可惜笔者没有读过原书,但想来西欧对文学风格的研究是很有一段历史了,我国《文心雕龙》和《典论论文》虽然是文学评论的专著,但对文体和风格做了不少精辟论述。《典论·论文》中提出的“本同末异”,用今天的话解释,就是说作家的创作个性与文学体裁要求在统一的文学语言中有不同的变体。但这两部书在谈论风格时,着眼点主要在文章体裁。依笔者的浅见,风格似乎可以分为五个层次:民族风格、时代风格、作者风格、体裁风格和作品(特别是小说和剧本)中人物的语言风格。我不认为这是一个很恰当的分法,因为这几重风格并不是并列的,五重或五重中的几重常常互相叠合,通过最主要的一层——作者风格表现出来。另一方面,在同一层次内又会出现极为复杂的差异。譬如说,同一时代(或甚至同一流派)的作家,其文章风格也绝不会是千人一面。同一作家也可以写出不同体裁、不同风格的作品,甚至在同一部作品或同一章节中风格也可能转换,从庄严转为幽默,在讽刺中也可能突然夹杂着一段抒情的文笔。对于翻译工作者来说,最重要的一点是提高自己的辨识力,首先炼就一双“慧眼”,发现原著的风格,进一步再在译文中尽量求其体现。
说来容易,追求译文在风格上的“神似”可能是一个译者毕生的目标。只举一个常见的情况就可以说明风格再现的困难。凡是翻译美国文学的都会遇到黑人讲的美国英语,在译文中该怎样表现呢?读一点社会语言就会懂得,She?Like?him?very?much。He?don’t?know?a?lot,do?he?只是与标准英语不同的一种变体,而不是有语法错误的句子。难道能用支离破碎的汉语翻译原文吗?即使不翻译美国文学,英国文学作品中也不乏满口方言的人物。有的翻译家试图用我国的某一地方话来体现原著中的方言,效果又如何呢?可能在读者的脑海里出现的是一个山东大汉或者说苏州话的小娘子,而不是一个苏格兰或爱尔兰的农夫农妇。看来翻译工作者还需要探索出一点比“俺”和“啥”更能表现原文的词语来,但是答案至今还没有找到。
另一个值得探索并且有争议的问题是,译者的风格如何与原作的风格统一起来,每一个从事文学翻译的人都有自己喜爱的词语、句型或表现法,一句话,有自己的文章风格。译者是否应该尽量抹杀自己的个性,以重现原著的风格为最高任务,还是允许译者在体现原作风格的基础上“呈现”译文的风采,以“便于各种翻译风格的形成……繁荣文学翻译事业”(引自某一探讨翻译风格的论文)呢?可能这个问题一时得不出结论,需要更多的讨论和翻译实践才能逐步解决。但是我想,没有一个认真从事文学翻译的人敢于公开声明:翻译就是再创造,可以撇开原作的风格。
(198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