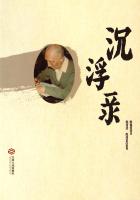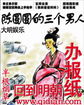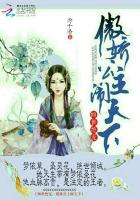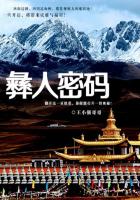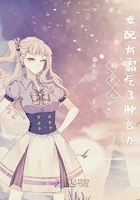表述、言说和命名正在当代遭遇着前所未有的困难。
我常常不知道自己到底可以说些什么,以及究竟说些什么才好。徐敬亚说,天空中飘满了观念和命名(这一句式,令人不由得回想起当年北岛“天空中飘满了死者弯曲的倒影”这句诗,但指涉的对象却完全不同了),但真正的东西却在别处,观念和命名已成了阻隔真实的一道严实的障壁。我还注意到了程光炜宣读论文过程中的几度中断,在我看来,这种不由自主的言说中断,是言说者发现真实不肯就范或逸出于自己预先设下的言说罗网时,所表露出来的一种错愕和踟躇。
说句极端的话,我始终觉得,真实不在或根本没有出场的地方,恰恰总是言说最为稠密和缠绕的地方;真实一旦出现,言说便会有如无边落木,萧萧凋零,因为此时的言说已显得多余。
在真实面前,任何言说都不能不是个累赘。这一情形,使我们对言说的功能和意义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沮丧和灰心,但另一方面,我们言说的欲望和势头却并没有因此而出现丝毫减弱的迹象。可能情况正好相反,出于捍卫和挽回人在言说上的自尊心的目的,言说的尴尬和受挫,反而激发起我们对言说的更为强烈的征服欲,新的一轮言说攻势将会由此而被重新挑起。人在任何处境下都是不会轻易服输的。只要真实不露面,这种言说攻势就可能一波一波永不停息。由此联想起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结尾处那句有名的话:可说的其实都是不必说的,而不可说的却只能对之沉默。其实孔子也早已说过类似的话。一次他和子贡不知为了什么事争执起来,情急之中大声嚷道:天何言哉!四时行焉,万物生焉。天何言哉!但事实上他老人家并没有说到做到,就此闭起自己的嘴来,一部《论语》记满了他东颠西踬、诲人不倦的絮叨。圣人尚且如此,我们不是圣人,自然更做不到。
以下的话,很大程度上,便是在维氏“不必说”的境况中说的。
谈论中国现代新诗,不能不涉及它与古典汉诗的关系这一敏感而又异常缠绕的话题。原则上我比较认同臧棣的看法:这里边绝不是一个继承者与被继承者之间的简单关系,所谓“创造性转换”,也绝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容易,认真追究起来,可能性甚至颇为可疑。但我也不想把话说得像臧棣那样决断。在我看来,与其将它们看作是一种二元对立、互不相容的紧张关系,不如看作是一种差异性关系,这一关系的重点是互为参照,互相阐明,互相对应,互为背景和界限,而不是继承与被继承、臣服与被臣服,更不是模仿与被模仿的关系。我的理由将在后面述及。情况也许更有可能如王家新所说,是一个“互文”过程:并没有一个现成的传统事先放置在那里,等着你去作思乡式的重返,传统很大程度上有待于我们当下的重新发现,本质上属于我们的创造物之一,所谓的传统,说白了,其实是我们这些子民一手抟造出来的“父亲”。
这里其实有两个问题可以追问。一个问题是,古典汉诗,它的可能性,其内在的诗意言说能量、感性和知性资源,是否已经开发殆尽?另一个问题便是,中国现代诗的可能性,它的内在诗意言说能量,感性知性资源,是否已经为我们所穷尽?
就前者而言,显然未必。郑敏先生近年来不满于中国现代诗不断增殖的简陋和贫乏,其令人敬畏的真心焦虑以及孜孜汲汲于对古典诗意的重新眷念和汲取,自不待言。更为直接的个案性举证,则有已故聂绀弩先生的《散宜生诗集》和荒芜先生的《纸壁斋集》及其续集。近在眼前的例子,还有骆寒超教授的十四行诗新作(收入《三星集》,即出)。这次开会我有缘与他同住一室,得近水楼台之便,寒超教授让我提前读到了它们的校样。我读时的直觉是,有一种久违了的古典诗意扑面而来。也许从福柯“知识构型”的角度上讲,由于当下年轻写诗者的知识构型已经改变,这种古典型的诗意在他们的诗学中可能已看得不怎么重要,甚至还会有意无意地加以轻慢,他们更看重的是现代思辨和心灵追诘的深度。程光炜论文中已征引的王家新《帕斯捷尔纳克》一诗中的两句诗,蕴含的正是属于这一知识构型的强烈诗意:“终于能按照自己的内心写作了/却不能按一个人的内心生活”。它言说了时代的严峻和诗人内心的庄严。读这样的诗句的感受,借用程光炜他们喜欢用的说法,是一个持久的惊喜,借用王家新常用的一个说法,则不啻是在内心深处听到了一声响亮的召唤。但像十四行那种显而易见的古典诗意的流失,毕竟是件令人惆怅的事。
现代诗在中国的历史,至今尚不足百年,与古典汉诗在时间长度上无法等量齐观,因而一味以这段新诗的流程,以及在这段时间里形成的诸多范式作为正在无限延伸中的中国现代诗的最高范式和唯一根基,至少从时间的尺度上说,根据不充分,换句话说,我们似乎没有理由以“五四”以来的新诗当作中国现代新诗的根本或唯一的传统。
另一方面,更值得检讨的是,中国现代诗这一言说方式,迄今为止,它本身的一些最好的、最有价值的方面,是否已经或正在为我们所触及和穷尽?是不是情况恰恰相反,它自身的资源,那种真正的诗意言说方式,至今根本还未为我们所洞悉和触及,自然更谈不上开发和使用?我想,处在这样一种情况并不明朗的境况下,我们似乎不必草率、匆忙地急于换汤换药,好像一感到现代中国诗言说方式的贫乏,便毫不迟疑地动念到古典或别的什么地方去搬救兵,好像真会在什么地方总会事先现成地替你备下了保治百病的救治方案可供你随时挪用似的,而事实上这种方案的所在,不过是出自病急乱投医者的心理幻觉。因为最清楚不过的是,古典诗意或别的什么诗意,与中国现代诗的诗意之间,分属不同的文化构型和知识构型。在这一点上,我很欣赏臧棣对中国现代诗的自足自律性所作的提示。任何事物的存在都有一个自我存在的理由,现代中国诗同样如是,它面对的是自己的处境,从根本上说,需要解决的是非己莫属的困难,问题更应该,并且也只能在自身所属的构型中去寻求探讨和解决,也就是说,中国现代诗所遭遇的困难,最终恐怕是无法指望由中国古典诗学或现代西方诗学来越俎代庖解决的。
今天,人们在评说或揣想中国现代诗的现状或前景时,差不多已经理所当然、不约而同地接受了古今中西交汇贯通之类的谈论,事实上这已经成了一种不折不扣的惯性视角。但越是容易谈论和接受的说法,往往就越是值得对之提出追问和质疑。中国现代诗的诗性资源,究竟真的是像人云亦云的那样山穷水尽贫乏不堪呢?还是问题更主要出在至今尚未有多少人对其真正的资源作出准确的触摸和开发?实在值得反思。与古典和西方诗学保持不间断的交汇融合,可能不失为一种补苴弥罅的方案,但更为主要的一面,即中国现代诗真正的动力源,只能是立足在自身资源的开发上。孰主孰次不能颠倒,是源是流不可混淆。事实上,任何改头换面的复古诗学和移植诗学,都救济不了必须由中国现代诗自己来作出承当的命运。一个自身没有存在论意义的东西,是不值得存在在世的。如果中国现代诗本身就是一个坚实的存在,那么它就是一个既非为他者,也非靠他者而存在在世的在者,无论这个他者是指中国古典诗抑或指当今别的什么国度的现代诗。
那么中国现代诗的言说根基,它的精神立场和出发点究竟在哪里呢?意象化方式,特定的感性知性结构,语词的配置和选择,以及韵律、节奏和隐喻……,所有这些方面固然都十分重要,但在我看来,它们基本上还属于具体操作层面,套用张之洞那个有名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体用概念,它们还只是一个“用”的范畴,那么它的“道”体精神是什么呢?我以为应该是对差异的坚持。在文学中,乃至在人的全部精神活动中,诗无疑是一种最个体性的东西,真正的诗性,诗的道体精神和言说方式,只能存在于诗人在差异中、在边缘处对个体精神立场的坚守之中。诗当然也有自己的认同,也有它自己的传统,但这种认同绝对不可能是对已有言说方式的认同,也不可能只是对传统知性/感性结构及抒情/意象范式的重返和依归。诗恐怕是世界上最不可以以己范人,同样也不可以以人范己的东西,诗和诗人将注定只能在一种不可重复、不可替换的差异状态中彰显自己。要说传统和规范,我以为这恐怕才是诗真正的传统和规范之所在。卡夫卡的变形记,对格里高尔来说是场灾难,但对诗人来说,恐怕不仅仅只具悲剧的意味。守住差异,拒绝和远离同化,应该是诗人不得不在内心所承受的最沉重的压力之一。写诗与其说是一门专业的积累和一份不断趋于成熟的技艺,不如说是对充满疑问的边缘地带永无尽头的迁徙和探险。现代物理学提出了熵的概念,自然生存秩序始终是个增熵的过程,趋同、规范、体制化、避难就易、求安逸、求平稳……,趋同的结果便是热寂,是耗散。诗在本质上是反熵的,其反熵的动力,即来源于对差异的坚持和对一切同化迹象的异常警觉。因为兼并和同化,只会给诗带来最糟糕的同义反复,除了向人出示虚假的稳定与和谐,使诗变得再也不会感觉和质询,不能形成新的思想,更不用说与别的思想之间的相互砥砺,它就再也不可能提供其他的东西了。
这几年间,从欧洲归来不久的诗人王家新,为我们写下了包括《卡夫卡的工作》《另一个维特根斯坦》在内的一系列因强烈地释放着内心尊严而令人惊异的文字。在这些文字的背后,诗人置身在生存的裂隙、边缘和差异处,那深度搜寻的眼神和沉静于思考的身影,因闪烁着思想在掘进中的力度和锋芒而显得格外的清晰动人。我想说,王家新这几年的诗文,是我近年所能读到的诗人对于我们所置身的这个时代状况最为深刻的剖析和警示之一。在《卡夫卡的工作》一文中,家新向我们出示了一个在此之前一直为我们所忽视的问题,即卡夫卡的“难以归类”。在另一个地方,他将他的这一独见作了这样集约性的表述:“在卡夫卡那里体现出的‘存在的勇气’,在我看来还意味着敢于把小说写得不像小说,从而在一种艰巨的历险中体现出叙事的可能性。”接着他诘问道:“那么,为什么我们不试一试?为什么我们总是画地为牢,而不让文学呈现出它本来的自由?”(《夜莺在它自己的时代》)正好前一段日子,我受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世纪的回响”编委会之托,承担了梁宗岱诗学文集的编缉工作,整个过程有幸得到了手头庋藏有梁先生几乎全部遗作的“七月”诗人彭燕郊先生无私的支持与呵护,这段经过我已把它写进了另一篇文章,这里不再重复。我想说的是,请益中,燕郊先生寄赠我一册他自己印制的非卖品长诗《混沌初开》,这个似乎有意违拗诗的整饬体式而写就的长篇巨构,同样激起了我内心一种持续的、隐秘的惊喜。如此迥然分属于两代的诗人,却在当今之世不约而同地作出了殊途同归的选择,这一事情的本身就足够让人寻味的了。这与其说是出于有意识的精心的选择,不如说是诗人无条件地听命于早已深深植根在生命本能之中的坚持差异这一诗性原则召唤的结果。他们无须像奥德修斯那样,将自己捆绑在船桅上,以抵御内心的呼唤。
把诗写得不像诗,或者不在乎自己在写的是什么文体,只要足以保证自己是在一种明显确切的差异状态中对这个世界言说,发出自己独特的声音,对他们说来,再也没有比这样一种足以保持一种精神自治高度的言说方式更具吸引力的事了。坚持在差异中的写作,是一种因心灵始终保持本质上的独特而显出令人欣羡的多面性和无限性的写作,这种写作如同写作者的思想和生命,永远逸出在现成的言说罗网之外,没有一张现成的有关诗的地图可以有效地标出它的位置,它使诗对世界的解释,自始至终具有一种复调的性质,而使一切意在将之纳入某种固定程式中的惯性力量归于失败。情况正如布罗茨基所言,在一个不再拥有中心文明的时代,保存文明的工作总是由身处边缘的人们来默默完成的,与人们一直深信不疑的情形正好相反,“边缘地区并非世界结束的地方——而正是世界阐明自己的地方”(《潮汐的声音》)。而我想说的是,维系着创造的尊严、智慧的高贵和在独见中对真实之物的洞悉,有意识地扩大着诗的感性/知性、追问/自我追问、对复杂性的认知、宽阔的想象力、对真实世界给予重新的读解和发现的,不可能是别的什么人,而只能是那些始终坚持在差异中的写作者。
与他们的写作相比,也许当代不少写得很像诗的东西,往往与真正的诗的道体精神显得风马牛不相及,距离更为遥远。那么究竟谁更是诗呢?答案显然已不言而喻。
来武夷山的前几天,在翻检一沓近时出版的杂志时,无形中被《天涯》上深圳王小妮的一篇东西吸引住了。它里边的一些相当朴素的想法一下子打动了我(我很高兴王小妮已把它带到了这个研讨会上作了分发)。从文体上你可以说它是散文,或随笔、絮语,但我以为从道体精神层面上说,可以说在它体内流贯着一种外人也许不易察识的真正的诗性精神。这篇东西名为《木匠致铁匠》。作者虚拟自己为一个淳朴的乡村木匠,他对自己干了多年的行当突然产生了厌倦和疑虑,便关了店铺门,弃家出走,在乡野里四处游荡,并由此引发出许多感悟。诗人的情况也是一样。在王小妮看来,在这冒名诗人者以及那些“显而易见地可以看出里面心灵与精神的怯懦”(布罗茨基语)的诗作滔滔者天下皆是的时代,沉默下来,或弃家出走,作出位之想,也许这才是一个真正的诗人所该作并且唯一值得认真去做的一件事。
从浮华的所谓主流和众声喧哗中抽身退出,在任何情况下也不轻易将不可剥夺的个人阐释权让渡与人,在一种前所未遇的新的限制和压力面前(如人文知识者在商业轴心时代所面临的消费性通俗文化的全面挑战,以及自身专业化、职业化的常规生活所带来的思想锋芒和精神视野的渐次狭窄、迟钝和泯灭),继续作出自己的感知和思考……,这跟我上面所说的,坚守在差异中,自始至终拒绝来自任何理由的兼并和同化,是当代诗人真正必须正面承担的内心压力,正是相近的意思。
我还要藉此机会对王小妮表示我由衷的谢意,因为她所讲述的这个寓言,使我对布罗茨基曾经作过的一段自我描述有了较为真切的理解,而在此之前,我对它的了解其实并不像想象中的那么了然。布罗茨基是这样说的,诗人绝不是一个遁世的人,但他对现实世务的关注采取的往往是跟别人不一样的方式,他称自己是“一个离群索居的人,一个珍重独往独来的自由而看轻抛头露面机会的人。”
王小妮一手虚拟的这个故事中的木匠所作的出位之想,也许就学理上推究的话,还欠单薄,因为其实庄子曾经说过的一些话要比她来得远为玄妙和深刻,并且里边有一处直接照搬的庄子的话,作者的白话解释显然出了错,但作为一种诗人坚守在差异和边缘中的立场和姿态,一种力拒同化诱惑的精神意向,我还是格外偏爱和佩服。
不必专家,也不必有出众的感知力,只需多少还具备一份正常的感知,我们将不难察觉,自80年代末90年代初起,中国的诗正在或已经发生着一场悄然而又深刻的构型转变。一种坚持在差异中的写作迹象正在渐趋明朗。我不想对此作出过于乐观的推测,至少目前我还做不到这一点。事情该怎么样就是怎么样。乐观也好悲观也罢,都于事无补。我只能说,也许以此为契机,中国现代诗正在为我们掀开一个重要历史时刻的一角帏幕。
李振声
(据1997武夷山现代汉诗研讨会发言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