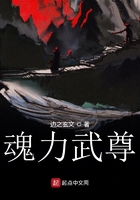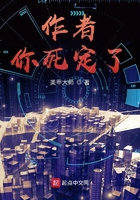眼见木桩没有把我拿下,雄山魈冷笑着,把双手猛地一拍,旋即错拧作握手姿,竟似在施展“寅字”手印。
这手印才结下,我身遭的那些大小木桩登时如被激怒的幽灵怨鬼般左右交互着摇攻摆撞起来。
这癫狂的攻击是虚招也是实招。
但目的却很相近——都是要致我于死地。
现在,木桩交互如牙,俨然成了一个巨大的木桩囚笼。
前前后后急冒而出的大小木桩不下七八十根,我早先未能及时闪躲出去,等到后面木桩交互攻击起来,哪里闪躲得了那么多,半柱香不到的光景,身上便挨了好几下撞,如果不是怀里揣了一面被宁平和尚改良过的地玄镜(现在它除了能更好地吸收直接击打在镜面上的伤害外,还能自主吸收胸背间受到的一部分击打伤害),哪还有什么余力想着扳回局面,怕是只能喘息着蜷缩于一角,沦为那雄山魈齿牙下一块块血淋淋的大肉了。
连施了好几个术,雄山魈似也有些疲倦,它一时间也没有别的大举动,只倒提着那个布满尖刺的大棒槌围着木囚笼绕圈子。
我双手抡剑,一阵猛劈猛砍,把近身处的木桩砍下八九根来。
这木桩大多碗口大小,颜色一例黝青,看不出是什么木材,但质地却相当坚实,并不亚于淬火冶炼过的铁与钢,猝然间,连这剑锋锐利的巨阙劈砍下去也有几分吃力。加上容身的地方又窄小,难以展开身形,是以,用出去的十份气力中真正起了作用的尚占不到一半。
只砍得二三十下,我便大汗涔涔,双臂间也有些酸痛。
照这样劈砍下去,木囚笼并不是破不了,但捱到出去之时,整个人即便不是精疲力竭,也绝难好到哪里去。
到了那时,不用雄山魈出手格杀,我自己就离死不远了。
雄山魈这会儿气咻咻地叫着,目中凶焰逼人。
我被困住,一时不出去,这是个坏消息,好消息则是木笼子对雄山魈也起了阻碍作用,它一时间也难以攻进来。
雄山魈的眼珠转了转,嘴里呜哩呜哩地低哼着,一边围着木笼绕圈而行一边轻轻拍打着身旁的木桩。
它的动作看起来很随意。
但它的用心却并不随意,里头潜藏着都是杀意,满满的杀意,令人悚然的杀意。
略一慌神的工夫,那些被它拍打过的木桩便刷刷刷地生出许多枝条来,倘若只是长出许多枝条来,倒也好对付,问题在于那些枝条都是张牙舞爪着向我的藏身处蔓延而来。
更要命的是那些枝条还在急变中,生出许多极尖极细极密的小刺来,刺尖上跳动着瘆人的绿光。
五行之中,对木克制作用最大是金而不是火。
而我被困在层层木桩之中,想用火来破这木笼更是难上加难。
可是,尖刺在急冒。
可是,尖刺也在急长。
下一瞬,也许它们就悚然暴射,把我刺成一个大刺猬……
形势凶险万分。
这样特殊的时刻。
这样要命的场合。
一个人若是想活下去,只能用一种亡命的打法。
心念疾转,悲壮又毅然,我掐出火诀,召唤出六个小火球,它们先是在木笼外急速盘旋上升着,接着便有一个疾若闪电地朝雄山魈俯冲了过去。
雄山魈的嘴角上挂着一点讥讽的笑意,也并不闪躲,只把那大棒槌朝那火球狠狠砸去。
毫无悬念的,火球被击个粉碎,流火四散,有几团火碎竟把木笼外围的一两根木桩引燃了。
我屏息凝神地遥控着第二个火球朝雄山魈急急撞去。
大棒槌的黑影一晃,火球轰然而裂,迸裂出许多碎炎火屑。
散落到木桩上的火更多了。
雄山魈狐疑地瞅了我一眼,忽地咧开嘴如癫似狂地欢嚎起来。
一个被困在层层叠叠的木笼中的人,竟以火来破木笼,说这不是引火烧身,坐等****,只怕很少人会相信。
确实呢,有那么一会儿,连我都觉得是不是自己脑子进水了。
如果不是,怎么会想出以火烧笼这样凶险的招儿。
这会儿,有好几根木桩哔哔啵啵地烧了起来。
热浪灼人。
我沉着脸把两个火球齐齐导引而出。
要来就来狠点。
以火破木,本就是险中求胜的打法。
破风声中,第三、第四个呼呼作响的火球一快一慢向雄山魈飞去。
雄山魈的大棒槌已经挥出,但两个火球却突地转出一个弯,斜斜的向木笼着火处的几根木桩撞去。
雄山魈似已猜到我的一些心思,它怒吼一声,往地上只狠狠一踩,又是嘭嘭嘭数声响,一大排的木桩破土而起,森立在那着火处的木桩外围。
这下木笼更不好破了。
木桩才冒出,雄山魈已长纵而出,反手把大棒槌甩抡了出去,嘭声乍起,急飞的一个火球被砸个粉碎。
另一个火球很突兀地急转了一个弯,朝雄山魈撞去。
雄山魈哇哇怪叫着躲开了袭来的火球。
这一刻,它的一对绿眼里跳动过一团火焰,不,也许不止一团,而是两团。
原本盘旋在木笼上空三四丈高的两个火球已融合成了一大个火球,砸落在木笼的一侧。
与之同时进行的还有巨阙的全力一刺,电光火花交替之际,木笼轰然塌落出一个缺口。
嘭。
大木笼成了一个大火笼。
火舌张扬。
火势汹涌。
火焰冲天。
雄山魈已拿回那根冷冷的大棒槌,倒拖在地,刺出一串低沉的嘎嘎声,它怔怔地望着眼前这一大片吞吐跌宕的火焰。
这时候,它的脸上会挂着怎样的表情呢?
一种将仇人逼入绝境后的满足感?
一种目睹木笼烧成火笼的悻悻然?
很抱歉。
我答不出来。
因为刚刚那一下“隐步”蹿出了十来丈的距离——比我以往任何两次的“隐步”的最佳表现加起来还要多。
我的心砰砰狂跳着。
惊讶?
欢喜?
庆幸?
还是兼而有之?
这会儿,我的注意力并不在雄山魈的身上。正如,它的注意力也不在我的身上一样。
在火球和燃烧木笼崩塌前,在好不容易才打开的缺口被火焰吞噬前,我瞬身闪了出去,完成了连自己也不敢相信的惊魂一逃。
我的气才平复了一点。
那冲天的火焰旁突又飘动起一团翻飞的烟尘。
滚滚热浪与烟尘之,有一个黑影狂风般奔蹿而出。
雄山魈发现了我!
尽管,它的脸上也很有些倦色。
那百十根的木桩和那枝条木刺本不是多么省力的招数。
或许问题并不在于招数是否省力,而在于一个人为了存活下去所迸发的强大的不确定性,以致于把它的计划谋算都一一打乱了,起初它以为木桩能重创我,可是没有;接着它以为重重的木笼能困死我,仍是没有;最后它以为那些急生而出的枝条和毒刺能把我逼入绝境,结果还是没有——这时,它已很有些不耐烦了。
人们总以为不耐烦这种情绪不会造成什么麻烦。
其实不然。
有的时候,只需一丁点的不耐烦就会造成足以致命的大麻烦。
比如说,在战场上,你原本是胜券在握的,可是你被你的对手一步步打乱了原有的节奏,让你一直在运转在谋划的心起了一点点的变化,如微风之下的水面般生出涟漪,一圈一圈地荡出去,荡出去,渐渐演变成一些些的不耐烦,一些些的焦躁激动。
公允地说,我的破笼而出,既惊险也狼狈。
在我本人的回想里,狼狈更是要远远多于惊险。
对手的提前察觉与几番迅疾行动几乎让我葬身在那一片火海。
但雄山魈却似乎不这样认为。
它好像觉得我一直在悄没声地耍弄它于股掌之间。
所以,它变得很愤怒。
它的吼声如雷,震得人目摇身晃。
它把偌大一根棒槌挥动得如风如龙如狂蟒,气劲之大,激引得沿途的碎石草屑都似喝醉酒般的狂跳狂舞。
可惜,它的对手我好像怯场了,一直在躲闪,一直用着一种奇怪的步伐和身法与它周旋,甚至在那如癫似狂的击打前,面上还始终带着一种微笑。
它的气力和状态仍是在我之上,却一直没打中我。
很快地,它被撩拨得暴怒起来。
我现在好像变得极其胆小懦弱,成了焉头焉脑、纯纯粹粹的一个胆小鬼。
雄山魈则不一样,斗志迸发的它已经连挥带扫地攻出一十六招大棒槌,期间还试着踢出两次猛踹,三记连砸带撞的长拳。
打了,没打中对手是一回事。
气息渐喘却是另一回事。
看到我的闪躲渐渐显出一些迟滞,雄山魈把大棒槌猛地抡起,狠狠砸下。
碎石激射。
电光火石之间,我堪堪躲开了大棒槌的怪力一击。
雄山魈咧嘴怪叫了起来,好像很开心似的。
它确实有开心的理由——我的左肩已被大棒槌上的三两根尖刺刺中,殷红的血如箭般飚射了出来。
不过,雄山魈好像忘记了这里能伤人的武器并不只有它的手中那个长满红色铁锈的大棒槌。
它好像也忘记了,我右手里那一柄一直或拖或拉的巨阙剑并不是用来躲闪的。
所以,它那很好像很开心的怪叫声忽地停了下来。
我骨子里的血性被彻底地激发了出来。
我要以牙还牙!
以眼还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