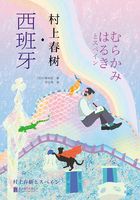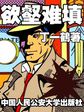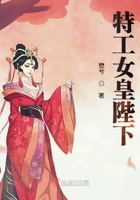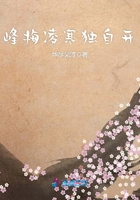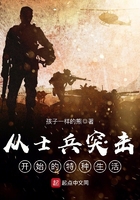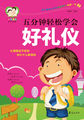以上是將性情分而言之,其實宋代對情進行規範後,性爲體,情爲用,二者皆依歸於天理,情也就與性合二爲一了。袁燮《絜齋毛詩經筵講義》卷一《詩序一》謂:
夫寂然不動之謂性,有感而發之謂情,性無不善則情亦無不善,厥名雖殊,其本則一,故孟子道性善,而又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禮運》一篇,孔子之遺言也,謂“喜怒哀樂惡欲,是七情者,弗學而能,人之良能也”,豈有不善者哉?大序之作所以發揮詩人之蘊奧,既曰“吟詠情性”,又曰“發乎情,民之性也”,合二者而一之,毫髪無差,豈非至粹至精,同此一源,不容以異觀耶?
也就是袁變所說的“厥名雖殊,其本則一”,“同此一源,不容以異觀”,也就是“性”與“情”有著本源的一致。但並不是說可以隨意發瀉情緒,這裏的性情皆善說有一個內在的規定,即“直已而發,粹然一出於正”,他這裏所說的“性”是“寂然不動”“粹然一出於正”的性,也就是這裏的“性”本然地具有善的性質,而“情”由這樣的“性”而外發,源的純淨一定程度上保證了流的清澈,所以有情亦無不善之說。所以宋代論詩與情性的關係,一般是將情性合而言之的。
宋代心性之學興,不僅在於對心性的探討,更在於對心性的提升,對於“氣質之性”必“反之”,使歸於“天命之性”,也就是李翺所說的“復性”。但作詩畢竟與心性修養又不同,因爲“性”爲“未發”,而詩則必須“發言爲詩”,屬“已發”的範疇,不能完全以“性”來要求,但只就是“情”來要求,又陷於矯僞,唯一的辦法就是對“情”“性”同時進行要求。
(一)止乎禮義
我們知道宋代以前要求對詩中所體現的“情”的進行規範的觀點主要是《詩大序》的“發乎情,止乎禮義”之說,這一提法在重情的六朝和唐代並未發生多大影響。而隨著宋代新儒學興起,“止乎禮義”的旗幟當然應該重新舉起。蘇籀(1091-?)《皇甫一首》:“灌溉所短誇雄渾,篇什性情禮義根” {《雙溪集》卷二}認爲詩歌須以止乎禮義的性情爲根本。姜夔《白石道人詩說》有謂:“吟詠情性,如印印泥,止乎禮義,貴涵養也。”他認爲詩人的情性與詩歌之間存在高度的一致性,也即他所說的“如印印泥”,所以當對情性進行規範,而“止乎禮義”則爲情感外發的規範標准。道璨《柳塘外集》卷三《營玉澗詩集序》謂:“詩主性情,止禮義,非深於學者不敢言。”認爲詩歌以性情爲主,但須以禮義爲規範,說的也是一個意思。“止乎禮義”成爲“情”的必要規範。
但漢儒“止乎禮義”終究只是將性情設定一個外在規範,與宋代從心性中和來要求詩歌距離甚遠,宋人更爲重視的是個人的修養來對性情進行自覺的疏導與規範,事實上上引蘇籀是將禮義與“灌溉”結合在一起的,姜夔在“止乎禮義”之後提出“貴涵養”,道璨在“止禮義”之後,更提出“深於學”的要求。他們都不將禮義視作一種外在規範,而更多將之內化爲個體的自覺修養。
(二)束其情性
宋代儒學興起,心性修養成爲時尚,士人們自覺對情進行約束,魏了翁《跋邵康節‘檢束’二大字》: “二字下注云:檢謂檢其行止,束謂束其情性。”{《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四} 提到邵雍自書“檢束”二字,表示自覺對情性進行約束是心性修養的重要方面。
“止乎禮義”的說法終究只是將性情設定一個外在規範,而沒有從性情的本來屬性來討論問題,而宋代詩學認為只有人之本性來談情感規範才能得其根本,故更深一層是從性情本身出發來規範的。
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中節謂之和,詩所以吟詠性情而已矣,感物而動,矢口而言,不失其性情之正,斯可也。(方逢辰(1221-1291)《蛟峰文集》卷六《汪稱隱松羅集序》)
詩本源於性情之正,當其遇物興懷,因時感事,形之於詩,何嘗拘拘然執筆學似某人而後爲詩哉!蓋所蓄既深,自有不期似而似之耳。(陳普(1244-1315)《石堂遺集·郭麟孫祥卿集》)
可見在宋人觀念中詩不僅“吟詠情性”,還得吟詠“性情之正”才行。只要得“性情之正”,自然發爲詩,不求工而自工。可以發現宋代對性情的規範還有一種說法即是“正”,我們在緒論中提到“中和”本身包含了“唯義所在”的含義,即“詩可以怨,當怨而怨,不害於義理之正。”{陳埴(1210年前後在世)《木鍾集》卷二《孟子》}通常意義上的性情之正,即有一個“合理”的問題。陽枋(1187-1267)《字溪集》卷三《與蘇坤珍書》謂:
大率正變萬殊,只情性二字,而風、賦、比、興、雅、頌,各隨時隨事,或可直陳,或當譎諫,皆流行一正理而已。
陽枋謂無論詩之體裁、技法、表達方式如何,“流行一正理”,於理則同,既然唯以正理流貫其中,性情自然中和。林景熙《霽山文集》卷五《王修竹詩集序》謂:
古者,閭巷小夫,閨門賤妾,其詩往往根性情而作,後之士大夫反異焉,何也?詩,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無邪者,誠之發,當喜而喜,當怒而怒,當哀而哀,當樂而樂。《匪風》、《下泉》之思是也。《大序》言:“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不變者猶於變見之,謂非豐鎬遺澤可乎?
林景熙所謂“無邪者,誠之發”,有“真”的涵義,也就是自然而發。“當喜而喜,當怒而怒,當哀而哀,當樂而樂”,這個“當”裏也暗含了一個“義”。義者,宜也。只有合乎義理,才能算“當”。這樣,他們就將性情與義理結合起來了。合乎義理的性情當然是中和、正、無邪,這裏所謂性情之正也即指以義理爲准的性情,當然也是合乎中和的要求,可證“正”也就是“中和”,性情之和也就是性情之正。
而所謂的“性情之正”,顯然也就是“思無邪”了。文天祥(1236-1283)《題勿齋曾魯詩藁》:“勿夫子語顔以作聖工夫也,作詩亦有待於此乎?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詩固出於性情之正,而後可。”{《文山先生文集》卷十}可謂思無邪即性情之正。文天祥《羅主簿一鶚詩序》又謂:
詩所以發性情之和也,性情未發,詩爲無聲,性情旣發,詩爲有聲。閟於無聲,詩之精,宣於有聲,詩之迹。{《文山先生文集》卷九}
此處“未發”“無聲”之詩,即是性情,“已發”而“有聲”之詩,則爲詩歌。文天祥將未發無聲的性情稱爲詩之精,即是認爲性情爲詩之本,這亦爲宋人常見之論,不足爲奇。只是他提出“詩所以發性情之和”,則可視爲對“詩固出於性情之正”的一個絕妙闡釋。宋人不倦於探討“未發”“已發”的奧義,按照宋人的邏輯,未發爲中,已發而皆中節爲和,所謂的“節”也就是“宜”的尺度問題。文天祥所謂作聖工夫以作詩,即意在於修養而得性情之正。我們知道儒家的尺度也不過是“禮義”,所以說性情之和、性情之正與原有的“止乎禮義”並不衝突,相反卻是“止乎禮義”的內化。文天祥此處將詩的功能定在“發性情之和”,可謂爲宋人對詩歌與中和性情之關係的最爲典型的表述了。
我們可以看到,與上述對情的限定一樣,宋人對“性情”“情性”加了種種限定,性情必須歸於正,才能爲詩之旨。“止乎禮義”、“性情之正”、“思無邪”、“性情之和”。總而言之,無非兩端:一是中和;一是禮義。宋代雖然也提止乎禮義,但宋代所指的禮義事實上已經內化爲性情的修養,不象漢代所指主要爲外在的禮義。
我們注意到《大序》在提出“在心爲志,發言爲詩”、“吟詠情性”、“發乎情”等一系列命題時,顯然是視其爲同一的,正如吳翌《澄齋問答》謂:“夫性也,心也,情也,其實一也。”{《宋元學案》卷四十二《五峰學案》}心志事實上可以概括情性二端,朱熹所謂“心統性情” {《朱子語類》卷九十八}已明言之。既然詩爲心志之外發,那麽詩的性質與風貌則直接受到心志,也就是性情的制約。
三、如印印泥
這樣我們可看到,中和、正、無邪、誠可以統一起來了,它們都是著眼於對性情的規範,要求性情與天理相合,真實無妄,中正平和、不偏不倚,成爲真與善的統一體。宋人認爲性情爲本,而詩爲末,如上引文天祥即認爲“閟於無聲,詩之精,宣於有聲,詩之迹。”“本”的中和,自然可得“末”的中和。我們前面討論姜夔的“止乎禮義”之說,已經提到他認爲詩歌與情性之間是“如印印泥”,認爲二者之間存在著高度的一致性。遊酢(1045-1115)《遊薦山集》卷一《論語雜解》:“詩之情出於溫柔敦厚,而其言如之”,其情合乎“溫柔敦厚”的要求,其實也就是上面所說的性情中和。作者將中和之性情發之於詩,“其言如之”,方得詩之中和。他又說:“詩之爲言,發乎情也。其持心也厚,其望人也輕,其辭婉,其氣平”, {遊酢《遊薦山集》卷一《論語雜解》}所謂的“持心也厚”“望人也輕”即德行修養的忠恕,也表現爲一種和柔的風貌,這樣其詩才能達到辭婉氣平的平和效果。魏慶之《詩人玉屑》卷十三“晦庵論讀詩看詩之法”有謂:“古人情意溫厚寬和,道得言語自恁地好。”亦是謂詩人之情若能溫和,則其詩自然好,此處的“好”當然也應是指呈現出和柔的風貌的。可見這樣的觀念在宋代頗具普遍性。馮山(?-1094)《讀劉賓客外集》有謂“大約晚年知性命,一時清韻入中和。森張劍戟雖無敵,隱約瑕疵惜未磨。”{《馮安嶽集》卷一十二}他認爲劉禹錫之詩年輕時多譏刺,而晚年由於“知性命”,詩歌才歸於中和,並表示劍拔怒張爲不可取,此正可視爲宋代心性中和詩學觀念的典型表現。
第三節 命遇與守道
中國文人自孔子以來就面對着命遇問題,心性學亦稱為性命學,“命”是必然要涉及到的問題。《論語·憲問》:“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指的道之行與廢皆爲“命”所定,聯繫《論語·微子》“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和孔子知其不可爲而爲之的精神,已經表現出“命”爲非人力所爲的意思了。從他的言語中所流露出的無奈與執著,一直成爲中國文人宦海沈浮、人生坎坷中的精神支持,歷數千年而不衰。
同樣莊子哲學中的安之若命觀念也每每成爲文人遷謫貶逐心靈創傷的良藥。歷史進入了宋代,這是一個右文的時代,士大夫的政治與經濟地位之高皆爲前代所不及。然而他們的窮通際遇問題並未由此亦減少,相反由於他們的“行道“的預期值較高而變得突出。但宋人對命遇問題的討論受到性命之學的影響,或者說性命之學讓他們的對命遇的順化與超越更具有理論的自覺。
中國文論一直注意詩人的際遇與文學創作的關係。詩人的際遇會對內心産生影響,而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文人們對自身際遇的態度也就影響到了詩歌的所體現出來的性情。我們在前面談才氣與情性時已經提到過宋代以道德的修養達到命運際遇的超越,他們提倡的是用對命遇的順化與對道的固守來填平宦途的不平與人生的坎坷。這雖然也屬於修養的範疇,但由於宋代詩人對際遇的態度可視爲中和性情的典型表現,所以單列一節進行討論很顯必要。
這裏我們需要對中國古代“命”的觀念,進行一下追溯。{可以參見張岱年《中國古典哲學概念范疇要論》P120-P127對於命的解釋。}《尚書·湯誓》云:“有夏多罪,天命殛之。”成湯伐桀,以天命爲號召,表示最初的命是天命之意。《周易》主張的“遁世無悶”、“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就是指的君子爲人處世不當以窮達爲意,君子的情緒應該是“無悶”“不驕”“不憂”,也就是性情中和的意思。《周易·文言》:
亢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
作爲對“亢龍有悔”的反拔,更表明了聖人處世之度即“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這成爲後來詩人窮通沈浮而不失其道的理論依據。
《孟子·萬章上》“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孟子將天與命合而言之,就是“非人之所能爲”的意思。《孟子·盡心上》孟子曰:
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主張在盡心、知性以知天,存心、養性以事天,在知天命的基礎上更進一步提出了修身以俟之的立命之處世方法。孟子又說“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墻之下。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這裏他要求的是一種“知命”以“順受其正”的態度。
“命”亦是莊子哲學的一個重要概念,《莊子·德充符》“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饑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莊子的命觀念所指還是窮達貧富等種種人生的際遇,與儒家所指相同,但莊子對於命的態度與儒家有所不同。《德充符》“知不可柰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人間世》:“知其不可柰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表示“命”的特性就是“不可奈何”,也就是人力不可爲的意思,更表示對命的態度是“安之”,也即是聽之任之。
由此可見周漢時對於際遇(命)的態度有兩種,一是儒家的“順受其正”的態度。儒家主張知命以立命,我們不妨稱儒家的態度爲積極的順應,一是道家的“安之若命”。 道家主張“安之”,則爲“不可奈何”的消極的順應。其共同點則均爲順應,順應則得性情的平和。
魏晉時期《列子·力命》否認力的作用,將一切歸之於命,表示壽夭、窮達、貴賤、富貧,都是自然而然的,與個人的賢愚善惡無關。這可以推出一個當然的結論,即順應自然,也就是《莊子》講的“不可奈何”則“安之若命”。南北朝時劉峻《辨命論》,論證死生禍福與賢愚善惡並無聯繫,他將天所賦與人所行進行了區分,與《墨子》《列子》所說的“命”“力”相似,其實天所賦就是命,而人所行就是力。但他並不象列子一樣否認力的作用,他認爲“修道德,習仁義,敦孝悌,立忠貞,漸禮樂之腴潤,蹈先王之盛則。此君子之所急,非有求而爲也!”認爲行(道德實踐)並不是追求富貴的手段,也就是力不爲命,主張修德不爲窮達而爲,要求以德超越命。在此我們可以看到魏晉南北朝對於命的兩種態度:一是順命不用力,就是道家的安之若命,以《列子》爲代表;二是修德(用力)不爲命,也就是順命亦用力,順命亦不廢用力,以《辨命論》爲代表。
唐代對於命遇的超越觀念,可以韓愈、白居易爲代表。韓愈以“立言垂範”來達到對命遇的超越,其《寄盧仝》謂:“先生抱才終大用,宰相未許終不仕,假如不在陳力列,立言垂範亦足恃。” {《全唐詩》卷三百四十}而白居易以“守道”來達到對命遇的超越,{《與元九書》謂:“故僕志在兼濟,行在獨善,奉而始終之則爲道,言而發明之則爲詩。”}他們的對命遇的超越觀念在某種程度上成爲宋代對命遇進行超越的先行者。
這樣我們在討論“命”的觀念時已經涉及了如下幾個問題:命、遇、時、才、力。遇與時都爲人爲不能改變,所以視同於命,而才爲先天的能,而力爲後天的作爲,才與命的關係是指先天的能與後天的機遇問題,而力與命的關係則爲人所行與天所賦的關係。當然力與才的關係也必須提及,就是先天的才能與後天的努力問題,這事實上就形成了三角關係,才與力、才與命、命與力,似乎不太容易理解。但我們不妨借用《孟子·盡心上》的“求在我”與“求在外”來進行再一次的區分,可以使問題進一步簡化。《孟子·盡心上》:
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