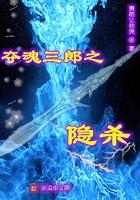李书亭的女儿也是贤良聪慧之人,在宫里很得皇后喜爱,收到父亲的信后,对香皂亲身做了尝试,果然清新美妙,肤滑生香,第一时间送给皇后几块,皇后用之甚爱,连称妙物!李妃又以皇后之名,赠与宫中各位妃嫔尝试,果然皆是喜欢,不由私下打探,才知这香皂出自李妃的家乡河州。
李妃私下和皇后谈及此物来历,皇后自然看出这妙物的前景和巨大商机,直接指派一位身边的心腹太监,随李家管事一起来到河州。李书亭不敢怠慢,马上通知张舟。
前世、今生,张舟都是第一次见到真正的太监。乾明宫总管福祥,一个身材富态,面带慈祥的老者。
福祥为人和善,做事稳妥,又忠心耿耿,很得皇后器重。先前在引路时,李书亭把女儿信中提及的,都一一告诉张舟,让张舟大体有个了解,千万别怠慢了对方,张舟虚心称是。心里已然有了应对的准备。
福祥对规规矩矩行过大礼后的张舟印象不错,微笑道:“你就是那香皂的主人?想不到这般年纪轻轻!”
张舟躬着身子,谦卑道:“总管大人,香皂的确是小人作坊所制!不过小的却算不上主人!”
“哦,此话怎讲?”
张舟认真道:“皇帝陛下拥有四海八方之地,皇后娘娘自然才称得上天下妙物之主!”
这马屁拍的,连福祥都不得不服,连连点头,一旁陪坐的李书亭,感觉自己的腰都要被张舟的无耻谄媚给打击断了,虽然自己秉持着,读书人的礼义廉耻才是为人正道,但也不得不承认张舟的谄媚行为,的确更能获得好处,心道:“凭这小混蛋的无耻劲,前途还真是不可限量啊!”
张舟继续道:“这香皂本就是去污涤尘的妙物,正合皇后娘娘恩浴天下的心意,小的断不敢做这妙物之主!总管大人,您是皇后娘娘最宠信之人,还得请您老帮小的拿个主意,取个什么名字,才能让皇后娘娘觉得满意呢?”
福祥笑容更盛,起身扶起一直躬身说话的张舟,道:“你这小子,年纪不大,心思却玲珑的很啊!至于名字,那还得皇后娘娘来定,当奴才的怎么敢逾矩放肆!”
张舟连忙道:“是小的想法不周,总管大人勿怪!不过,说句真心话,小的毕竟是乡野小人,一辈子都不可能近慕凤尊,就算有天大的心愿美意,还不得辛苦您老人家代为承禀?而您又是天下最懂得皇后娘娘心意之人,说到底,小的欲得皇后娘娘照拂,不如说是真心希望求得您老人家的庇护啊!”
话完,以只有他们二人可以听见的话音道:“这妙物利润的三成是送给皇后娘娘和您老的,日后小的生计,全靠总管大人的帮衬和周全了!”
说白了,三成利润,就给福祥了,至于皇后得多少,那他可管不着。
谁不喜欢自己的重要性被他人认可,张舟马屁拍的福祥心里很是舒服,红包给的也足够大。福祥自然满意。已经成了大股东,自然要为自己的腰包着想。
“那香皂成本多少?月产多少?”
“总管大人,实不相瞒,这香皂制作极为复杂,一块香皂成本就需要五两银子。这还不算运输费用!产量也不大,一个月也就五千块左右!”张舟自然不可能告诉他,制作的成本是一两银子可以制造十块。
福祥点点头道:“产量的确少,估计京城那些夫人小姐的用度都怕不够。你想办法提高产量,杂家回去禀报皇后娘娘,这香皂对外销售,怎么也不能低于二十两一块!”
张舟难掩内心的欣喜,道:“一切按总管大人吩咐!小的有个不情之请,今晚总管大人能否赏光,到寒舍小酌几杯?”
“那杂家却之不恭了!”
入夜,张舟的家里,屋内只有福祥和张舟两个人。福祥在宫里这么多年,什么美食没有见过尝过,张舟这一桌小菜却别具匠心,很称心意!尤其那河州烈,让福祥大开眼界,连声称赞。张舟与人结交,极易“以貌取人”,很大程度决定于“个人喜欢”,对喜欢的人可以喋喋不休,不喜欢的人则少言寡语,也是他性格偏执的一面。对福祥的第一眼印象,他就觉得面善喜欢,愿意亲近,交谈起来也如鱼得水,舒心适意。几杯酒下肚,张舟也忘记了身份,说话也随意起来,而福祥也不喜欢阳奉阴违,张舟的随性让他很喜欢,两个人越聊越投机。
“小舟,你别总管大人、总管大人的称呼,杂家与你投脾气,你喊我一声福叔即可!”
张舟也有几分醉意,举杯道:“福叔,我听你的,小舟说话如有不妥,您老别挑理啊!”
“说吧说吧,没事儿,杂家在宫里这么多年就剩下谨言慎行了,今儿在这里没那么多规矩!”
“叔!”张舟这叔喊得那个自然,让福祥爽心不已,张舟继续说道:“叔,我这辈子从小没娘,八岁爹也走了,这么多年,爹的样子都模糊了,就这样深一脚浅一脚的走到现在,有时候我就想啊!我凭什么就不能在遇到难事的时候,可以喊来爹娘,任任性、撒撒娇啊!”
不由得想起前世父母妻儿,情不自禁,泪流满面。这份对亲人思念的情感绝不虚假。福祥也联想自身,如有好家世,谁会入宫!感同身受,鼻子发酸,却又一时不知如何安慰!
张舟擦一把眼泪,继续说道:“叔,我并不是想攀您老的高枝,如果有一天,您老岁数大了,退下来,就来河州,我养着你,你想干啥就干啥!说不准,到时候我有了孩子,你也过过含饴弄孙的日子!”
张舟与这个世界有着尽然不同的人伦观念,自己没有直系长辈,就算供养几个老人,让孩子喊他们爷爷,也没有一点思想压力。可福祥不同啊,一时间举着酒杯,心绪翻涌!太监当权之时,人人都会敬畏,可是落魄之时,那绝对是落了毛的凤凰不如鸡,谁会搭理你?
福祥一辈子什么人没有见过,是不是虚情假意,一看便知,而张舟这份真挚,他看不到丝毫作伪!
但福祥还是慢慢放下酒杯,神情有些淡漠,道:“张舟,你可是戏弄杂家!”
张舟仿佛没有看见他的变化,手指高举发誓状:“叔,你看啊,小舟现在发誓,如果小舟有虚伪欺骗,天打雷劈,不得好死!”
世人极为看重誓言,福祥最后一丝疑虑也消除,“啪”拍了一下桌子,道:“胡说八道,还不掌嘴,收回那话,呸呸呸,不吉利!”
张舟抽抽鼻子,又擦擦眼睛,笑道:“叔,人在做,天在看,小舟又没有说谎,怕那个作甚?叔,你把酒都弄洒了!”
福祥又好气又好笑的骂一句兔崽子。张舟对福祥有一种亲近感,而且他对这些身残之人,有一种本能的怜悯之心,所言也是出自本意,并非纯心利用。用真心换善缘,张舟未觉得有何不妥!
这一晚,张舟很多情绪得到发泄,有对前世的念念不忘,雨儿离开的伤心,自己无计可施的愤懑,得罪清霖的压力等等,哭一阵,笑一会,和一个孩子似得,而福祥眼里,才十九岁的张舟,不就是一个孩子?酒醉的福祥也被勾起许多心酸,不时伤感,陪着他又哭又笑,直到双双醉倒。
一夜酒醉人情暖!
张舟亲自为福祥驾马车,护送出城。一路上说了很多话,却没有一句谄媚恭维,更无一句提及生意,只是叮嘱福祥如何照顾身体,如何看淡宫内斗争,一再絮絮叨叨。
“叔,您可千万记住,觉得不妥,赶紧告老还乡,别贪恋那点权利啊!说好了,您给我看孩子,我才养您,记住没有?”
“叔,后面车里,是我送您的沙发,可舒服了,你累了多躺会,保准解乏!”
“叔,给你那个敲背的小木槌,别弄丢了,那个用起来力量轻重自己心里有数!还有那个脚踩的按摩轮,烫完脚自己踩着按摩按摩,可以长命百岁!”
“还有那些河州烈,你可悠着点,宫里不比外面,喝多了误事,还伤身!”
福祥这辈子没有后辈,心里别提多暖心,最后张舟偷偷给他一万两银票,竟然被他一脚差点踢倒。
“叔,你这是干什么啊!京都宫里什么事不需要银子啊!侄儿给您点日常花销的银子,你也计较啊!”
“滚你的蛋!杂家还需要你那点银子?”
张舟低头自顾揉着屁股,又哪里看见,福祥在笑骂时偷偷擦拭眼中湿润。
张舟敬老是由衷的,这一点,七爷百分百身有体会,七爷选择退下来了,陈年旧伤,也让他无法应付驿站的一些事物。
唐雨儿的事,他已经知道。粗鄙汉子并不懂得如何安慰人,只能最大心力的帮着张舟看家守业,四处走走,监督一下,多少给他省点气力。
张舟自有心细之处,偷偷把七爷心仪已久的老相好给“弄”到家里,七爷看见那一脸幽怨,又难藏喜意的妇人,别提表情多精彩,用张舟那句话。
“都什么年纪了,还矜持个啥?”
这些日子,张舟花尽心思做能做的事,忙的马不停蹄,就是不让自己闲下来,没有几个人知道,他在用这种方式,遮掩心里那份黯然、那份恐慌、那份思念!终于盼来了陈朝英的一个字条:码头归人,速来!
张舟岂敢怠慢,领着二牛骑马而去,一路上,各种不妙的感觉不断冲击心头,“为什么是陈朝英来信?”“到底出了什么状况?”“千万不要有事!”张舟感觉自己的身体都有些颤抖。
二牛身体太壮,那马早已经吃不消,张舟哪有功夫等他,丢下他自行处置,自顾的快马加鞭直奔码头。
码头是飞蛟帮的地盘,而飞蛟帮经过上次那件事,又有谁不知河州府张舟的恶名?飞子的势力发展迅猛,已经不输飞蛟帮分舵,可是飞子是谁的手下?张舟的!飞子什么时候在张舟面前不是毕恭毕敬!人家还是河州刑捕主事,真正是河州府黑白两道的一哥。
早早有人看见飞马而来的张舟,立刻报告给在码头守着的陈朝英。陈朝英得到禀报,连忙走出人群。而张舟远远看见码头上围了一群人,直接就跑了过来,看见陈朝英后,飞身下马,丢下缰绳,不顾礼节的直接扑到陈朝英面前,抓着他的胳膊,脸色苍白,声音发颤的问道:“告诉我,出什么事了?”
陈朝英想了想没有说话,而是反手拉住他的手腕,就往人群中走去,众人主动为二人让开一条路,容他们通过。张舟很快就看见,地上有一副担架,上面躺着一个人,快跑几步便看清,正是杨小郎。
杨小郎双目紧闭,嘴唇抿紧,脸色苍白如纸,表情痛苦,胸口包裹厚厚的白布,已然透出大片的血污,极为醒目。张舟扑过去,想抱又不敢抱,生怕加重他的伤,手足无措,已经泪流满面,口中念叨。
“这是怎么了,到底怎么了,小郎!......”
在场所有人,包括陈朝英,还从未见过一个大哥级人物,会对一个扈从这般紧张失态,不由得心起潮绪。多是听说过,当初张舟为了飞子这样一个贼偷,敢舍身犯险,今日看见他这般动情,才深信这张舟的确重情重义。然而实话实说,张舟之所以如此失态,实在也是太久的焦急和压抑,太多的愤懑和担心所致!
陈朝英蹲在张舟身边,轻声道:“张大人,杨小郎胸口受了弓箭伤,在登岸时过于着急,加上心有积火,才导致伤口崩裂,昏晕过去,我已经给他摸过脉,应该没有大碍,只是不易上路颠簸,还是留在这里,等伤情稳定再回城吧!”
张舟擦擦眼泪,回头道:“多谢陈大哥,求陈大哥派人去河州,去我家里,就说我要找最好的大夫,最快的速度赶到这里!”
陈朝英点头,吩咐一个手脚麻利的汉子前往,陈朝英又提醒道:“杨小郎是坐船回来的,兄弟们没有让船离开,你问一下船老大,应该会得到一些消息,或许事情没有那么糟!”
那船就在码头拴着,船夫战战兢兢的站在岸边,如果可以,他早跑路了,他实在不想惹这无妄之灾。张舟找他问话,哪敢有丝毫隐瞒。
“这位受伤的小兄弟,是被一位高壮的汉子送上船的,那时候小兄弟还清醒,只是让我最快速度到河州来。”
船夫对着张舟边比划着边说道:“那个送他的汉子,到没有看见什么伤,和小兄弟说几句话就离开了!小兄弟在船上除了让我快点,别的只字未提,具体什么事,我也不知道啊!大爷,真的不关我事啊!”
张舟没有为难船夫,如他所讲,那个汉子应该就是柳青山,但并没有关于唐水儿的描述,究竟出了什么问题不得而知。
张舟也一时想不出对策,只能守着杨小郎,焦急的等在码头。两个时辰后,一大队人马出现在码头,因为知道缘由,所以并没有引起飞蛟帮太大的波动,不然那些人气势汹汹的样子,也容易引起误会。尤南七,林老九,曲十三,马黑子,飞子,甚至关玉娘也来了,身后更是跟来近百人,其中还有换了马匹的二牛。
大夫、郎中来了七八个,不用吩咐,就把已经抬进码头茅屋的杨小郎围了起来。这些医官并不是城里请来的,而是九州医馆的成员,正巧到城里采购药材,被关玉娘一起带了过来。行动上虽然还有些紧张,但是步骤还算清楚,这是在九州医馆几个月下来,经过不断的摸索演练,制定出来的“急救处理”法!各有分工,麻利地重新处理好伤口,上药包扎!
陈朝英还没有见过,这么多大夫一起处理过一个患者的,但是效率惊人。
杨小郎没过多久就缓缓醒来,郎中帮杨小郎用温水服下了药丸,示意张舟已经没有大碍后,张舟让人员都退了出去。自己则坐在床边,握住杨小郎的手,轻声道:“到底出什么事了!”
杨小郎情绪正欲激动,张舟忙止住他道:“小郎,现在不是你激动的时候,把力气省下来,告诉我经过!”
杨小郎慢慢深呼吸几下,强忍着胸口的伤痛,渐渐平和情绪,断断续续讲述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