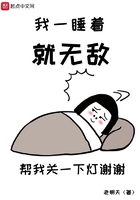我的哲学之路
1947年,我选择读北大哲学系,是想做一个“哲学家”,能通过自己的独立思考,来探讨一些宇宙人生的根本问题。但到1949年,一切都改变了,我很快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但严格说来接受的是苏联式的教条主义,开始虽然还有点怀疑,很快在各种运动中,我真的把那些教条主义当成真理了。在“文化大革命”前,我写过不少文章,大概有两类:一类是批判所谓的“资产阶级学术观点”,例如我参加了批判冯友兰、吴晗的“资产阶级学术观点”;另一类是对中国哲学史上的哲学家的研究。在20世纪50年代末与60年代初,曾经举行过几次“孔子学术讨论会”、“老子学术讨论会”、“庄子学术讨论会”等等,我都参加了,并且写了文章。这些文章几乎都是武断地给那些哲学家扣上“唯物”或“唯心”、“进步”或“反动”的帽子,算不得什么学术研究,只是把“学术”作为“政治”的工具而已。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80年代,也许我才做了一点哲学研究工作。而开始,我还不敢想成为一个“哲学家”,只想做一个稍有独立思考的“哲学史家”。所以在80年代初,我把在北京大学讲的《魏晋玄学与佛教、道教》一课的讲义修改成《郭象与魏晋玄学》一书,于1983年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后又于2000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郭象与魏晋玄学》(增订本)。在这本书中,我主要讨论了以下几个问题:(1)找出魏晋玄学发展的内在理路;(2)通过魏晋玄学范畴的研究寻找中国哲学的范畴体系;(3)探讨哲学方法对认识哲学思想变迁的重要意义;(4)尝试把哲学的比较方法运用于中国哲学的研究领域;(5)勾画了魏晋玄学到唐初重玄学发展的原因。这些问题的讨论,对当时哲学思想的解放起了一定作用。后又将1983年所讲《魏晋玄学》的讲稿和其后对“魏晋玄学”的研究论文整理成《魏晋玄学论讲义》,于2006年12月由鹭江出版社出版。此书对“魏晋玄学”的若干问题进行了讨论。80年代中期,我把《早期道教史》一课的讲稿修改成《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在1988年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在该书的“序言”中,我提出必须把“宗教”与“迷信”区别开来,要肯定“宗教”对人类社会生活的重要意义;在承认“理性”对人类社会生活的重要意义的同时,必须也承认“非理性”的意义。这本书除讨论了道教思想,还讨论了道教仪式、经典和它的组织形成。特别是从四个问题讨论了当时的佛道之争:关于老子化胡问题的争论、关于生死神形问题的争论、关于“承负”与“轮回”问题、关于“入世”与“出世”问题,这些问题是前此的道教研究很少讨论到的。自80年代以来,由于对中国文化现代化问题的考虑,自然要涉及文化交流的问题。为此我对历史上印度佛教文化的传入中国,参照我父亲用彤先生的研究路子,写了一系列有关佛教传入中国以及在中印两种文化交流中所涉及的问题写了一些文章,如《魏晋玄学与魏晋时期的佛教》、《文化的双向选择——印度佛教输入中国的历史考察》、《论禅宗思想中的内在性与超越性》等等。这些论文后来编入《佛教与中国文化》一书,1999年由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佛教文化传入中国,我认为大体上经过了三个阶段:初传入时依附于中国传统文化;传入日久,发现两种文化确有重大不同,而发生矛盾和冲突;之后由于在碰撞中相互吸收而融合,而使文化进入一新的发展时期。我想,这可能是两种不同传统的文化相遇之后的一般进路。在进入21世纪后,我在《中国现代哲学的三个“接着讲”》中试图用这个不同文化相遇后的“三阶段”进路来讨论西方文化传入中国的问题。这三本书都是对中国哲学史所进行的研究,但我实际上并不甘心只做一个“哲学史家”,因此从80年代初起,我也在考虑一些哲学问题,虽然这些问题大都仍然是围绕着中国的哲学问题展开的,但多少使我的视野关注到若干哲学问题。我曾经在冯契先生80岁生日之前,为祝贺他的八十大寿,给他写过一封信,向他提出他应回到40年代写《论智慧》一文的心态,来推动当代中国哲学的研究,而不要只做一位“哲学史家”,这也反映了我内心的矛盾。(其实冯契同志早已做着他的哲学研究了,以后出版的他的巨著《智慧说三篇》就是证明,但当时我不知道。)1997年夏,我去比利时访问鲁汶大学,有一位该校的女学生Vanessa Verschelden写了一篇论文《汤一介为什么不说自己是哲学家?》。这位同学还对我做了两小时的访问。我当时对她说:“这个问题得由中国近半个世纪的历史来回答。1949年后,当时有个普遍的看法:只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这样一些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或者社会主义国家伟大领袖才可以被称为哲学家,而其他的人只能是哲学工作者,他们的任务只是解释这些伟大人物的思想。这样的思想幽灵紧紧地缠绕着我们的头脑至少三十年。80年代后,我们开始对此有所怀疑,而后逐渐摆脱这一思想幽灵的困扰。但是我们真能从1949年以来的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吗?我们这一代学人,甚至我上一代和下一人的学人中,谁也难以明确回答。”我又向她说:“我虽不敢自称是哲学家,但我却有思考一些哲学问题的兴趣。”确实是这样,从1980年初我思考“中国哲学的范畴问题”到20世纪末我提出“创建中国解释学问题”和“新轴心时代中国哲学的走向问题”,就说明我对“哲学问题”的思考并没有停止。
一、关于中国传统哲学概念体系的问题
1980年,学术界出现了一定程度解冻的情况,有的学者提出要为唯心主义翻案,来说明它对哲学的发展是有贡献的。此时,我考虑如何突破五十年以来关于“唯心与唯物两军对垒”、“唯心主义”是“反动的”、“唯物主义”是“进步的”等教条,写了《论中国传统哲学范畴体系的诸问题》一文,后发表在1981年的《中国社会科学》第5期上,企图把哲学史作为一种认识发展史来考察。后来在《郭象与魏晋玄学》(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中对这个问题又做了若干补充,而后又在《在非有非无之间》(正中书局,1995)中做了一些修正。
我认为,一个哲学体系必由一套概念(范畴)、判断(命题)和经过一系列推理活动的理论所组成。也就是说,在一个哲学体系中总有其一套概念,并由概念与概念之间的联系构成若干基本命题,经过推理的作用而有一套理论。从西方哲学的观点看,中国传统哲学似乎没有一套概念体系,我认为这个看法是有一定根据的。中国古代哲学家没有像亚里士多德那样有他的《范畴篇》,也没有像康德那样提出与人的认识有关的原则或者说构成经验条件的十二范畴。但我想,我们却也不能说中国传统哲学没有一套不同于西方哲学的特殊的概念和范畴(按:范畴是指其哲学体系的基本概念)。先秦各家哲学都有他们所使用的特殊概念,否则就无法表达其哲学思想。后来在中国还有一些专门分析概念的书,如汉朝的《白虎通义》、宋朝陈淳的《北溪字义》、清朝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等等,其实在对先秦经典的注疏中也包含了对哲学概念的分析。佛教和道教都有解释他们专用概念的著作,如《翻译名义集》、《道教义枢》等等。不过我们也可以看到,在中国传统哲学中确实没有像西方哲学家那样的比较严密的概念体系。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我认为,这或许由于中国古代哲学家没有自觉到应该建立自己的概念体系,因为中国古代哲学家并不重视对自己的哲学思想做理论分析;同时中国古代哲学家也并不认为有建立其哲学思想的概念体系的必要。中国传统哲学的主题是追求一种人生境界,而不是追求知识的体系化。在那篇文章中,我明确地提出:“哲学史的研究最终要解决的问题应该是揭示历史上哲学思想发展的逻辑必然性。”这个看法,今天看来并不很全面,但对当时反对极左的教条主义却起了一定作用。那么,我们应如何着手研究中国哲学的概念问题呢?
我在上述那篇文章以及《郭象与魏晋玄学》中提出可以由以下几方面着手:(1)分析概念的涵义;(2)分析概念涵义的发展;(3)分析哲学家(或哲学派别)的概念范畴体系;(4)分析不同概念的种类。对中国传统哲学做上述各个方面的分析虽然也很难,但相对地说大体还可以做到,但如果我们要为中国传统哲学建构一个概念体系那就困难得多了。因为我们从总体上为中国哲学建构一概念体系,这个体系当然应是中国传统哲学所可能有的,这又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而且,我们确也可以从各种角度来为中国传统哲学建构适当的概念体系,如我那篇《论中国传统哲学范畴体系的诸问题》就是一种尝试。它是从存在的本源、存在的形式、人们对存在的认识三个方面来建构中国传统哲学的概念体系的,这样一种建构的思考方式大体上仍反映了1949年以来哲学教科书的某些影响。[1]现在我想,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考虑中国传统哲学的概念体系问题。如果我们从“真”、“善”、“美”这样一个角度来考虑建构中国哲学的概念体系或许更有意义。
照我看,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天”(天道)和“人”(人道)是一对最基本的概念,也就是说它是关于宇宙人生的最基本的概念,它属于“真”的问题;由“天”、“人”这对概念可以推演出“知”和“行”这对概念来,它应属于“善”的问题;由“天”、“人”这对概念还可以推演出“情”和“景”这对概念来,它应属于“美”的问题。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属于“天”和“人”概念系列的有“自然”和“名教”、“天理”和“人欲”、“理”和“事”等等,而说明这对概念关系和状态的概念可以有“无”和“有”、“体”和“用”、“一”和“多”、“动”和“静”、“本”和“末”等等。属于“知”和“行”概念系列的有“能”和“所”、“良知”和“良能”、“已发”和“未发”、“性”和“情”等等。属于“情”和“景”概念系列的有“虚”和“实”、“言”和“意”、“隐”和“秀”、“神韵”和“风骨”、“言志”和“缘情”等等。当然,在这三套概念之中也存在着交叉,例如“虚”和“实”也可以列入“天”、“人”这对概念系列之中,而说明概念的关系和状态的概念往往又和这三个不同概念系列有关。如果我们把“天”和“人”这对概念看做是中国传统哲学最基本的概念,那么我们就可以说天人关系是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问题,从而就扬弃了长期以来把“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作为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问题的教条,而能根据中国哲学的实际来考察中国传统哲学了。我并不认为,我这样建构中国传统哲学的概念体系是唯一合理的,不过它总不失为一种较为合理的和较为有意义的尝试。
二、关于中国传统哲学的命题——中国哲学中的“真”、“善”、“美”问题
如果我们认为上述对中国传统哲学概念体系的建构是一种合理的有意义的建构,那么我们就可以由上述三对基本概念构成三个基本命题:这就是“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这三个基本命题正是中国传统哲学对“真”、“善”、“美”的表述。
1983年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召开第十七届世界哲学大会,这次会议特设了“中国哲学圆桌会议”,我在圆桌会议上有个发言,题为《儒家哲学第三期发展可能性的探讨》。我在会上提出,儒家第三期发展可以从“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上来探讨。刘述先兄《蒙特利尔世界哲学会议纪行》有一段记述我当时发言的情形说:“会议的最高潮是由北大汤一介教授用中文发言,探讨当前第三期儒学发展的可能性,由杜维明教授担任翻译。汤一介认为儒学的中心理念如‘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在现代都没有失去意义,理应有更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这一番发言虽然因为通过翻译的缘故而占的时间特长,但出乎意料的清新立论通过实感的方式表达出来,紧紧地扣住了听众的心弦,讲完之后全场掌声雷动,历久不息。”1984年我把上述发言加以补充,以《论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真善美问题》为题发表于该年《中国社会科学》第4期上。后来又加以补充,以《从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命题看中国传统哲学的特点》为题,收入《儒道释与内在超越》(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一书中。
在我的论文中,不仅认为“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是儒家哲学的基本命题,而且也是道家甚至中国化的佛教(如禅宗)思想的基本命题。所谓“天人合一”,它的意义在于解决“人”和整个宇宙的关系问题,也就是探求世界的统一性的问题。在中国传统哲学中重要的哲学家大都讨论了这个问题,而且许多古代哲学家都明确地说:哲学就是讨论天人关系的学问。“知行合一”是要求解决人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应如何认识自己、要求自己,以及应如何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的问题,这就是关乎人类社会的道德标准和认识原则的问题。“情景合一”
是要求解决在文学艺术创作中“人”和其创作物之间的关系问题,它涉及文学艺术的创作和欣赏等各个方面。但是,“天人合一”是中国哲学的最根本的命题,它最能表现中国哲学的特点,它是以人为主体的宇宙总体统一的发展观,因此“知行合一”和“情景合一”是由“天人合一”这个根本命题派生出来的。这是因为,“知行合一”无非是要求人们既要知“天(道)”和“人(道)”以及“天”与“人”之合一,又要在生活中实践“天(道)”和“人(道)”以及追求“天人合一”之境界。“人(道)”本于“天(道)”,所以知“天(道)”和行“天(道)”也就必然能尽“人(道)”。人要知和行“天(道)”,这就不仅是个认识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个道德实践问题。人要知和行“天(道)”,就必须和“天(道)”认同,“同于天”,这就是说必须承认“人”和“天”是相通的,因此“知行合一”要以“天人合一”为前提。“情景合一”无非是要人们以其思想感情再现天地造化之功,正如庄子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这就是说“情景合一”也要以“天人合一”为根据。
“天”与“人”是中国传统哲学中最基本的概念,“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最基本的命题,在中国历史上许多哲学家都以讨论“天”、“人”关系为己任。那么中国传统哲学关于“真”、“善”、“美”的问题为什么要追求这三个“合一”呢?我认为,中国传统哲学或许与西方哲学不同,它并不偏重于对外在世界认知的追求,而是偏重于人自身价值的探求。由于“人”和“天”是统一的整体,而在宇宙中只有人才能体现“天道”,“人”是天地的核心,所以“人”的内在价值就是超越性“天道”的价值。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精神就是教人如何“做人”。“做人”对自己应有个要求,要有一个理想的“真”、“善”、“美”的境界,达到了“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的真、善、美境界的人就是圣人。中国传统哲学如果说有其独特的价值,也就在于它提供了一种“做人”的道理。它把“人”(一个特定关系中的人)作为自然和社会的核心,因此加重了人的责任感。在中国古代的圣贤们看来,“做人”是最不容易的,做到与自然、社会、他人以及自我身心内外的和谐就更加困难。这种“做人”的学问就是孔子所提倡的“为己之学”,也就是张载所追求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理想人生境界。这种“做人”的道理表现在道家的思想中就是“顺应自然”、“自然无为”,正如老子所说的“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也像庄子所向往的“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那样。中国化的佛教禅宗要求人们“无念”、“无住”、“无相”,以达到“识心见性”、“见性成佛”的境界。这就是说,中国传统哲学的儒、道、释都是为了教人如何“做人”、提高人的精神境界的学问。如果我们要给中国传统哲学一个现代意义的定位,了解它的真价值所在,我认为它正在于此。因此,我在另一篇文章《再论中国传统哲学的真善美问题》(载《中国社会科学》,1990[3];台湾《哲学与文化》,1989[10])中,把孔子、老子、庄子和德国康德、谢林、黑格尔三大哲学家加以对比,提出孔子、老子、庄子虽然在价值上对真、善、美的看法不同,但他们对真、善、美的追求都是为了提高人的精神境界,而德国三大哲学家讨论真、善、美则属于知识系统方面的问题。我在上述那篇文章中说:“孔子的哲学和康德的哲学从价值论上看确有相似之处,但是他们建构哲学体系的目标则是不相同的。孔子无非是以此建构他的一套人生哲学的形态,而康德则是要求建立一完满的理论体系。这也许可以视为中西哲学的一点不同吧!”“中国传统哲学所注重的是追求一种真、善、美的境界,而西方哲学则注重在建立一种论证真、善、美的价值的知识体系。前者可以说是追求一种‘觉悟’,而后者则是对‘知识’的探讨。”
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是和其“体用一源”的思维模式有着密切关系的。我们知道在中国传统哲学中“体”和“用”是一对非常重要的概念,不过它并不完全是一对实体性概念,而主要是有关关系性的概念。“体”是指超越性的“本体”或内在性的精神本质,“用”是指“体”的功用。“体”和“用”是统一的,程颢说“体用一源,显微无间”,就是最明确地表达了“体”和“用”之间的关系。从思维模式上看,“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正是“体用一源”这种思维模式的体现,所以“合一”的思想是中国传统哲学的特色。
从以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由“天人合一”及其派生的“知行合一”、“情景合一”,以及由这些基本命题所表现的思维模式“体用一源”,可以引发出中国传统哲学的三套相互联系的基本理论来,这就是“普遍和谐观念”、“内在超越精神”、“内圣外王之道”。这三套理论是从三个方面来表现中国传统哲学的理论:“普遍和谐观念”是中国哲学的宇宙人生论;“内在超越精神”是中国哲学的境界修养论;“内圣外王之道”是中国哲学的政治教化论。这三套理论就构成了中国传统哲学的理论体系。从这三套理论,我们不仅可以看出中国传统哲学的价值,同时也可以认识到中国传统哲学的问题所在。
三、关于中国传统哲学的理论体系问题
“关于中国传统哲学的理论体系”会有种种不同看法,这可能是好事。正因为有不同看法,才会因不同而推动对中国传统哲学做不同的整体研究,而且可以在诸种不同的思考中来发展中国哲学。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是从三个方面来考察中国传统哲学问题的,即“普遍和谐论”,这是宇宙人生和谐论的问题;“内在超越论”,这是境界修养论的问题;“内圣外王论”,这是政治教化论的问题。而这三套理论又都可以从“天人合一”这个基本命题推演出来。
(一)普遍和谐观念
关于“普遍和谐观念”是我从20世纪80年代初就开始考虑的问题,而且在一些论文中已有片断的论述,但写成一篇完整的论文,则是在1992年夏秋之交。是年《世纪风》杂志社约我为该刊创刊号的“世纪之交”栏写篇文章,谈谈中国文化对当前世界文化发展的意义。我当时想到,即将过去的20世纪,曾经发生过两次世界大战,使数千万人丧失了生命,使人们多少年来创造的文明遭受到难以估计的损失。它是一个悲惨的时代。而今,虽无世界大战,但局部战争不断,人类社会仍然面临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其中最需要解决的应该说是“和平与发展”问题了。要实现“和平共处”,就必须解决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扩而大之就是要解决好“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地域与地域之间”的关系。要实现“共同发展”,不仅要解决好“人与人的关系”,而且还要解决好“人与自然”的关系。那么,中国哲学能否为解决这两个问题提供有意义的资源?于是我就把《在世纪之交——论中国文化的发展》一文寄给了《世纪风》。其后,1993年10月在苏州召开“现代化与中国文化研讨会”,我又以《中国哲学中“普遍和谐观念”的现代意义》为题做了发言,经过修改补充以《中国传统文化之特质》为题发表在我主编的《国故新知:中国传统文化的再诠释》(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中。其后,我又写了《中国哲学中和谐观念的意义》发表于台湾的《哲学与文化》(1996[2])。这些文章,我是从“天人合一”这个命题展开来讨论问题的。
我认为,由“天人合一”这个基本命题和这个命题所表现的“体用一源”的思维模式,从根本上说它要求有一套表现此命题和此思维模式的宇宙人生理论,这就是“普遍和谐观念”的理论。此“普遍和谐观念”的理论大体上包含着四个层次:自然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自我身心内外的和谐。就中国哲学中的儒道两家看,他们的路向是不同的:儒家是由“人自我身心内外之和谐”出发,认为有“人自我身心内外之和谐”才有“人与人之和谐”,有“人与人之和谐”才有“人与天(自然)之和谐”,有“人与天(自然)之和谐”才会领悟“自然之和谐”。道家则是由“自然(天)之和谐”推演到“人与自然(天)之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自我身心内外的和谐”。中国化的佛教,如禅宗,因受儒、道两家的影响(特别是庄子思想的影响),在“普遍和谐”问题上也有其独特的看法。如果我们能对儒、道、释关于“普遍和谐观念”加以梳理和总结,将有助于当前人类社会存在的“和平与发展”问题的解决。
“普遍和谐论”作为一种世界观有其独特的视角,它强调的是宇宙的和谐与人的和谐的统一性。在中国传统哲学中,无论儒、道,都把“天”(或“道”)看成是神圣的、圆满无缺的,而人是效法“天”(或“道”)的,儒家提出“圣人法天”,道家提出“人法道”,并且通过一系列描述,把自“天”至“人”的和谐系统化,形成一套理论。这套理论为中国自古以来的哲人所接受。就这一点看,中国哲学或许与西方和印度哲学不同,它是把对宇宙人生的领悟建立在“天”、“人”和谐的基础上。
在我对中国传统哲学的世界观——宇宙人生和谐论做了一些研究之后,我又写了《“太和”观念对当今人类社会可有之贡献》(载《中国哲学史》,1998[1])、《儒学的和谐观念》(载《中华文化论坛》,1997[4])、《略论儒家的和谐观念》(载《社会科学研究》,1998[3])等论文专门讨论了儒家的“和谐”观念,我把它称作“普遍和谐”观念,它包含了由“人”至“天”的一系列的“和谐”。我特别引用了《中庸》的一段话:“唯天下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与天地参矣。”可见儒家关于“和谐”的路向是:由自身之“安身立命”,而至“推己及人”,再至“民胞物与”,达到“保合太和”而与“天地参”。儒家这一由“人”至“宇宙”关于“和谐”观念的路向确实能成为一个系统。但这个系统也可能并不完善,它比较多地强调了“人”的道德修养,容易走上泛道德主义。儒家的“普遍和谐”观念作为一种宇宙人生论,无论如何可以给人类社会提供一种十分有意义的世界观。为了使“普遍和谐”观念能为解决当前人类文化发展遇到的一个重大问题做出贡献,我写了《“和而不同”原则的价值资源》(载加拿大《文化中国》,1995[12])。这篇文章是针对亨廷顿《文明的冲突?》写的。在这篇文章中,我根据中国的文献材料,说明如果我们把“和而不同”作为一条原则,那么在不同文化传统之间,并不会因文化的不同就一定引起冲突,更不会因之而发生战争。此文后在国内多种刊物转载过,引起广泛注意。为了进一步阐明此问题,我又于2003年写了一篇《“文明的冲突”与“文明的共存”》(载澳门《中国文化研究》,2004[6])。
(二)内在超越问题
关于“内在超越问题”,是我在1985年看到余英时教授《从价值系统看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一文后,受到启发,因而写了一系列文章讨论此问题。1984年在我的《论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真善美问题》中讨论过中国传统哲学作为一种“做人”的道理,作为一种追求理想人生境界的学说,它对今日矛盾重重的人类社会说仍然有着重要的意义。1987年夏在香港中文大学举办了一次“儒家与基督教对话国际讨论会”,我给这次会议提供的论文为《论儒家哲学中的内在性与超越性问题》,在会上引起与会者广泛的兴趣,接着我又写了《论魏晋玄学中的内在性与超越性》,并提供给1990年在台湾成功大学召开的“魏晋南北朝文学与思想学术讨论会”。在我对中国化的佛教禅宗做了一些研究之后,我写了《论禅宗思想中的内在性与超越性》和《禅师话禅宗》两文,分别发表于《北京社会科学》与《百科知识》之中。最后写了《论老庄哲学中的内在性与超越性》,此文先发表在台湾东海大学的《文化月刊》上,后经过修改补充发表于《中国哲学史》杂志复刊的创刊号上。上列四文组成一组,收入拙著《儒道释与内在超越问题》一书中。
在我上述的文章中,根据史料论证了中国哲学的儒道释(禅宗)三家的学说均以“内在超越”为特征。如果说以“内在超越”为特征的儒家哲学所追求的是道德上的理想人格,超越自我而成“圣”;以“内在超越”为特征的道家哲学所追求的是个人的身心自由,超越自我而成“真”(“仙”)(按:“真”即《庄子》书中的“真人”,“仙”此处借道教的“神仙”意,所谓“仙”即《庄子》书中的“真人”、“神人”);那么,以“内在超越”为特征的中国禅宗则以追求瞬息永恒的空灵境界,超越自我而成“佛”。这种以“内在超越”为特征的哲学的价值何在?照我看,这种哲学的价值正在于把“人”看成是具有超越自我和世俗限制能力的主体,它要求人们向内反求诸己以实现“超凡入圣”的理想,而不要求依靠外在的力量。盖因人具有“超凡入圣”的内在本质,故人应该是自己的主宰,人的一切思想行为全靠自己的自觉性,以此来达到理想的人生境界。因此,中国哲学要肯定的是人的内在价值和其实现“超凡入圣”的能力。在儒家看来,这种品质和能力来自“良知”、“良能”,以提高道德修养,而达到“同天”的境界。在道家看来,人的这种品德和能力来自“顺应自然”、“无为无我”,实现精神的升华,而达到“逍遥游”的境界。在禅宗看来,人通过“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而达到“涅槃”境界。
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很不相同,古希腊哲学,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大体上都是把世界二分为超越性的本体世界和现实性的世界,近代自笛卡尔以来也以世界为二分,因此西方哲学的主流多有一个外在于人的世界,至于基督教更是有一个外在于人的超越性的上帝,这与中国不把“天”看做外在于“人”的看法很不相同。四百多年前,有一位天主教的耶稣会士利玛窦来到中国,他在中国住了二十多年,对中国文化有相当的了解,并深深地爱上了中国文化,但在他的《天主实义》中有一段话,对此我们应该注意,他说:“吾窃贵邦儒者,病正在此常言明德之修,而不知人意易疲,不能自勉;又不知瞻仰天主,以祈慈父之佑,成德者所以鲜见。”利玛窦用另一种眼光看中国哲学,也许不是没有道理。当然,利玛窦的观点是否正确,是可以讨论的。不过我认为,他的看法或者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中国哲学,应有可取之处。照利玛窦看,仅仅靠个人内在的道德修养是很难使人人都达到完满的超越境界,必须有一外在的超越力量来推动,因此要有对上帝(天主)的信仰或某种超越力量的崇拜。照我想,个人超越性的境界可以靠其内在的道德修养来实现,但整个社会并不一定能因此而合理和完美;要使整个社会合理和完美,除了提高个人内在的道德修养之外,还需要有另一套外在的力量来配合,这就必须建立一套客观的行之有效的、公正的政治法律制度。以“外在超越”为特征的西方哲学和基督教应该说对建立客观有效的政治法律制度更适合。盖因西方哲学要求有一个外在的客观准则,基督教则把上帝视为一外在的至高无上的超越力量,并提出“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理论,因此在罗马帝国基督教最盛时,也相应建立了一套对后来西方社会有重要影响的“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理论和制度。看来,中国哲学更加适合“人治”的要求,而西方哲学则更有利于建立“法治”。面对现代社会,我们是否应该在发展以“内在超越”为特征的哲学的同时,也引进或建立一套以“外在超越”为特征的哲学理论呢?我认为这是当前我们必须加以考虑的。对人类社会说,人们除了应要求以其内在的道德修养来提升自己而达到“超凡入圣”的境界,同时也应承认外在的超越力量可以帮助或推动人们达到“超凡入圣”的境界。如果东西方哲学能在更高的层次上建成包含着以“内在超越”为特征的中国哲学和以“外在超越”为特征的西方哲学,那么东西哲学不但可以以多种形式相会合,而且将使人类的哲学能在更高的层次上得到发展。
为此,我的文章中讨论了建立一个包含“内在超越”和“外在超越”的中国哲学体系是否有可能的问题。我认为,这需要我们回答两个问题:一是中国哲学能否较充分地吸收西方哲学和西方宗教的精神;另一是中国哲学自身中是否有“外在超越”的资源。对于前一问题,我们可以从中国哲学吸收印度佛教哲学得到如下的看法:由于中国哲学有很强的包容性,故有能力吸收外来文化。关于后一问题,我认为在中国传统哲学中也有若干“外在超越”的因素。本来孔子思想中就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有“为仁由己”,“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另一方面也有“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畏天命”是继承了殷周以来的“天命”观)的说法。前者为孔子思想中的“内在超越”方面,后者为孔子思想中的“外在超越”方面(或者说它表现了孔子思想中的某些“外在超越”因素),而这方面还有着更为古老的传统(如殷周以来的“敬天”、“尊天”等等)。但是,后来儒家发展了前一方面,而后一方面没有得到发展。如果历史的发展不是如此,而孔子思想中的两个方面都能得到平行发展,而又相互补充,那么中国哲学也许会更加丰富。因此,现今我们是否能充分吸收以“外在超越”为特征的西方哲学,并在此基础上把中国哲学发展成一包容“内在超越”与“外在超越”的思想体系呢?我认为,为发展中国哲学这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也是必要的。我们知道,在中国并不是没有以“外在超越”为特征的哲学,在春秋末期比孔子稍晚的墨子,他的哲学可以说是一种以“外在超越”为特征的哲学体系。墨子哲学由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组成:一是具有人文精神的“兼爱”思想;另一是具有宗教性的“天志”思想。这两方面看起来似乎有矛盾,但在墨子哲学体系中,却认为“兼爱”是“天”的意志的最根本的表现,所以“天志”应是墨子哲学思想的核心。墨子的“天志”思想认为,“天”是有意志的,它的意志是衡量一切事物的最高准则,人应该上同于“天”,“天”具有赏善罚恶的力量,它是外在于人的超越力量,也就是说墨子的“天志”具有明显的外在超越性。由于墨子这种哲学思想较之儒家或道家具有较多的外在客观性,因此后期墨家的思想中有着比较多的逻辑学、认识论和科学的因素,同时对建立客观的政治法律制度有利。可惜在战国以后墨家思想没有得到发展而逐渐衰亡了。如果我们对墨家思想做认真的研究并加以发展,那么它是否也可以成为我们所希望建立的包含“内在超越”与“外在超越”的中国哲学的资源呢?我认为这是可能的。
总之,以“内在超越”为特征的中国哲学为人类提供了一种极有价值的学说,这应为人们所肯定,但它也有不足的方面,也是我们必须注意到的。我提出,中国哲学应在“内在超越”的基础上来吸收以“外在超越”为特征的西方哲学的某些因素,但这只是一个设想,这种较之传统中国哲学包容性更为广泛的新的中国哲学体系的建立绝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很可能要经过若干次失败,在出现若干不同形式的以“内在超越”为基础并包容着“内在超越”和“外在超越”的新的哲学体系之后,才能形成比较圆满的现代中国哲学,这也许就是中国哲学的第三期发展吧!
(三)内圣外王之道
“内圣外王之道”是中国哲学特有的问题,它可以说是一种政治哲学,一种政治教化论。这种学说是和“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思想相联系的。我在《论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真善美问题》、《再论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真善美问题》以及《儒学能否现代化》等几篇文章中,都谈到儒家学说中极有意义的部分就是“教人如何做人”。“做人”的最高极致就是要成圣成贤,要有一个理想的人生境界,这个境界就是“天人合一”的境界;而圣人的境界必须实践于日用伦常之中,这就是要做到“知行合一”;圣人的境界还要能以情化景,因景生情,体现人生的“大美”。
为了比较全面的讨论“内圣外王之道”的问题,我于1987年写了一篇《论儒家的境界观》(载《北京社会科学》,1987[4]),后又在我的一本书《在非有非无之间》中对此问题加以补充论述。从现存史料上看,“内圣外王”最早见于《庄子·天下》。照《庄子·天下》的看法,“内圣外王之道”本是天下治道术者所共同追求的目标,但因百家纷争,道术不行,天下大乱,使之而不明,郁而不发,这是很不幸的事。这就是说“内圣外王之道”并不是《天下》作者创造的,而是它描述中国自古以来治道术者所追求的目标。确实如此,因“圣王”观念是先秦时期普遍流行的观念。孔子就把尧舜视为“圣王”,他们行的就是“内圣外王之道”,如孔子说:“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在《墨子·公孟》中有这样一段:“公孟子谓子墨子曰:‘昔者圣王之列也,上圣列为天子,其次列为大夫。今孔子博于《诗》、《书》,察于礼乐,详于万物,若使孔子当圣王,则岂不以孔子为天子哉!’”
《荀子·解蔽》为“圣王”下了一个定义:“圣也者,尽伦者也;王也者,尽制者也。两尽者,足以为天下极矣,故学者以圣王为师。”可见“内圣外王”之观念在先秦已相当流行了。时至近代,诸多学者也以“内圣外王之道”为中国传统文化之精神所在,如梁启超、熊十力、冯友兰都以“内圣外王之道”为“中国哲学之精神”。
在我看来,“内圣外王之道”如果理解为内在的道德修养必见于外在的伦常事功上,这是很有价值的。我们考察中国历史上的先哲们,多以此为立身行事之目标。也许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最能表现“内圣外王”之真精神。张载的这四句话,既体现了“天人合一”的思想,盖“为生民立命”即是“为天地立心”;又体现了“知行合一”的思想,圣学必须落实到“为万世开太平”。但我当时对“内圣外王之道”是重点看到它可能产生的弊病。我认为:“如果把‘内圣外王之道’理解为,一个道德高尚、学识深博的人(圣人),在适当的条件下更可以实现其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努力实现其理想,这也许是有意义的。……但‘内圣’不必‘外王’,‘内圣外王之道’只有非常有限的意义,它不应也不可能作为今日中国哲学之精神。”为什么?我从分析《大学》中的修、齐、治、平得到对“内圣外王之道”的怀疑。照《大学》看,“修、齐、治、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这在理论上是有弊病的,“因为‘身’之修是由个人的努力可提高其道德学问的境界,而国之治、天下之太平,那就不仅仅靠个人的道德学问了。……人类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统一体,它至少要由三个方面共同运作才可以维持,即经济、政治、道德(当然还有其他方面,暂且不论)。在一个社会中,这三方面虽有联系,但它们绝不是一回事,没有从属关系,要求用道德解决一切问题,包揽一切,那将会走上泛道德主义的歧途。由于中国传统哲学把‘内圣外王之道’作为追求的目标,因此造成道德政治化和政治道德化。前者使道德屈从于政治,后者使道德美化了政治。……在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儒家所塑造的那样的‘圣王’,所出现的大都是有了帝王之位而自居为‘圣王’的‘王圣’,或是为其臣下所吹捧起来的假‘圣王’。……所以,道德教化和政治法律制度虽有某种联系,但它们毕竟是维系社会的不同两套,不能用一套代替另一套”(《论儒家的境界观》)。今天来考察我们这个看法,它多少有些不周全处,这是由于我们没有充分考虑到道德教化和政治法律制度虽是两套,但这两套是可以互相影响的。不过,就中国哲学(特别是儒家哲学)方面看,夸大了道德教化的作用,无疑是其缺陷。这正如我们谈到的,中国哲学往往为“人治”提供理论依据,而忽视了“法治”。
我对“内圣外王之道”采取否定的态度,应该说是与没有深入了解它的真精神有关,但也是事出有因的。这是因为我囿于中国历史和现实,特别是有见于“文化大革命”那种中国传统的“圣王”思想所产生极大的负面作用。但是,我们跳出现实,只从一种可能的理想方面考虑,也许“内圣外王之道”确有其不可忽视的价值。“内圣外王之道”可能包含着以下三层意思:(1)“圣”和“王”应是统一的,不是“圣”就不应是“王”;不是“王”也难以行“圣人”之道。这是由于在中国历史上已经塑造了尧舜这样的“圣王”,有了“圣”、“王”统一的榜样,这样的理想社会的蓝图就深深地根植在中国人的心中,形成一种牢不可破的信念。(2)只有在实践中才可以实现“圣人”的社会理想,而实现“圣人”的社会理想必定要依赖于“王”(圣王)。这就是说,“内圣外王之道”体现着一种“实践理性”。盖中国哲学(特别是儒家哲学)不仅仅是一种“认识世界”的理论,而且是一种必须见之于“实践”的理论。儒家自孔子以至孟、荀,而后历代大儒无不以天下为己任,所以中国传统往往以“实践”高于“理论”,孔子说:“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荀子说:“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行之明也,明之为圣人。”(《荀子·儒效》)王阳明说:“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传习录上》)中国的这一传统或者与西方不同,它强调的更在于“行”(实践),所追求的要见之于事功,不能治国平天下的不能算作“圣王”。(3)冯友兰说:“所以圣人,专凭其是圣人,最宜于做王。”(《新原道·新统》)这样的看法早在先秦时已经有了,如孔子弟子宰我说:“夫子贤于尧舜”;又如荀子的弟子尝颂扬他们的老师“德若尧舜,世少知之”,“其知至明,循道正行,是以为纲纪,呜呼,贤哉!宜为帝王”。看来,“内圣外王之道”所重在“圣”,这是把道德修养放在首位。这无疑是中国哲学的特点。基于此,中国常常被称为“礼仪之邦”。“内圣外王之道”虽不能说已是一种十全十美的政治哲学理论,但在今日世风日下、道德沦丧的时候,仍应为我们所重视。
当然,中国哲学还有其他许多理论问题,不过我们上面讨论的三组问题——普遍和谐观念、内在超越精神、内圣外王之道,应该说表现了中国哲学的特色。
(四)关于“文化问题”的思考
从20世纪90年代的中后期起,我的兴趣由中国传统哲学问题的探讨,逐渐转向“文化问题”和“当代中国哲学走向问题”。
关于“文化问题”,是由于两个方面的问题引起了我的关注。一是1993年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提出;二是百多年来在我国文化上的“中西古今之争”。亨廷顿《文明的冲突?》引起了各界广泛的批评和讨论,我可以说是中国大陆最早参与讨论者之一。1993年底我写了一篇《评亨廷顿〈文明的冲突?〉》,该文发表在《哲学研究》1994年第3期上。这篇文章,我主要是用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资源对亨廷顿的理论进行了批评。我提出“从人类文化发展的总趋势看,不是以相互对抗为主导,而是以相互吸收而融合为主导”,并用儒家的“普遍和谐”观念驳斥了亨廷顿对儒家学说的无知论断,指出“文明冲突论”是为西方霸权服务的“西方中心论”。为了说明在不同文明之间,在文化(宗教、语言、价值观)上的不同可以和平共处,我写了《“和而不同”原则的价值资源》,讨论了中国文化中的“和同之辨”,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理想是“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万物并育”和“道并行”是“不同”;“不相害”和“不相悖”是“和”,这种思维方式为多元文化共处提供了极其宝贵的理论原则。与此同时,在与意大利学者讨论“在不同文化之间是否应该有墙”时,我提出有生命力的文化一方面要坚持文化的主体性,另一方面又要善于吸收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因此往往是“在有墙无墙之间”而得发展。此外,我还写过《“太和”观念对当今人类社会可有之贡献》、《“文明的冲突”与“文明的共存”》、《关于文化问题的几点思考》等等,都是要说明从中国传统文化看,在不同文明之间,并不一定会由于文化的不同而引起冲突以至战争,而可以在对话交流中取长补短而形成共存共荣的局面。
在20世纪我国学者对中国近现代哲学史、思想史、文化史的研究是以“中西古今之争”作为百多年来中国近现代思想发展的基本线索来论说的,并认为革命的激进主义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维护传统的保守主义是阻碍社会前进的力量。在80年代后期我对这种看法有所怀疑。1989年,在夏威夷召开的“第六届国际中国哲学会议”,我提出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路向大体上是在激进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三种力量的矛盾、斗争中前进的,也可以说是在这三种力量合力的情况下文化得到发展的。在这个问题中我特别关注的是“保守主义”对文化的意义。德国著名知识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认为保守主义者对“社会的历史的理念”做出过重大贡献。保守主义的思想构成历史的一部分,要完整地了解历史,不能不对它做一番认真的研究。事实上,保守主义、激进主义、自由主义三者往往在同一框架中运作,试图从不同的途径解决同一问题,它们在同一层面上构成的张力和冲突正是推动历史前进的重要契机。为此我写了《论转型期的中国文化发展》一文,其后又从中国历史上两个重大历史转型期先秦与魏晋来说明,转型期的文化发展往往都是由上述三种合力实现的,这就是我写的那篇《论文化转型时期的文化合力》。为纪念五四运动八十年周年我写了一篇《五四运动与中西古今之争》,其后又写了《略论百年来中国文化上的东西古今之争》以及《走出“中西古今之争”,会通“中西古今”之学》、《“拿来主义”与“送去主义”》等文章,主要说明五四以来在不同的历史情况下,激进主义、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对文化有着不同的意义,并对有些学者对我提出的“三种合力推动文化发展”的批评做了回答。
(五)关于当代中国哲学走向问题的探讨
在西方,解释学(诠释学,hermeneutics)早已对众多学科产生了重大影响,可以说已经形成了一种“解释思潮”。“解释学”虽在三四十年代已经传入中国,但真正发生影响是从80年代开始的,它的影响已表现在中国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研究等等诸多方面。我注意到西方解释学是在80年代初,在我的那本《郭象与魏晋玄学》中用了一些解释方法。我一直在想,中国有很长的解释经典的历史,我们是否可以利用中国解释经典的经验来丰富“解释理论”,或者创建中国解释学?因此,我在庆祝北京大学百年校庆时写了一篇《能否创建中国的“解释学”?》发表在《学人》1998年的第13期上,此后又连续写了数篇讨论这一问题的文章,后都收入《和而不同》(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一书中。我考虑这个问题是如何使中国传统哲学从传统走向现代,能否在一些方面与西方哲学接轨。我注意到在中国传统哲学中有着丰富的解释经典的资料,我们应可以从中总结出一些解释的理论与方法。同时我注意到“符号学”、“现象学”在中国也有一定影响,例如龚鹏程写有《文化符号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主要讨论的是中国符号学问题;康中乾写的《有无之辨——魏晋玄学本体思想再解读》(人民出版社,2003),该书接触到中国现象学问题。我为这两本书都写了序,谈到我对创建“符号学”和“现象学”的看法。我认为,这些尝试都应受到重视。
1999年在费孝通先生主持的第一届“二十一世纪中华文化世界论坛”中,我提出“新轴心时代”的问题。当人类社会进入经济全球化、科技一体化的时代,是否会出现一个“新轴心时代”;当我国处在一个民族复兴的前夜,作为“轴心时代”文明的重要一支,中华文化是否将会迎来它的“文化复兴”,我认为这是需要研究的问题。为此,我写了《新轴心时代的中国文化定位》,发表在2001年的《跨文化对话》第6辑中,后又从哲学的角度考虑这一问题,修改成《新轴心时代的哲学走向》,发表在2001年《南昌大学学报》第4期上。其后又写了《新轴心时代的中国儒家思想定位》(收入新加坡出版的《儒学与新世纪的人类社会》中)。为什么会出现一个“新轴心时代”,我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做了说明:(1)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殖民体系的逐渐瓦解,原来的殖民地国家和受压迫民族得到了解放,他们有一个迫切的任务,就是要从各个方面确认自己的独立身份,而民族的独特文化(语言、宗教、价值观等等),正是其独立身份的重要支柱。(2)经济可以全球化,科技可以一体化,但文化不可能单一化,因此文化多元化的势头将长期存在。(3)当前人类社会可以说主要有着四个大的文化传统:西方文化、东亚文化、南亚文化、北非中东—伊斯兰文化,这四种文化传统所影响的人口都在10亿以上,必定会主导当前世界文化的发展。因此,文化(哲学)将会呈现为在全球意识观照下的多元化发展的新趋势。(当然其他地区的文化,如南亚、非洲等,也会对人类社会文化的发展有影响。)为了进一步讨论“新轴心时代”中国现代哲学的走向问题,我写了《中国现代哲学的三个“接着讲”》、《在中欧文化交流中创建中国现代哲学》、《在西方哲学冲击下的中国现代哲学》等论文。中国哲学必须创新,要“创新”一方面要“接着”前此的中国哲学讲,特别应重视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中国哲学家为创造现代型的中国哲学的努力;另一方面又得走出西方哲学框架的束缚,来讨论中国哲学特有的问题,并使之具有世界的普遍意义;同时还应更加系统地研究和吸收其他各民族哲学,特别是西方哲学。中国哲学必须创新,这是中国哲学家的责任。
自2003年起,我又接受了一项新的任务,编纂《儒藏》。在中国历史上,儒、道、释三家并称,但三家在中华文化中的地位是不同的,儒家思想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主体。从经典体系来看,儒家所传承的“六经”,都是孔子以前形成的,这些经典是夏、商、周三代文明的精华;而孔子开创的儒家与先秦各家不同,就是儒家始终以自觉传承“六经”为己任,“六经”所代表的中国古代文化正是通过和依赖于儒家的世代努力而传承至今。我国历史上已经多次编纂过《佛藏》和《道藏》,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又编辑出版了《中华大藏经》和《中华道藏》,但没有编纂过《儒藏》,这和儒家思想在中华文化中的地位很不相称。明、清两代曾有学者提出编纂《儒藏》的建议,但因工程浩大,没有能够实行。今天,中华民族正处在民族伟大复兴的前夜,重新回顾我们这个民族文化的源头及其不断发展的历史,必将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发挥重大作用。为了能系统地、全面地、深入地研究儒家思想的方方面面,把儒家经典以其各时代的注疏和历代儒家学者的著述以及体现儒家思想的各种文献编纂成一部儒家思想文化的大文库《儒藏》,并进行若干专题研究,无疑对当今和后世都十分必要,特别是对使中国文化成为世界文明新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现在,“《儒藏》编纂与研究”已成为“2003年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攻关项目”和“2004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这个项目完成至少要用二三十年的时间,我只希望能把这个项目的开头做好,以便别人能接着来完成。
我真正开始做哲学和哲学史的研究应该说是在1980年,那时我已经53岁了,但我没有气馁,仍然希望能为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尽一点力,但毕竟最好的年华已经过去了,要想真正成为一名有创造性的、有重大影响的哲学家已不可能,“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而已。
原收入《我的哲学之路》,北京,新华出版社,2006;后收入《家学与师传》,第2卷,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7
我为什么没有成为哲学家
一个外国学生向我发问:“为什么不说你自己是哲学家?”
1997年夏,我去比利时访问鲁汶大学,该校的一位女同学Vanessa Verschelden写了篇论文《汤一介为什么不说自己是哲学家?》。她把这篇论文送给了我,可我不懂比利时文,所以至今我都不知道她写的内容。但是,在鲁汶,我们谈了两小时。现在,对于当时谈了些什么,我大都记不清了。但我却记得对她的论文发出的问题(即“为什么不说自己是哲学家?”)所做的回答,因为这也是我常常问自己的问题。我的回答是:“这个问题得由中国近半个世纪的历史来回答。1949年后,当时有个普遍的看法:只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这样一些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或社会主义国家的伟大领袖(各国共产党的领袖)才可以被称为哲学家,而其他人只能是哲学工作者,他们的任务只是解释这些伟大人物的哲学思想。这样的思想紧紧地缠绕着我们的头脑至少三十年。20世纪80年代后,我们开始对此有所怀疑,而后逐渐摆脱这一思想的困扰。但是我们真能从这种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吗?我们这一代学人,甚至我们上一代和下一代的学人中,谁也难以明确回答。”
我曾经也想要做一个有创造性的哲学家
但是,是不是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做一个哲学家呢?不是的,我曾经也想要做一个哲学家,而且想做一个有创造性的哲学家。
1947年,我选择读北大哲学系,就是想做一个哲学家,能通过自己的独立思考,来探讨一些宇宙人生的根本问题。在1946年至1948年期间,我曾写过一些文章,如《论善》、《论死》、《论人为什么活着》等等,可是这些论文的手稿都已丢失了,但我手头还保存了一些当时写的文章的手稿,如《我所认识的玄学》、《对维也纳学派分析命题的一点怀疑》、《论内在关系与外在关系》等等。后一文,贺麟先生曾看过,并有个批语:“认柏拉得列所谓内在关系仍为外在关系,甚有道理。对内在关系的说法,亦可成一说,但须更深究之。”以上这些文章都未发表过。近日我又翻看所存的这些文章,虽深感其幼稚,但却也感到自己是在独立思考一些问题。另外,我还写过几篇散文和诗,其中也反映出当时我确实在思考着一些宇宙人生的问题。1946年至1948年中国社会正在发生大变动,许多青年人不知道摆在他们面前的前途,很容易产生一种悲观的情绪,而这种情绪正促使他们去思考。现在我重读这些诗文,深感自己再也写不出这样有真情的东西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把许多人都变得很实际,没有幻想,没有激情,不再有发自内心的爱与恨了,这难道是人们特别是年轻的知识分子应有的生活?
1949年,一切都改变了,由于感受到毛主席一声“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震人心弦的强音,我们绝大多数中国的青年知识分子很快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但是当时我们却不知道,我们接受的实际上是苏联的列宁斯大林的教条主义。自此,也许是心甘情愿地或半心甘情愿地抛掉了“当哲学家的梦想”,而自愿地或半自愿地做个“哲学工作者”或者叫做“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员”。确实,在1949年后,由于当时的“革命”形势的感染,像我这样的青年学生很快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当时决不是假的,而是真心的接受。1951年初,我被分配到中共北京市市委党校工作,在那里我认真地读了《毛泽东选集》四卷、《斯大林全集》、已出版的《列宁全集》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的部分。我努力做笔记,讲课很认真,不仅在市委党校受到学员的欢迎,而且在市委机关讲课也受到欢迎。但这一切都只不过是教条式的解释,我所读的马克思主义的书的篇章字句,没有一点创造性,也可以说没有一点自己的思想。这样下去自然不会成为“哲学家”,严格地说连“哲学工作者”也算不上。
1956年,我越来越感到在党校教书,没有什么前途,今天教《联共(布)党史》第九至十二章所谓“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明天又换成教“中共党史”,后天可能又要去教“马克思主义哲学”,没有一个专业,这样下去可能连混饭吃的资格都没有了。于是我于1956年10月回到北京大学,想从事“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在1957年至1964年的八年中,我写了三四十篇文章发表在报刊杂志上,也参加了当时所谓的“学术讨论会”。我写的文章大概分两类:一类是批判所谓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例如我写过批判冯友兰、吴晗等先生的文章;另一类是有关中国哲学史上的历史人物的文章,这类大多是根据日丹诺夫关于“哲学史的定义”,批判中国历史上的那些哲学家,给每位哲学家戴上“唯心主义”或“唯物主义”的帽子,定性为“进步”或“反动”。这样的研究根本算不上什么学术研究,这样的研究方法只能把自己养成学术上的懒汉,败坏“学术研究”的名声。上面说的这两类文章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把学术作为现实政治的工具。这简直是对“哲学”的亵渎。
如今,成为一个有创造性的哲学家已不可能了,但至少我还可以算得上一个“哲学史家”
“文化大革命”给了我非常深刻的教训,在“文化大革命”后,我总结了一条教训就是:“我今后不能听别人的,得用自己的脑袋思考问题。”因此,从20世纪80年代起,我一直在清洗自己头脑中“教条主义”的毒素。但是真要清除那些“教条主义”的毒素也并不容易,常常感到力不从心,又自觉受困于那些“教条”。自80年代起,我主要研究的是“中国哲学史”,但我实在并不甘心,也时常提出一些“哲学问题”,不过都没有成系统。现在我已年近八十,要想成为一个有创造性的、为人们所公认的“哲学家”已经是不可能了。不过我仍可自慰,至少我还可以算得上一个“哲学史家”。“哲学家”是要创造出一套思想,让别人来研究;而“哲学史家”是研究历史上哲学家的学者。而尚可告慰的是,我仍在不断地研究着“哲学问题”。我探讨着中国传统哲学的价值所在,我思考着中国现代哲学的走向,我关注着当今人类社会存在的文化问题,甚至我还雄心勃勃地设计着创建“中国解释学”。我想,活着就应该不断地想问题,生活才有意义。
今天想来,我没有能成为一个“哲学家”,从我自身说,也许我没有这个天分,但更主要的是我没有完全摆脱中国现实社会政治对我束缚的勇气;从社会环境说,20世纪后半叶缺少产生“哲学家”的条件。我们回想一下,这五十年是否产生了哲学界大多数人公认的有创造性的“哲学家”?而且在三四十年代所出现的一批有创见的“哲学家”,为什么后来也没有能继续发展他们的哲学思想?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我认为,最主要的是缺少“思想自由”,把思想禁锢在一个框框里,这样怎么能产生真正的哲学家?哲学思想的发展往往是由“异端”突破,而开创新的局面。因此,必须打破束缚人们思想的条条框框,才可以真正实现“百家争鸣”,从而推动哲学的发展,而且这样才可能避免使思想“教条主义”化。我们期待着“哲学的春天”早日到来,这才是中华民族的福祉所在。
原刊于《北京日报》
2006-07-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