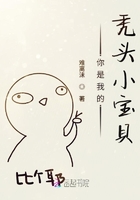“本来打算再过段时间把这个事交给你,但怕是等不了太久了。”一个头发已然花雪白的男人半卧在一袭通体碧绿油亮的翠竹摇椅上缓缓说到。摇椅边上站着一个年龄大约二十岁的少年。少年清清秀秀,眼神中有些慵懒不恭。这个透着不恭的少年此时恭恭敬敬的垂手站在一旁,但听了老人的话,身形微微晃了一晃。
“父亲,别这么说,大清早的。”少年的声音透着些鼻音,像是感冒了,又像是才哭过。前额的头发有些长,挡着一半眼睛,看不出眼睛是不是有着红血丝。
“小北啊,这件事,还是趁着你老头子清醒,早些同你说的好,我呢,一时半会儿也不会咽气,只不过这件事如果没个结果,我没脸去见你亲爹呀。”男人的声音不疾不徐,声音有些悲壮,又透着些不甘。
“父亲,可咱们不是说好了,等我二十五岁,再一块去办么?”少年仍然在抗拒,但少年心性,哪有不爱个秘密的,如此看来,少年是个孝子。
“不等啦,我等上半年或许没问题,但要我等上三年,老子怕连灰都不剩了,怎么你个臭小子打算带着我骨灰去办事啊。宁愿我死了还要折腾我,也不听老头子的话,好让老头子能安安稳稳体体面面去见你亲爹吗?”男人拿眼斜着少年,语调阴阳怪气,脸上皮笑肉不笑得佯装生气。
被叫做的小北低下头,叹了口气,如果在以前,少年一定会一字一句驳回,虽然知道自家老头子挺倔。虽然现在,小北觉得应该陪老头子养病是正理,家里下人虽多,但侍疾这等事,还是亲力亲为更为妥当也放心。而过去的事,总归是过去了,再去探究也不能改变些什么,但话到嘴边,真的是不忍心。
但现在,他决定妥协了。或许,抓紧点时间,快点办完事,还可以得一个两全也说不定吧。于是,小北顺手抄起小几上的一个紫砂壶给自己倒了杯凉茶,轻轻喝了口,倒也不是因为口干,纯粹是为了压一压心里的焦虑。
“好吧,我同意了,不过我有个条件,我让未晞来照顾你,你可得配合,不能使性子,不管是诊脉还是服药,一切都得大夫的。”未晞是小北亡母的贴身侍女,虽说是个下人的身份,但其实是世交家的女儿,为了躲避仇家而送来避难的。未晞在家中的吃穿用度教养都是照着世家小姐的规矩,安个侍女的身份实则是隐人耳目。
“同意同意,你要是去办这件事,我也想多活几天,一定配合,省得万一差上半口气没脸去见你亲爹。”
小北摇摇头,心道老头子果然是老头子,病着也不糊涂,一番话讲得滴水不漏。
“好,那就定了,告诉我吧。”妥协的少年拉过一个带着靠背的椅子,一屁股坐下,估摸这个故事挺长,也就找了个舒服的姿势坐着。
男人点点头,说:“打小我就告诉你,你是我养子,你亲爹与我同属察院,为监察御史里行。你亲爹的死因,这个事要从斯里城说起了,斯里城,呵,虽然地图上再也没有这个地方了……”
“这些年,我其实一直在找当年和斯里城有关的人,但找来找去,也只找到你们丁家,而你们丁家也只剩一个你了。”
小北盯着手里的茶杯子,斯里城这个地方,他曾听老头子提过,小时候以为是个普通的地名,多半也是个好山好水的地儿。记得刚入宗学的时候,有次突然想起了“斯里城”,便一不做二不休找了张地图,用小胖手巴拉个便,结果看着地图的蝇头小字眼睛都快成了对眼儿,也愣是没有找到“斯里城”这三个字。
小北记得自己还特别好问,拿着地图乐颠颠的去找夫子,特有礼貌的问夫子斯里城是不是一个很小的地,它在哪个省。那时尚且年轻的夫子摸了摸他的头,说他八成睡迷糊了把梦里的地名儿拿来问。
不服气的小北十分不甘,又跑去问了老头子。结果老头子只给他撂了三个字:“不存在!”
骤然听到“斯里城”三个字,小北觉得自己这些年被老头子诳得不轻。
小北,姓丁,名月北,无字。他口里称的老头子,也就是养父,本是御史台察院下一名监察御史,后不知什么缘故患了疯病,只得告病。先皇怜悯,给他在老家置了几亩田赏了些银子。老头子回老家之后,隔了很久,疯病居然被治好了。再之后后便办了个宗学,赖以生活。
老头子姓何,名浩然,字足道,因为任监察御史时刚直不阿,刚刚入察院,作为一个小小的监察御史里行就参过尚书大人,后被朝中同僚称为老头子。
老头子本是个狂妄的性子,但又相当纠结,叫他何大人,他觉得显不出自己的与众不同来。同辈们称他做足道兄,他又觉得自己像是从事某种服务业的,又不喜。但老头子三个字,他听着到觉得入耳,以致后来人都叫他老头子。
老头子换了个舒服的姿势继续说道:“其实这个事情,如今就算弄得真相大白,你爹也回不来了,但大丈夫有所为有所不为,这件事不光是查个真相,也是还枉死冤魂一个公道。”
当年斯里城可以算得上除了王都之外最为富饶的一个城池了,而且地处中部,也无邻国外敌的滋扰,四季分明,一道江水环城蜿蜒,当地百姓的日子过得颇为泰和。
就是这么平和的一个地方,突然发起了瘟疫,这瘟疫来得奇怪,与所知的瘟疫不同,来得颇为温和,染上的人起初也只是觉得自己得了风寒。一时间城中药铺里的艾条、银翘等治疗风寒的事物变得畅销,推拿泡澡的地儿生意也相当红火。
原本也没当个事的事,一个月后变成举国大事。因为斯里城的棺材铺子的订单已然接不过来,所以临城的棺材铺子接了些斯里城的订单,然后在临城也开始有大部分人得了伤寒。人们聊起来,发现死了人都是之前得了伤寒的,而且死状几乎一样,嘴唇发紫,都是窒息而死,据他们的亲人说,都是最后喘不上气。
一道奏折到了圣上手上,龙颜大怒!
小北的父亲丁泽中,便被派到了斯里城去调查。老头子说,下圣旨的那天,泽中刚刚同他青梅竹马的表姐圆了房。朝廷命官带着公务,何况去的地方又闹瘟疫,自然不便带着发妻。只是家中也无人能托付,想了想自己同朝中的何浩然也就是老头子交情一向不错,何况老头子为人自不会做出有违兄道义的事,托给他,很放心。
泽中快马加鞭到了斯里城,原本记忆中富饶的斯里城一片颓败之象。记忆中在还没有入仕途前,有幸拜访过的云香阁现如今也大门紧闭。抬头看看,窗子倒是开着,只是少了拿着大红帕子倚窗而望的姑娘。
沿街其他的店也没好到哪里去,但凡有个铺子的,除了医馆,都是大门紧闭。零星有几个领着筐子卖点蔬菜水果的小贩蹲在街边,幸亏还有几个小贩,让人觉得斯里城还有点烟火样儿,要不斯里城可成了死里城了。
初到一个地方,先要驿站落脚,接下来才是去当地官府处去了解情况。谁曾想,泽中一进驿站,便看见站得齐刷刷的几个官员,面如菜色,抖如筛糠,手里拎的暖手炉子里应该是放了不少艾草,说是辟邪祛瘟疫的。
泽中此时年少气盛,又是监察御史,看着当地官员如此站了一地,也没觉得不对。当下招呼了一名看着最为老实的官员仔细问了问当地情况。
据这个看着十分老实的官员所说,起初不觉得有什么不对,只是很多人伤风,加上正值冬季,此地寒冷且因为四周环水,潮湿也是有的。往年这个时节,患伤风的人也不少。对付伤风,百姓也都是同往年一般,驱寒祛湿加上清饿一天,如若不见好,再喝上两副汤剂也就是了。谁曾想过这其实不是伤寒而是瘟疫,待到大家反应过来,已经收不住了。
泽中看着站了一地的战战兢兢的官员,心道的确也怪他们不得,便让官员整理一份斯里城患病者的名录交给他,名录上要著名住址街道现在患病的情形。此外,在准备一个一比一的斯里城的沙盘,务必求细,街道住家商户要一应俱全。
一个看着十分精干的官员马上上前递上一份卷轴,说道:“御史大人明鉴,名录下官已准备好,此份所录为昨日统报,下官已经下令每五家为一户,设户长,每五户为一令,设令长。斯里城共三百二十八户,皆已悉数记录。沙盘下官便去办,恐需两日。”
泽中点点头,心道此人确实精干,便记了一记该人的名讳,曾仕梵。
“这些事,是你父亲寄回的信上所写。那时他新婚燕尔,每隔十天便会给你母亲传回一封信,因为我被托付照顾你母亲,自然也会给我一封。”老头子想是一个姿势觉得有点累了,支起半个身子给自己的杯子里续了些水,抿了一口说道。
“那给母亲的信和给你的信,你还留着吧。”小北问道。
“自然是留不得,当然原本我们也没想到你父亲去了斯里城便再也没有回来,因为他传回的信除了问候,也都会简单说说斯里城的状况。”老头子说罢,顿了一顿,“其实他去的时候,情况看着是不太好,但自他过去,就没有大量的人新增的感染者了,而你父亲可以说是自他去后的第一个感染者,而且还是呆了很久才感染的,所以我一直觉得蹊跷。”
“那些信,被当今圣上下令交出,说是要引以为戒,但我呈上去后,没有多久便传出了,斯里城封城的消息,随后又去了轻骑十三队,再后来“斯里城”三个字变成了禁语,一旦发现有人谈论或者著作中提起,株连九族。如果不是我假装疯癫,圣上又突然发了点怜慈之心,恐怕就再也没有人知道以前还有斯里城三个字了。”
“不过么,我其实矫了你父亲的笔记,誊了一份,交上去的是老子我写的,其实当时没多想,只是觉得那些信是你父亲留给你母亲最后的一些物件,觉得应该留给她做些念想。可因为给我的信也得交上去,而你父亲给你母亲的信所用的丝绢又不是寻常的,为了不露馅,我只好全部誊了一遍。”老头子悠悠说着,“幸亏如此啊。如今,这些都在宗学后面佛堂门口的后墙上第三块青砖后面。你自己取来看看就知道我为什么说这个事办不完,我没脸去见你亲爹。等你取了信,你就知道了,最后一封信上,你父亲说不日便可回来。但送来你父亲身故的消息,同那封信只差了两天。我开始疑惑便是这里,因为你父亲提过,这个瘟疫不会那么快要人姓名,就是最初大家都不清楚时,这个病也是会缠绵数日也会让患者命归黄泉。”老头子说罢,挥了挥手看上去是真的倦了,讲了半天的话,确实也该倦了。
“父亲,那我先去取信,不明之处再向你讨教。”小北站起来,行了常礼便退下了。
三月的江南时节,草长莺飞,自是一片好风光。宗学处偏又得着另一宗妙处,虽然院落自然谐趣没有过多装饰,但院子中几树的玉兰确开得正好。其中一树不同与其他,花朵带着粉紫色,远远望去心旷神怡。
小北心中揣着事,途中也没多停留,便来到宗学,恰逢春耕时间,宗学放假,先生回家照料田地便也给学生放了假。小北依着老头子所指,干净利落得找到了第三块砖,在其中找到一个金丝楠木盒子,许是老头子怕信被虫子蛀了而特意寻来的吧。
携了楠木盒子,小北即刻原路返回住处。吩咐下去给他备好四色茶点,没事别来找他,顺便叫未晞去老头子那看着,照料到他过去为止。
既然答应了老头子,事情还是尽快完成的好,虽说曾有圣上的禁令,但禁令是先帝下的,前年先帝驾崩,新帝继位,尽管新帝十分了得,但料想对二十年前的事可能还不会太过在意。看着旁边再无他人,打开了楠木盒子。
小北看着里面的信,心里有点恍惚,数了数有二十封。老头子说每十天会送一封信回来,这么一算在那边也就是三月有余的样子。待全部的信看完,小北心中已经理了个大概。
老头子说不办完合不上眼去见小北生父,诚然不假!
合着给母亲和给老头子的信,小北算是知晓那时的一个大概。
泽中当日前去时,叫人备了斯里城的沙盘和感染瘟疫的人名册。乍看起来,确实是瘟疫,一个城池感染者过半,症状一样,死因一样。只是泽中发觉,城北的感染者远远多于城南,而城南的感染者在泽中调查后发现,这些人的营生都在城北。
就是那个邻城,也是位于斯里城城北,同斯里城隔了一条水路。
这是一个奇,想必老头子也觉得奇怪,然而为何城北多于城南,小北没有到过斯里城,自然不知道城中风貌,看来确实必须去一趟才好。
前去斯里城,确实需要费些功夫。地图上都已除名的地界,现在要么是换个名字,要么是一方死土。如果换了名字,前去打探二十年前的旧事,无疑是给自己脑门上刻了三个字“不要命”。但若是一方死土,就不晓得途中会不会有暗探,毕竟牵扯到了皇家。皇家的事,尤其是不想为外人知的事,谁沾上也没个好。
不过小北有种预感,斯里城如今多半是方死土。二十年,说长不短,但也不足以生出一座没人知晓过往的城来。如此,调查死土虽然也凶险,但总不至于没有一丝生机。
第二日,小北向老头子此行,顺道要了地图——二十年前的地图。当年先皇实是雷霆手段,相关记录文字一点不剩,办事的人据说也都染了瘟疫不治身亡。但千算万算,没有算出一个疯子还有如此好的记性,楞是将二十年前的地图生生记了二十年才默出来。
地图是老头子当着小北的面默的,小北看着老头子干干瘦瘦,握着笔的手也颤颤巍巍,但下笔之爽利依然同往常一样。待墨迹一干,小北便揣着地图出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