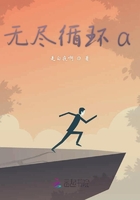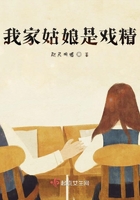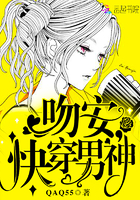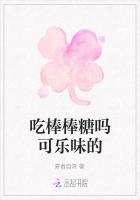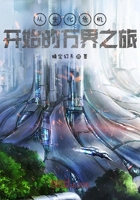二十岁的觉醒
每个人的生命都应当有一场属于自己的觉醒。可以是保尔·柯察金在烈士公墓悟出的“人最宝贵的东西就是生命,生命属于我们只有一次而已。人的一是生应该这样来度过的:当他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过去的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样,他在临死的时候就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可以是卡尔·马克思在高中毕业论文中写到的:“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但是永恒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可以是司马迁在遭受宫刑后体悟出的“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也可以是慧能大师所悟“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菩提只向心觅,何劳向外求玄?听说依此修行,西方只在目前!”。
而后的人生里,保尔·柯察金将他的余生投入到苏俄的社会主义革命事业中;卡尔·马克思把他的生命奉献给了社会主义事业,直到最后一秒;司马迁终其一生忍辱负重只为以秃笔著世间“离骚绝唱”——《史记》,他们人生最为人称道的,除了他们开创的事业和留下的丰功,还有他们与众不同的觉醒。
觉醒是文学常见的手段,是以制造矛盾,承接转折,升华主题,丰满人物,没有矛盾起伏跌宕的故事是寡淡无味的,是任最伟大的作者也无法写得精彩的。《流浪者之歌》中,悉达多如果没有面对浩浩江河时的明悟,那么他对父亲的忤逆、对美色物欲的沉沦、对宗教的背叛都将显得苍白而毫无意义;《幽谷百合》里,费利克斯在莫尔索夫人猝然长逝后,连同他仅剩的最后一丝温情也埋葬在了那个他最爱的女子逝去的土地,向未知的险恶的复杂的金钱铜臭的政界迈出了步伐;《月亮与六便士》中,斯特里克兰德在长达三十多年的循规蹈矩的生活中偶然得到一抹觉醒的光辉,于是他抛弃了他曾努力顺从、最后坚决背叛的世俗,用生命谱出了一瞥浓重的礼赞。《刀锋》、《麦田里的守望者》、《岛上书店》、《活着》、《人间失格》、《白鹿原》、《人生》、《红楼梦》……几乎所有伟大的文学作品都是一个个挣扎和觉醒的故事,题材不同,人物不同,性别不同,视角不同,但核心总是相同的,不约而同地默契地告诉我们一个相同的道理:真正的人生是应当有一场觉醒的。
苦行的沙弥终其一生所寻找的不过是无限趋近于佛法的真谛,平凡的世界里旅居的行客漫漫一生所追求的不过是在生命诞生之初和死亡凋零之时的中间的意义。有的人在经历大风大浪后幡然醒悟,选择一种和世俗背离的人生;有的人在死亡之前回溯前生,涕零不止;有的人任生命的沙漏一点一点地流尽,无动于衷;有的人似乎触碰到了与众不同,可是又怯弱地融入芸芸众生。《百年孤独》中有过这样一句话:“买下一张永久车票,登上一列永无终点的火车。”在生命有限朴实的行程里,我们都是向死而生的舞者,不同只是在于有人茫茫无措,有人欣然规往。
十八岁在盛夏汗水中悄然而逝,由于入学年龄较大,我并没有赶上最早一批千禧之年青年的成人礼,以至于那一年的记忆始终停留在高考出题人留给前辈们的难题上。个中心情是怎样的呢?说实话,有些幸灾乐祸,彼时的我心态稚嫩,思想肤浅,行为随性,还没有准备好迎接数以万计的考生煎熬十余年的高考。此外,也有一种说不清楚的感觉,一点点对明天和未来的担忧和惶恐,一点点对未知的随机的徘徊和怯懦,还有一点点怀揣着的希望和不同,以及一点点对结束高中生活的学长学姐们的羡。记得十八岁那一年的六月八号晚,对面楼层的一个师兄畅意地对着窗外大喊:“老子毕业了!”我循着声音望去,眼里除了空无一人的教室一无所有,余光中一个带着黑框眼镜、短发一寸的男生在楼下撒欢似的狂奔。我那一刻的心情就如上面所写下的那样。此后,我成为了那栋文脉最盛、风水最好的楼里的一员,在哪里度过了我的十八岁、十九岁。一年之后,我坐在一个完全陌生的教室里仍然会想起那个学长肆无忌惮地奔跑。
二十岁悄然而至的时候,我正绞尽脑汁地写着一篇总结性的长文,用以给自己过去的二十年一个交代,给自己之后的人生一个不错的开端。写《双十年华》时,我端着一颗怀旧的心,字里行间尽可能地逃避着对难以捉摸的未来的憧憬,只是用一些模糊的字词去搪塞过去。一来是篇幅有限,题目限制;二来是其实当时的我不敢不愿不想不会把看似遥不可及实则触手可及的未来摆在面前,当时的我已经很久没有做过梦了。记得高中的时候,睡觉之前脑海里全是课堂上老师的声音,每一句话都清楚地重现,而且可以删繁就简,还能调节速度,根据我的记忆重新编排顺序。每一本翻阅过的书籍也都有生命似的在脑海中再次翻阅起来,每一个页码,每一行文字,每一张插图都活灵活现地闪出来。我能到过很多后来出现在试卷上的考题,老师说那是上天在帮助勤奋的人,同学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心理学家说那是脑子里一种叫做海马体的储存记忆的物质对于相似印象的感知错觉。我觉得他们一个都没有说准,因为二十岁的我再也没有做过类似的梦,甚至把睡觉之前的回忆都给记不起来了,在人生三分之一的时光里,我连做一个记得起来的梦的机会都没有了。每天,陪伴我起床的是日上三竿的正午,那时我脚下踩着我一整天最小的影子,跟着我度过白昼的是简单的饭食烟火和等待下一餐开始的无聊时光,随着我煎熬黑夜的是倦倦慵慵的酣睡。我做不了梦,于是我拼命地想要做梦,像要证明什么的样子,可是又不知道自己想要在睡梦中寻找什么,但是除了闭上眼睛,我想不到其他可以迎来明日太阳的等待。那便是毫无意义地虚度年华的生动形象,颓废倾丧是最衬当时状态的词语,那是二十岁还未来临时的鲜明状态。
即使二十岁生日那天,心里也并没有太多动荡,除却朋友暖心的祝福,生活依旧贫瘠而没有精彩,三三两两跑到脑海中的故事也随之搁浅。记得我在家待了近八个月,几乎没有出过门,没有找朋友玩,为数不多的娱乐是上课时明目张胆地打游戏,和翘课无异,和许多人无异。父母在外为家里上学的四个孩子每年厚积的学费和生活费打拼,归家是年底的事情。二弟高中学校早早开学,一去就是半年;三弟和小妹一周也只有周末回家,其余时间待在学校。家里只有我一个人,一个似乎被遗弃的人,被时间遗忘,被别人遗忘,被自己遗忘。我每天最大的课余活动除了睡觉,就是挪着窝地晒太阳,以至于半年的时间里,我并没有白,反倒是晒黑了不少,加之没有好好吃饭、没有锻炼的缘故,瘦下来不少,脸上不时浮现若有若无的苍白,始终萦绕在一种挥之不去的孱弱病态里。那是我所有已经历过的一生之中最接近死亡和腐朽的时期,对于堕落和颓废等词语,我早已麻木不仁。有时候我会觉得自己像死了一样,每天躺在床上等着阴间的鬼差来带走我并不值得一提的生命,有时候又会积极地审视周遭的一切,即使是半年之后的现在,回想起那段时间的一切,还是会有一种慭慭然的局促。好在我不太容易记得住事情,回学校之后,整个人仿佛重生了。无聊的时候有朋友陪谈至深夜,相谈甚欢,相识无尽言,谈一些很少有机会和外人交流的话题。也不必担心下一顿吃什么,因为只要有钱就饿不着,不用自己动手做。课堂和睡眠之间的时间能够用书本来打发,不必借着学习的幌子,仅仅只是读书,享受一下文字浸润生活的感觉,把自己之前翻开第一页就再没有翻动的书从头至尾读一遍,慢慢地用笔摘录一些有趣的词句,写下几句寥寥的零星的感想,做着一个文化人应该做的符合身份的事。读马克思,读哲学,读文学,读社科,读娱乐,那便是我最为欢乐的时光。那段时间我又开始做梦了,七个小时有限而深沉的睡眠里,我梦到了一些消失了的人,记不起来的事,那是我十几个钟头慢慢冗长的半夜惊觉醒来又悻悻睡去从来没有梦到过的事情。之前,除了一身淋漓的冷汗和倦怠的疲惫,例行的睡眠带给我的只有一而再再而三的浑噩;如今,潜意识作祟的迷梦让我记起了很多事情。终于,有一天,我决定找一个没有任何俗事的时间,认真思索我贫乏的生命平凡的走向,一场二十岁的思索,后来我称之为觉醒,也可以说是抉择,当然,神经质也行。
我偶有新奇想法:一个无聊静坐在自习室的下午,我一股脑儿地想到了十几个可以写成一本本长书的有趣故事;一个昏昏欲睡的夜幕,我忽然想要号召朋友成立社团;一个烈日当空的正午,走在快要融化的柏油路上的我倏忽地想要拥有一座属于自己的房子,甚至有想要和一个姑娘结婚的念头;一个平平无奇的周末,我大快朵颐时忽然质疑起马克思的理论……而那一天的思考却算不上一时的心血来潮,更多地像蓄谋已久。
我端坐在长桌前,手边是一杯氤氲着热气的淡茶,只为给阴沉的色调增添一点儿清新的活力。我闭上眼睛,像每一个夜晚枕在枕头上一样,眼缝之间有若有若无的亮光透过来,逼得人不由把眼睑闭合得更紧些。炫亮的气氛是为了明白地思考,只有黑漆漆的空间才适合睡大觉,虽然现在很多人已经不遵循这一套了。他们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通宵欢愉,在街灯幽暗的巷道狗苟而生;他们在暖光灯和黑白墙壁的房间里酣睡,在清晨晨曦还没有出露时躺下。眼前的世界一点点被墨色隐没,耳边原本沉寂的世界一下子活跃起来,头顶天花板上层拖鞋的“吧唧”声,楼道里走窜的小提琴声,不时闪过的电波声……还有各种各样的精彩纷呈的声音。不过这种屏息闭目带来的听觉的活跃并非冥想思索的理想环境,于是脑海里一层层地过滤着嘈杂无章的声响,水龙头滴水的声音,公共浴室零碎的歌声,隐隐的键盘声响,连同所有的除了心跳和呼吸以外的声音一并被剔除隔绝了。房间里只有我一个人,我只有呼吸心跳和思维,思维只有满溢的活力。
我曾经在一部香港电视剧里学习到一种记忆方法,就是把自己的大脑想象成一个巨大的房间,这个房间里有几扇大门,一扇写着人,一扇写着事,一扇写着知识,一扇写着秘密,一扇写着睡梦,还有几扇没有名字的紧紧关闭着的大门。打开一扇门,数百个数千个抽屉样的盒子摆在你的面前,有些盒子是空的,还没有装填进入经历和故事,有些盒子是满的,装着一些片段式的记忆。那些装满记忆的盒子上面有一把锁,有的容易打开,有的需要很吃力地想才能勉强打开,还有一些盒子被沉甸甸的大锁困住,无论如何也打不开,还有一些盒子掩藏在黑暗之中,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放置在那里了,没有人知道那里面装的是什么。研究爱因斯坦大脑的科学家可能会把它称之为人类为开发的潜藏的智力,一个名叫弗洛伊德的人把它称之为潜意识,那里住着和潘多拉一样丑陋的本**望。我思索的正是那一个个被锁上的能够打开的盒子,我在里面装填了我力所能及的记忆。整个过程就是一场风暴似的意识流,看似荒诞,看似毫无章法,可就是实实际际在脑海中搅动着。我的记忆开始于七岁,七岁之前的记忆仅只停留在父母拍摄的几张模糊不清的照片和他们口头传述的故事,我看着照片里被母亲抱着的孩子愣着神,仔细观察着他的眉宇,勉强地能认出自己,至于那些久远的故事,感觉从来没有在我的生命中出现过,那个和现在多愁善感的我迥然不同的孩童,让人感慨,又让人陌生。一扇大门开启了,二十年的成长经历像潮水一般涌出来,慢慢淹没了所有的盒子。我看见一个孩子背着书包,打着手电,在还没有浮白的清晨摸索着去上小学;我看见他把一把钥匙交给他的玩伴,然后随着父母回到老家;记忆的下一站,他在朴素艰卓的农村从一个背着挎包的八岁小孩慢慢地长成一个初中生;高中他跑到了市区里读书,认识了许许多多有趣善良可爱的人,度过了他人生最后一段美好单纯得掺不下任何杂质的年华;后来他远赴北京,带着父母的期盼前往下一个站点。从地图上看,他人生的轨迹简单得可以用笔连成一条直线,他终究没有把脚印踩遍每一块他向往的土地。所有我曾经看到过的建筑、见到过的人,一个接着一个地出现,在一卷时间无法计数的胶卷上放映着。那些房屋和那些土地仿佛从无形的抽象变成了一张图片,又变成了拔地而起的真实图景,我一秒钟可以走过五所不同时间不同空间的学校,踩着不同地方的土地,呼吸漂浮着煤渣的流淌着玉米芳香的弥漫着苹果清新的洋溢着肃杀粗犷的空气。我有些理解极致的意识流《追忆似水流年》的写作状态了,这是真正的随性而为,一个片段还没有完整便被另一个碎片打断,不停更迭,一个世界建立了,一个世界又崩塌了。化学家和生理学家努力用机械的化学物质和物理电子的流动解释一切发生在人脑中的意识,可是他们始终无法解释清楚。他们最终把记忆归结给一个称之为海马体的东西,再无言语。紧接着,另一扇大门打开了,又一扇大门也打开了,所有的大门都打开了,一个又一个毫无关联又相互纠缠的记忆一瞬间喷涌而出,脑海里无数的链条交织着。那些小学到中学的课本,练习册上的每一篇文章,每一幅插图,似乎都在脑海中复活了,每一个曾陌生别扭记忆不住背诵不了的文字一行行的写在没有书页的印象里。几千个日夜,重复单调的,新奇不同的,都以各自不同的姿态回环交纵,时间一瞬间变薄了,薄到不需要反应就已经过去,倍速毫无意义,因为时间又好像无比的缓慢,缓慢得每一个细节都被一一复现,分毫不差,丝厘不池。我面前出现了一个熔炉,容纳所有的过去,熔铸所有的曾经,熔铸一切的度过,熔铸成一个人的前二十载,风起云涌又波澜不惊,波涛汹涌又风平浪静,张狂又清诙,无揩无皆。刘慈欣在《三体》里想象过高维空间的模样,在天文学中,点是零维度,无方向无长度,是一切的伊始,或许也是一切的结束;二维为线,是以构建平面,高等级文明毁灭太阳系就是靠一个叫二向箔的装置把立体的三维太阳系变成一张瑰丽的图画,悄无声息地抹杀在黑暗森林中,《十万个冷笑话》电影里有这样一个片段,主角们被拉入脑洞空间,从三维变成纸片人,然后变成线条,最终变成文字;三维空间即我们日常所见行走的人,跑动的猫狗等一切具有长宽高的事物;三维之上便是四维,《三体》中,四维是一个空间的秩序,身处其中的人可以用肉眼洞见物体的结构,清晰到粒子级别;再往上的维度便不是我能理解的存在了,或许能够找出它们的存在,或许那些美梦一般的概念只存在于幻想之中。可是我却无法用我所知道的知识来定义片刻之前在脑海中喷涌的一切,它似乎超越了维度的定义,又似乎从来就不属于维度的范围,在没有比脑子中的一切更要让人惊奇的了,即使是世间最繁奥的哲理也比不上脑海中掠影的千万分之一。我似又重新活过一遭,就连长桌上的清茶也仿佛活透了生机,越发清亮温软起来。
桌子的另一面,一个与我一般的人正襟危坐着,带着审视的目光打量着我,懵懂又仔细,像一个智者端详后生,又像一个风霜饱经的人思量前世。他是理智的我、冲动的我、感性的我的集合,他是善良的我、心怀叵测的我、邪恶无知的我的集合。其实,他就是我脑海中臆想出来的我,他拥有我所有的记忆,也拥有我所有的秘密,我对他是透明的,他对我也是透明的,我是什么样他就是什么样,不同的是只有我一个人能够看到他。从前,他没有出现,一来是没有人精心把自我挖出来审视;二来是三魂七魄还没有融合归一,依然各自分离。就在今天,一个多年后不知身处何方的我定会想起来的一个静坐冥想的下午和晚上,我不仅把自己又活了一遍,还把很多曾经割裂的东西缝合熔铸成了骨血里的东西。我是一个文科生,这是我很不被世俗,乃至于亲缘称之为骄傲的身份,却是我这一生最为正确的决定之一。与此同时,我不太占优的理化学科我并非一窍不通。身为一个不错的学习者,海内外的文学作品我有过微薄的积淀,虽然对于那些从小在书山辞海里成长的人而言不足以称道,但数量并不少,读得也还算认真,多少有些自己的认知;史学、政治学、哲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多少有所涉猎,要侃侃而谈称不上,但也不至于盲人抓瞎;数理化也还是有些常识的,虽然不多。此外,我对不少体育项目有所了解,精通算不上,但多少有点儿样子,懂些技巧。如此算下来,懂得不少。只是之前有个毛病——难以贯通,即谈经济绝不聊文化,一码归做一码,难以汇通,兼顾不了两头,容易一个劲儿地往远处扯,不容易往中间拉。后来慢慢地,随着对生活的感受力逐渐加强,平凡里也能看到孕育萌发的希望和精彩,恍惚之间也能偶尔触碰微妙的境界,越发觉得自己观点之片面,想法之狭隘,方案之独善,只有待自己走进死胡同才发觉自己原本可以利用其他路径到达目的地时,才会猛然想起自己曾经学过的知识,那一刹那,就好比不用数学的绘画一下子找到了黄金比例,看问题便越发通透,越发灵性,越发圆润。那些扯着头皮也没有解决的困境也便迎刃而解。对面那个人便是融合了所有知识的人,他与昨日的我已然不同,智慧的天花板似乎有了松动的痕迹,孤零零的学科分解的游戏融合成了它原本就应该拥有的样子,就像纸笔至于双手,以前总是宣纸必须配以狼毫笔,现在,钢笔可以配白纸,黑墨可以蘸墙院。一张大网对着海洋铺开来,满足它的只有更多的知识汇集而成的大鱼。做题的生疏感曾让我厌倦学习,可现在,知识的快乐让我有些跃跃欲试地想探索更多已知的未知的,另一种截然不同的快乐充盈着我的躯体,我又感受到了久违的愉悦。我的记忆重新活过,我的知识重新融合,我还是我,却又有些不一样。
清茶渐凉,热气已消,我仰视着洁净得一尘不染的天花板,以一种同样纯净透亮的不掺杂人为干预的思想思索前方的路。我不信仰宗教,我相信希望,相信明天,相信之余我需要给自己的明天一个剪影,一个轮廓,一个可以支持我度过今天的标杆,就像昨夜入睡之前我便想好了今天的三餐一样。我所有的片刻的冗长的思绪都变成了一个端坐在长桌另一侧的我,他虽拥有我的一切,他也如我一般迷茫,也需要指引以支撑下去。关于写作,我想不起来是什么时候开始喜爱的,但我知道这会是一种长期进行下去的习惯,乃至融入我的生命,成为我的一部分。说来可能有些夸张,但事实确实如此。我想不到其他的表达,正如安分的不喜欢冒险的我,只有写作能够让我找到一些定位自己的凭据而不至于给自己下个定义都要别人指点一二。至于生活,我友善地包容出现的一切,就像我曾经接受过所的善良一般,我平静地接受一切离去和转折,因为一切存在的即有意义,一切发的都无法更改。至于未来,我热忱地热爱我活过的每一天,以最饱满的态度去准备迎接,去储备资本,去完备人格,去装备知识和美德。我活在切实的真实之中,以勃昂的精神面对即将到来的模糊与虚幻,以期把它变成抓握得住的真切。
从前有个故事,一个坐在椅子上的人想要站起来,有一双手用力地按着他的头,他无论怎么努力也站不起来,于是他便安分的坐着。有一天,那双大手消失了,可他却不想在站起来了,因为站立的疼痛远没有静坐来得舒适,于是椅子陪伴了他一生。有人说人在25岁之前都应该是一个诗人。这句话不是让每一个人都拎起笔墨纸砚舞文弄墨,而是让生命多一些被允许的肆意妄为,少一些故作的年少老成和厚黑世故。的确,等到撒开绳子还不愿离开时,谁都不是当年为自由抗争到头破血流的小象了,二十岁的觉醒正当时。我不想把这样一个以后一生都会挣扎的命题放到下一个永远没有确定期限的明天,然后是二十一岁,三十岁,五十岁,甚至放到我临死前的最后几个光景的日子。我不是没有想过一生都远未涉及这些话题是怎么样,因为世界上只有两种人没有烦恼,傻子和圣人,只是不能清醒地活过的一生是不能称之为成功的一生的,一个人可以不必抱着拯救世界的夙愿,但是他必然会怀揣为明天寻觅的意义而存在着,哪怕最后意义并没有任何意义,至少还能留下寻找和赋予的经过。
卡夫卡的一生都在寻找终极的意义,可是他失败了,穷其一生他的梦都没能做完;拉里怀疚于战友的死亡,于是他用尽一生,背负着常人不理解的痴狂去寻觅人生真谛,错过了一个他爱也爱他的人,成为了一个出租车司机。但是卡夫卡的一生是成功的,他的生命在寻觅的旅程中绚烂,并给予后人奔赴向前的力量;拉里辜负了所有人,但是他的内心一片清明,没有留下任何负累和霜赘。虽说偶有的觉醒注定偏执和狂热,但它恰恰也诠释寻觅和赋予。人的一生终究是要为自己活一次的,不如就从现在开始。
我的一位老师说过,人生就是给一张白纸添加内容的过程,有些已经画好的不可更改,但无尽的空白可以随意填涂。二十岁,有人迷惘,有人不惑,有人刚刚醒过来。
每个人的一生都应当有一次觉醒,因为每个人的一生都是一段传奇,每一次觉醒都在成就可能得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