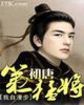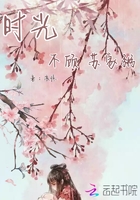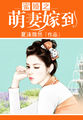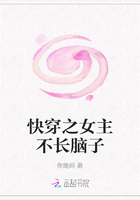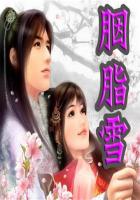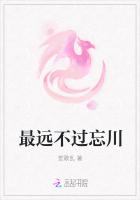中国长城作为一种治国方略,是政治理念的实践,精神力量的体现,哲学思想的结晶。长城从始筑到历代对其修筑,在中国延续使用了将近3000年!一项工程,历经千秋万代传承使用,遗存至今而辉光永照,这在世界上除了长城别无它!因此,长城的出现与存在,总是自有适合它存在的环境、理由和哲学。
长城起源于防御垣墙。防御垣墙起源于原始人类的房屋墙壁和院墙。当时,建筑房屋、院墙是用以防御来自自然、野兽及他人的伤害或侵犯的。后来,院墙发展为聚落人群的围墙。聚落围墙发展为城市城墙。
中国的城市建筑起源非常古老。《补史记·三皇本纪》说:人皇兄弟九人,分长九州,各主城邑。《汉书·食货志》说:神农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汤池百步。《轩辕本纪》说:黄帝筑城造五邑。《黄帝内经》说:帝既杀蚩尤,因之筑城。新石器时代的湖南城头山古城遗址,距今约6000年。据考古发掘,确认它是我国目前已知建筑年代最早,保存最完整,内涵最丰富的古城遗址。
廓是最早的长城。《淮南子》说:夏鲧作三仞之城。《吴越春秋》说:鲧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此城郭之始也。为了扩大城市的防卫范围,环绕城市再建垣墙,这就产生了廓(郭)。廓范围的不断扩大,形成了具有各种防卫功能的长城体系。环绕京城的廓,这实际上就是保卫京城的长城,后世有的被称作“畿上塞围”。 也有建置烽堠、堡寨、栅栏、种树、镶嵌撅子或开挖壕沟等作为长城防御的辅助设施的。环绕边境要害地区的长垣墙,就被称为“长城”“方城”或“长山”。有许多大山、地方是因筑有长城而以“长城”“方城”或“城”得名的。
边防壕堑起源于原始人类用以自卫的环屋壕沟,进而发展为保卫城市的护城河。后来,借用挖掘护城河的办法,在边境、通道、要害地区或长城一侧挖掘壕沟、深坑,或在壕沟沿上再垒砌垣墙,用以自卫或阻敌。这也是一种功用与长城等同的防御设施,后世也有沿用的。
唐初著名学者太史令傅奕说:《易》称王候设险以固其国。筑长城、修障塞,《易》之设险也。今朔塞上多古长城,未知起自何代。七国分争,国有长城。赵简子起长城以备胡,燕秦亦筑长城以限中外,则长城之作其来远矣。秦兼天下,益理城壍,城全国灭,人归咎焉。自汉至隋,因其成业,或修或筑,无代无之。
纵观历代王朝边境防御史,自西周至晚清,除蒙元王朝外,各朝皆筑长城。
周宣王筑长城阻隔猃狁
周族姬姓,是生活在我国西北地区的一支古老族群。从《尚书》记载看,周族尊崇夏人。我国古文献称周族为黄帝后裔,与夏人同祖。夏人本古氐人。“氐”、“狄”同音。周族实为北狄的一支。
西周早期,周都镐京(今西安西边)的西北地区有鬼方、 玁狁、犬戎等戎狄部落。当时,义渠国虽臣服于周,但叛服不常,是周王朝的西北边患。《诗·小雅·采薇·序》说:文王之时,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猃狁之难。《采薇》有“靡室靡家,猃狁之故”,“岂不见戒,猃狁孔棘”的说法。猃狁即义渠,即后世匈奴。从周穆王到周宣王,多次派兵攻伐义渠诸戎,时战时和。
周代自周懿王、周厉王时,北方猃狁崛起,对周朝威胁最大。周穆王曾讨伐戎狄于大原。周宣王(前827—前781年)即位以后,对猃狁进行讨伐,史称“宣王中兴”。周宣王讨伐猃狁的战争,从两方面展开:一方面是进行兵力讨伐,另一方面是建筑长城。
首先,周宣王收复了周孝王予秦的始封故地犬丘,即今甘肃天水县的秦亭。接着,周宣王收复了周人故地大原,即今宁夏固原地区。周宣王料民于大原,迁戎于大原。所谓迁戎于大原,即将戎(即猃狁)迁徙到大原的北境。在此前提下,周宣王命令南仲在今宁夏固原地区建筑了一道长城,即今宁夏固原长城。
宁夏固原是丝绸北路的交通枢纽,南下可以直抵中原王朝的京畿重地长安、洛阳等古都,北上可以经河西走廊通达中亚和欧洲,是丝绸北路必经之道。西周时期,为了保证其京城北方的安全,周宣王在今固原市原州区(原宁夏固原县城)北面15里处修建了这道长城。
固原长城西周时期属朔方长城。朔方长城始建于西周宣王时期,是西周西北边防长城的一部分,位于西周西北境。
固原朔方长城现存遗迹,依《水经注》的记载,位于今固原县城“北一十五里”处。它在宁夏境内横穿西吉、固原、彭阳三县,长约四百华里。
固原长城,它从西吉县往西出宁夏进入甘肃,经静宁、通渭、陇西、渭源、临洮,直抵洮河东岸;它从彭阳县往东,经彭阳县城阳乡、孟源乡出宁夏境进入甘肃镇原、环县、华池入陕西,经吴旗、静边、榆林抵内蒙古准格尔旗东北十二连城。这道古长城,秦汉时期称之为“故塞”,以区别于秦昭王所筑的“故河南塞”和秦始皇派蒙恬所筑的万里长城。这是西周至春秋时期周朝防御北方戎狄族群所筑长城的遗迹遗址,它是中国最古老的长城建筑。1927年王国良先生在其《中国长城沿革考》中以“相传为秦所筑”将固原长城误说成战国秦昭王长城,其后学界照抄误说,致使这道中国长城之祖埋没至今。
周宣王筑长城隔离猃狁这件事,当时可谓惊天动地,后世赞誉不绝,历代仿效不断。《诗经·小雅·出车》歌颂说:“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这就是说,周宣王命令南仲到周都镐京北方的大原地区建筑了一道长城。《汉书·匈奴传》称赞说:至懿王曾孙宣王,兴师命将以征伐之,诗人美大其功,曰:“薄伐猃狁,至于太原”;“出车彭彭”,“城彼朔方”。《文献通考·四裔考》载:北魏皇兴中(467~471年),蠕蠕犯塞,北魏征南将军刁雍给北魏献文帝拓跋弘上表说:“臣闻北狄悍愚······所长者野战,所短者攻城。若以所短夺其所长,则虽众不能成患,虽来不能内逼。又狄散居野泽,随水逐草,战则与家产並至,奔则与畜牧俱逃,不赉粮而饮食足。是以古人伐北方,攘其侵掠而已。历代为边患者,良由倏忽无常故也……昔周命南仲,城彼朔方;赵灵、秦始,长城是筑;汉之孝武,又踵其事。此四代之君,皆君王之雄杰,所以皆同此役者,非智术之不长,兵众之不足,乃防狄之要事,其理宜然故也。”北魏名将刁雍说,周宣王城彼朔方;赵武灵王、秦始皇修筑长城;汉武帝修筑长城。此四代之君“皆同此役”。所谓“皆同此役”,即说此四代之君都是在建筑长城。
史籍记载,古代帝王将相臣僚都知道周宣王“城彼朔方”是建筑长城,不是建筑城堡。隋炀帝大业初,右光禄大夫段文振以高祖容纳突厥启民居于塞内,妻以公主,赏赐重叠,及炀帝即位,恩泽弥厚,狼子野心恐为国患,乃上表曰:“臣闻古者远不间近,夷不乱华,周宣外攘戎狄,秦帝筑城万里,盖远图良算,弗可忘也”, 段文振将周宣王城彼朔方与秦始皇修筑万里长城等同,即说城彼朔方就是修筑长城。(唐太宗)修缘边障塞以备胡寇,下诏曰:“城彼朔方,周朝盛典;缮治河上,汉室宏规;所以作固京畿,设险边塞,式遏寇虐,隔碍华戎。”唐太宗将周宣王城彼朔方与汉高祖修筑沿河长城(缮治河上)等同,即说城彼朔方就是修筑长城。唐玄宗开元二年二月以鸿胪少卿王晙为朔方军副大使总管,八月庚申制曰:“昔者命彼南仲城于朔方,军出陇西,劳於渭北,此其备也。”唐玄宗说周宣王城于朔方在陇西、渭北,此方位正是今固原长城走线。唐德宗贞元八年中书侍郎陆贽上疏曰:“夫中夏有盛衰,夷狄有强弱,事机有利害,措置有安危。故无必定之亲,亦无长胜之法。夏后以序戎而圣化茂,古公以避狄而王业兴,周城朔方而猃狁攘,秦筑临洮而宗社覆。”陆贽将周宣王城彼朔方与秦始皇筑临洮长城等同,即说城彼朔方就是修筑长城。宋《册府元龟·备御》载:“周文王为西伯,以殷王之命,命南仲为将卒往筑城於朔方为军垒,以御北狄之难,故作《出车》之诗曰:‘天子命我,城彼朔方。’”于此看出,宋代也知道周宣王(宋人以《毛诗序》定《出车》为周文王时作,证据不足,当以周宣王时作为定论。)筑城於朔方是构筑“军垒”。军垒即军队用土石之类的材料垒砌构筑的防御工程,亦即长城之类防御工程,如:《国语·吴语》载:“今大国越録,而造於弊邑之军垒”,《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载:“军垒成,秦人闻之,悉甲而至。”杜甫《雨过苏端》诗:“妻拏隔军垒,拨弃不拟道。”今人不省,以为周宣王城彼朔方的“城”就是专指建筑城堡,这是误解。
周宣王筑长城隔离猃狁这件事,开创了中国历史上修筑长城的先河,引领了中国历代王朝在长约2800年中不断修筑长城的大浪潮。中国西北地区自周宣王筑长城之后,魏惠王、秦昭王、赵武灵王、燕昭王、秦始皇、汉高祖、汉武帝、后汉光武帝、三国曹魏、北魏、北齐、北周、隋朝、唐朝、宋朝、辽国、金国、明朝、清朝共计19个朝代都在其西北边防的全线或局部地区修筑过长城。
周宣王筑长城隔离猃狁这件事,对世界历史也产生了巨大深远的影响。北匈奴西迁,与华夏地区长城林立,汉军与南匈奴又联合駐守长城,阻隔胡骑驰骋有关。所以,中国历代长城的修筑,引领了大漠南北、东西方古族在长城沿线的争斗、交流、迁徙、融合与开发建设,导演了大漠南北地区、东西方世界一个又一个的历史大变幻,改写了亚、欧、非行政区划、民族格局、种族融混一次又一次的大变局,演奏着大漠南北、东西方文化交流一曲又一曲的新乐章。
中国长城始筑于西周,至春秋战国盛行。今宁夏固原长城实为西周朔方长城,修筑于公元前827 ~前781年。楚方城修筑于公元前688或678年,齐长城修筑于公元前685年,魏长城修筑于公元前359年,韩长城修筑于公元前约356年,赵长城始修于公元前333年。西周朔方长城(今宁夏固原长城)比楚方城、齐长城早100多年,应该说,中国之有长城,蓋始于此!
宁夏固原西周朔方长城始筑于周宣王时期,距今已二千八百多年,固原长城是中国长城的始祖,固原地区是中国长城的故乡。固原长城在长城史上的源头地位是史无前例的,是真正的长城之父。
春秋战国筑长城保境安民
长城起源于防御工程,各国诸侯修筑长城都是为了防御别国入侵,与霸权及侵略无关。
春秋战国时期,国家不论大小强弱及族别,许多都筑有长城。修筑长城的原义是用于本国防御,保境安民。
楚国长城。《国语?齐语》载:“(齐桓公)即位数年,东南多有淫乱者,莱、莒、徐夷、吴、越,一战帅服三十一国。遂南征楚,济汝,逾方城,望汉山,使贡丝于周而反。”“逾方城”即穿越长城。《左传》鲁僖公四年(公元前656年)载,齐桓公率领鲁、宋、陈、卫、郑、许、曹、等8个诸侯国攻伐楚,楚国大夫屈完对齐桓公说:“君若以德绥诸侯,谁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虽众,无所用之。”屈完所说的“方城”,就是楚国的长城防御工程。《战国策·楚策一》说:“楚,天下之强国也。楚地西有黔中、巫郡,东有夏州、海阳,南有洞庭、苍梧.北有汾陉之塞、郇阳,地方五千里。”楚国地域辽阔,属强国,修筑长城约千里。
齐国长城。齐国筑长城,《古本竹书纪年辑证》载:烈公十二年,王命韩景子、赵烈子、翟员伐齐,入长城。《管子·卷二十四·轻重丁·第八十三》载:“管子问於桓公。敢问齐方于几何里?桓公曰:方五百里。管子曰:阴雍长城之地,其於齐国三分之一。·······长城之阳,鲁也;长城之阴,齐也。”齐桓公在位于公元前688年至公元前643年,齐长城存在于东周早期。《?史记?赵世家》载:(成侯)七年,侵齐至长城。齐国境内建筑有长城,晚近出土的骉氏编钟铭文可证:“唯廿又再祀,骉羌作戎,厥辟韩宗 撤率征秦迮齐,入长城,先会于平阴。武侄寺力,言敓楚京。赏于韩宗,令于晋公,昭于天子,用明则之于铭,武文咸烈,永世勿忘。”编钟铭文中的“入长城”一语,经诸家考证,一致认为这是指齐国境内的长城,存在于编钟铭文纪年之前。关于编钟铭文首句“唯廿又再祀”记载的年代,多数考家认为是东周周灵王二十三年或二十二年,时当公元前550年或549年,此时也正值东周中期。三晋伐齐侵入齐国长城。周威烈王二十二年(前404年)三晋伐齐,“入长垣”。《水经注》汶水注引《竹书纪年》记载:“晋烈公十二年(前404年),王命韩景子、赵烈侯及我师伐齐,入长城。”《史记·齐太公世家》载:“太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齐国是春秋五霸之一,当时富甲天下,亦修筑长城。
庸国长城。《左传》文公十六年(前611年),载:“楚大讥……庸人帅群蛮以叛楚。……楚人谋徙于阪高……使庐戢梨侵庸,及庸方城。……遂灭庸。”庸国在今湖北省竹山县西南,是“百濮” 之首,为群蛮之国,春秋时期就修筑有长城。
韩国长城。《史记·苏秦传》注集解徐广曰:“荥阳、卷县有长城,经阳武到密”。《水经注·济水》引《竹书纪年》记载:“梁惠王十二年(前358),龙贾率师筑长城于西边(河西长城),自亥谷以南,郑所城矣。”韩国地处中原,被秦、楚、魏、齐包围,其长城约修筑于公元前356年。
中山国长城。《?史记?赵世家》载:“(成候)六年(前369年),中山筑长城。”?中山国是北方姬姓白狄鲜虞部落建立的蛮夷小国,地处燕赵之间,在今河北省中南部,其长城修筑于公元前369年。
燕昭王筑长城抗拒东胡
燕国长城。《史记·匈奴列传》载:秦昭王时……其后,燕有贤将秦开为质於胡,胡甚信之。归而袭破走东胡,东胡却千余里。与荆轲刺秦王秦舞阳者,开之孙也。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史记?张仪列传》载:(张仪说燕昭王)今大王不事秦,秦下甲云中、九原,驱赵而攻燕,则易水、长城非大王之有也。燕国北边长城西起今河北张家口、宣化一带,经
围场县、内蒙古赤峰,东至辽东。
燕国建筑的这道长城后成为秦皇长城辽东段的基础。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对燕国北境“拒胡”长城,蒙恬全部修缮利用,并将赵国北境拒胡长城在代(今河北省蔚县东北)的东端与燕国北境“拒胡”长城在造阳的西端补筑连结为一道长城。
赵武灵王筑长城抗拒匈奴
赵国长城。《汉书·匈奴传上》说:后百有余年,赵襄子踰句注而破之并代,以临胡、貉。后与韩、魏共灭知伯,分晋地而有之,则赵有代、句注以北,而魏有河西、上郡,以与戎界边。《?史记?赵世家》载:(肃候)十七年,围魏黄,不克,筑长城。《史记·匈奴列传》载:而赵武灵王亦变俗胡服,习骑射,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而置云中、雁门、代郡。……当是之时,冠带战国七,而三国边于匈奴。其后赵将李牧时,匈奴不敢入赵边。
赵武灵王所筑的这道长城从今河北蔚县到黄河河套西北部狼山南麓内蒙古抗锦后旗东北狼山口。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在北河这一线,蒙恬全部利用了赵国西从高阙(今内蒙抗锦后旗东北狼山口),东至代(今河北蔚县东北)的这道长城。为了使从北地黄河东岸延伸到今内蒙古磴口附近黄河东岸的长城与赵国北河高阙长城西端连结,蒙恬“又渡河, 据阳山、北假中”筑长城,使北地傍河东岸长城北端与北河高阙长城西端连结为一道长城。
魏惠王筑北长城与戎界边
魏国长城。《?史记?魏世家》载:(惠王)十九年(前351年),诸侯围我襄陵,筑长城,塞固阳。《史记·秦本纪》载:孝公元年,河山以东疆国六,与齐威、楚宣、魏惠、燕悼、韩哀、赵成候并。淮泗之间小国十余。楚、魏与秦接界。魏筑长城,自郑滨洛,以北有上郡。
关于《史记》“魏筑长城,自郑滨洛,以北有上郡”和魏“筑长城、塞固阳”这两条史料,张文华先生《中国长城建置考》中说:“魏之疆域,自始至终未至今河套之境内”,“不能北达汉固阳境”,既然如此,“魏又何以得塞固阳!”因此他认为“汉棝阳(固阳)不会有魏惠王所筑的长城。”史念海先生在《黄河中游战国及秦时诸长城遗迹的探索》中说:“魏长城当起于今华阴县城西南,北渡渭河后,循洛河东岸北上,于许原北长城村附近趋向东北,经澄城、合阳、韩城诸县,而至于韩城县城南黄河之滨。”他认为,这才是司马迁说的“魏筑长城,北有上郡”。他还说:“固阳是赵国旧地,魏国何能远筑其长城于赵国境内?其为谬误固不待烦言。”所以,他认为“固阳应为合阳的误文”。张文华、史念海先生的说法有误,其观点须待商榷。
三家分晋前,晋国国都在今山西省南部的唐(今山西翼城),但这不等于晋国疆域仅限于今山西省南部。晋国最盛时,其北部疆域统括今山西北部、河北西部、陕西东部及陕北、宁夏、内蒙河套南部。《史记·匈奴列传》说:“晋北有林胡,楼烦之戎。”“晋悼公使魏绛和戎翟,戎翟朝晋。后百有余年,赵襄子踰句注而破并代以临胡、貉。其后既与韩、魏共灭智伯,分晋地而有之,则赵有代、句注之北,魏有河西、上郡,以与戎界边。”从三家分晋看,韩得晋南之地,都城在今河南禹县;赵得晋北之东,都城在今山西太原东南;魏得晋北之西,都城在今山西夏县西北。晋北之西即延、银、绥诸州。胜州、固阳在延、银、绥之北的北河南北。银州、胜州、固阳,春秋战国时期属晋国北部疆域。此地虽为戎翟所居,但“戎翟朝晋”说明晋势力已达戎翟所居之地。魏得晋北之西,此地“白狄所居,七国属魏”,这也是顺理成章的。《史记·。匈奴列传》载:“魏有西河、上郡,以与戎界边。其后义渠之戎筑城郭以自守,而秦稍蚕食。至于惠王,遂拔义渠二十五城。惠王击魏,魏尽入西河及上郡于秦。” 魏国强盛时,西河、上郡皆为魏境。西河、上郡入秦后统属秦上郡,入汉后复分为西河、上郡。汉西河郡治富昌(今陕西府谷西北),辖境约在今陕北东北部、晋西地区及内蒙杭锦旗东部、伊金霍洛旗、东胜市、准格尔旗一带,属县有美稷、徒经、蔺、增山、广衍、离石等三十六县,汉上郡治肤施(今陕西榆林东南),辖境约在今陕西北部、内蒙伊克昭盟西部、南部诸地,属县有肤施、阳周、白土、漆垣、奢延、雕阴等二十三县。战国魏西河、上郡属县或许少于汉西河、上郡,但其大部地域应在秦汉上郡、西河境内。所以,战国时固阳属于魏地,亦在理中。魏武侯二十五年(前371年)时,魏败赵于蔺,说明今山西离石地区尚属魏控制地区。魏惠王十年(前361年),魏将榆次(今山西榆次)、阳邑(今山西太谷附近)交换给了赵国,这说明魏武侯时代今山西榆次、太谷地区原属魏国。据《汉书·地理志》,在汉西河郡下辖36县中,其中就有“广衍”县。汉西河郡是从秦上郡析出的,“广衍”县自属秦上郡、汉西河属县。秦上郡原系魏上郡、西河属地,秦惠王十年,“魏纳上郡十五县”于秦,“惠王击魏,魏尽入西河及上郡于秦”(《史记·。匈奴列传》)。魏襄王七年(前312年),“魏尽入上郡于秦”(《史记·魏世家》),由此可知“广衍”本魏西河属县。1975年,内蒙古准格尔旗勿尔图沟古城外先后发掘战国末至新莽时的土坑墓二十六座。其中有十四座与关中秦墓类同,大多屈肢葬,随葬具有秦文化特征的小口广肩瓮,罐形陶釜,双耳铜釜,以及罐、壶、甑、盒等日常生活实用器。其中有一件长颈壶上有“广衍”刻文,同墓地收集的铜戈、铜予上又有“十二年上郡”、“广衍”刻文,三器刻文风格接近,均属秦或汉初刻划,为古城名称及其设置沿革的研究,提供了可靠依据(《文物·秦汉广衍故城及其附近的墓葬·1977年第5期》)。内蒙古准格尔旗勿尔图沟古城出土的“广衍”县刻文证实,此地属魏国鼎盛时期的疆域。
魏惠王“筑长城,塞固阳”一事发生在惠王十九年(公元前352年)。三家分晋(前359年)后,魏国势力雄强之时,西河、上郡尚在魏境,固阳自属其中,魏“筑长城,塞固阳”要比 “魏尽入西河及上郡于秦”(前312年)早40年。赵武灵王向晋西北扩张,“二十年……西略胡地,至榆中”。后击败了林胡、楼烦,夺取了今山西北部至今内蒙河套内外的大片土地(包括固阳),建立了雁门郡、云中郡,时在赵武灵王二十六年(前300年)。魏惠王“筑长城,塞固阳”时,固阳本在魏国境内,这要比固阳并入赵国境内早50多年,魏惠王在自己国家境内“筑长城,塞固阳”,这与赵国何涉?张文华、史念海先生所认为的魏境、魏长城,应是魏尽失西河、上郡地区之后的魏国疆域遺迹。
魏惠王 “筑长城,塞固阳”,史籍多载。对这一地区的长城遺迹,今人多有实地调查。经吴旗、静边、榆林抵内蒙古准格尔旗东北十二连城的这道长城,战国时代即已存在,现存遺迹尚在。陕西延安市的文物工作者对富县境内洛河两岸的长城作过考察,此地确有战国时期的长城,全长约30公里。据张耀民先生调查,甘肃庆阳市正宁、宁县、合水境内亦有战国时期的魏长城。这道长城经正宁、宁县、合水,过子午岭娘母子湾东行,经太白镇与陕西富县魏长城相接。上述地区的古长城,基本上沿洛河而上。滨洛地区的长城,有秦筑,有郑筑,谁夺取了长城所在地区,长城就归谁所有,所以时称秦长城,时称魏长城。郑绍宗《河北省战国秦汉时期古长城和城障遣址》介绍,河北省文物考古工作者从1977年开始,在承德、张家口地区对古长城进行了广泛的实地调查,发现明代长城以北还遗存着三道古长城,这三道古长城和内蒙赤峰、宁城、喀喇沁发现的长城有互相延续和衔接的关系。从调查所绘地图看,固阳南北共有五道古长城,其中固阳南面有三道,固阳北面有二道。按自南向北的顺序排列,第一道是明代延绥长城。第二道被推断为赵秦长城,从乌拉特前旗经包头、土默特旗,呼和浩特、卓资北,在固阳南面。第三道从高阙经五原北、武川南,在固阳北,被定为赵秦长城。第四道在乌力吉、潮格旗、马不浪北面。第五道在宝音图至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一线,这是最北面的一道,被定为汉武帝太初三年外城。固阳南北遗存的五道长城中,除最南面的明代长城和最北面的汉代长城外,固阳南北还有三道战国至秦时期的古长城。这三道古长城的发现,说明该地区在战国时期已入魏国疆域。因此,汉固阳地区的魏长城是不能轻易否定的。
秦昭王筑长城抗拒胡虏
春秋战国时期,义渠戎国已成为秦境西北的大国,与秦抗争不断。
秦躁公十三年(前430),义渠伐秦,侵至渭阳(《六国年表》)。
秦惠文王三年(前335),义渠败秦师于洛(《后汉书·西羌传》)。
秦惠文王后七年(前318),义渠败秦师于李伯(《后汉书·西羌传》)。
秦惠王后九年,义渠君闻“五国伐秦……乃起兵袭秦,大败秦人李伯之下”(《犀首传》)。此事《秦本纪》则记为“韩、赵、魏、燕、齐帅匈奴共攻秦。”由此可证,义渠即匈奴。
公元前306年,秦昭王立为国君,昭王母宣太后摄政,她对义渠国采用了拉拢腐蚀的策略。公元前272年,义渠戎王中了宣太后的美人计, “宣太后诱杀义渠王于甘泉宫”,接着发兵消灭了义渠戎国。《史记·匈奴列传·卷一百十》载:“秦昭王时,义渠戎王与宣太后乱,有二子。宣太后诈而杀义渠戎王於甘泉,遂起兵伐残义渠。於是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 秦昭王所筑的“拒胡”长城,是在秦昭王据有陇西、北地、上郡之后修筑的。秦昭王修筑“拒胡”长城,必然要将陇西、北地、上郡这三郡包括於他所筑的“拒胡”长城以内。否则,他所筑的“拒胡”长城就失去了应有的疆域、战略、军事、经济意义。所以, 秦昭王所筑的这道长城从今甘肃岷县长城坡沿洮河东岸、甘、宁黄河南岸经宁夏灵武、盐池地区抵达陕西东北黄河西岸。
秦昭王修筑的这道“拒胡”长城,后世许多朝代都曾对其加以修缮利用。特别是明代宁夏镇的河东长城,延绥镇的延绥长城,都是在秦昭王“拒胡”长城的基础上修缮加筑而成。
秦始皇筑长城驱逐匈奴
先秦以来,匈奴一直是中原王朝的劲敌,经常南下骚扰。秦、赵、魏、燕等国相继在其北境修筑长城,派重兵驻守。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忌惮匈奴反叛,派大将蒙恬率兵将匈奴逐出河套地区,修筑万里长城以防匈奴。《史记·匈奴列传》载:后秦灭六国,而始皇帝使蒙恬将十万之觽北击胡,悉收河南地。因河为塞,筑四十四县城临河,徙适戍以充之。而通直道,自九原至云阳,因边山险壍溪谷可缮者治之,起临洮至辽东万余里。又度河据阳山北假中。
蒙恬修筑的秦皇长城,是在战国秦、赵、魏、燕西北边境长城的基础上,进行连接、修补、增筑、改筑。它从榆中(今属甘肃)沿黄河至阴山构筑长城,据阳山(阴山之北)逶迤而北,连接秦、赵、魏、燕5000余里旧长城,构筑成了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的万里长城,以阻止匈奴南下。
宁夏黄河东岸、南岸沿河长城的西南段始筑于春秋战国秦时期。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派蒙恬修筑长城时,蒙恬对沿河旧有长城加以修缮,对新增长城予以补筑,并将傍洮长城临洮段(洮河东岸段 )、傍河长城榆中段(今兰州黄河南岸段)、并河以东段(黄河红山峡、黑山峡南岸段,宁夏平原黄河南岸、东岸段,内蒙古黄河东岸段)连接贯通,此即黄河南岸、东岸的秦皇长城,属秦皇长城的西段,位于秦朝西北境。
宁夏黄河南岸长城西接甘肃靖远黄河南岸长城,与兰州黄河南岸长城、临洮洮河长城连为一体;宁夏黄河东岸长城北接内蒙古乌海市巴音陶亥、凤凰岭长城、阴山长城,与河北围场长城、辽宁辽东长城连为一体。这道长城路线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派蒙恬修筑的秦皇万里长城的遗迹、遗址。
蒙恬驻守秦朝北部边防十余年,匈奴慑其威猛,不敢再犯秦边。贾谊《过秦论》说:及至秦王,续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棰拊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
汉高祖筑长城护卫华夏
汉初,长安北七百里即匈奴之地,侵掠未尝暂息(《新唐书·突厥上》)。匈奴前锋距西汉都城长安仅有七百里程,匈奴轻骑一日一夜就可以扫荡长安,这是汉朝的心腹大患。汉高祖刘邦建国之初,就开始修筑故塞长城。
《史记·高祖本纪》载:汉高祖二年,汉王东略地,塞王欣、翟王翳、河南王申阳皆降。韩王昌不听,使韩信击破之。於是置陇西、北地、上郡、渭南、河上、中地郡;关外置河南郡。更立韩太尉信为韩王。诸将以万人若以一郡降者,封万户。缮治河上塞(“集解”晋灼曰:晁错传秦时北攻胡,筑河上塞。)《前汉书·高帝纪》载:二年冬十月……汉王如陕,镇抚关外父老。河南王申阳降,置河南郡。使韩太尉韩信击韩,韩王郑昌降。十一月,立韩太尉信为韩王。汉王还归,都栎阳,使诸将略地,拔陇西。以万人若一郡降者,封万户。缮治河上塞(“晋灼”曰:晁错传秦北攻胡,筑河上塞。“师古”曰:缮补也。“宋祁”曰:史义云,塞,先代反。北河灵、夏州地也,秦时缮治。)《前汉书· 晁错传》载,晁错上言曰:臣闻秦时北攻胡貉,筑塞河上。
关于汉高祖“缮治河上塞“、秦时“筑塞河上”,这究竟具体指的是在哪一段黄河上修筑了长城?宋祁说:秦始皇在黄河上修筑长城,汉高祖在黄河补修长城的具体地段是在“北河灵、夏州地也,秦时缮治”, 宋祁确指秦始皇修筑、汉高祖补修的“河上塞”是在今甘肃、宁夏境内的“陇西”、“灵、夏”黄河段上,即至今尚存的黄河南岸红山峡、黑山峡长城、宁夏沿黄河南岸、东岸长城遗迹。
汉朝时期,宁夏境内黄河南岸、东岸的黑山峡长城,宁夏平原沿黄河南岸、东岸长城,在《史记》《汉书》中记载是非常清楚的。《汉书·地理志》载:秦陇西郡有“羌道,羌水出塞外。” 羌水所出之“塞”,正是秦“陇西塞”,即战国秦、秦始皇修筑的“旁洮”、“旁河”长城,汉代依然存在。特别需要注意的是颜师古、宋祁对于晁错所说“秦时北攻胡,筑河上塞”的解释。关于这段沿河长城的始筑年代,颜师古说是秦“缮补也”,宋祁说是“秦时缮治”,既然是秦始皇“缮补”、“缮治”,就不是秦始皇始筑。那末,“陇西”、“灵、夏”境内的沿河长城究竟始筑于何时?据《史记·匈奴列传》载:秦始皇之前,在秦国境内的“陇西”修筑长城始于春秋秦国诸公,《史记·秦本纪》载:秦历共公“十六年(公元前461年)堑河旁。”《六国表》载:秦灵公“八年(公元前417年)城堑河濒。” “堑河旁”就是把黄河岸边的山坡劈削如墙,作为长城墙体之一种;“城堑河濒”就是在黄河岸边劈削山坡,用石块垒砌长城墙体。战国时,在“陇西”“灵、夏”地区大规模修筑长城的首推秦昭王。秦昭王伐残义渠,於是,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史记·匈奴列传》载:汉元朔二年,“卫青复出云中以西至陇西,击胡之楼烦、白羊王于河南,得胡首虏数千,牛羊百余万。于是汉遂取河南地,筑朔方,复缮故秦时蒙恬所为塞,因河为固。汉亦弃上谷之什辟县、造阳地以予胡。”这说明汉代在西北“陇西”“灵、夏”地区的“河南地”修缮的沿河长城应是春秋秦国诸公始筑、秦昭王修筑、秦始皇派蒙恬沿着黄河继续建筑的秦皇长城。因为这道秦皇长城是“因河为固”的。
汉武帝筑长城经略西域
汉武帝即位以后,“马邑之谋”成为汉朝与匈奴冲突的导火线,“匈奴绝和亲”打破了秦昭王长城两侧的安定局面。汉武帝开始陆续修筑西北长城,为北击匈奴作准备。
修缮原秦皇长城。匈奴攻武州塞、当路塞、上郡塞,汉武帝派卫青、公孙贺、公孙敖、李广等北出上谷、云中、代郡、雁门、朔方一线的秦昭王、秦始皇长城,将匈奴逐出河南地,在朔方修缮秦皇长城,并将汉朝的防线推进到朔方秦皇长城一线,“以拒河逐胡”。
修筑光禄塞。《史记·匈奴传》载:太初三年(前102年)、太初四年“汉使光禄徐自为出五原塞数百里,远者千余里,筑城障列亭,至庐朐。而使游击将军韩说、长平侯卫伉屯其旁,使强弩都尉路博德筑居延泽上”。光禄塞,指阴山山脉及河西的长城障塞,是西汉武帝时派光禄勋(皇宫守卫官号)徐自为等在黄河河套外沿阴山、贺兰山兴筑的长城体系,其遗迹分布在今内蒙古固阳县、乌拉特中后旗、抗锦后旗、宁夏贺兰山、卫宁北山一线。因其修筑在秦皇长城之外,故史称其为“塞外列城”。《史记·匈奴传》“正义”地理志云:五原郡稒阳县北山石门障,得光禄城,又西北得支就城,又西北得头曼城,又西北得虖河城,又西北得宿虏城。按即筑障列亭至庐朐也。服虔云:庐朐,匈奴地名也。张晏云:山名也。稒阳,战国魏固阳邑,汉置稒阳县,后汉因之。《后汉书·和帝纪》载:永元元年,度辽将军邓鸿出稒阳塞,与匈奴战于稽落山,大破之。《魏书·太祖纪》载:“登国六年,卫辰遣子直力鞮出稒阳塞,侵及黑城,帝垦五原,屠之。”遗址在今内蒙古固阳境内。“宿虏城”,依《地理志》载“五原郡稒阳县北山石门障,得光禄城,又西北……又西北得宿虏城”,筑障列亭至庐朐”的方位考之,“宿虏城”在今宁夏石嘴山境。“庐朐”山即今贺兰山。“光禄城”,据《旧唐书》、《新唐书》记载,宁夏古有御史、尚书、光禄、七级等渠名,是 “废塞岁久”的古渠。宁夏旧志明确指出,光禄渠“本汉时导河溉田处也”。“光禄渠”既在今宁夏境内,“光禄城”亦当在今宁夏境内(详见周兴华、周晓宇著《从宁夏寻找——长城源流》)。
修筑令居塞。令居塞即令居长城。元朔五年(前124年),汉武帝以卫青为大将军,带领六个将军,统兵十余万人,出朔方、高阙进击匈奴,远出朔方秦皇长城“六七百里”。元狩二年(前121年),汉武帝派霍去病出陇西、皋兰、北地进击匈奴,过居延攻祁连山,远出陇西、北地秦皇长城“二千里”。经过反复争夺,“汉击走单于於幕北”,“而幕南无王庭。”“金城,河西、西并南山至盐泽空无匈奴。”“汉度河,自朔方(今内蒙古杭锦后旗黄河西北岸)以西至令居(今甘肃永登西北),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稍蚕食,地接匈奴以北。”霍去病“度河”夺取了“自朔方以西至令居”的土地以后,汉朝开始在这一带沿黄河至令居筑长城。
宁夏黄河北岸、西岸的沿河长城属令居长城的一部分。《史记·骠骑列传》载: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年),霍去病数破居於河西一带的昆邪王,“昆邪王与休屠王谋欲降汉。”“是时,大行李息将城河上”。这则记载告诉我们,元狩二年,汉军渡过黄河后,李息开始沿黄河筑长城。李息沿黄河建筑的长城,在汉武帝对霍去病的嘉奖中可以证实。汉武帝说:“骠骑将军去病率师攻匈奴西域王浑邪……十万之众咸怀集服,仍与之劳,爰及河塞,庶几无患,幸既永绥矣”。汉武帝所说的“河塞”,就是指汉朝度过黄河后李息沿黄河建筑的长城。朔方(治今内蒙抗锦后旗黄河西北岸)以西至令居(今甘肃永登西北)一带的长城,分布在黄河以北、以西的近河地带,现仅存在于今内蒙乌拉特前旗阴山南麓至宁夏贺兰山东麓、中卫至甘肃景泰黄河北岸。这一地段黄河外侧的沿河长城,正是遗存于今内蒙的阴山长城、宁夏的贺兰山长城、中卫、中宁北山长城和甘肃景泰长城。
修筑河西走廊长城。河西走廊长城亦属令居长城的一部分。关于宁夏黄河以西至甘肃永登西北的古长城,也是大行李息、徐自为始筑。《汉书·匈奴传下》载:“时先零羌与封养罕姐种解仇结盟,与匈奴通,合兵十余万,共攻令居、安故,遂围抱罕。汉遣将军李息、朗中令徐自为将兵十万击平之,始置护羌校尉,持节统领焉。羌乃去湟中,依西海盐池左右。汉遂因山为塞,河西地空,稍徙人以实之。”这里的“因山为塞”,就是李息、徐自为在河西走廊始筑的汉长城。
明清时期,今宁夏境内的光禄塞、令居塞统称宁夏西长城。宁夏西长城即宁夏河西长城。宁夏河西长城包括今宁夏黄河西岸的贺兰山长城和黄河北岸的中卫、中宁北山长城,现存遗迹位于黄河外中卫、中宁北山、贺兰山一线。它西自今甘肃省景泰县入中卫境,东向经中卫迎水镇营盘水村红湾墩,沿腾格里沙漠南缘、卫宁北山、贺兰山出宁夏境,长约800里。
宁夏河西汉长城西接甘肃河西走廊汉长城,东接内蒙高阙汉长城。这道长城是汉武帝长城的遗迹、遗址。其中的甘肃、宁夏河西汉长城,成为明代河西走廊长城、今中卫、中宁北山长城、贺兰山长城修补利用的主体与基础。明代对这道古长城的修缮利用有明确记载。今宁夏境内沿黄河西岸、北岸的贺兰山长城,中宁、中卫的北山长城,中卫西部古皋兰(今中卫长流水、甘塘、营盘水、甘肃景泰)至武威的古长城,均始筑于西汉元狩二年(前121年),始筑人是西汉大行李息(大行,古官名,掌接待宾客。司马贞索隐引韦昭曰:大行,掌宾客之礼,今谓之鸿胪。)
关于宁夏西长城的始筑年代,《乾隆宁夏府志》说:“西长城,旧志不载修筑年岁”。 根据明代以前的文献记载,这道长城始筑于汉武帝时代。一些学术著作依据明代修补记载的时间将这道古长城的始筑年代定为“明代长城”是没有根据的。
《汉书·西域传》载:自周衰,戎狄错居泾渭之北。及秦始皇攘却戎狄,筑长城,界中国,然西不过临洮。汉兴,至于孝武,事征四夷,广威德,而张骞始开西域之迹。其后票(骠)骑将军击破匈奴右地,降浑邪、休屠王,遂空其地,始筑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后稍发徙民充实之,分置武威、张掖、敦煌,列四郡,据两关焉。关于令居塞的所在。《汉书·西域传》说秦始皇筑长城“西不过临洮”。《史记·大宛列传》说匈奴右方“居盐泽以东,至陇西长城。”《汉书·西域传》说汉武帝派骠骑将军“击破匈奴右地,降浑邪、休屠王,遂空其地,始筑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由上可知,令居塞位于匈奴右地,东起陇西长城(陇西塞),西至酒泉郡。这道长城即是从今宁夏中卫黄河北岸长城西接甘肃河西走廊的汉武长城。正是这道长城,切断了西羌与匈奴的南北交互作用,保护了河西走廊丝绸古道的畅通。
修筑酒泉至玉门长城。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至元封元年(前110年),《史记·大宛列传》载:匈奴奇兵时时遮击使西国者。使者争遍言外国灾害,皆有城邑,兵弱易击。於是天子以故遣从骠侯破奴,将属国骑及郡兵数万,至匈河水,欲以击胡,胡皆去。其明年,击姑师,破奴与轻骑七百余先至,虏楼兰王,遂破姑师……王恢数使,为楼兰所苦,言天子,天子发兵令恢佐破奴击破之,封恢为浩侯。於是酒泉列亭障至玉门矣。《汉书·西域传》:“初,武帝感张骞之言,甘心欲通大宛诸国,使者相望於道,一岁中多至十余辈。……放是汉列亭障至玉门矣。”这里所说的亭障,是长城障塞、城堡、烽燧,俱属于长城的防御体系。
修筑敦煌(玉门)至盐水(今新疆罗布泊)长城。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至太初四年(前101年),《汉书·西域传》载:自贰师将军伐大宛(今乌兹别克费尔干纳盆地)之后,西域震惧,多遣使来贡献。汉使西域者益得职。于是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而轮台、渠犁皆有田卒数百人,置使者校尉领护,以给使外国者。《史记·大宛列传》载:敦煌置酒泉都尉;西至盐水(今罗布泊一带),往往有亭。而仑头有田卒数百人,因置使者护田积粟,以给使外国者。
主汉武帝修筑蒙古草原北方长城、河西走廊长城、西域长城的战略目标十分明确:一是逐匈奴于漠北,阻隔胡骑南下,使大漠南北归为一统。二是经营西域,使西域与中原同为华夏。三是保障丝绸之路畅通,促进东西方交流。这正如《汉书·张骞传》所说:汉始筑令居(今甘肃永登)以西,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国。《汉书·赵充国传》说:“窃见北边自敦煌至辽东万一千五百余里,乘塞列隧有吏卒数千人,虏数大众攻之而不能害。今留步士万人屯田,地势平易,多高山远望之便,部曲相保,为堑垒木椎(师古曰:谓为高楼以望敌也),校联不绝(师古曰:言营垒相次),便兵弩,饬斗具。烽火幸通,势及并力,以逸待劳,兵之利者也。”所谓“塞”、“燧”、“堑垒木樵”,即指汉代长城、烽燧。赵充国说的“万一千五百余里”仅指敦煌至辽东的长城长度,若加上敦煌至西域及漠北长城,汉武帝修筑西北长城、烽燧、亭障,总长度约在20000里。
汉光武筑长城保障中原
两汉之际,南匈奴为汉朝驻防长城一线。从光武帝刘秀开始,匈奴就已转徙塞内,侵扰沿边郡县。东汉大修旧长城,抵御匈奴。
东汉初年,修筑长城的重点是防御匈奴南下中原。《后汉书·杜茂传》载:时卢芳据高柳,与匈奴连兵,数寇边民,帝患之。十二年(36年),遣谒者段忠将觽郡驰刑配茂,镇守北边,因发边卒筑亭候,修烽火。《后汉书·南匈奴列传》载:建武十三年(37年),遂寇河东,州郡不能禁。于是渐徙幽、并边人于常山关、居庸关已东,匈奴左部遂复转居塞内。朝廷患之,增缘边兵郡数千人,大筑亭候,修烽火。建武十三年,卢芳与匈奴、乌桓连兵,寇盗尤数, 缘边愁苦。诏(王)霸将弛刑徒六千余人与杜茂治飞狐道(即古之飞狐口,在今蔚州飞狐县北。)堆石布土,筑起亭障,自代至平城三百余里(《后汉书·王霸传》)。建武十四年,马成屯常山﹑中山以备北边,并领建义大将军朱佑营。又代骠骑大将军杜茂缮治障塞,自西河至渭桥,河上至安邑,太原至井陉,中山至邺,皆筑保壁,起烽燧,十里一候(《后汉书·马成传》)。朝廷派人监造巨型战车,“可驾数牛,上作楼橹,置于塞上,以拒匈奴”(《后汉书·南匈奴列传》)。
东汉前期,联合乌桓、南匈奴驻守秦皇河套长城及秦昭王拒胡长城一线,助击北匈奴及鲜卑。《后汉书·乌桓传》载:二十五年(49年),辽西乌桓大人郝旦等九百二十二人率众向化,诣阙朝贡,献奴婢、牛、马及弓、虎、豹、貂皮。是时四夷朝贺、络驿而至,天子乃命大会劳飨 ,赐以珍宝。乌桓或愿留宿卫,於是封其渠帅为侯、王、君、长者八十一人,皆居塞内,布於缘边诸郡,令招来种人,给其衣食,遂为汉侦候,助击匈奴、鲜卑。……於是始复置校尉於上谷宁城,开营府,并领鲜卑,赏赐质子,岁时互市焉。及明、章、和三世,皆保塞无事。《后汉书·南匈奴传》:二十六年(50年),遣中郎将段郴、副校尉王郁使南单于,立其庭,去五原西部塞八十里。……郴等反命,诏乃听南单于入居云中。遣使上书,献骆驼二头,文马十匹。……冬,前畔五骨都候子复将其众三千人归南部,北单于使骑追击,悉获其众。南单于遣兵拒之,逆战不利。於是复诏单于徙居西河美稷,因使中郎将段郴及副校尉王郁留西河拥护之,为设官府、从事、掾史。令西河长史岁将骑二千,驰刑五百人,助中郎将卫护单于,冬屯夏罢。自后以为常,及悉复缘边八郡。南单于既居西河,亦列置诸部王助为扞戍。使韩氏骨都候屯北地,右贤王屯朔方,当于骨都侯屯五原,呼衍骨都侯屯云中,郎氏骨都侯屯定襄,左南将军屯雁门,栗籍骨都侯屯代郡,皆领部众为郡县侦罗耳目。据《光武帝纪》:缘边八郡即云中(今内蒙托克托)、五原(今内蒙五原)、朔方(今内蒙抗锦旗北)、北地(今甘肃庆阳西北)、定襄(今山西右玉)、雁门(今山西雁门)、代郡(今山西大同)、美稷(今内蒙准格尔旗北黄河内)。
东汉中期,国力增强,对北匈奴展开反击,复夺汉武帝长城控制范围。东汉明帝永平十六年(73年)春二月,东汉派窦固等四路
大军出击北匈奴。窦固破呼衍王于天山,留兵屯伊吾卢城(今新疆哈密西北),汉置宜禾都尉。《后汉书·南匈奴传》载:休兰尸逐侯鞮单于屯屠何,章和二年(88年)立。时北虏大乱,加以饥蝗,降者前后而至。南单于将并北庭,会肃宗(章帝)崩,窦太后临朝。其年七月,单于上言:臣伏念先父归汉以来,被蒙覆载,严塞明候,大兵拥护,积四十年。臣等生长汉地,开口仰食,岁时赏赐,动辄亿万,虽垂拱安枕,慙无报效之地。愿发国中及诸部故胡新降精兵,遣左谷蠡王师子、左呼衍日逐王须訾将万骑出朔方,左贤王安国、右大且渠王交勒苏将万骑出居延,期十二月同会虏地。臣将余兵万人屯五原、朔方塞,以为拒守。臣素愚浅,又兵觽单少,不足以防内外。愿遣执金吾耿秉、度辽将军邓鸿及西河、云中、五原、朔方、上郡太守并力而北 ,令北地 、安定太守各屯要害,冀因圣帝威神,一举平定。臣国成败,要在今年。已敕诸部严兵马,讫九月龙祠,悉集河上。唯陛下裁哀省察!东汉和帝永元元年(公元89年),派征西将军耿秉、车骑将军窦宪率骑兵八千,与度辽将军邓鸿及南匈奴的军队三万人,出朔方塞,大败北匈奴于稽落山(今蒙古国额布根山)。窦宪、耿秉登燕然山(今蒙古国杭爱山)刻石纪功而还。永元三年(91年)窦宪派大将耿夔、任尚,出居延塞(内蒙额济纳旗境),在金微山(蒙古阿尔泰山)围歼北匈奴,俘获北匈奴皇太后亲王以下五千余人。此战役中仅北单于突出重围向西逃窜。
东汉后期,驻防长城重点是防御鲜卑。《后汉书·南匈奴传》载:东汉顺帝永建元年(126年),以辽东太守庞参代为将军。先是,朔方以西障塞多不修复,鲜卑因此数寇南部,杀斩将王,单于忧恐,上言求复障塞,顺帝从之。乃遣黎阳营兵出屯中山北界,增置缘边诸郡兵,列屯塞下,教习战射。《后汉书·卷六·顺帝纪》载:永建元年夏五月丁丑,诏幽、并、凉州刺史,使各实二千石以下至黄绶,年老劣弱不任军事者,上名。严敕障塞,缮设屯备,立秋之后,简习戎马。……(冬十月)鲜卑犯边。庚寅,遣黎阳营兵出屯中山北界。告幽州刺史,其令缘边郡增置步兵,列屯塞下。调五营弩师,郡举五人,令教习战射。《后汉书·鲜卑传》载:顺帝永建元年(126年)秋,鲜卑其至鞬寇代郡,太守李超战死。明年(永建二年)春,中郎将张国遣从事将南单于兵步骑万余人出塞,击破之,获其资重二千余种。
曹魏筑长城守备西境
魏晋时期,沿长城一线的匈奴、鲜卑等经常入“塞”出“塞”,与保塞南匈奴及汉军征战于长城内外。
《三国志·魏志·明帝纪》载:青龙元年“秋九月,安定保塞匈奴大人胡薄居姿职等叛,司马宣王(司马懿)遣将军胡遵等追讨,破降之”。当时,安定郡在今宁夏境内辖有乌氏、朝那、西川三县,辖境包括今宁夏固原、吴忠、同心、盐池县的绝大部分。安定郡境内有二道古长城,一道是南境的“故塞”,即西周朔方长城(今宁夏固原长城及其延线长城),一道是北境的“故河南塞”,即战国秦昭王长城(今宁夏河东长城及其延线长城)。南匈奴在安定郡所保之“塞”(长城),理应是安定郡外围的“故河南塞”(今宁夏河东长城及其延线长城),即战国秦昭王“拒胡”长城。
曹魏名将邓艾为安西将军,假节、领护东羌校尉时,曾修缮利用洮河、黄河沿岸的秦长城,与蜀国名将姜维对垒于秦陇西长城一线。《三国志·邓艾传》载:魏高贵乡公曹髦即位,甘露元年(256年)下诏表彰邓艾说:“逆贼姜维连年狡黠,民夷骚动,西土不宁。艾筹画有方,忠勇奋发,斩将十数,馘首千计;国威震於巴、蜀,武声扬於江、岷。今以艾为镇西将军、都督陇右诸军事,进封邓侯。”景元四年(263年),邓艾奉命伐蜀,功成被害,时人冤之。泰始元年,晋武帝司马炎登基。三年,议郎段灼上疏为邓艾鸣冤说:“艾心怀至忠而荷反逆之名,平定巴蜀而受夷灭之诛,臣窃悼之。……昔姜维有断陇右之志,艾脩治备守,积谷强兵。值岁凶旱,艾为区种,身被乌衣,手执耒耜,以率将士。上下相感,莫不尽力。艾持节守边,所统万数,而不难仆虏之劳,士民之役,非执节忠勤,孰能若此?……锺会忌艾威名,构成其事。忠而受诛,信而见疑,头县马巿,诸子并斩,见之者垂泣,闻之者叹息。”其中“脩治备守”就是指邓艾修缮长城一事。《邓艾传》说:“艾在西时,修治障塞,筑起城坞。泰始中,羌虏大叛,频杀刺史,凉州道断。吏民安全者,皆保艾所筑坞焉。”当时,邓艾修缮秦陇西长城,建筑城坞,对保障吏民安全,丝绸之路畅通是立有功劳的。
北朝筑长城防禦北狄
南北朝时期,北朝各国对其境内的古长城进行了修补、改筑、增筑。
北魏修筑了环绕平城的“畿上塞围”。《魏书·世祖纪下》载:(太平真君七年,即元446年)六月甲申,发定、冀、相三州兵二万人屯长安南山诸谷,以防越逸。丙戌,发司、幽、定、冀四州十万人筑畿上塞围,起上谷,西至于河,广袤皆千里。……(九年)二月癸卯,行幸定州。山东民饥,启仓赈之。罢塞围作。遂西幸上党,诛潞叛民二千余家,徙西河离石民五千余家于京师。诏于壶关东北大王山累石为三封,又斩其北凤皇山南足以断之。这条长城,东起上谷郡治居庸县境(今北京延庆县)八达岭长城,沿太行山西南行至今山西灵丘、繁峙、宁武,再向西北至偏关县,最后达河曲县的黄河岸边,全长千余里,呈环状分布于平城的南面。
北魏还在其北境修筑了东自赤城(今河北赤城),西至五原(今内蒙五原)的二千多里长城。北魏征南将军刁雍在给献文帝拓跋弘的奏章中说;“臣闻北狄悍愚,……是以古人伐北方,攘其侵略而已……昔周命南仲,城彼朔方;赵灵、秦始,长城是筑;汉之孝武,又踵其事。……今宜依故,於六镇之北筑长城。六镇东西不过千里……计十万人一月必就。………帝从之,边境获其利。”献文帝采纳了刁雍的建议,在薄骨律和六镇之北修筑了长城。《魏书·太宗纪》:泰常八年(423年)正月丙辰……蠕蠕犯塞。二月戊辰,筑长城于长川之南,起自赤城,西至五原,延袤二千余里,备置戌(戍)卫。这道长城东自今河北赤城,经张北、尚义、内蒙武川、固阳,抵达阴山,是在秦皇长城、汉武长城基础上修缮、补筑、改筑而成。北魏还沿这道长城在今宁夏、内蒙、河北境内设置了薄骨律(今吴忠市北)、沃野(今内蒙五原境)、怀朔(今内蒙固阳境)、武川(今内蒙武川境)、抚冥(今内蒙四子王旗境)、柔玄(今内蒙兴和境)、怀荒(今河北张北境)七镇。七镇境内皆有古代长城,在刁雍修筑的长城中,许多段落都是对古长城的维修加筑。
东魏修筑了阻扼漠北诸族南下的长城。《魏书·孝静纪》载:(武定元年,543年),是月(八月),齐献武王召夫五万於肆州(今山西忻州)北山筑城,西自马陵戍(今山西宁武西),东至土隥 (今山西宁武东),四十日罢。这是东魏长城,在今山西忻州境内,横亘宁武东西,杜绝柔然。这里是柔然、突厥等南下马邑(今山西朔县)的历史古道。
北齐长城是在战国秦、赵、燕长城的一些段落上,进行增补,改筑和延伸。经多次修筑,整体连接,最终构筑成自西河至东海的“东西凡三千余里”的长城。这道长城,从今山西河曲县黄河岸边起,经山西大同、北京延庆县八达岭、燕山南麓、河北抚宁县,在山海关附近入渤海。
北周修筑了陇西长城。《北史·李贤传》载:李贤,字贤和,自云陇西成纪人,汉骑都尉陵之后也。陵没匈奴,子孙因居北狄。后随魏南迁,复归汧、陇。……四年,王师东讨,西道空虚,虑羌、浑侵扰,乃授贤河州总管。河州旧非总管,至是创置。贤乃大营屯田,以省运漕,多设斥候,以备寇戎,于是羌、浑敛迹。五年,宕昌寇边,乃于洮州置总管府以镇遏之。遂废河州总管,改授贤洮州总管。属羌寇侵扰,贤频破之,虏遂震慑,不敢犯塞。俄废洮州总管,还于河州置总管府,复以贤为之。
隋唐筑长城防禦突厥
隋朝时期,隋文帝、隋炀帝对秦昭王“拒胡”长城及其延线的北魏、北齐长城进行了修缮、增筑。
隋朝修筑长城的特点是沿西北边防维修利用古长城,是“因其成业,或修或筑”,每此修筑时间不长。
《隋书·崔仲方传》载:开皇五年(公元585年),隋主 “令(崔仲方)发丁三万,于朔方、灵武筑长城,东至黄河,西拒绥州,南至勃出岭,绵亘七百里。明年,上复令仲方发丁十五万,于朔方已东缘边险要筑数十城,以遏胡寇。”开皇五年崔仲方是在“朔方、灵武” 筑长城;开皇六年崔仲方是在“朔方已东”筑长城(古长城沿线的戍逻所)。显然,开皇五年崔仲方筑的是“朔方以西”的长城,长城的
西端在隋灵武(东至黄河,西拒绥州应为西至黄河,东拒绥州)。
崔仲方在朔方郡筑长城,理应将朔方郡所统三县包括于其所筑长城以内。今盐池县最北边的 “二道边”一线的长城,正位于隋朔方郡和灵武郡东境内(今陕西靖边县、定边县、内蒙鄂托克前旗与今宁夏盐池县、灵武县),此长城即隋代崔仲方在战国秦昭王“拒胡”长城基础上修补而成的隋长城。崔仲方在灵武郡筑长城,理应将灵武郡所统六县包括于长城以内,特别是黄河西面的弘静、怀远、灵武、丰安四县。北宋初年成书的《太平寰宇记》载:废怀远县,本汉富平(今宁夏吴忠市)县地……隋长城,隋炀帝大业中筑,在县西北大河外……《太平寰宇记》说:隋长城在废怀远县(今银川市境)“西北大河外”。 宋距隋不远,此记载当有所据,应为信史。按此记载,灵武郡境内的隋长城西端当在今宁夏贺兰山、卫宁北山一线,而这一线的古长城正位于废怀远县(今银川是市境)“西北大河外”。汉唐时期,贺兰山、卫宁北山就遗存有古长城,唐朔方灵武龙兴寺的高僧释增忍就曾经“访古贺兰山中”,“薄游塞垣”。隋长城在灵武郡境内的河外段(河西长城),即是遗存于今宁夏贺兰山、卫宁北山一线的古长城。
崔仲方开皇五年所筑长城大致是沿着秦昭王“拒胡”长城和贺兰山汉武长城线路修筑的,以今地言之,它东起今陕北靖边境,中经定边、盐池、灵武,西越黄河沿贺兰山南下至其南端的“灵武口”约为700余里,这与《隋书·崔仲方传》《资治通鉴》所载崔仲方于朔方、灵武筑长城,“绵亘七百里”相符,与《太平寰宇记》说隋长城在废怀远县(今银川市境)“西北大河外” 相符,也与《万历朔方新志》
所载定边至贺兰山南端“大山根”的760古长城里程相近。
隋朝还在许多地方都修筑过长城,见诸文献记载的有:雁门至碣石;临渝镇;合河县至幽州;榆林至紫河;榆谷(榆林谷)以东。隋代还在夏州、胜州之间挖掘过横堑。
由上可知,隋文帝、隋炀帝修筑的长城,其明确记载的地理位置是灵武、朔方、榆林(榆谷,榆林谷)、紫河、雁门、幽州、临渝镇、碣石。其长城所经地方,自西向东,以今地言之,依次为宁夏河西隋灵武县、贺兰山、盐池县,陕西定边、靖边、横山、绥德,内蒙准唯格尔旗东北,山西右玉,北京西南,河北抚宁县山海关等。将上述地方的现存长城遗迹连为一线,正是今所谓明代长城的走线。这一线的古长城,基本是战国秦昭王所筑的“拒胡”长城和隋以前西汉等王朝所修筑的长城。隋朝修筑时,是在上述长城遗迹、遗址上进行修缮,个别地段进行过加筑、补筑、改筑。但其西段、中段的主要框架沿续的是汉武长城、战国秦昭王所筑的“拒胡”长城的遗迹、遗址。《隋书·杨素传》载:突厥“达头可汗犯塞,以素为灵州通行军总管,出塞讨之。”达头所犯之“塞”,即今宁夏贺兰山、灵武、盐池境内的古长城。《资治通鉴·隋纪五》载:大业九年,三月“乙丑,车驾幸五原,因出塞巡长城。”五原,西魏为五原郡,隋大业三年改为盐川郡,治今陕西定边县南。隋炀帝到陕西定边县出巡长城,可见定边县境内的古长城隋代就已存在。所以,今人所说的这一线的明代长城,其实基本上是隋代所修长城的遗留,明人是在隋代所修长城的基础上又进行了修修补补和新增。
现代也有人将明长城误考为隋长城的。1997年,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盐池县博物馆考古人员在头道边北250米地方新发现了一条与明内长城走向基本平行的堤状人工堆积。堆积整体与明长城分分合合,不重合部分长约25公里。考证认为,这段人工堆积是崔仲芳修筑的隋代长城遗址。关于宁夏考古人员在王琼“深沟高垒”外侧发现的这条壕堑与堤状堆积物的来历,明代史籍有明确记载,肯定不是隋代长城,属误考。据《嘉靖宁夏新志·边防》载:王琼深沟高垒“其在兴武营者,以其土沙相半,不堪保障。十六年,总制尚书刘天和沿边内外挑壕堑各一道,袤长五十三里二分,深一丈五尺,阔一丈八尺,人斯有恃。”从宁夏考古人员的调查资料看,新发现的这条壕堑与堤状堆积物:一是在兴武营以东,明代属兴武营管辖;二是与王琼“深沟高垒”靠近并行;三是堆积物呈弧状形土层堆筑,土层表面是用大平面重物拍打而成,不见夯迹;四是墙体外侧挖有壕堑;五是这条堆积物长约50里。从明代文献记载与考古调查反映出的以上特征判断,新发现的这条壕堑遗迹与明代文献所载刘天和沿王琼所筑“深沟高垒”旁侧挑挖壕堑“长53里”等资料完全相符。因此,宁夏考古人员新发现的这条壕堑遗迹不是隋代崔仲方在朔方、灵武所筑的长城遗迹,而是嘉靖十六年总制尚书刘天和沿王琼所筑深沟高垒内外挑挖的一条约50里的壕堑遗迹(见周兴华 周晓宇著《从宁夏寻找——长城源流》)。
过去说唐代不修长城,但史籍记载唐朝同样重视塞防建设,利用古长城,修筑长城的形式多种多样。
唐代修筑塞防体系的特点是因地制宜,烽堠、堡寨、壕堑、长城墙体因地设置,各有侧重。史载:“(武德)二年二月癸酉,令州县治堡,同以备胡”。“( 武德)七年六月,遣边州修堡城,警烽堠,以备胡”。“(武德)八年正月己酉帝与群臣言备边之事……中书侍郎温彦博又进曰:昔魏文帝掘长堑以遏匈奴,亦因循其事,帝并从之,於是遣将军桑显和堑断北边要路” “(八年)六月丙子……水部郎中姜行本筑断石岭之道以备胡”。“武德九年正月辛亥,突厥声言入寇,敕州县修城堡,警烽堠”。唐太宗武德九年即位后,为修缘边障塞以备胡寇,下诏说:“城彼朔方,周朝盛典;缮治河上,汉室宏规;所以作固京畿,设险边塞,式遏寇虐,隔碍华戎。……其北道诸州所置城寨,粗已周遍,未能备悉。……其城塞镇戍,须有修补,审量远近,详计功力,所在军民,且共营办,所司具为条式,务为成功”( 《册府元龟·卷九百九十·备御》)。《新唐书·地理志》载:妫州妫川郡(今怀来)“妫水贯中。北九十里有长城,开元中张说筑;东南五十里有居庸塞,东连卢龙、碣石,西属太行、常山,实天下之险。”孙逖撰《张公说遗爱颂碑》记述,张说筑的这道长城堑山泽,起亭障,塞鸡鸣之扼,守阜陵之冲,遮大厦之路,距卢龙之口,延袤千里,横绝一方。
唐代,秦皇长城依然存在。唐代《括地志·卷八》载:“秦陇西郡临洮县,即今岷州城,本秦长城,首起岷州西十二里,延袤万余里,东入辽水。”这说明临洮长城确为秦时所修建。《龙筋凤髓判·卷三》载:武则天“圣历元年(689年),突厥暾欲谷南侵之后,武后曾召集群臣,征询筹边方略。为防止胡马南牧,中郎将田海请“沿旧长城开堑,东至东海,西至临洮,各阔十步,深三丈。”田海所说的“东至东海,西至临洮”的“旧长城”,就是当时遗存于世的秦皇长城。
唐代,宁夏灵武、盐池及陕西定边境内的战国秦昭王长城,唐代称之为“灵州塞”。元和三年(808年),沙陀部众在其酋长朱邪尽忠的率领下,他们沿河西进入陇西,“旁洮水,奏石门,转斗不解,部众略尽,尽忠死之”。最后剩下“二千骑、七百杂畜、橐它千计”,在其妻朱邪执宜的率领下,终于抵达今宁夏灵武,“款灵州塞,节度使范希朝以闻,诏处其部盐州,置阴山府,以执宜为府兵马使。”这里的“款灵州塞”,就是到灵州长城下归顺唐朝。唐朝将其安置在盐州,即今宁夏盐池、陕西定边一带,并买牛羊送给他们,让他们发展畜牧。
唐代贺兰山中遗存有古长城,许多古籍记载甚明。《宋高僧传·唐朔方灵武龙兴寺增忍传》载:释增忍,俗姓史氏,沛国陈留人也。典谒之年,登其乡校。百氏简策,寓目入神。艺文且工,乃随计吏,数举不捷。会昌初,薄游塞垣,访古贺兰山中,得净地者白草谷,发菩提心,顿挂儒冠,直归释氏。“会昌初年”,约公元842年前后,时当唐武帝李炎时代。增忍大师到今宁夏贺兰山中寻访古迹,游历了贺兰山古代长城(薄游塞垣),并在今贺兰山拜寺沟内发现了佛教圣地白草谷寺院。白草谷寺院即今拜寺沟方塔所在地。这说明,贺兰山长城在唐代就已存在。在唐人眼中,贺兰山长城是作为古迹存世的。
宋辽金筑长城划守边界
宋辽金时期,各国都修筑长城、边堡、烽堠、开挖堑壕及利用古长城作为边界标志,以防侵越。
宋、辽以古长城作为两国的分界表志。宋代,河东秦昭王长城保存尚好。特别是其东段,曾是北宋与辽国解决疆域争端的界标,非常引人注目。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年),辽国与北宋谈判划分边疆界址。辽国代表萧禧提出以“蔚、朔、应三州分水岭土垄为界。”北宋代表韩缜不同意,但反驳无据,致使萧禧的意见占了上风。这时,沈括“诣枢密院阅故牍,得顷岁所议疆地书,指古长城为分界。”沈括依据国家所藏长城档案,向皇帝上表提出了以“古长城”作为界址的划界意见。据《宋史·沈括传》载:辽国提出以“黄嵬山”“土垄”,即所谓古长城为界,此界在雁门西南七十里。沈括争辩说,两国应以“古长城”为界,但黄嵬山上没有“古长城(土垄)”;真正的“古长城(土垄)”在黄嵬山北面的天池县,此地北距今雁门还有一百六十多里。沈括所说的天池县古长城,也就是辽国所谓的“土垄”,实即遗存于今山西北境老营、平鲁一线的古长城,亦即现今通常所说的明代长城。由于沈括指出了“古长城(土垄)”真正的所在位置,辽国“遂舍黄嵬而以天池请”,同意以“古长城(土垄)”,即今人所说的明长城所在位置作为宋、辽分界线。由此可见,今山西北境老营、平鲁一线的长城,宋代以前就已存世屹立。宋神宗读了沈括的划界表章,“帝喜愕,谓括曰,两府不究本末,几误国事。命以画图示禧,禧议始屈。乃赠括白金千两。”
辽国修筑长城防御女真南侵。《辽史·太祖本纪》载:太祖二年(908年)冬十月,“筑长城于镇东海口。”东海口是古代东北地区由海路通向中原的通道。为阻断渤海与中原王朝的联系,契丹人在此修筑了长城。《辽史·圣宗本纪》载:太平六年(1026年)“黄龙府请建保障三、烽台十,诏以农隙筑之。”此长城位于契丹与女真的边界地区,主要是防止其境东北部的女真人南侵。
北宋修筑长城防御西夏。《宋史·梁迥传》载:(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征太原,以迥为行营前军马步军都监,督军攻城,中流矢四。车驾还,命与孟玄哲、崔翰率兵屯定州,以功迁引进使。五年,受诏与潘美城并州于三交,及筑缘边堡障。七年,李继迁寇边,以迥领兵护银、夏州。
宋朝开挖壕堑与西夏界边。《宋史·秦翰传》载:(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五月,夏州属户扰泾原。先是,西部无藩篱之蔽,秦翰规度要害,凿巨堑,计工三十万,役卒数年而成。继迁遂不能忍。时,夏州属户以德明纳款,辄越堑侵略泾原,德明不禁。宋帝遣翰巡视边郡,夏人闻翰至,惧而退。《长编》载:(宋大中祥符二年, 1009年),宋环庆都钤辖曹纬发兵,开凿庆州界壕堑,德明移牒鄜延路钤辖李继昌言其事。……诏玮罢其役。《西夏纪· 卷十七》载:(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年),攻宋德顺军静边、隆德两寨。夏人过壕,掳掠老幼千人。宋夏边防壕堑始建于北宋时期,是北宋防御西夏的边防壕堑的一部分,在北宋西北境。现存遗迹在今宁夏中卫海原、固原地区和甘肃环庆一带。
金朝修筑边界长城,史称 “界壕”“边堡”“堑壕”。《金史·地理志》载:金之壤地封疆,东极吉里迷兀的改诸野人之境,北至蒲与路之北三千余里,火鲁火疃谋克地为边,右旋入泰州婆卢火所浚界壕而山,经临潢、金山,跨庆、桓、抚、昌、净州之北,出天山外,包东胜,接西夏”。《金史·世宗纪》载,大定五年(1165年)正月,“诏泰州、临潢接境设边堡七十,驻兵万三千。《金史·完颜襄传》载:因请就用步卒穿壕筑障,起临潢左界至北京路,以为阻塞。《金史·仆散揆传》载,揆升西南路招讨使后,沿徼筑垒穿堑,连亘九百里,营栅相望,烽堠相应,人得恣田牧,北边遂宁。以上是金朝在东北修筑边界长城。《金史·地理志》载:皇统六年,(西夏人庆三年,1146年)以德威城(州)、西安州、定边军等沿边地赐夏国,从所请也。正隆元年(西夏天盛八年,1156年),命与夏国边界对立烽候,以防侵轶。《金史·海陵本纪》载:金正隆四年(西夏天盛十一年,1159年)三月丙辰朔,遣兵部尚书萧恭来经画夏国边界。以上是金朝在今宁夏中南部修筑的边界长城。
明代筑长城抵御鞑靼
明代各朝几乎都修筑过长城。为了加强长城的修筑、管理,明朝把整个长城划分为9个防御区,即辽东、蓟州、宣府、大同、太原、榆林、宁夏、固原、甘肃,各派重兵驻守,史称为九边重镇。《明史·兵志》载:“元人北归,屡谋兴复。永乐迁都北平,三面近塞。正统以后,敌患日多。故终明之世,边防甚重,东起鸭绿,西抵嘉峪,绵亘万里,分地守御。”明朝“初设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四镇,继设宁夏、甘肃、蓟州三镇,而太原总兵治偏头,三边制府驻固原,亦称二镇,是为九边。”
明代修筑长城大多是在前代古长城基础上进行选择利用,修缮增补,连缀改建。在河套北河一线,明初曾利用过秦皇长城,后弃河不守。在甘肃、宁夏的河西地区,明代主要修补利用了河西走廊、卫宁北山、贺兰山一线的汉武帝长城。在宁夏河东、陕西北部的河套地区,明代主要修补利用了北魏、隋代使用过的秦昭王“拒胡”长城。在今山西、河北、北京西北、东北一线,明代是在战国秦、魏、燕等北方长城的基础上,主要利用了北魏、北齐、北周、隋代所使用过的长城。在宁夏固原、甘肃陇西地区,明代还修补利用了春秋战国时秦国使用过的西周朔方长城。
明代在古长城的始基上,再对其补筑、增筑、连缀,构成了明朝保卫其东北、西北边防和京畿重地的长城防线。当然,明代也有自己新建的长城。经过接续不断的修筑,终于构筑成了东起今辽宁鸭绿江,西到甘肃嘉峪关的明代“九边”万里长城。
明长城东起辽东的鸭绿江畔,西至甘肃的嘉峪关旁,横贯今辽宁、河北、天津、北京、内蒙、山西、陕西、宁夏、甘肃等省区,全长6300多公里。
清朝修长城区划农牧
清代大一统,满族入主中原,长城内外皆属清朝疆域。清代不修筑长城,这曾是学术界的定论。但是,清代对宁夏中卫黑山峡秦皇长城的修筑,却打破了学术界的这一定论。查阅史料記載,清朝不但依然修筑长城,而且还将长城的功能作用推而广之。
长城是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和谐相处的分界线。清代康熙年间,康熙皇帝曾在西北甘、宁地区修筑过长城。
康熙皇帝修筑长城。《甘肃新通志》记载:“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总督佛论题请丈量,应修一万二百八十四丈。四十一年(1702年),黄河犯涨,冲外边墙三百一十八丈。按年修筑。”从文中可以看出,当时的甘肃总督对今甘肃、宁夏境內的长城进行维修的提请得到了康熙皇帝的批准,長城修筑才得以進行,仅康熙年间就曾兩次修繕甘、宁长城。只是此时此地所修的长城並非用於軍事防御目的,而是將其用於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互不骚扰的分界线了,長城的功能已从军事作用演变为农耕民族和遊牧民族和睦相处的界碑了。现在沿宁夏、甘肃境内河西走廊古长城遗址考察还可以看见一些清代设置的界碑,碑文约定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以长城为标志,不得越界放牧、采樵。当时修筑长城,清朝以之作为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互不骚扰的分界线。
清代对秦、汉古长城的这种利用方式,一方面是为了防御游牧民族越河,越界游牧,糟踏农耕民族的庄稼;另一方面是为了禁止农耕民族越界开荒采樵,破坏草原生态。清代将长城用于农耕经济和游牧经济互不骚扰的分界线,应该说,这不失为一种高明之举。
中国长城历史悠久,规模弘大,文化积淀深厚,内涵丰富多彩,被视为中华民族勇敢、坚韧、智慧、精神的象征,是中国最具代表性的文化遗产,也是举世注目的世界文化遗产。
青山青史话未休
历史上,长城事关江山社稷,国泰民安,其地位是崇高的。所以,自周秦以来,对长城修筑不断,研究不断,可谓史不绝书。
长城作为冷兵器时代历代王朝最重要的国防建设,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建立了丰功伟业。《史记·索隐述赞》称赞秦始皇“长城首筑,万里安边”;时代先驱孫中山說秦始皇筑长城“古无其匹,為世界独一之奇观”,“长城有功於后世,实与大禹治水等”; 毛泽东说“不到长城非好汉”;邓小平说“爱我中华,修我长城”。长城是国防建设的大业,不是暴政的代称和亡国的证据。
长城在保境安民、维护秩序方面发挥了无以替代的作用。长城历经近3000年盛行不衰,因为是它是阻扼胡骑南下的森严壁垒。匈奴自逐鹿中原以来,其特长是金戈铁马,横冲直闯。农耕王朝抗拒骑兵最有效的防御工事就是构筑长城,阻隔胡骑。西周宣王筑长城,将匈奴阻隔于王朝门外。战国秦昭王筑长城,将匈奴阻隔于国境之外。秦始皇筑长城,将匈奴阻隔于河套之外。汉武帝筑长城,将匈奴阻隔于大漠以北……《后汉书·卷九十》说得好:“天设山河,秦筑长城,所以别内外,异殊俗也。”如无长城,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将会是另外一种形态。
长城作为农耕经济和遊牧经济的区划界址,奠定了中华各族数千年来赖以生存的基本经济基础。历史上,农耕经济和遊牧经济是以长城为界的。以宁夏为例,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经侍郞喇、提督孙率同蒙古部落协商,“自中卫边墙起至石嘴子沿河一带止”的黄河北岸、西岸地区,经清王朝圣旨裁定:“由贺兰山之阴六十里以内为内地,给民人樵采放牧;六十里以外为夷地,蒙古插帐驻牧。夷、汉各守定制,彼此不得越界侵占。”乾隆六年(1741年),厄鲁特额附阿宝请定边界,经理藩院咨川陕部堂尹后发布公告:“照依康熙二十五年题定界址,踏看定议,详复咨部,重申前禁。口内民人不得出边六十里外樵采放牧;蒙古不得在近边六十里内驻牧。至今夷、汉遵守,边境宁谧。”
长城作为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和谐关系的缓冲地带,缓减了两个不同生产方式的经济集团在争夺生存空间方面的剧烈冲突。以宁夏西长城内外民族关系为例,清代《中卫县志》说,长城“内外一家,民人樵牧,至出边六十里,山泽之利,与蒙古共之。”农耕民族的“驼、羊、牛、马寄牧边外,夷达或包揽保牧,类给钱文粮食;而蒙古游牧,亦时至近边六十里内,衅隙不生。出入口隘,虽驰稽查之防,而边境安帖,从古莫及也。”在这里,长城已成为区分长城内外民族生产、生活、习俗差异的历史标志,它提示长城内外的民族,“各守定界,勿相侵越”,自我规范,互相尊重,和谐相处。
长城是牧区产品与农区产品互相交流的商贸通道。以历史中卫为例,中卫长城既是塞防关隘,也是长城内外民族的“互市”场所。据明《实录》,今中卫城北长城关隘是明朝皇帝批准的长城内外民族的 “互市”场所。直到清代,长城内外民族在此地的 “互市”已成习惯。清代《中卫县志》载:黄河北岸“边墙口隘二十九处,夷达入城市交易食物,各带该管蒙古所给腰牌,至边口城门查验,听其入内地交易。”“夷人入城,汉民入夷,彼此交易,熟悉者往来便利,素鲜争竞。”
长城的功用绝非“界中国”,限“华夷”。 周秦以来,华夷皆筑长城,无所谓“界中国”,限“华夷”。 许多夷狄族群都曾先后入主中原,修筑长城;长城、界壕内外各族都有,入乡随俗即可,非以长城区分“诸夏”与“夷狄”。 明代尤重边防,大修长城用于军事防御是众所周知的。但即使在这个以长城作为救命稻草的朝代,长城也曾作为长城内外各民族和睦相处的界碑使用过。《明史·列传第六十二·王玺传》载:“(成化)十二年擢(王玺)署都督佥事,充总兵官,镇守甘肃。黄河以西,自庄浪抵肃州南山,其外番人阿吉等二十九族所居也。洪武间,立石画界,约樵牧毋越疆。岁久湮废,诸番往往阑入,而中国无赖人又潜与交通为边患。玺请‘复画疆域,召集诸番,谕以界石废,恐官军欺凌诸部,今复立之,听界外驻牧,互市则入关。如此,番人必听命,可潜消他日忧。’帝称善,从之。”由上可知,在西北沿边地区,长城、关隘在许多时候是作为、牧猎、农耕、樵牧、互市的界线的。所以,长城是维持社会大环境安定的盾牌,是保护区域经济、地方习俗的界标,它从来都不仅仅是“内诸夏外夷狄”“界中国”的族界、国界。
长城是多元文化传播的纽带。周秦以来,河西走廊、贺兰山、阴山长城内外,从来就是东西方文化、大漠南北文化交流、撞击、融合创新的传媒区域,导引多元文化的交流融合与新生。秦、汉、隋筑长城,沿长城修建道路、屯堡、驿站、烽燧,水利、城镇,保障了丝绸之路和草原古道的畅通与安全,给东西方交通、大漠南北交流、商旅往来、信息传递、长城沿线开发建设提供了标志、方便和保障,加速了长城内外的开发建设,推动了长城内外经济地理的繁荣,扩大了长城内外经济优势的互补,文化地理的互容,促进了东西南北各族的交流融合,推动了华夏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
长城是科学研究的宝贵财富,是底蕴深厚的历史文化。长城荷载着社会历史、民族关系、建筑艺术、文物古迹、经济地理、边境贸易、自然环境等方面的巨大信息,是历史、考古、文化、地理、文学、美学、军事、建筑、交通、商贸、旅游、民族、宗教、社会、环境等科学研究的资料源泉或证据标尺。
长城是多种艺术创生的源渊。长城在作为军事壁垒的同时,也是区域经济、民族关系、商贸通道的界标,更是文化传播、科学研究、艺术创造的源泉和民族形象的象征。长城积淀着太多的文化底蕴,激发着人们的思考、想象与创造,是许多文化艺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头活水与摧化剂。
长城是祖先传留给我们乃至世界的一份极为珍贵的文化财富。建筑长城的历史随着中国封建王朝的消失而落幕,但长城作为历史文化遗产却永远存留在人类的记忆中,是人类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财富。经历了近三千风雨的中国长城,一九八七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长城保护任重道远。长城保护将与长城遗产共同继续谱写长城文化的灿烂辉煌。作为文化古迹,长城的人文价值则永远彪炳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