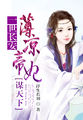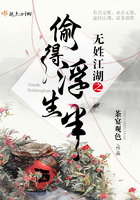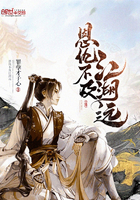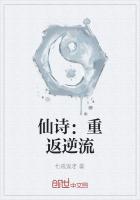吃过早饭后,参加批斗会的农民陆续来到会场,男女老少都有。被批斗的是一个姓何的地主,大约有五十来岁。他穿着一身破旧的粗布衣衫,除了左胸有块写着“地主”两字的白布外,和其他农民并无两样。他身体干瘦,头发和胡子花白,这也和其他农民无甚区别,只是脸上的表情是卑怯的。这和我们想象中的地主大相径庭。他站在主席台下,面向批斗者,低头弯腰。他的老婆和几个儿女坐在第一排陪斗。批斗会开始,先由公社书记宣读他的罪状。
我们初到大巴山,对川东北方言不熟悉,听起来很吃力,边听边问总算弄明白大半。
原来他的罪状是故意把自家饲养的牛放出去践踏了生产队的庄稼,这充分暴露了他对人民公社的仇恨心理。姓何的地主嗫嚅着说:“我有罪,我破坏了集体财物,我不该让牛挣断牛鼻索跑出圈去……”他话还没说完,人群中就有人大声呵斥他:“你还在狡赖!你明明是故意的!”公社书记高声说:“社员同志们,知识青年们!阶级敌人是狡猾的,阶级斗争是尖锐复杂的!我们要随时提高革命警惕,严防阶级敌人的破坏!”
听了公社书记的话,几个男知青愤怒地冲上前去揍那地主,直打得他双手抱住头,连连躲闪,嘴里哇哇乱叫。人群中马上有人喝彩:“打得好!”受这叫好声的鼓舞,我不假思索地大步冲上前去,对那地主说:“把你的变天账交出来!”因为我在学校上政治课时,老师告诉我们,地富分子都有一本“变天账”,上面记着谁分了他的田地和财产。一旦国民党反攻大陆回来,他们就要挨家挨户变本加厉进行清算。老地主鼻孔流着血,昏花的眼睛木然地望着我,似乎没听懂我说的什么。我气愤了,一耳光抽在他的脸上,然后又踹了他一脚。
老地主倒下了,他的老婆哭喊着扑上前,跪在我面前哀求我莫打了。我心里感到一阵厌恶,用手推开她,但我随即看到坐在前排的他的几个儿女眼里露出的仇恨的目光。
批斗会结束后,公社书记表扬了我们,说我们阶级立场坚定,敢于和阶级敌人作斗争。他同时又提醒我们要时刻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注意提防地富分子的报复。他的表扬使我们都很兴奋,大家议论纷纷,都认为今天收获很大,学到了很多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
第二天中午,我们正在吃饭的时候,一个十三四岁的农村女子背着菜走进院子。我们初到林场,没有菜吃,公社领导号召附近生产队的农民为我们送菜,所以几乎天天都有人来送菜。看见这个农村女子送菜来,我们赶忙收下并连声感谢她。她放下菜却磨磨蹭蹭没有走的意思。正当我们感到奇怪的时候,那女子鼓足勇气小声说:“知青哥哥,求你们以后别打我爹了……我爹现在都起不了床……”
哦,一瞬间我们醒悟过来:她是被批斗地主的女儿!我们面面相觑,一时不知该怎么办。突然间不知是谁说了声:“狗地主想收买我们!”这句话提醒了大家,众人捡起菜朝她扔去,边扔边说:“谁要你的菜?想收买我们没门!”
那女子愣了一下,“哇”的一声大哭起来,转身跑了。看见这种情景,几个女知青不满地嚷道:“不要太过分了!欺负人家小女孩算啥子英雄?”
这天夜里我失眠了,脑子里总是重现批斗会的情景和送菜小女孩饱含泪水的眼睛,还有她哀怨的神情。
我出身于书香世家,从小受的教育就是要懂礼貌,要与人为善。我从来没和别人打过架,更别说先出手打人,在老师眼里我从来都是品学兼优的学生。我为自己在批斗会上的举动感到惊讶。“我为什么要这样做?”我思索着。答案其实很简单:我的父亲被打成反革命分子正在劳改中,我无非要用行动来证明我与反动阶级划清了界限!
后来与农民交往多了,才知道姓何的地主在当地算一个人精。解放前,他家原本也不富裕,但这家伙脑瓜子活络。大巴山到处是桐子树,盛产桐油,当地农民用来点灯、漆水桶,除此以外别无他用,因此卖不起价钱。这姓何的不知怎么打听到桐油在外地是紧俏物资,就低价收购,贩运到成都卖大价钱,不久就富起来。临到解放前一年,附近一个财主家因抽大烟家境败落,姓何的就趁机低价把他的几十亩田地买过来成了地主。解放后搞土改,按政策他自然被划定为地主成分,而那卖地的财主反倒成了贫农。这正是“聪明反被聪明误”。难怪农民谈起他时笑他“捡了顶地主帽子戴”。
了解到这些情况后,我为自己当初的举动感到不安。后来文化大革命爆发,在“横扫一切阶级敌人”的运动中,我那中央大学毕业、曾当教授的父亲被造反的红卫兵“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用带铜扣的军用皮带暴打,那简直就是上天给我的报应。有人说“与人斗,其乐无穷”。我看未必!它除了在人与人之间制造仇恨,还能有什么作用呢?农村生产力的大解放、大发展靠的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是后话。
在以后的岁月里,我们还多次被叫去参加全公社的批斗会。几十个地主富农被民兵用枪驱赶着来到会场。他们衣衫破烂,表情呆滞。印象中最深的是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地主婆,走路颤巍巍的,似乎站都站不稳,由她的两个儿子搀扶着也来挨斗。他们左胸前都缝着一块标明地主或富农身份的白布。(后来上大学时读了美国作家威廉·夏伊勒着的《第三帝国的兴亡》这本书后,才知道这种做法源于纳粹德国。那时在德军占领区的犹太人都得在左胸上缝上一块白布,上面画上一个黄色的六角星,表明自己是犹太人。)批斗会的形式一般都是先控诉他们的罪恶,然后专门有一人带领大家高呼“打倒×××”和“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之类的口号,会场气氛肃杀。
最初参加这类活动还有新鲜感,逐渐就感到索然无味。到后来“文革”爆发,一些出身不好的知青的父母也被批斗,同病相怜,大家终于对这种阶级斗争失去了兴趣,再逢开批斗会就纷纷当了逃兵。
1986年暑假,我带着儿子重返大巴山,去看望在改革开放中已初步摆脱饥饿贫穷的乡亲们。我又看见了姓何的地主。只不过现在他已不是地主了。“文革”后,党中央拨乱反正,在宣布撤销人民公社的同时,为全国几百万地富分子摘掉了“帽子”(这无疑是最能体现实事求是精神的政策之一),他现在是劳动人民中的一员了。他早已忘记我曾经打过他,热情地邀请我去他家做客。在摆谈中我得知他又干上了经商的老本行,把乡亲们家里的鸡鸭及蛋类收购起来贩运到城里去卖,从中赚差价,这使他又成为农村中率先富起来的人。我为他感到高兴,我更祈愿那荒唐的阶级斗争闹剧永远不要再在这块饱经磨难的土地上重演。
作者简介
章孟杰,男,1964年7月初中毕业于重庆二中,当年9月5日下乡,落户巴中县双凤公社林场,任林场团支部书记。1978年7月考入大学中文系学习,毕业分配于重庆小龙坎职业中学任教。现为中学高级语文教师,中国民主促进会沙坪坝区常务副主委,区第八届、第九届政协委员,区第十四届、十五届人大代表,区台胞台属联谊会副会长。
天上掉下招工馅饼
吴三学
1971年7月初,又有招工消息从公社最高权力机关传出,说是成都市沙石公司要在本公社知青中招收20名精壮劳动力,以补充“深挖洞”、“反修防修”力量之不足。此前,已有12名听话、优秀的知青被成都饮食公司相中招走。初闻此消息,我反应木然,未往心里去。不像有的人那样亢奋、跃跃欲试、上蹿下跳。因为我深知自己底气不足,天上掉馅饼之事绝不可能降临我头上。
论家庭成分,我属于问题“麻五类”,论表现我无疑属于不思进取、行为不轨的另类知青,俗称“散眼子”知青。其实,我先前并不这样,也是好同志。当年,跟风赶浪头脑发热的我,曾坚拒亲朋好友的善意劝阻,义无反顾地奔赴“革命第一线”。下乡伊始,我就自断后援,要求经济条件尚好的父母别寄钱寄物,我要凭借自己的双手自食其力,干一番事业。秋收时节,我一人连续摇打谷机两个小时是常事,肩挑毛谷一两百斤不在话下。修筑西礼渠(西昌西宁至礼州干渠),我与同队知青李娃曾创造个人单日挖土6.5立方米的纪录。当时,一个全劳力能挖两三立方就很不错了,为此,受到西昌西礼渠工程指挥部的通报表扬……这豪气,用我当时炮制的一句打油诗:“愚公传人非我谁,定教山河谱新篇”
或可印证。“文革”一来,几经大风大浪颠簸折腾,微贱小命虽得以苟全,理想信念的圣殿却已倾塌,陷入苦闷彷徨。于是便到处漂泊,于是便消极怠工。即便大忙季节,我与患难兄弟洪友伦君也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常常躲在狭窄的阁楼,或睡大觉,或阅读当时所谓的禁书,或听收音机,有时也外出游荡。我们给自己兴了个不成文的规矩,戏称八不出(出工):一曰,天气不好不出;二曰,睡过了头不出;三曰,不喜欢的工种不出;四曰,赶场天不出;五曰,外出游玩不出;六曰,朋友来访不出;七曰,取汇款不出;八曰,心情不好不出。
好在双方都有家庭接济,饿不着也冻不着。我们的倒行逆施,必然招致社员的忌恨与指戳。不外乎:你们是来干活的,不是来吃闲饭的,生产队不养懒人。站在他们的立场,没有什么不对。但我们也有我们的歪理:生产队人手本来就不缺,我们工分少分得也少,并未亏欠任何人;要恨,就去恨那些工分迷,就去恨把我们骗到这鬼地方来的人……如此想来,心就放平了,依然我行我素。一意孤行的结果,与社员关系更加恶化。处境如此尴尬,岂敢有上调回蓉的非分之想?更何况全公社有二十多个生产队,僧多粥少,说什么也轮不到我。
然而,过了几天,事情出现了转机:我们生产队居然分得两个招工名额。我本不抱任何幻想,闻讯不禁怦然心动:机会不是来了么,何不参与竞争,碰碰运气?再说,我的身体在本队男知青中数一数二,优势明显。但仔细掂量,又觉很难,最难难在过社员关,没有他们恩准,万万不行。可关系已弄成这样,一时半会怎么扭转?正感希望渺茫,抱有同样想法的洪友伦君来了灵感:“走,找队长疏通疏通,看看能否对我们网开一面。”于是,我们在获知消息当晚,趁天未黑尽来到队长家。队长不猜就知来意,揶揄道:“平时难见你们的影子,是哪股风把你们吹来的?”“队长,这次调工作有没有我们的分?”我避过锋芒,直入主题。“调工作就得有表现,你们自个说你们的表现够不够格?”队长一脸严肃地打起了官腔,还把我们的“罪过”一一列举,就像威严的法官对犯人无情地宣判。“是我不对,还影响了友伦,请你高抬贵手,放我们一马。”我向来没有求人的习惯,此刻也不得不违心地在队长面前下矮桩。“放过我们,一辈子忘不了你的大恩大德。”洪友伦君也在一旁敲边鼓。游说了半晌,队长才缓和了语气,不置可否地说:“招工表该给哪个我做不了主,明晚开社员会就知道了。”队长把话说得很玄,但毕竟还未将路完全堵死。次日晚,我们早早来到生产队的固定会场大库房。以往,我们难得参加队里的马拉松会,即使参加,也只打个照面就溜,而今晚的会却不同寻常,将决定我们的“生死存亡”,非来不可。其时,先于我们到达的队干部们正在研究事情。我们找了个角落坐下,点燃了兰雁牌香烟,虔诚地恭候其他人光临。不知等了多久,社员知青才陆续到齐。终于开会了,队长讲完生产上的几件事,然后拉大嗓门说:“成都省的人防单位要在我队招收两名知青当工人,大家说推荐哪两个合适?”社员们先是七嘴八舌地议论,然后提名。洪友伦君鸿运高照,第一个被提名并获全票当选。他平日面带微笑,待人友善,不得罪人,受到众人“拥趸”,亦属“实至名归”。随后,有人提到别的名字,其反响并不强烈,赞成的人也不多,却令我方寸大乱,头脑嗡嗡作响,血直往上冲。“为什么不提我,为什么?老天爷也太不公平了!”正在怨天尤人,就听见饶舌的赖二婶的喊叫声:“吴三学懒得很,不想做活路,把他推荐出去算了!”此言一出,附和者众,社员们都齐刷刷地举起了手,连队干部也一个不少。我做梦也没料到自己竟然还有如此多的“粉丝”,且在过经过脉之时挺身而出,为我化解危局。欣喜雀跃之余,又有一种被淘汰出局的无奈与悲哀。很明显,全队上下一致推荐,并非真想成全我们,而是趁此机会掀掉包袱。这样一来,生产队就少了两个抢夺他们口中食,给他们添乱的懒虫。他们并不知道:推荐可以从根本改变人的命运,给他们提供新的生存空间,从而提升其人生价值。不过,我仍从心底感激那些勤劳、质朴、憨厚的山里人,正是他们的抬爱,他们的义举,我才侥幸拿到了那张朝思暮想、弥足珍贵的招工推荐表。
接下来是填表、政审、体检,所幸都很顺利。深感遗憾的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洪友伦君不幸在政审关卡了壳,未能如愿以偿。(事隔不久,他又遇上招工机会,在峨眉矿山机械厂当了工人,后来念过大学教过书,凭借睿智与才干,担任峨眉师范学校校长长达十年之久,为乐山地区的发展造就了大量师资人才,使学校财产增值一千多万元,成为当地口碑甚好颇有影响的人物。以事实证明了“塞翁失马,焉知非福”那句老话的颠扑不破。)因为洪友伦君的缺位,我有幸成为本队第一个通过正规渠道跳出“农门”的知青。尽管这份工作是块烫手的山芋,我还将继续接受特繁重体力劳动的洗礼,但它毕竟满足了我一时可怜的梦想,毕竟是我在失意沉沦时抓住的一根稻草。
遵照“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最高指示,由家里寄钱,偿还了欠生产队的口粮款22元1角6,卷裹起破烂,我终于于1971年8月25日踏上归途。从此,远离了这块剥蚀我青春、扭曲我灵魂的伤心之地。
作者简介
吴三学,1945年7月生,成都市人,大专文化,1964年7月成都四中高中毕业,1965年8月至1971年8月在西昌阿七公社桂花四队当知青。
从大学生到农民
徐孝清
1964年4月8日,一个原本极普通的日子,但这一天对我来说,却有着不同凡响的意义。这一天,我们500名知识青年从成都人民南路出发,奔向大凉山插队落户。这一四川大学中文系五九级乙班毕业照。摄于1962年5月12日。后排左起第二人是徐孝清。
239天,改变了我们每个人的人生轨迹;这一天,永远定格在我的脑海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