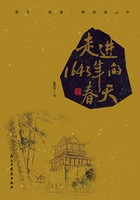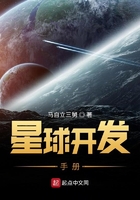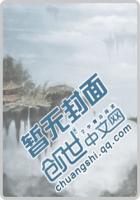间接自由式引语,经常用于第三人称叙述,其特点是引述人物的言语或想法时,不用“他说”或“他想”之类的引导语,而且在引语中说话者提到自己时也用第三人称(不然就会变成直接式引语)。由于这个特点,间接自由式与叙述语流,经常界限不清。但是这种界限不清也达到一种效果,尤其现代作家喜欢使用这种技巧,有时候,能使行文如行云流水般顺畅,不受引导语的阻隔。
《红楼梦》第二十一回,薛宝钗听见袭人埋怨宝玉与女孩子混得太多:“宝钗听了,心中暗忖道:倒别看错了这个丫头,听他说话,倒有些识见。宝钗便在炕上坐了,慢慢地闲言中套问他年纪家乡等语,留神窥察,其言语志量,深可敬爱。”这里,“其言语志量,深可敬爱”,是谁的话?也就是说,是哪一部分主体的声音?很明显,这不是《红楼梦》叙述者的声音,这是薛宝钗仔细观察袭人后形成的想法。不嫌累赘,可以改成:“她觉得其言语志量,深可敬爱。”
据叙述学家的分析,女作家作品中的女性人物,间接自由式特别多,可能的原因是女性的思维方式,比较耽于幻想。张爱玲《怨女》:“她的眼镜不能看着他的眼镜,怕两边都是假的。但是她的冰冷的两只手握在他手里是真的,他的手指这样瘦,奇怪,这样陌生,两个人都还在这儿,虽然大半辈子已经过去了。”严歌苓《第九个寡妇》中的一段:“二大还在给平说着故事,声音弱了,字字吐得光润如珠。葡萄用袖子擦了一把眼泪。谁说会躲不过去?再有一会,二大就太平了,就全躲过去了,外头的事再变,人再变,他也全躲过去了。”
这是比较典型的间接自由式,使用得很顺畅自然。在西方现代小说中,也有几位女作家善用间接自由式。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的短篇名著《园会》中,戈伯达店的伙计问劳拉:“知道下面不远处那些小房子吗,小姐?知道吗?她当然知道。”这个问题本来是小说人物劳拉的回答,但是却用了叙述者评论的方式,做一种类似解释的补充。曼斯菲尔德的另一篇小说《幸福》,宴会结束时丈夫哈里抢着去送富尔顿小姐。对于这行为:“贝莎知道他后悔刚才不该那么粗鲁,就让他去了。有些地方他真像个孩子——那么任性——又那么——单纯。”后一句显然是贝莎的声音。
因此,人物抢话,可以被解释为一种非常特殊的间接自由式引语,抢话用一个形容词或副词,点出人物的感觉,人物的思想,但是与间接自由式一样,没有采用引语的形式。抢话与间接自由式引语不同的地方,是简短得不成为句子,嵌在叙述者的语流中,不露声色地抢过了话语权,是叙述中出现了自己主观需要的评价。就拿我们用的第一个例子《三国演义》中曹操“兵败淯水”的例子,我们所关心的,渐渐变成担心曹操是否能脱险。这个态度转换是很细腻的,叙述的话语权是赢得读者同情的主要手段,这个权利可以在不经意间转让,一个“贼”字就在一定程度上转换了读者的态度,所以这个细微的语言现象,还是应该仔细研究的。
人物抢话与叙述者评论的区分
至今没有论者讨论这个现象,原因之一是因为它比较细微,不太容易发现,而且很容易与几种我们已知的语言方式相混淆。尤其容易混淆的是叙述者评论,即叙述者直接解释或评价他讲的故事中人物性格与行为。《儒林外史》第七回:“次年宁王统兵破了南赣官军,百姓开了城门,抱头鼠窜,四散乱走。王道台也抵挡不住,叫了一只小船,黑夜逃走。”《儒林外史》评点者惺园退士说:“哪会‘抵挡’?自称‘抵挡不住’耳。”惺园退士认为这是人物的推脱责任用词,因此这是人物“抢话”。但是也可以理解成王道台的确是抵挡不住,那么这是叙述者在描写情节。
上面这种情况,可以算是模棱两可。大多数情况下,究竟是叙述者的语言,还是在写人物特有的感觉,还是比较容易分清。下面这段,来自莫言的名著《透明的红萝卜》:
“谁他妈的泼了我?”小石匠盯着小铁匠骂。
“老子泼的,怎么着?”小铁匠遍体发光,双手拄着锤把,优雅地歪着头,说,“你瞎眼了吗?”
这里的“优雅地”,是叙述者对小铁匠姿态略带反讽的描写,但是这反讽态度不是人物的想法,而是叙述者对小石匠回话神态的夸张描写。
这里有一个明显的区分法:叙述者的评论词可以短达一个词(见上例),也可以长达一段,更重要的是可以加上“在他看来”,“他心中的”。钱锺书《围城》中的一例:“这几天来,方鸿渐白天昏昏想睡,晚上倒又清醒。早晨方醒,听见窗外树上鸟叫,无理由地高兴,无目的地期待,心似乎减轻重量,直长升上去。”这里的一连串情态描写,是叙述者用揶揄口吻,评论方鸿渐的懒散无聊,这不是方鸿渐本人的自觉的想法,不能加上“在他看来”。因此不是人物抢话。而上引《三国演义》的例子,“贼兵追至”,不嫌累赘,可以改成“他心中的贼兵追至”。
人物抢话与人物视角相区分
《红楼梦》第六回那著名的一段“刘姥姥一进荣国府”中写到刘姥姥来见凤姐:“只见门外錾铜钩上悬着大红撒花软帘,南窗下是炕,炕上大红毡条,靠东边板壁立着一个锁子锦靠背与一个引枕,铺着金心绿闪缎大坐褥,旁边有雕漆痰盒。那凤姐儿家常带着秋板貂鼠昭君套,围着攒珠勒子,穿着桃红撒花袄,石青刻丝灰鼠披风,大红洋绉银鼠皮裙,粉光脂艳,端端正正坐在那里。”这是以刘姥姥为视角人物写出的典型名段:以人物的意识为来描写他们经历的事件,经验是人物的,但是语汇却是叙述者的,上面这段对贾府奢侈的描写,是刘姥姥所见,却完全不是刘姥姥的语汇。而抢话不可能延续如此长的篇幅,最主要的是,抢话必须是人物会用的语汇,与叙述者的语气正成对比。
可以看到肖洛霍夫的作品《静静的顿河》中,葛利高利埋葬了阿克西妮亚后,有一句是:“仿佛是从噩梦中惊醒,他抬起头,看见头顶上黑沉沉的天空和一轮闪着黑色光芒的太阳。” 这是格里高利的感觉,诗意带哲理的语言却是叙述者的,因此不是抢话,而是采用人物视角的叙述。
在白先勇的《游园惊梦》中,“钱夫人又打量了一下天辣椒蒋碧月,蒋碧月穿了一身火红的缎子旗袍,两只手腕上,铮铮锵锵,直戴了八只扭花金丝镯,脸上勾得十分入时,眼皮上抹了眼圈膏,眼角儿也着了墨,一头蓬得像鸟窝似的头发,两鬓上却刷出几只俏皮的月牙钩来。” 可以看到,这样形成的是一种“方位转换”,不仅延续有一定长度,而且并不是引语,不是人物说出来或“想出来”的话(想说未说的话,“口对心说”),而是叙述者的描写,加人物的感觉。
二我差中的“自我抢话”
以上说的各种情况,都是第三人称叙述中的问题。在第一人称叙述者中,因为作为背景的叙述语流是第一人称,各主体争夺话语权的局面,会很不相同。甚至同一个“我”,作为叙述者,作为人物,两者之间也会争夺发言权。从叙述学角度说,叙述者“我”与人物“我”是同一个人,又不是同一个人。叙述者“我”出现在后,在“叙述现在”,人物“我”出现在前,在“被叙述现在”,此刻的我是叙述者,讲述过去的我的故事。莫言小说《红高粱家族》中选择“我”为叙述者,讲述爷爷奶奶那一辈发生的故事。那时有无“我”这个人物,并不是小说叙述的必需条件:“有人说这个放羊的男孩就是我,我不知道是不是我。”过去的“我”并不具有充分的叙述主体性。
于是,在结构似乎很简单的小说中,赫然出现了完全不同的“我”。似乎叙述者“我”在讲的不是自己的故事,而是一连串不同的别的“我”的故事。有时,甚至叙述的语言都不再是叙述者的语言,而是人物的语言,这时就可能出现人物“我”抢叙述者“我”的话。
老舍的中篇《月牙儿》中有一段,“我”大约十七岁,主人公初恋了,落入情网:“他的笑唇在我的脸上,从他的头发上我看着那也微笑的月牙。春风像醉了,吹破了春云,露出月牙儿一两对儿春星。河岸上的柳枝轻摆,春蛙唱着恋歌,嫩蒲的香味散在春晚的暖气里。”叙述者“我”是久历人世,见惯男人薄幸的妓女,怎么说出这样纯情甚至滥情的语言?回答很简单:这是人物当时的心态,是人物的语言。
再看另一段:“刚八岁,我已经学会了去当东西。我知道,若是当不来钱,我们娘儿俩就不要吃晚饭;因为妈妈但凡有点主意,也不肯叫我去。我准知道她每逢交给我个小包,锅里必是连一点粥底儿也看不见了。我们的锅有时干净得像个体面的寡妇。”一个八岁的孩子怎么会说出“干净得像个体面的寡妇”这样泼辣的比喻?回答很简单:这是叙述者在回忆时的口气。叙述者是个饱经人世风霜的妓女,对生活完全绝望,在狱中回忆一生,想到八岁时的情境。
在第一人称小说中,叙述者与人物似乎是一个人,因此叙述言语主体与经验主体似乎合一。从《月牙儿》的例子,我们可以发现,这二者实际上是不同主体:叙述者“我”成熟,饱经风霜,愤世嫉俗,认清这世界一片黑暗,毫无出路;人物“我”是个在渐渐长大的女孩子,经常是幼稚天真、充满希望而又因无依无助而感伤。前者的语言犀利尖刻,后者的心理生动、亲切。
这是所有的成长小说(Bildungsroman)的通则:一个成熟的“我”,回忆少不更事的“我”,如何在人世的风雨中经受磨炼,最后认识到人生真谛。成熟的我作为叙述者当然有权利,也有必要,对这成长过程作评论、干预和控制;作为人物的“我”,渐渐成长,要去掉身上许多不适应这个世界的缺点,免不了要被成熟的“我”评论并且嘲弄。这两个“我”的间距,笔者称之为“二我差”。
在启悟小说式的格局中,“二我差”最终会渐渐合龙、消失,因为人物渐渐成熟,在经验上渐渐接近叙述者“我”。《月牙儿》的最后二分之一内容,当人物“我”已成为这个恶浊世界的一员后,“二我差”就几乎看不见了。因为叙述者“我”的身份是仇恨冷酷世界,最后被关入监狱的暗娼。
除了年龄的成长外,二我差还发生在二者的其他品格变化之间(如果叙述者“清醒”地回忆的“我”当时愚笨的话)。阿来《尘埃落定》:“那个麦其家的仇人,曾在边界上想对我下手的仇人又从墙角探出头来,那一脸诡秘神情对我清醒脑子没有一点好处。”“我”作为人物,是一名傻子,本该一无所知。然而作为叙述者,却能辨别周围的是是非非,因此叙述者能说此时仇人的神情是“诡秘”的。
美籍阿富汗作家卡勒德·胡赛尼的名著《追风筝的人》,叙述者26年后讲小时候的故事,开始时两个人格有鲜明的对比,渐渐二者合一,但是在关键时刻两个人格依然显现。小时候的“我”面对坏人时的反应:我逃跑,因为我是懦夫。我害怕凶徒阿瑟夫,害怕挨打。26年后,面对同一个人,更加危险的场景,主人公没有退缩,因为“我”明白“我”必须成长了:
我不知道自己何时开始发笑,但我笑了。笑起来很痛,下巴、肋骨、喉咙统统剧痛难忍。但我不停笑着。我笑得越痛快,他就越起劲地踢我、打我、抓我。
“什么事这样好笑?”阿瑟夫不断咆哮,一拳拳击出。他的口水溅上我的眼睛。索拉博尖叫起来。
“什么事这样好笑?”阿瑟夫怒不可遏。又一根肋骨断裂,这次在左边胸下。好笑的是,自1975年冬天以来,我第一次感到心安理得。我大笑,因为我知道,在我大脑深处某个隐蔽的角落,我甚至一直在期待这样的事情。
一直在“期待”的是正在成长中的“我”,主人公在成长过程中对世界的种种磨难,看法发生了转变,他在成长中“二我”渐渐弥合,主人公一步步走向成熟和勇敢,和叙述者“我”越发接近。
这并不是说叙述者“我”与人物“我”年龄差较大时,肯定会出现主体安排的困难。如果处理得好,“二我差”可以变成使叙述主体复杂化并且复调化的手段。《月牙儿》应当说是一个比较成功的例子:“妈妈的屋里常有男人来了,她不再躲避着我。他们的眼睛像狗似的看着我,舌头吐着,垂着涎。我在他们眼中是更解馋的,我看出来,在很短的期间,我忽然明白了很多事。”
这一段中,两个主体相混,互相交流。“我在他们眼中是更解馋的”,是人物我“看出来”的,那时的“我”才是小学毕业的年龄;“在很短的期间……”却是叙述者回忆的总结。两个主体交流互相补充,使叙述富于动力,既不是叙述者我完全控制,使语言过于精明、老练,失去真切感,又不是人物我完全控制,使语言过于天真、稚嫩,失诸戏剧化,缺少内察的深度。
可以说,对“二我差”的掌握,是第一人称回忆式小说成功与否的关键。由于许多作者对此并不自觉,我们看到少数成功,也看到一大堆失败。
无论作何种处理,“二我差”问题总是第一人称回忆式小说的内在矛盾?为了避开这个困难,某些小说有意把叙述时间与被叙述时间的间隔缩小。例如塞林格的《麦田守望者》,把叙述时间安排在少年主人公结束冒险经历之后不久,而不是在他长大之后若干年。这样,全文的戏谑性街头少年的语言,就同时属于两个“我”,不会发生二我差。
要消除二我差的另一个办法,是坚持说两个人格之间(在某个具体问题上)始终一致,没有差别。例如林白《一个人的战争》:“阿姨扬手一拨,蚊帐落下,床就是有屋顶有门的小屋子,谁也不会来。灯一黑,墙就变得厚厚的,谁都看不见了。放心地把自己变成水,把手变成鱼。鱼在滑动,鸟在飞,只要不发出声,脚步就不会来。这种做法一直延续下来,直到如今。在漫长的日子中,蚊帐是同谋,只有蚊帐才能把人彻底隔开,才安全。”儿时的情感,与叙述者现在的感慨,因为在喜爱蚊帐这个具体问题上,人物“直到如今”变成叙述者了,都没有变化。这样就迫使两个主体的话语权争夺暂时休战。
人物争夺话语权的现象,在影视中也会出现。只是因为媒介变了,“抢话”就变成了“抢镜”,人物的主观感觉可以抢过镜头。例如电影《红楼梦》中,刘姥姥进大观园,小说中用刘姥姥视角写的一段,就可以用得很具体。但是这就需要另一本书进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