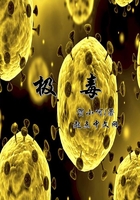说完我就挂了电话。一定是雷恩沃特下的令。15分钟以后,梅沙撤出了期货市场。我与另外一位董事约翰·考克斯有一个户头,这让股东们安心了许多。我们投资的方向也与梅沙一样。由于保留了账户,我们又赚了1500万美元。梅沙的户头要是还在,赚钱的金额是我们的两倍。
没过多久大通银行的人又来找我,这次下的令更多,说我在首席执行官位子上坐一天,他们就没办法对公司进行改革。
我说:“那好,这个问题我已经与达拉谈过了。”大通和雷恩沃特夫妻俩似乎还没有猜到我早已作好离开的准备了。他们一定想,我在梅沙公司40年了,离开肯定不是件容易的事。
我告诉他,等新的首席执行官来了我就走。
“就这样?”他问道。
“就这样。”我答道。
10年后的2007年,我在鲍勃牛排馆又遇到了大通那个人,他正和我的朋友道格·米勒喝酒。道格看到我,朝我走了过来。
“那个人有话跟你说。”
“有必要吗?”
“有。你过去听听他要说什么。”
于是,我过去了。
他开门见山地说:“有些话在我心里已经憋了10年了,今天要跟你说清楚。是雷恩沃特让我对你说,只要你当首席执行官,我们银行就不能给你贷款,其实,谁当首席执行官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他长舒一口气。
“以后我再也不会想这事了。”
到了1997年第一季度,梅沙公司的情况开始好转。天然气价格升到了每千立方英尺2.26美元,是1989年以来首个盈利的季度。“红脸”登台。
“干吗不留下?”理查德问我,还说他早就不找人接我的班了。
“不,我还是要走。”
那个时候我已经知道自己应该去做什么了,我要做的与梅沙公司一点关系也没有,并且是雷恩沃特夫妻不愿意看到的期货贸易。我们将能源这个老本行作为发展基础。公司1986年成立,到1997年已经10年了。我对公司的发展前景非常乐观。我从公司带了5个人出来,在外面租了办公室。我对理查德说:“我已经找到下一个办公室了。”
梅沙的管理层、雷恩沃特以及赫什开始筹备推广“新梅沙”。我还继续留在那里做什么呢?于是我在纽约打电话给理查德,约他在1996年6月12日跟我在新泽西泰特伯勒机场见面,我要给事情做个了结。他同意将我的辞职信发给全体员工。我想他花区区500万美元就将一家公司的创始人,一个领导了公司40年的领袖人物赶下台应该是非常得意的。第二天我的辞职信就下发给了全体员工,正式宣布离开梅沙公司。下面是辞职信的全文:
我与理查德·雷恩沃特决定一起努力为梅沙公司寻找下一任首席执行官的最佳人选,找到之前我将继续留任,找到之后我依然保留梅沙公司的股东与董事身份。
40年了,我相信大家的心也越来越齐了。从1956年我用2500美元创业到今天,梅沙公司走过了一段漫长的发展之路。
如今,梅沙的触角已经遍及全球,钻探的油井超过4800个,成功率达到75%。1959年我们用35000美元打开加拿大市场,20年后以6.1亿美元售出全部资产。我们生产的天然气达3万亿立方英尺—相当于5亿桶石油。股东分红等其他收益近20亿美元。这40年对我来说是无比精彩的40年。与我共事过的人以及我参与过的交易,我永远都不会忘记。
同年7月,我在梅沙公司年会上作了最后一次致辞。我的心里非常难过。虽然我跟一个记者说:“我不会过多留恋,但是这次讲话真的很难。”另外一个记者注意到了这一点,说我看起来“一直在强忍泪水”。
《达拉斯晨报》刊登了那天对我的专访。封面上的我靠在椅子背上,双脚放在桌上,鞋底还有个洞。离开梅沙公司的前一周,我作了一次结肠镜检查,并且从家里搬了出来,跟妻子提出离婚。所有这一切都没有我离开梅沙公司心痛。但是即便如此,我还是愿意往好的地方想。就在那个周末,我还与约翰·考克斯、他的律师蒂·凯利,还有我的律师鲍比·斯蒂尔维尔一起去城堡松林俱乐部打高尔夫。我们一起坐在阳台上休息,喝喝酒、赏赏景。我对他们说:“你们知道吗,静下心来想想,我觉得自己其实是世界上最幸运的人。因为我还能坐在这里,身体健康,同时还有好朋友在我身边,你们也很健康。来,为我们4个干杯吧,为我们是世界上最幸运的人。”
我和约翰一起经历过大风大浪。无论顺境,还是逆境,他始终站在我这一边。但是这次他没有。
他说:“我不这么认为。你事业惨淡、生意失败、老婆也快没了,你甚至连工作都没有,但是你竟然说自己是世界上最幸运的人,我想你是最傻的人才对。”
以期货贸易和天然气另辟新天地
1996年8月,梅沙邀请已经退休的CrossTimbers石油公司前总经理庄·布朗雷再次出山,并任命他为首席执行官,是我推荐他的。我在董事会有3张投票权,足以左右首席执行官的人选。没有董事会全票通过,任何任命都不会生效。我与布朗雷有多年交情,他是鲍比在得克萨斯州大学兄弟会的哥们儿。我跟他私下谈了整整两个小时,最后他说:“我接受,但是不光是首席执行官,我还要当董事会主席。”
“好的。这个主席我已经当腻了。”我回答说,事实上也是这样。
1997年4月,梅沙公司与Parker&Parsley石油公司合并,组成了美国第三大独立石油公司先锋自然资源公司。合并的消息给公司股价注入了一剂强心针,但是我认为这只是暂时的。从长远来看,这对梅沙公司的股东并不是利好消息,而且当时就应该抛出股票。就在我以每股34美元的价格抛出并辞去梅沙公司的职务之后不久,我的话果然应验了。不到一年时间,梅沙公司的股价就跌到了5美元,不过后来又反弹上去。
合并之后,跟随公司40年的“梅沙”两个字成为历史。先锋决定弃用梅沙这个名字之后,我们立即申请在我们的新公司使用“梅沙”二字,比如梅沙水力、梅沙电力。两个公司目前正努力在得克萨斯州的潘汉德尔建设世界上最大的风电场。“梅沙”二字对我来说就等于我40年的奋斗生涯。就像我一样,它也有历史。
比起雷恩沃特让我带走的,我离开其实算不了什么了。这一点首先表现在新公司的经营上。1986~1996年之间,公司连续10年盈利。在我与庄·布朗雷的共同努力下,梅沙公司1.5亿美元的管理成本早已全部赚了回来。我一直自诩为有远见的人。之前寻找新油气田已经困难重重,一方面成本飞涨,另一方面前景堪忧,那时我就应该放弃,转而将精力放在期货市场。但是我没有,现在我想应该这样做了。
公司的第二笔大生意是收购了一家天然气燃料公司。1997年4月,我从梅沙公司那里花了110万美元买下这家公司。110万美元里还包含一张价值210万美元的应收票据,也就是说我买他们的公司,他们还倒贴我钱。公司命名为“皮肯斯燃料公司”,后更名为清洁能源燃料公司。如今下属的燃气站数量已经从最初的两家发展成现在的185家,总市值也增加了一倍。开始他们都认为期货和天然气燃料没有什么发展潜力,事实上他们想错了。
离开梅沙公司前夕,大家为我在鲍勃牛排馆举办了送别晚宴,雷恩沃特夫妇和小跟班赫什不在邀请之列。布朗雷送给我一个非常好的送别礼物—《新都流浪者》,是我的好友G·哈维画的一幅油画,挂在梅沙大厅已经好几年了。宴会上大家相互举杯,为我祝福,一两个人哭了。我站起身来,说了说自己的感受。我爱梅沙,我感谢每一个辛勤工作的员工。我没有说要“退休”,因为我永远也不会退休,也不会流泪。我一心想要开始新生活。我一直强调梅沙最大的财富是员工,所以当我要离开的时候,我带走了几个最优秀的人才。
在梅沙公司最后一天的傍晚,我向窗外看了看,最后一次。我68岁了。以前我一直想我最后会以什么样的方式离开这里,是默默地退休?被众人欢送出去?还是装在箱子里抬出去?
我知道早晚会有这么一天。很多年以前我就已经想好,结束就结束了。不再留恋这个主席头衔,不再在办公室里摆样子。很久以前我就意识到变化的力量有多强,一个变化会引起另一个变化。所以离开并不是结束,而是一个新的开始。一扇门关闭,另一扇门就会开启。即将最后一次关上灯,回到我临时的家—四季酒店了。我站在空荡荡的办公室,无数记忆的片段在眼前闪过。我一直在想,我们究竟是前进了,还是后退了。发生了什么,没有发生什么,什么该发生却没有发生。一切都是对未来的热身。
我一直说“怎么来的,怎么走”。我在梅沙的最后一天,依然是在6点准时关上灯,关上门。跟了我多年的助手塞利·盖穆勒也收拾好要走。她17岁就来到梅沙,之后去中央资料部做兼职,最后成了我的得力助手。
她问我:“就要离开了,有什么感受?”
我说:“我终于要离开这个鬼地方了。”
她双手紧握,脸上绽放出灿烂的微笑。
“我也是。我们一起离开这个鬼地方!”
我们谁也不知道未来等待我们的将会是什么。但是我对未来很有信心,新生活开始了。
②绿票讹诈,指投机者购买公司大量股票,企图加价出售给公司收购者,或者是以更高的价格把股票卖回给公司以避免这部分股份落入公司收购者之手。—编者注
③DIP,占有中的债务人。—译者注
④HCA,美国医院有限公司—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