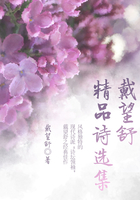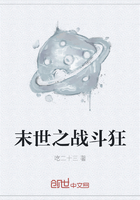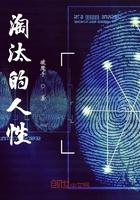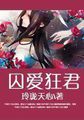第二节 崇尚通俗的艺术追求
在清初的时代氛围中,李渔走着一条与众不同的亦文亦商的人生道路。李渔集剧作家、导演、书画经销商等于一身,以一介布衣专事戏曲、小说等创作,组织家庭戏班,经营芥子园,依靠卖文演出交游维持一家近五十口人的生活,尤其是编撰剧本和组织戏班演出成了他谋生的主要手段和职业。为了养家糊口,李渔创作戏曲十分注重舞台搬演的效果、观众的欣赏趣味和接受心理。所有这些使李渔在《闲情偶寄》里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古代戏曲实践和理论时,自觉地融入自己的艺术经验,贯穿强烈的观众意识,从剧作家、导演、演员和观众多维视角建构起他的观众本位的戏曲接受观。从戏曲接受的观众本位出发,李渔特别崇尚戏曲的通俗性。崇尚通俗的戏曲接受观因此成为李渔戏曲理论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之一。
一、曲文音律的通俗性
李渔生活在明末清初,而戏曲活动主要在清初。其时,哲学思想界产生的对抗程朱理学的进步思潮和富有叛逆精神的异端情绪影响了人们的人生价值观。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扩大影响了人们的社会价值观。封建士大夫们纷纷兼并土地,大兴园林,追求享乐奢糜的生活。商人的社会地位较前大大提高。文人经商业贾逐渐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随着社会风气的变化,不少文人从事戏曲活动,蓄养家庭戏班,争奇斗胜。民间演剧也日益兴盛。戏曲理论论争与戏曲特征探讨空前活跃。李渔崇尚通俗的戏曲接受观主要体现在强调戏曲曲文、音律和题材的通俗性上,以使戏曲适应舞台搬演并为观众欣赏接受的理论。
就戏曲的文学体制而言,曲文是为揭示人物思想感情、推动情节发展而设的。曲文的通俗与否直接制约着观众对戏曲的理解、欣赏和接受。李渔在《闲情偶寄·词采第二》中特辟“贵显浅”、“重机趣”、“戒浮泛”、“忌填塞”四款详细论述了曲文的通谷性问题,而“贵显浅”作为纲要具有统领其它三款的重要作用。对于曲文,李渔不像明人论诗那样单从文辞、意境的角度去论述,而是结合舞台搬演和观众接受的实际,崇尚含义深刻但是语言浅显明白、不假雕饰的风格。李渔说:“曲文之词采,与诗文之词采非但不同,且要判然相反。何也?诗文之词采贵典雅而贱粗俗,宜蕴藉而忌分明;词曲不然,话则本之街谈巷议,事则取其直说明言,凡读传奇而有令人费解,或初阅不见其佳,深思而后得其意之所在者,便非绝妙好词”。【41】在这里,李渔运用比较的方法阐明了曲文与诗文语言特点的区别。李渔还清楚地认识到戏曲是以下层市民为主不同文化层次的观众为接受对象,曲文只有通谷易懂,老少皆宜,才能真正实现戏曲的审美价值和社会功能。李渔说:“传奇不比文章,文章做与读书人看,故不怪其深,戏文做与读书人与不读书人同看,又与不读书之妇人小儿同看,故贵浅不贵深。”【42】戏曲最早起源于民间。戏曲本身就是俗文化的一种。再加上观众到剧场观赏戏曲表演主要是为了娱乐、休闲和消遣,而观众的文化水平高低不一,所以,无论是戏曲本体还是戏曲的欣赏接受,都要求戏曲曲文通俗化。显然,李渔强调曲文“贵浅不贵深”是符合戏曲本质的。
当然,李渔并非认为曲文一味浅显就好,也未把曲文浅显通俗与文采精致对立起来。李渔说:“然一味显浅而不知分别,则将日流粗俗,求为文人之笔而不可得矣。”李渔指出元杂剧也有“极粗极俗之语”,其原因“乃矫艰深隐晦之弊而过焉者也”。对此,李渔提出要把握浅显与文采的区别和分寸,认为曲文创作要根据人物的身份、地位,符合人物的思想感情,展示角色鲜明的个性,“说何人肖何人,议某事切某事”。【43】李渔特别指出“能于浅处见才,方是文章高手。”【44】这个观点可谓李渔崇尚曲文通俗性的理论核心。它表明李渔不仅为曲文创作确立了以通俗性为尺度的审美判断标准,而且将这一标准置于文白兼擅、雅俗相济的审美理想高度。“能于浅处见才,方是文章高手”,就是要求剧作家具有不凡的艺术功力和创作才情,能在浅显通俗的曲文中蕴蓄极丰富的内容,包容极深广的意境。它防止了剧作家对曲文浅显的庸俗理解甚或曲解,避免了使浅显流于肤浅和一般化,丧失艺术性的弊病,显示了李渔对曲文通俗性的辩证认识。从艺术思维上说,李渔这种以浅见深的观点表明他主张曲文浅显与文采有机融合为一,以俗为美的起点和归趋本质上结合着以雅为美,通俗化的现实思维、大众思维中凝聚着典雅化的经典思维,这对提升戏曲的艺术品位并且有利于雅俗共赏不无裨益。
不仅如此,李渔还强调曲文创作要“重机趣”。李渔认为曲文创作在讲究通俗性时绝不可缺少“机趣”二字。李渔指出曲文表达要自然通畅,生动有趣,精神贯注,“血脉相连”;曲文的句与句之间、曲与曲之间、折与折之间要贯通一气,“勿使有断续痕,勿使有道学气”,不使观众对戏曲情节的理解和剧情线索的把握无故中断。李渔说:“机者传奇之精神,趣者传奇之风致,少此二物,则如泥人土马,有生形而无生气”,不仅剧作家创作曲文时“心口徒劳,耳目俱涩”,“以此自苦”,而且使观众欣赏接受感到腻烦,“复苦百千万亿之人”。【45】通俗而又富有机趣的曲文表里相应,相得益彰,必然增强曲文的灵气和韵味,使戏曲在自然、和谐、融洽、完善的语境中给予观众欣赏接受以极大的艺术魅力和极强的艺术感染力,戏曲接受效果因此得到增强。无庸置疑,李渔提倡“重机趣”,说明李渔对曲文通俗性有独到的深刻的见解。
就戏曲的音乐体制而言,明清传奇为南北曲整编合流。它博采南戏和北杂剧得益于民间养育的长处,形成了大量规范化的曲牌。这些新的曲牌和新的唱腔与剧情内容相一致,对广大观众来说既熟悉又新鲜,适合南北方观众的欣赏趣味,很快成为雅俗共赏的音乐旋律程式。随着戏曲的发展,按谱填词也成了约定俗成的音律成规。按照这种音律成规创作的戏曲一二百年来为广大观众喜闻乐见,最终以其通俗易懂的音乐体制熔铸了广大观众共同的欣赏趣味和接受习惯。明清传奇盛行二百年之久,流布范围几遍全国,搬演和欣赏戏曲成了上至朝庭下至市民热衷迷恋的时尚,无不证明了这一点。从这个意义上说,音律成规是保持戏曲本质和特点的稳定因素。在戏曲创作中遵守音律成规就意味着坚持戏曲质的规定性和艺术形式的通俗性。换言之,像曲文创作要求文学体制上的浅显通俗一样,剧作家按谱填词也有一个音乐体制上约定俗成、讲究规范的通俗性问题。剧作家不能随心所欲逾越戏曲的音律成规,破坏观众日久形成的审美意向和接受习惯,否则,戏曲接受效果必差。为此,李渔也十分崇尚戏曲音律的通俗性。
围绕着音律问题,李渔批评由《北西厢》改编而成的《南西厢》“但知关目动人,词曲悦耳”,可是不懂北曲与南曲的音律区别,不合昆调的声律,“词曲情文不浃”,致使观众“废卷掩鼻而怪秽气熏人”。李渔指责当时剧作家盲目仿效《南西厢》,说:“玷《西厢》名目者此人,坏词场矩度者此人,误天下后世之苍生者,亦此人也。”【46】李渔提出要“恪守词韵”,“凛遵曲谱”;认为集曲首先音调要协,其次“亦顺文理贯通”,否则,“生扭数字作曲名者,殊失顾名思义之体”,【47】扰乱观众的听觉,观众难以欣赏接受。李渔说拗句难好,“新造之句,一字聱牙,非止念不顺口,且令人不解其意”,【48】势必达不到戏曲接受的目的。李渔还说合韵易重,不应为了合韵而将分唱混同于合唱,使角色不能表达各自的情意,从而违背分唱的曲理,不然,角色演唱时曲、情、意分离,观众不能准确把握角色的思想感情,对戏曲的客观理解和主观想象、联想等都会受到不必要的抑制。李渔从长期的舞台实践中认识到汉字声调在说话时或演唱中的声高不同,告诫剧作家慎用上声,否则,观众将无法从演员的歌唱中领略声情并茂的旋律美。明清传奇的音乐结构是以南曲为主,吸纳北曲,而南北曲有不同的声情素质。李渔看到了南北曲在运用入声字作韵脚时因北曲无入声字而有区别,提出“入声韵脚,宜于北而不宜于南”,作传奇宜“少填入韵”【49】,使观众能够分别欣赏到南北曲独特的声情之美。李渔把“务头”理解为“曲眼”,等同于“诗眼”、“词眼”,认为“有此则活,无此则死”,演员唱则“发调”,观众听则“动情”,要求剧作家在创作“务头”时“阴阳平仄断宜加严”。【50】李渔甚至认为词采欠佳,但是协律合调的戏曲仍然能够受到广大观众的喜爱,藉此传播世上,比如“《荆》、《刘》、《拜》、《杀》之传,则全赖音律;文章一道,置之不论可矣”,【51】便是以具体实例说明了戏曲创作遵从约定俗成的规范化的音律成规对保证戏曲通俗和观众欣赏接受的重要性。
难能可贵的是,李渔没有片面强调曲文或音律的通俗性,不是将曲文与音律割裂开来,而是提倡曲文与音律互相统一,融合通俗的美学意蕴。李渔非常赞赏“油盐柴米酱醋茶”、“日出东边西边雨”、“道是有情却无情”、“事非偶然”一类的曲文,认为诸如此类的曲文“系家常俗话”,观众耳熟能详,不仅创作起来“易工”、协律,而且听起来“便觉自然,读之溜亮”。【52】李渔在强调曲文的通俗与音律的通俗紧密结合、有机统一的同时,清醒地看到了音律成规与剧作家创作才能之间的矛盾,确认音律成规的客观存在有形地增加了剧作家创作的难度,“令人搅断肺肠,烦苦欲绝。此等苛法,尽勾磨人”。【53】然而,李渔认为剧作家应该妥善处理发挥自己的创作才能与恪守音律成规的关系,要在有限的戏曲音律规范中创造性地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充分展示自己无限的艺术才华,从心所欲不逾矩,卓有成效地利用音律规范的合式性实现戏曲创作的审美理想。例如,曲谱是戏曲音乐结构的定型准则。李渔说:“情事新奇百出,文章变化无穷,总不出谱内刊成之定格。是束缚文人而使有才不得自展者,曲谱是也;私厚词人而使有才得以独展者,亦曲谱是也。”李渔的意思是说剧作家按谱填词,不应被动地受曲谱限制,消极地屈从于曲谱,而应该主动利用腔格规律,根据剧情内容表达需要积极发挥曲谱音乐上的优势,尽情施展自己的艺术才华。这样的话,所填的词就不会成为内容空虚、缺乏生气的一串串音符,相反,会成为内容充实、生机勃发、才情横溢、“新奇可喜”、“有伦有脊之言”。【54】李渔在此表达的思想与强调曲文创作“能于浅处见才,方是文章高手”一样富有哲理性和辩证性,内在精神实质是一致的,的确耐人寻味。基于戏曲按谱填词的特殊性,李渔从戏曲接受的角度呼吁观众给予剧作家驾驭音律成规的才能以正确的认识,说:“作者能于此种艰难文字显出奇能,字字在声音律法之中,言言无资格拘挛之苦,如莲花生在火上,仙叟弈于桔中,始为盘根错节之才,八面玲珑之笔,寿名千古,衾影何惭!而千古上下之题品文艺者,看到传奇一种,当易心换眼,别置典刑。”【55】相比较而言,李渔要求剧作家按谱填词,“恪守词韵”,“凛遵曲谱”,扬长避短,咬字清晰真切,正五音,清四呼,明四声,辨阴阳,与明代沈璟提出“合律依腔”【56】的主张不尽相同。李渔强调音律的精严,不仅着眼于音律的音乐形式和戏曲的舞台性,而且考虑到观众的欣赏接受,旨在使戏曲的唱段在内容和形式的统一上以通俗易懂的品质始终给观众以声情美的感受,使观众在听清听懂的基础上提高戏曲接受的效果。所以说,李渔对音律的认识确实比沈璟略高一筹,是在沈璟维护音律的规范性、通俗性基础上的发展与进步,对丰富戏曲的审美文化价值具有重要意义。
二、故事题材的通俗性
除了在文学体制上崇尚曲文的通俗性、在音乐体制上崇尚音律的通俗性之外,李渔还崇尚戏曲题材的通俗性,因为戏曲的曲文、音律与戏曲的题材有密不可分的血肉联系,戏曲的通俗性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剧作家选取的题材所决定的。郑振铎在《中国俗文学史》中明确地把明清戏曲归入“俗文学”的范畴,说:“‘俗文学’就是通俗的文学,就是民间的文学,也就是大众的文学”。【57】显而易见,戏曲的题材必须像曲文和音律一样具有通俗性,才能真正使戏曲成为名副其实的“通俗的”、“民间的”、“大众的”文学,才能被广大观众喜闻乐见、欣赏接受。李渔虽然不可能像现代人那样提出正式的“俗文学”的概念,但是,他深深懂得戏曲题材的通俗性像曲文和音律的通俗性一样事关戏曲的艺术生命和观众的接受效果。
李渔说:“王道本乎人情,凡作传奇,只当求于耳目之前,不当索诸闻见之外,无论词曲,古今文字皆然。凡说人情物理者,千古相传;凡涉荒唐怪异者,当日即朽。《五经》、《四书》、《左》、《国》、《史》、《汉》,以及唐宋诸大家,何一不说人情?何一不关物理?及今家传户颂,有怪其平易而废之者乎?”又说:“鬼魅无形,画之不似,难以稽考;狗马为人所习见,一笔稍乖,是人得以指摘。”【58】李渔这番话内容相当丰富,它至少表明李渔具有以下认识:一是戏曲要反映现实的社会生活,要以再现和表现现实生活中的人情物理为基点。人情物理是现实的本来面貌,事物的本色的情理。戏曲反映现实生活是它的本质的规定性。二是戏曲不能按照不切实际的主观臆想,“索诸闻见之外”,敷演“荒唐怪异”、神仙鬼魅之事,脱离现实生活。三是现实生活存在于观众的“耳目之前”,具有通俗、“平易”、“为人所见习”的特点。剧作家按照生活的真实、生活的逻辑和客观事物的情理,以现实生活为题材,所创作的戏曲就能取信于观众,为观众欣赏接受并传播开来,以“家传户颂”的接受方式流芳千古。三是以合乎“人情物理”的现实生活为题材,对剧作家来说,就无异于开辟了创作的广阔天地,作品也因此具有现实意义;对观众来说,欣赏接受就不再止于耳目之乐、声色之欲,而能够从中获取教益。李渔从文学史的宏观高度切入戏曲创作的微观领域,强调戏曲题材的通俗性及其对戏曲接受的意义,艺术视野开阔远大,立论说服力强。与强调戏曲创作以现实生活为题材以便确保戏曲的通俗性的主张一致,李渔认为导演在选用剧本时也要是以反映人情物理的现实生活为题材的,因为剧本的通俗性影响和制约着舞台艺术形象的展示、观众的欣赏趣味和戏曲的接受效果。他提出选剧应透过剧本外在的冷热场面,看它的内容是否表现了人情,说:“传奇无冷热,只怕不合人情。如其离合悲欢,皆为人情所必至,能使人哭,能使人笑,能使人怒发冲冠,能使人惊魂欲绝,即使鼓板不动,场上寂然,而观者叫绝之声,反能震天动地”。这就是说合乎人情的剧本在戏曲接受过程中被具体化时能够激起观众喜怒哀乐的感情爆发,使戏曲艺术形象及其寓意深入人心,即使戏场上没有喧闹激扬的器乐声,也能够搅动人心,强化戏曲接受效果。李渔认为这较之那些“满场杀伐,钲鼓雷鸣,而人心不动,反欲掩耳避喧”的搬演更为可取,是“冷中之热,胜于热中之冷;俗中之雅,逊于雅中之俗。”为此,李渔主张剧作家要选取“外貌似冷而中藏极热,文章极雅而情事近俗者”为题材,“稍加润色,播入管弦”。【59】
李渔崇尚通俗的戏曲接受观丰富了中国古代戏曲理论的艺术宝库,不仅具有戏曲理论建构的审美艺术价值,而且在当时具有匡时济俗的现实文化意义。首先,李渔崇尚曲文的通俗性表明了他反对“时文风”及其流弊的坚定立场,本质上与明代何良俊等人提倡的“本色”论有一脉相承的内在联系和共同之处。自从明代邵灿创作《香囊记》以来,戏曲创作便盛行“时文风”。骈俪派创作的戏曲不仅骈四俪六,扭捏作态,而且好引古文、古诗,在曲文中炫耀才学,根本不顾大众能否看懂、听懂,能否欣赏接受。直到清初,这种流弊依然存在。面对这种戏坛上的严重危害,自明代嘉靖年间起,徐渭、何良俊等人便先后标举“本色”、“当行”的旗帜,坚决抵制这股歪风,提倡戏曲剔除脂粉,通俗易晓。王骥德更是站在戏曲接受的角度说道:“作剧戏,亦须令老妪解得,方入众耳”。【60】从反对“时文风”和倡导曲文的通俗性两方面结合看,“本色”论是符合戏曲的本质、特点和发展规律的,是有裨于观众对戏曲的欣赏接受的,对推动戏曲创作走上正道起了积极作用。李渔继承和发扬了这一战斗精神和优良传统,反对“时文风”及其流弊,反对“后人之曲则满纸皆书”,【61】给予曲文的通俗性以高度的重视,有利于促进戏曲的健康发展和提高戏曲的接受效果。其次,李渔处在昆曲兴盛时期。曾经产生于民间以曲文和音律的通俗性受到观众普遍欢迎的昆曲此时由于文人的参与出现了由质朴古拙趋向典雅绮丽、脱离现实、脱离群众的不良状况。文学上不顾内容一味追求词藻华美、曲文深奥;音乐上脱离内容片面追求曲调婉转缠绵,或者不分四声阴阳,讹念讹唱;这种现象严重危及昆曲的命运,损害了观众的欣赏接受。李渔崇尚曲文与音律的通俗性维护了昆曲内容与形式上的规范性、通俗性,对防止昆曲迅速脱离人民大众在舆论上起了积极作用。清代乾隆年间及其以后,由于各种原因,昆曲由于雅化逐步由停滞走向衰落,花部后来居上,这自然是李渔未曾预料的。但是,无论如何,李渔强调曲文与音律的通俗性,顺应了戏曲的发展主流,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有贡献的。最后,李渔崇尚戏曲题材通俗性的实绩从他的戏曲艺术实践中可见一斑。李渔为了使戏曲成为观众所嗜好、所喜悦的艺术,自觉地以日常生活中男女青年婚姻爱情之事为题材创作了十部传奇。以这些通俗题材为内容的戏曲有效地缩短了戏曲与观众之间的心理距离。当观众观看这些戏曲时,他们感到剧中的人和事颇为熟悉,好像发生在自己身边那样有一种似曾相识之感,因而对戏曲产生浓厚的兴趣,观剧热情陡然高涨。戏曲因此受到观众普遍青睐,迅速传播开来,久演不衰。李渔说:“所撰新词,及改前人诸旧剧,朝脱稿而暮登场”;【62】又说:“(《凰求凤》)此词脱稿未数月,不知何以浪传,遂至三千里外也。”【63】李渔的戏曲如此受观众的欢迎,接受效果如此之佳,除了曲文和音律的通俗性之外,不能不说其题材的通俗性是主要原因之一。郑振铎说:“(俗文学)其内容,不歌颂皇家,不抒写文人学士们的谈穷诉苦的心绪,不讲论国制朝章,她所讲的是民间的英雄,是民间少男少女的恋情,是民众所喜听的故事,是民间的大多数人的心情所寄托的。”【64】这其中的“民间少男少女的恋情”正是涵盖了李渔戏曲作品在题材上的通俗性的特点。李渔的戏曲在中国古代戏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李渔也无愧于中国古代通俗文学大家。
总而言之,无论是曲文还是音律,甚或是题材,李渔都要求它们具备通俗性的特质,以利于观众的欣赏接受,充分体现了李渔的艺术追求和审美理想。在反对“时文风”及其流弊和昆曲日趋雅化的时代背景下,李渔崇尚戏曲的通俗性,维护戏曲的本质,持论公允合理,反映了广大观众要求戏曲雅俗兼顾、雅不伤俗、雅不绝俗的审美趣味和接受意向。李渔这种坚持正确的艺术方向,不趋从流俗不盲目附庸典雅的艺术精神是值得后人称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