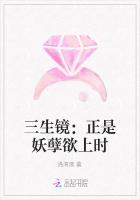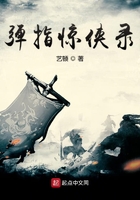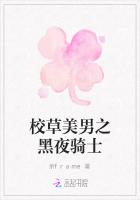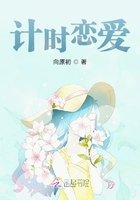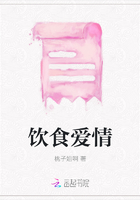不过,对于中国知识分子而言,这类的“疏忽”将伴随着资讯的爆炸式进程,变得数不胜数。有时,可能还会引发其中的一部分人,从原初的理性主义者的位置上产生精神逃逸,直至发生异变。
那要等到1990年代的到来。
《第二性》
西蒙娜·波伏娃以其在萨特身边重要的配角地位,引起读者的兴趣。《人都是要死的》《名士风流》《波伏娃回忆录》等相继被译成中文,但这其中,最体现波伏娃思想价值的还是《第二性》。中译名叫做《第二性——女人》。
从某种意义上说,《第二性——女人》代表了在1980年代被泽介过来的这样一批文化经典~一轰轰烈烈地出版和媒体介绍,平平淡淡的书店销售,最后,大批的存书流人城市各色新旧书摊。它们早早晚晚在人们的眼前闪烁,或者因为话题不够大众而被冷落,或者因为话题被误读为与某些敏感趣味有关,而底层人士以低价买走,翻过几页后便被失望的主人束之高阁。而它对人们在文化上那有限的启迪或滋养,则要等候漫长的岁月,才能被体现出来。《第二性》的主旨是为女人而探讨女人。从女性的社会属性——在人类漫长历史中所扮演的角色、所处的地位,到女性的性心理、女性解放……进行了全方位的论述和探究。对于关注波伏娃的读者而言,无论是否赞同作者在书中所提出的理念和观点,本书的建设性,可能都要远甚于波伏娃那些对存在主义的空洞论述,以及她那所有试图图解存在主义的“小说”。
不知道新世纪以后的内地女权倾向者、思想史或同性恋研究者,如何看待《第二性》的价值。反正现在许多国人自以为新鲜的“自创观点”,早在1949年问世、1986年登陆中国内地的《第二性——女人》(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中,已有足够前瞻和高级的论述了。有意思的是,这部显得前瞻和高级的中译本,才仅仅是对原著第二部的节译(同时期问世的另一个译本《女人是什么》也一样)。
一个不为人知、今天才有些弄清的背景是,直到2004年中国书籍出版社推出《第二性》的首个内地全译本,内地所有《第二性》的中译本都是根据美国诺福出版社的帕什利英译本转译的。可问题是当初这位译者帕什利先生不懂哲学和文学,他只是一位退休的动物学教授,法语还是在学生时代学的,所以全书错译、误译,甚至不懂装懂的硬译之处颇多,而且还有不少删节。据说当年波伏娃本人对此十分不满,甚至要求出版社印上此英译本与作者本人无关的声明(当然被出版社拒绝了)。二十年了,我们反复翻译出版的竟是一本原作者很不满的“伪书”,大约这除了证明我们某些研究的可笑之余,又会给人带来新的怪味感觉吧。
我相信,《第二性》绝不是我们读过的唯一一本这样的书。岁月只不过凑巧选中了它这只麻雀,通过解剖它来给求知者提个醒儿。
《日瓦戈医生》与《跨世纪抒情》
1985年,法国流行钢琴手理查德·克莱德曼的名字,伴随着一盘叫作《命运》的盒带来到中国,从此开启了他二十多年在远东市场的声誉。那盘《命运》里,有一首叫《拉拉主题变奏曲》,就是根据英国导演大卫·里恩执导的奥斯卡获奖电影《日瓦戈医生》的主题曲改编的。《拉拉主题变奏曲》也是中国大众第一次从广义的范围里接触到“日瓦戈”,不过那时大多数听众并不清楚这一层,更不知道一个叫帕斯捷尔纳克的作家。
其实帕斯捷尔纳克的名字,在这之前的几年就已经出现在了国内的出版物中。记得1980年代初,诗人邹荻帆主编过一本诗人译诗集《月照波心一颗珠》,里面收有乌兰汗(高莽)译的帕斯捷尔纳克诗作。还有一本《苏联当代诗选》,也对乌兰汗译的帕氏诗作有着零星收录。
《日瓦戈医生》较著名的两个中译版本应该都是出版于1987年前后的。分别是外国文学出版社蓝英年、张秉衡的译本,和漓江出版社力冈、冀刚的译本。从全部译文在叙事文与诗这两种文体的整体协调和把握上讲,前一个译本似乎更好一些,影响也更大。
“《日瓦戈医生》是反苏(联)的”——曾经有几十年的工夫,全世界几十年中对该小说这样定位,中国的宣传媒介当然也不例外。每个读者读小说前,恐怕都有一种好奇: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作家,是怎样赤手空拳反抗一个超级大国的。当然,这种强烈的好奇,最后只能带来失望,《日瓦戈医生》没有任何否定和干预超级大国国策的举措。它只写了几个边缘人在动荡年代聚散离合中匆忙的一生,最多只给人留下了“好人总是命运坎坷”的印象。
“艺术家与时代的格格不入”是作者真正要呈现的东西,是一个诗人超越时效的微言大义,但谁会像对待《论语》那样去做解读呢——只要它们还不够流行。
对于许多中国读者来说,像《日瓦戈医生》这样有点靠近半回忆录、半意识流性写法的小说,与他们以往印象中的俄苏小说大相径庭,乍读之下也并不觉得流畅。而作为全书最后一章、也是很关键一章的《尤里·日瓦戈的诗作》,与人们惯常见到的译诗差异更大,这也无形中增强了读者对小说的艰涩印象。应该说,人们还是更愿意接受大卫·里恩执导的同名电影,虽然对比原著,它只是一个影像精致、但却充斥着太多夸张的情感与冲突的媚俗版电影——是啊,小说太长了,也太晦涩,公众则永远只关心情节、冲突、爱情与结局;至于少数的知识分子,又仅仅把它作为自己妄断世界的工具,止步于对某些“情结”的阐释。
帕斯捷尔纳克的诗引起文学圈读者的初步注意,要等到1989年荀红军译的《跨世纪抒情——俄苏先锋派诗选》出版以后。苟译中关于帕斯捷尔纳克的诗歌,译得富有力度和跳跃性,很有感染力。不过在我看来,曾为诗人的译者也有可能在这过程中加入了太多的个人色彩。帕氏诗歌迄止到2000年以后,在汉语里都没有一个权威译本出现。已有的译本中,乌译本中的透明,荀译本的现代感,张秉衡在《日瓦戈医生》诗歌部分中的奇、险与韵律,还有力冈、吴笛后来在其所译帕氏个人诗集《含泪的圆舞曲》中表现出的朴实……这些结合起来,大约才能反映帕氏整体风格在其人生不同阶段的流变。
作为国内第一本介绍俄苏“白银时代”诗歌的选本,《跨世纪抒情》的意义当然绝不止于为人们带来了一个不一样且富有朝气的帕斯捷尔纳克,其对曼杰利施塔姆、茨维塔耶娃、谢维里亚宁等人的译介也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只是由于时间与当时社会环境,这种影响要到进入1990年代后,才有明确显现。
不管怎么说,《日瓦戈医生》与《跨世纪抒情》作为被小范围的精英阶层或日“知识阶层”接受的俄苏文学作品,在1980年代体现出某些共同的特点:一是较以往几十年中译介的“主流”俄苏文学,显得更带个人气质,也更有来自文学本身的锐利;二是这两本书,以及为数不多的其他同类作品(比如《大师和玛格丽特》《金蔷薇》《红帆》《白轮船》《渔王》以及蒲宁等人的作品),相对于当时蔚为风尚的欧美文学,更多地带有某种“暗流”色彩。它们享受着被一部分爱好者私密性质的爱戴,这种爱戴跟共和国几十年的译介历史或许依然有关,但更深刻的原因我认为来自千百年来,人们试图从文学中达成灵魂摆脱束缚的愿望。俄苏作家的作品,有时会给人以一种散发着酒精气息、带着镣铐挣扎下去的勇气——这种勇气,在中国人缔造的文化和文学里实在是太缺少了。
米兰·昆德拉很怀念坐在北师大数学楼前小凉亭畔,边看浅池里几朵孤零的睡莲,边捧读米兰·昆德拉、抚卷长叹的日子。不管是诗人球评家大仙嘴里的AC米兰·昆德拉,还是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昆德拉都是1980年代绕不过去的一个话题。
1987年8月和9月,作家出版社在“作家参考丛书”的名目下,接连推出了小说《为了告别的聚会》
和《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开始走人中国内地读者的视野。
1980年代刚被译介了两部长篇的米兰·昆德拉,跟1990年代被译介了五六部乃至全部作品的米兰·昆德拉,给人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前者显得另类、沉重,还有一丝灵动;后者则带有明显的风格复制意味,作家敲击生活琴键的力度也日渐轻柔,甚至有点趋于无力……在1987年或者1988年阅读《为了告别的聚会》与《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你绝难以想象它们在将来的某个时日,会成为翻译小说里的畅销书(与其命运类似的是《挪威的森林》)。虽然两本书的卖点是性爱和政治,但有头脑的读者都能看出,它们最大的特点,是描写了一种我们既陌生又似曾相识的“人的生存”与“世事的无常”。从这个角度上,昆德拉完全可以被看作是一位“存在作家”(至于是不是构成“主义”,则是可以讨论的话题)。
两本小说以《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名气为盛,实际它也是昆氏所有作品中名头最响的,“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这本是小说后面所附的一篇昆德拉的获奖演说题目,但它很快就变成了一个滥俗的标题句式,充斥到了从文科论文到媒体评论等形形色色的文体里。由此也可以想见小说的“深人人心”。“性爱和政治”自然是首要原因,被导演菲利浦·考夫曼改编成同名电影(丹尼尔·刘易斯和朱丽叶·比诺什主演),更扩大了书的影响力。虽然考夫曼的电影版改编,与原著气韵大相径庭。
我个人倒以为《为了告别的聚会》是昆氏长篇小说中水准最高的。它减少了惯常在昆氏小说中所出现的那些偏于理性的内心分析和枯燥的命题性探讨,而保留了昆德拉小说里特有的残酷的幽默和某种无常感。克利玛和茹泽娜,雅库布和奥尔加,以及巴特里弗、斯克雷托这些人,要较托马斯、弗兰茨、特丽莎、萨宾娜那一组符号化的人物,更具备某种生活的润泽感。米兰·昆德拉写小说,对笔下人物的控制力太强,这既构成了昆氏小说的特色,也阻碍了他超越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欧美小说所普遍存在的“理性病”。
而长篇小说《为了告别的聚会》和短篇小说集《可笑的爱》,在昆氏小说里,是这方面程度最轻的。
据说李欧梵教授曾在1980年代中期米兰·昆德拉作品尚未被译介的时候,就曾将其和加西亚·马尔克斯并列,视为将给中‘国文学带来巨大影响妁小说家,可谓有先见之明。不过,李教授只预见对了一半:与马尔克斯明显影响了莫言、张炜、韩少功等当代小说家不同,昆德拉除了后来在市场上赢得了巨大成功外,对内地小说的创作影响实际有限。毫无疑问,昆德拉的小说是一种智性小说。
可奇怪的是,在喜欢这种小说的内地作家中,并没有因此衍生出几个与昆氏具备同类型思维的个性作者。知名小说家中只有曾出任张艺谋电影《有话好好说》编剧的述平,形式上带有一些昆氏印迹。
还是让我们回到1980年代后期:那时候的米兰·昆德拉小说,虽然已被公开翻译出版,但读它们的人却或多或少还能从中体会到某种阅读禁书的快感。人们也还对这位来自法国的捷克流亡者怀有一丝审慎和疑惑,而不是像几年之后那样——进入到一种知识界的顶礼膜拜,或索性是膜拜后的性情逆反。
《布赖顿硬糖》
关于1980年代的读物,我最后的记忆是《布赖顿硬糖》。它显然不是那个年代人手传阅的译作,比如《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比如《百年孤独》、《日瓦戈医生》……那么,是什么使我记住了《布赖顿硬糖》?打从最早知道书名,到当时初读、再到今天重读,我都觉得它跟我和大家一起回望的这十一年(1980~1990),尤其是最后那两年,有着一种难以言传的联系或隐喻。
《布赖顿硬糖》是20世纪后半叶英国首席作家格雷厄姆·格林的长篇。1989年,由浙江文艺出版社推出它在内地的第一个中译本(姚锦清翻译)。格林在这本小说里,讲了一个英国海滨城市中不良少年沦为恶棍、并最后覆亡的故事。主人公宾基是一个只有十七岁的小混混。他所在的那个小团伙刚刚被人灭了老大,群贼无首,地盘也开始被别的团体瓜分,宾基一门心思给老大报仇,重振团伙声势。他和同伙杀了与老大之死有密切关系的海尔,接下来却陷入了销毁罪证所带来的多米诺骨牌式烦恼。为此,他向一个目击线索的十五岁的女招待罗斯献殷勤,试图以恋爱、结婚堵住对方的嘴,可他又非常讨厌和女人进行性接触;他杀同伙,拉来一个律师作伪证,然后再动员律师去国外旅行;与此同时,一个一厢情愿自认为是海尔红颜知己的过气歌女艾达,因为好奇海尔之死,开始了无休止的私下调查:她跟踪宾基一伙,也跟踪罗斯,这加剧了宾基的紧张,他试图骗罗斯殉情自杀,来掐断艾达和警方的最后线索,终因艾达和警察的到来而失败。宾基与警察在搏斗中被自带的硫酸烧坏,坠人悬崖下的大海。宾基死后,罗斯去教堂见了神父,她希望宾基能给她留下一个孩子,她将把孩子养大成人,并像神父建议的那样,“培养成一个圣徒——为他的父亲祈祷”。
从文学角度上讲,《布赖顿硬糖》大概是整个1980年代第一本出现在读者眼前的以“流氓”为主人公的小说(备受争议的王朔小说,与格林的主人公相比,不过是一些俗脸过于突出的假流氓罢了)。格林在这本小说中宣示了他文笔中那种“冷酷的流畅”。这种笔触在当时的翻译作品中极其罕见,比如他这样写宾基:“一回想起自己已经干掉那个人,而这般自作聪明的雷子却还没有聪明到能搞清真相的地步,他就把瘦小的肩头猛地向后一摆。他身后拖曳着一团体现他自身光荣的云雾——他在襁褓中就跟地狱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准备迎接更多的死亡。”底层少年出人头地的欲念,荷尔蒙所催生的愤怒,恶是怎样从小到大一点点地滋生……格林都以纪录片甚至外科手术般的精确予以不动声色的呈现。人是复杂的,社会邪恶的生长也是复杂的,格林在描写这些时表现出了文学家应有的对生活原生态的尊重与提炼。他甚至也没有因为自己的天主教背景,在小说结尾给幸存者罗斯留一道善意而微茫的天光,而是以这样的一句结尾,颠覆了书中神父的劝喻:“在这六月的微弱阳光下,罗斯疾步走向那世上最不堪忍受的恐怖”。作为读者,我要说,这“恐怖”不仅仅拘谨于小说中的英国海滨,它来自全人类各时代生活的本相。格林的这种充满着生活肉身气息的超迈,也正是内地1980年代所有作家们所不曾具备的。
《布赖顿硬糖》中译本的面世,只是1980年代内地文化启蒙大潮于众多无意间结出的一个小小果实。但这果实预告并预言了内地文化下一个“冷酷时代”的来临:所有关于欲望、生存、市场、情感、人文,甚至文学与艺术家的境遇,此后都将进入到一个镀金的“冷处理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