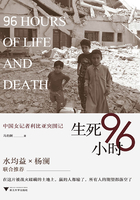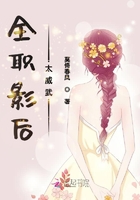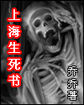前文说到,萧也牧是从秦兆阳那里得知《青春之歌》落到了人文社的。而在此之前的几年中,他因挨批判而骤然从文坛消失,致使秦兆阳竟不知他已调到中青社当文学编辑了。他之所以和秦兆阳断了联系,当然是因为那篇挨批的小说《我们夫妇之间》是经秦兆阳之手而发表的,怕招来搞黑串联的罪名,而如今他壮着胆子又去找秦兆阳,也正是为了《我们夫妇之间》,他敏锐地感到政治气候似乎有了变化,该是为它遭受批判鸣不平的时候了。
关于那时的政治气候,著名学者费孝通当年是这样描述的:
陡年来,经过了狂风暴雨般的运动,受到了多次社会主义胜利高潮的感染,加上日积月累的学习,知识分子原本已起了变化。去年一月,周总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像春雷般起了惊蛰作用,接着百家争鸣的和风一吹,知识分子的积极因素应时而动了起来。但是对一般老知识分子来说,现在好像还是早春天气。他们的生气正在冒着,但还有一点腼腆,自信力不那么强,顾虑似乎不少。早春天气,未免乍寒乍暖,这原是最难将息的时节。逼近一看,问题还是不少的。当然,问题总是有的,但目前的问题毕竟和过去的不同了。(1957年3月24日《人民日报》)
可以说,费孝通的这番话,表达了广大知识分子的心声。而作为一个作家和文学编辑,萧也牧此时也还有更深切、具体的感受。那就是对文艺创作中的公式化倾向和文艺批评中的粗暴、武断和专横风气,他和绝多数作家、艺术家一样,早已不满。1956年初,这种不满借着苏联“解冻文学”之风,为中国文艺界冲击教条主义樊篱提供了一个契机。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苏联文艺界发生任何一件重大事件,都曾在中国文艺界产生反响。斯大林逝世后,一批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受到迫害的苏联作家被“平反”和恢复名誉,尤其是1954年召开的苏联第二次作家代表大会对文艺的行政命令、官僚主义,文学创作的模式化和“虚假”作风提出了质疑。苏联《共产党人》杂志1955年第18期发表了题为《关于文学艺术中的典型问题》的专论,对斯大林时期的文艺思想提出了挑战,特别是对马林科夫在苏共十九大上的有关说法提出批评。1956年2月,《人民日报》、《文艺报》全文发表了这篇专论,随后,中国作协创作委员会理论批评组就这篇专论和“典型问题”展开了讨论。专论所批评的现象与中国存在的问题如出一辙,很自然地在中国文艺界引起了强烈的共鸣,一批“干预生活”的作品,如刘宾雁的《在桥梁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耿简(即柳溪)的《爬在旗杆上的人》在国刊《人民文学》上发表了。此后不久,即1956年5月26日,陆定一在怀仁堂向科学界和文艺界的代表人物作了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6月13日,《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了这篇长达一万五千字的报告。这是中宣部长代表中央所作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一篇报告。这篇报告一开始就说:“中国共产党对文艺工作主张百花齐放,对科学工作主张百家争鸣,这已经由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宣布过了。”“双百”方针提出以后,在中国作协的多次会议上,茅盾、周扬、老舍、冯雪峰、吴组缃、臧克家、严文井、康濯、秦兆阳等纷纷发表意见,指出近几年来文艺工作中的弊病:作品题材范围狭窄、单调,创作风格不够多样化,文艺批评缺乏自由讨论的风气……并一致期望在艺术创作上和学术探讨上提倡独立思考,鼓励不同流派、不同风格的发展。
就在这样的“乍暖还寒”的“早春”时节,萧也牧联想到1951年《文艺报》对他小说《我们夫妇之间》的批判,便写了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有感》的文章,送给了已是主持《人民文学》常务的副主编的秦兆阳。萧也牧之所以把他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有感》先送给秦兆阳给看,不仅是因为秦兆阳当年《我们夫妇之间》的责编,而且更在于他佩服秦兆阳的胆识,敢于最先打起“干预生活”的旗帜,亲手编发了刘宾雁的《在桥梁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和耿简的《爬在旗杆上的人》,并在亲加的编者按中称:“我们期待这样尖锐提出问题的批评性和讽刺性的特写已经很久了……”
据秦兆阳回忆,自《我们夫妇之间》遭批判后,直到1956年夏天,他跟萧也牧只接触过三次。一次是萧也牧来约他为新创办的《红旗飘飘》丛刊写稿。第二次是来让他看《红旗谱》的原稿,让他提供一点参考性的意见。两次接触中他都没有问过萧也牧对受批判的感想和看法,以及批判对其处境有什么影响。秦兆阳说:“虽然我在暗暗为他难受。为什么不问?也许是不愿意触及他的内心的伤疤,但更主要的是他那坦率真诚的态度一如既往,向我约稿时那么耐心,请我看稿时那么诚恳,好像并没发生过对他有什么影响的大事。”第三次--1956年夏天,就是给他送来了这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有感》。秦兆阳也果然是萧也牧的真知音,看完此文后就极力赞赏:“感得好!”或可以说,他期待这样的文章也已经很久了。
萧也牧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有感》,有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诚恳地承认过去那次批判对他有益的一面;二是说了一些他被批判以后到处难以见人的情况;三是由此提出建议:文学评论不要把自己人当做敌人来打,要采取与人为善的态度。秦兆阳感到有关第二个方面的内容,写出的比他当面谈到的要少,就问他:“是不是对遭遇和建议说得不够?为了有益于改变文学批评的风气,是否可以作点修改?”他同意秦兆阳的意见,说:“由你全权处理。”于是秦兆阳替他作了一些修补,发表在1956年9月号的《人民文学》上。
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有感》中,萧也牧在回顾《文艺报》对他小说《我们夫妇之间》的批判情况时,着重提到了那封编者认为“很好”的“读者来信”,把他比作“要踢它一脚”的“癞皮狗”,在思想品质上、阶级成分上,政治上作了全面的鉴定和判决。然后他这样写道:
陆定一同志说:“批评有两种。一种是对敌人的批评,所谓‘一棍子打死’的批评,或打击式的批评。另一种是对好人的批评,这是善意的同志式的批评,是由团结出发,经过斗争,来达到团结的目的的。这种批评,必须顾全大局,采取多说道理,与人为善的态度,而不能用《阿Q正传》中假洋鬼子的‘不准革命’的态度。”以上所说的那种对我几篇作品的批评,我以为多少有点对待敌人的“一棍子打死”的味道的。这主要的倒不在于批评的当时给被批评者的刺激,主要的是在于它所产生的更广泛更深刻的后果--它在社会上所形成的一种空气,使被批评者再也不能“复活”,并且给与了其他作者造成了一种无形的威胁。
接着,他例举了一大批编剧、导演、演员以至业余的工人作者因受他牵连而纷纷遭受批判,“坚决与萧也牧划清思想界限”的情况,忿忿不平地问:(我)“写了这两三篇有错误的小说,它给整个文艺事业带来的危害,是不是当真那么严重,需要展开那样严重的斗争呢?”他还指出:“当时在某些人中间,批评萧也牧似乎成了一时的风尚,连某文学史家都认为我的作品中的错误有写进文学史的必要,把一些批评我的作品的文章连同我的检讨,经过剪裁,放到他所著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中去了。重庆的一位文学教授,在他所编的一部讲义中,竟然把我的为人(不知他从哪里收集来的材料)以及关于我的作品中所犯的错误,整整写了一章。”
事情才过去短短几年,这两位教授就迫不及待把对萧也牧的批判写进了文学史,足见这场运动所造成的影响有多恶劣!如果单是写对他作品的批判倒也罢了,可偏偏还写了他的为人,这岂不是罗织罪名,有意整人吗?在这样的舆论环境下,他就不可避免地遭受到了种种难以忍受的歧视。让我们来听听他的倾诉吧--
我原先是全国文协的会员,当时文艺界有什么活动,总是通知我去参加的,就连春节联欢一类的活动,也没有把我忘记。自从我的几篇小说受到批评以后,直到前半个月为止,文艺界的一切活动都不要我去参加了。我也就失去了种种学习的机会。当我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我得不到文艺界的任何帮助。
我的几篇作品受到批评的第三年,组织上分配我到一个出版社去担任现代文学编辑。作为一个编辑当然要对自己所处理的稿件直率地提出自己的意见,所提的意见也不一定正确,但编者作者之间可以商量,也可以争论,这是常识范围以内的事。可是在一小部分作者的眼里,似乎因为我写过几篇有错误的小说,受过《文艺报》那样严重的批评,因而我对旁人作品的意见,也必然是错误无疑的了。冷嘲热讽者有之,没等我把话说完,拂袖而走者有之。作为一个编辑,当然要和作家们作广泛的接触,当然要向作家们组织稿件。然而这也遇到了种种出乎意外的困难,在这里我不想一一细说了。为了工作的方便,每逢我出去进行组稿活动的时候,我是不用“萧也牧”这个名字的。然而这也不行,据说这是萧也牧经不起批判,连真实姓名都不敢用了。甚至,我到某些从未到过的机关去有事情,会客单上填的是我的真名而非萧也牧,不知怎么竟也有人知道,会客室的窗户外边竟会出现了许多好奇的、含有轻蔑神气的眼睛,和“萧也牧、萧也牧”的声音。
当然,其所以形成这种情况,一方面也是因为我的作品的错误,但恐怕也不能完全归到我的错误上去吧?因为,在我们这个社会里,一个人在某种事业上犯了错误,并有决心改正,人们是不会永远不能原谅他的。这,即使是对于文学作者,也是不例外的。只有当一个人坏到成了“林语堂”、“癞皮狗”和“敌对阶级”时,人们才决不会原谅和信任他了。这种批评所形成的这种空气,想来也是当年批评我的同志们始料所不及的。这不能怪一般人之不会评判批评是否恰当,而只能怪批评本身是否恰当。
句句是真,字字有力,令人动容。最后,他说出了憋在心里整整5年的话:“批评要恰如其分,要讲究分寸,不要把他的错误提高到不应有的高度,更不要把‘莫须有’的罪名加上他的头上,不要污蔑他的人格。”正如秦兆阳当年所说,他感得多好啊!
在这一期《人民文学》上,还刊登了经秦兆阳修改的王蒙的成名作《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当年在《人民文学》工作的资深编辑涂光群在《求索的苦果》一文中曾这样回忆:“1955年12月,秦兆阳受命重返《人民文学》,任副主编,主持该刊编政。《人民文学》杂志的面貌很快发生了变化。秦兆阳以自己的编辑思想,统一全编辑部的思想。他在编辑部内宣布,要将《人民文学》办成像俄国19世纪《现代人》那样有影响的第一流刊物,要有自己的理论主张,要不断推出新人新作。《人民文学》的版面明显地加强了党组领导人所期望的群众性、战斗性,刊物的发行份数一年内由十余万份跃至近二十万份。秦兆阳也被吸收进作协党组,成为新成员。历史地看,秦兆阳主持编政的1956-1957年,是《人民文学》最好的时期之一,这也是读者公认的。”(《中国三代似作家纪实》第353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5年出版)而正值这样秦兆阳在文学编辑工作中实践他的创造性思维的黄金时段,他编发了萧也牧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有感》,表明他与萧也牧在对“双百”方针的理解和有关的重大文艺理论问题上,是一拍即合、志同道合的。这就难怪他说,若是早知萧也牧调到了中青社,就把《青春之歌》转给萧也牧了。
其实,在秦兆阳将《青春之歌》推荐给作家出版社后,因纸张供应短缺,直到1957年1月,也未能将《青春之歌》列入当年的出版计划。为此杨沫心中不快,便又去找了秦兆阳,询问既然缺纸,可不可以少印一点,先把书弄出来呢?秦兆阳说:“情况确实如此,赶到了这个时候,谁也无能为力。《人民文学》每期19万都不够卖,可现在因缺乏纸张,每期要少印3万册。”而萧也牧闻讯后,立即表示,他完全有办法解决纸张问题。他先托海默告诉杨沫,如果作家出版社不出杨沫的稿子,中青社有能力出。几天后,柳溪去找他谈书稿时,他又请柳溪转告杨沫:“要和作家出版社谈好、砸死,如果他们不出,我们出!”这表明,在他的心目中,秦兆阳是一个既懂理论又有创作经验的编辑大家,对《青春之歌》思想和艺术质量的判断,是充分信任的。他是多么希望这朵香花早日在文艺的百花园里开放啊!
杨沫当时心里也很清楚,人文社之所以对《青春之歌》大放绿灯,其主要原因是赶上了政治气候的“清朗”时期。正如她在6月28日的日记中所说:“看起来,什么都是一阵风。现在是赶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机上了,否则这小说的命运还不知如何呢?”(《杨沫文集》第6卷,第253页)1958年1月,难产的《青春之歌》终于出版了。北影很快将它搬上了银幕,周恩来总理看了片子,大为赞赏。一下子,《青春之歌》和杨沫都红了。杨沫不仅成了单位的先进工作者,还成了全国人大代表,继而从北影调到北京市作协,成了专业作家。功成名就的杨沫在1959年12月22日的日记中不禁感叹:“人生的际遇,变化无常。随着社会的需要、机遇,和人们的认识,一个庸人可以变成英豪,一个英豪也许成了庸人。陈学昭的小说《工作着是美丽的》,萧也牧的小说《我们夫妇之间》,刚一出版就被打回去了。而我呢,则万般幸运……同是写知识分子的作品,而遭遇却大不相同。天命乎?人意乎?看来,际遇该是何等的重要!”(《杨沫文集》第6卷,第359页?)后来的历史证明,《青春之歌》是一部在当代文学史占有重要地位的优秀长篇小说,秦兆阳、萧也牧是培植这朵文艺香花的好园丁。可是,就在《青春之歌》出版后不久,秦兆阳、萧也牧相继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开除了党籍。他俩受难之时,正是《青春之歌》炙手可热之日,千千万万的读者,根本不知道、也不可能相信他俩为《青春之歌》的出版所起的巨大作用和不可磨灭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