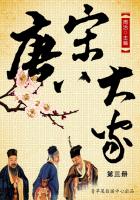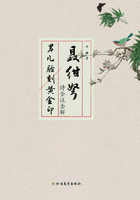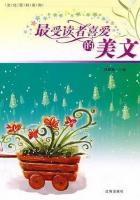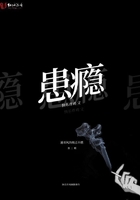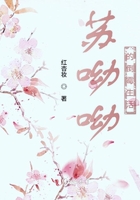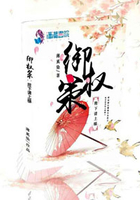(一)媒体在九十年代
张:媒体的问题是与我们前面谈的种种问题紧密相关的。它既是市民社会与国家交互作用的“场”,又是消费化、商品化的纽带,又是全球化的发展的一个结果。媒体在我们的日常经验之中也是相当重要的,我们每个人的家里至少都有一台电视机。至于报纸,像街头摊上的小报等也有了空前的繁荣。媒体的影响力的扩大也的确让人震惊,这里面有一些基本的对媒体的看法,一种是“压抑论”,认为媒体导致了人们对自己的真实的要求的误认,因而是一种完全负面的东西。这种看法好像是相当流行的。但在具体分析上也有不同的方法和策略,海外的研究者强调政治性的东西多一点,往往还是将中国内地的媒体视为一种平面的宣传工具。而本土的学者则往往强调经济因素,强调商业化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或是导致了文化的低俗化等等。这里面其实有许多问题值得更切实、更仔细地加以讨论,而不是仓促下结论。这样才能得到较为明澈的认知。
我觉得对于“媒体”的理解中,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对“大众”和“大众文化”的看法。我们以往的文化思路中是没有“大众”的,只有一个极为神圣、极为超验的“人民”的概念,往往我们连起来说“人民大众”,但却只是关注一个永恒的历史主体——人民。这个“人民”是非常崇高和理想的,它也不是指某一个具体的人,而是从根本上超出了具体的人。“人民”是十分抽象的概念。这让我想到有关“文革”的一个笑话,一个人去买东西,售货员对他态度不好。他很生气,念出了语录:“为人民服务。”可售货员来得也很快,说:“我为人民服务,不是为你服务。”这里因为人民是历史主体的象征,一个个人不足以承载这么大的概念,所以他也无话可说。这里还有个事值得一说,就是《大众电影》杂志,50年代、60年代一直叫这个名字,可是70年代后期复刊时却叫《人民电影》,到了1979年以后才改回到《大众电影》。你可以发现这里面用词看起来差不多,还是有很微妙的差异的。“人民”是比较抽象,比较高的,而“大众”则是比较世俗的,比较低的。在中文中这两个词之间的意义的差别还是很耐琢磨的。我的想法是“新时期”虽然追求崇高,追求总体性地解决一切问题,但它是承认与“人民”有区别的“大众”的存在的。实际上离开了世俗的“大众”,“人民”又何在呢?从1979年以来,媒体崛起了,它与商业化是联起来的。1979年中国电视里播出了第一条广告,还有1978年底中央电视台播出了《望乡》、《追捕》等几个日本电影。我还很清楚地记得我当时还是一个中学生,坐在邻居家的一台九英寸的电视机前面,看这些电影时的兴奋的心情。巴金的《随想录》的第一篇都是为“大众文化”的出现辩护的,题目就是《谈〈望乡〉》,回击了一些保守的人的看法。当时对于“大众”的多样的需求通过媒体的发展来得到满足这一点,好像是没有任何疑义的。以至于把这几部同时在影院里刚刚放映的首轮电影拿到电视这种媒体来上映。这一方面说明那时电视还不足以威胁电影院线的生存,它本身还不够普及;但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大家对于媒体发展的巨大热情。所以七八十年代好像人们对媒体的看法还不是相当消极的。你作为一个与整个“新时期”同步走过来的作家,不知对于媒体的这种发展有何看法?
刘:我觉得媒体是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兴起的。它在70年代末、80年代都有一个与改革开放相联系的背景。
张:我还记得1979年3月,邓小平访美时,电视里演了一些美国节目的实况转播。当时看着的确非常新鲜。
刘:我觉得你举出的许多现象之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这从70年代末就形成了,而且一直保持到了今天,这就是国家媒体内部也有了一些有差异的声音。这在五六十年代是根本不可能的。过去我们一看就看“两报一刊”,这是领导、中央的声音,声音是完全一致、完全统一的。但现在这些年的情况是有变化的。《红旗》杂志已逐渐分流出去了,它已经变为了《求是》,虽还有一定的影响,但已难以从其中了解当下国家意识形态运作的内容了。甚至还出现了像《中流》、《真理的追求》、《当代思潮》之类的刊物。它持有一种和主流不同的声音,有时甚至公开和主流思想争论,也是和主流的社会文化思路争论。我觉得这种情况民间往往是不太重视的,但它的意义也不应该忽视。它喻示了一个过去的传统的社会模式中所没有的一些东西。从这么一种很特殊的国家内部的差异性的存在中,也可以看出中国当下的社会选择的独特性。这是相当有趣的。这种和当前的思想、社会发展方向不尽一致,在党内,或在用党的经费办的报刊上发出有差异的声音,让人觉得是提供了新的东西。我觉得这种现象是我们思考媒体时,绝不能忽略的。
回到你刚才说的那个问题上,我们如果从你说的角度再往下分析的话,我们可以发现,媒体的确是有了极大的变化,原来的媒体无论是一份晚报,或是一台晚会综艺节目,一般要主要反映党的方针政策,或是宣传一种精神。现在的变化可以从下面几个方面来看。
一个就是广告现象,现在广告几乎弥漫于各种媒体之中。即使是很大的报纸也刊出几乎整版的广告。这些广告宣传的都是一种过去严格拒绝的生活方式和文化趣味。甚至有不少都采用了在过去的意识形态之中是被否定和批判的东西,诸如什么富豪、贵族、帝王等等。这些似乎都是对敌人的称谓。可如今这些都变成了生活消费的一种时尚。甚至国家的报纸、电视台中也都有大量的广告。这在国外也是不多见的,如我在瑞典时,发现他们的官方电视台里根本就不播广告。那里有商业电视台,才以播广告为主。我们这里中央电视台却是最大的广告经营者。这说明广告的确表现了中国媒体的转型。我在上海的许多地方看了一种大的显示屏,上海这种显示屏比北京多得多。这种显示屏上不断地在播放许多的广告,当然其间也有些是新闻或口号之类的穿插,但时间是比较少的。我看到人民广场上的那块显示屏上有各式各样的广告,这个广场的名字也很有趣,正好合乎你刚才的分析。而东方明珠电视塔边的大屏幕,也是充满了广告的。这恐怕也是世界上自有社会主义国家以来,最为独特,恐怕还没有过的现象。这恐怕也是文化人的许多焦虑产生的原因,以至于我有时候也提问,能这么做么?这么做合适么?
另一个很明显的事情是许多报纸走的都是市民化的路子。各省市除了那份主要报纸国家仍给予充足的补贴;或是由于它传统上的发行量相当大,广告收入很多,不需要做什么变动,就能维持运转;但其他报纸都不能不走市场的路子,不能不适应大众文化的趣味。这种现象在广东的报纸中尤其多。不少新创刊的报纸,只是拿到一个号,有一个主管单位,其他的运作都是在市场中自己发展的。像《南方周末》、《羊城晚报》都还是大报格局,跟我联系的还有《粤港信息日报》、《粤港企业家报》等等。各色报纸就在广州这么一个地方林林总总地存在、发展。深圳是个弹丸之地,但和我联系的报纸就有《深圳特区报》、《深圳晚报》、《金融早报》、《开放日报》等等。这么多报纸都是有合法的登记证号的。像惠州有一个报叫《现代生活报》,这个报就是一个外地女士,做生意发了财,就办了一份报纸,给一些文化人、知名人士寄赠。这些报纸的民间色彩是相当浓的。现在有一个现象是很有趣的,本来新闻出版署宣布再也不批准增加新的报刊了,但我几乎每个月都能收到一份新创刊的刊物或报纸的约稿信。这些报纸、刊物几乎都登记成功了,这些报刊实际上并不真的属于一个党政机关,虽然它可能挂靠在某个机关,找到一个刊号之后,它就可以运作。实际上,可能它里面的编辑和工作人员都是些没有正式编制的人。另一方面,它如果在法律法规的限制之内活动,几乎就没有任何行政性的干预,其可供运作的空间是极大的。不但可能是我们国家没有过这样大的自由度,恐怕也是原来的社会主义国家或是许多第三世界国家难以做到的。第三个方面是它的赢利目的,商业色彩非常浓,正因为它不商业化就没法存在,所以不能不制造许多颇有耸动性的话题,有时是没事找事。由于他们这些报纸非常活跃,抢占了不少地盘,导致了不少国家报纸,那些不太重要的国家报纸,由于编辑人员相对年轻,管理也不那么严格,这些报纸也往往趋于离心化。像《北京青年报》,它确实是北京团市委的机关报,但它却采取了相当特殊的方式,采用了很明确的市场的导向。从版式的设计,到标题的安排都有它的独到之处,有时候甚或超规范地“抢新闻”。这些报纸一定程度上也是那种社会填充物,是所谓“摊报摊刊”,它的编辑记者也往往采用合同制、临时聘用等办法雇用,所以其走向必然受这种状况的制约。这就决定它一定要包装好。它们还有一个方面的特点,也就是这些刊物追求与国际接轨,还标榜它是国际发行。它很希望超出自己特定的意识形态的特点,做得很国际化。
(二)媒体、知识分子、大众
刘:这些传媒景观确实很芜乱,很复杂,很难界定,很难弄清,它会造成很多种面向的效应。但总的来说它还是充满活力的,文化人对它还是不能采取一种消灭的、敌视的态度,而是必须直接面对这种现状,作出分析阐释,不能把“大众”视为仇敌。目前的“文化冒险主义”,恐怕就是对文化领域的一些这样的现象,十分恐惧和激愤,导致了极端主义的诉求,要在文化领域中进行一种“清扫”运动。这样的事情我们这几十年来的教训实在是已经很深了。诸如胡风集团,显然是认为不够清洁因而要清扫掉,到了反“右派”时一下子有几十万人被宣判为不清洁,也清扫掉了。但这以后又发觉像邵荃麟这样的原来反右斗争中没问题的人也仍然不清洁,居然主张“中间人物论”,也要扫掉。到了“文化大革命”,不清洁的人那就已经成千成万了。像周扬这样领导文艺界,做过许多批判的工作的人,在姚文元一类人看来也仍然不清洁,于是《反革命两面派周扬》这样的文章就成了战斗的檄文。这样高举“清洁”的旗帜,最后当然是“成果累累”。清洁到最后,诸如什么《创业史》、《红旗谱》、《青春之歌》这样很革命的作品也不清洁,像赵树理这样的以农民语言写作、最为深入民间的作家也不清洁。所以高举清洁的旗帜,横扫千军,可谓是痛快淋漓,不过这里的界限和限度问题却是无法确定的,只有这么无限地清洁下去了。其实连毛泽东这样极具理想精神的人物都反复强调“水至清则无鱼”,强调“人无完人”,更何况今天高举“清洁”口号的了,最后只能变成奥姆真理教式的向普通人宣战,进行肉体消灭了。所以“清洁”的旗帜本身是有相当的消极性的。我们也一定要对此保持一些清醒的、仔细的分析。
张:你的分析相当清晰,讲得很透了。实际上有些文化冒险主义者,也是生活在媒体之中,如在充满着他认定有不洁的气息的广告的报纸上接受采访。像张承志有些提法的确是非常之可笑的。如他有一篇文章名为《撕名片的方法》就要撕掉所有的名片,拒绝与俗世俗人打交道,但却又不断在俗世的报纸、杂志上发文章。当然有人就写杂文挖苦了,问他为什么既然已撕掉了所有名片,不和俗人交往了,却又能准确无误地将文章寄发到大杂志的编辑那里?这的确相当可笑。这些人的尴尬处境在于,他们既要反对、彻底否定媒体的作用和功能,但又不能不处于媒体之中,不能不依靠媒体来自我宣传,这就使得他们进入了难以摆脱的困境。当然这也有它可以理解的一面,也就是体现、反映了一部分知识分子难以进入市场化的社会进程,也对于这种进程提不出任何有力的解释,产生了很大的焦虑。他们对于传媒的仇恨恐怕还是来源于解释失灵的精神的震荡的结果。这个困境如果没有改变,这种文化冒险的思路恐怕很难消除掉。
刘:他们有一种说法,把目前的许多文化现象均称之为“泡沫”,认定这些泡沫是极其有害的。他们要求写出作品就要伟大,一办刊物即求不朽。这种高见高则高矣,却也是并无道理的。其实“泡沫”也要作具体分析,没有“泡沫”,也不会有伟大的作品。“泡沫”的出现,是活水在流动的标志,是生机和活力的标志。我想“泡沫”的确是转瞬即逝的东西,但它却装点了一个时代的文化,也还是有它自己的价值的。而且有些甚至当时被视为“泡沫”的,后世也许会有不同的看法。像《红楼梦》,也并非是绝对的清洁之作,里面也有诸如贾宝玉与秦钟的关系之类的描写,也在当时以诗词为高雅文学的时代里用的是一种相当通俗的形式,而它的意义却是“五四”以后才为人们所深识的。由此看来,对于“泡沫”恐怕也不能笼而统之,远远一望就加以清扫,所以媒体的问题要复杂得多。
张:我还有一个想法,目前还出现了一批不可忽略的大型的文化、文学类的刊物,被记者们称之为“白领丽刊”的,像《东方》、《大家》、《战略与管理》、《上海文化》等等。还有我们几个朋友办起来的《今日先锋》。这些刊物里有一些是由政府资助的,但更多的却是由民间的力量进行运作的。这些刊物都相当精美,其定位也是文化性、思想性的探讨,或是纯文学的刊物。这也是在市民社会中发展出来的,得到国家的认可的刊物。它们探讨的问题都是大文化的,其关切也相当高层次,而且销售也日渐看好。这种新的媒体也只有在这个市场化的时代里才可能出现。如果没有今天这样一个文化市场,我们就会只有《求是》,不会有《东方》。而现在我们既有《求是》又有《东方》,情况就非常有趣。像《读书》杂志,它定位非常明确,这些年来也在非常平稳地增加销售量。它可以说是很清楚地成为知识阶层的刊物,提供新的知识视界,一定程度上也反映知识阶层的一些利益的和情感的诉求。这个刊物却越办越成功,几乎成了当下文化中的一个很独特的现象。所以随着市场化的成长,一个相对收入较高,有很好的文化素养的白领阶层也在形成之中。他们对于文化是有关切和了解的,他们的存在也是市场的发育日渐成熟的结果。市场化固然造成了比较俗的文化的扩张,但也为雅俗分流、雅文化本身的自我发展创造了条件。过去雅俗文化是一锅煮,没有比较清晰的差别和界定。读书看戏大家都是欣赏同一些东西,这些东西究竟是雅是俗也不清楚,所以产生了雅文化极为发达的印象。其实五六十年代的文化里究竟什么算是“雅”的,什么算是“俗”的,是极难区分的。那时的文化与计划体制的一体化的管理是同构的。但现在是雅俗的分流比较清楚,多样化为人们创造了不同的文化空间,人们可以在其中比较明确地进行选择。同时这种市场化,也使得国家更明确地支持和扶助高雅艺术,国家开始将自己的有限的资源投入高雅艺术之中。过去的大众化、通俗化的诉求反而由市场自身来实现了。过去多少年要求作家下去,要求喜闻乐见,但似乎总是成效不彰,以致有一种强烈的“大众化”焦虑,如认定中宣部是“阎王殿”,其原因出于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之类在占领舞台,工农兵不够多。但现在许多年达不到的目标却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下悄然达到了。当然目前文化市场中问题仍然不少,但却毕竟建立了较为有效的机制,都已达到了国家不必再强调大众化的程度,足见市场本身的力量。原来在五六十年代或70年代前期,一直在被批判、被否定的“大、洋、古”,几十年没有被政治的声浪弄垮,但在市场中却反而风雨飘摇了。不过分流之后,这种雅文化的自身运作也进一步规范化了。国家对它的支持创造了一个稳定的、规范的自身运作的“高雅艺术”,像交响乐芭蕾舞等等都是这样依赖国家的支持。现在这些都有相当大的资源的支持。所以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些要清扫的、觉得社会不洁的人,一方面硬是认为国家对高雅艺术没有支持,另一方面要消灭大众文化,这就形成了他们相当模糊的立场。我想高雅艺术的确是亟待支持的,而且也获得了支持和稳定的观赏群。但现在我们似乎也应加强对于大众文化的研究,有一些实事求是的解释和分析,而不是采用一笔抹杀的方法。这似乎是我们与文化冒险主义的区别。其实进行文化冒险主义的写作的人,发出自己声音的途径也依然是市场,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了。它也是市场里的一部分,尽管它可能影响力较为有限,但它也是市场中的多极的一极。像最近炒得非常热的“抵抗投降书系”,也是依靠二渠道运作的,依靠书摊来卖的。虽然它宣传张承志和张炜的思想,激烈地批判市场和世俗文化,但却是依靠市场和世俗文化来运作。我想重要的还不仅仅是这种矛盾,还有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就是需要在这种市场化的多元的选择之中,有不同的声音出现。如对于张承志、张炜的那些非常激烈的、相当情绪化的言论,确实不应沉默,不应只让这种反对世俗文化,压抑差异和不同的意见的观念发出声音,而其他声音则不能发出,这种现象是不能接受的。这些文化冒险主义者已发出了挑战书。他们当然有权发出他们自己的声音,但其他人也应该发出他们与之争辩的声音。任何人也没有什么对于真理的垄断权,而是必须有许多不同的声音构成“众声喧哗”。一个开放的社会需要不同的声音。我们也有责任发出声音,这也是我们应有的社会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