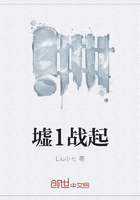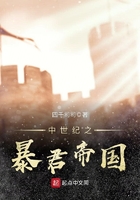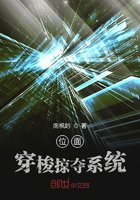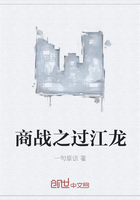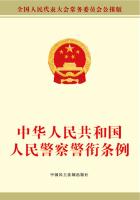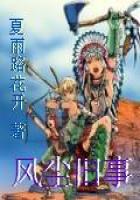李其琼
敦煌莫高窟是我国美术史上唯一的保存着北朝至唐宋时期大量艺术真迹的殿堂。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有个别画家不辞劳苦,不避道路险阻,前来莫高窟临摹敦煌壁画。1944年,以常书鸿为所长的敦煌艺术研究所宣告成立。
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是代表国家在莫高窟设立的研究保护机构。研究所成立之初,就有一批学者随常书鸿先生来到敦煌,当年就开展石窟摄影、洞窟测绘、石窟内容调查、编号、壁画临摹等工作。此后,尽管时事变迁,敦煌的美术研究工作则如涓涓细流,从不枯竭,为宣传介绍敦煌艺术起到了广为人知的作用,因此人们常说“敦煌研究院是从临摹起家的”。时至今日敦煌的美术工作已历六十春秋。敦煌的美术工作也从临摹小组提升为研究所,具有临摹、研究、弘扬创新的广阔天地。古人说“温故而知新”,回眸惨淡经营的过去,将会有利于我们今天的美术工作继续前进,迎接新的时代挑战。
一、敦煌艺术研究所时期
1943年,常书鸿所长领着第一批自愿者来敦煌创业时看见的莫高窟,仅是背依鸣沙山,面对三危山的断壁秃垣,许多洞窟崖壁坍塌,绘塑裸露,高处难于攀登。窟前是清代修建的上、中、下三寺,仅上寺还有两位喇嘛,是当时唯一的居民。初建的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所址,就选在中寺(原皇庆寺)内。大家清除古庙尘土,因陋就简,略加改造,放几张桌椅就成了研究所的办公地。修建员工宿舍更方便,撤除寺侧一排牲口槽,将原夯土墙利用起来,用土块分隔成小间,上面盖顶,前面开门,内置土块嘞成的土桌、土凳、土炕、土书架,白灰饰面,一排整齐的职工宿舍就成功了。上至所长下至员工一律土房、土家具。一个省钱省时,与环境协调一致的国家直属机构就算建成了。这种以土为主的房舍一直沿用到60年代才稍有改善。
考古组是艺术研究所内唯一的业务组,集中领导石窟调查、壁画临摹等工作。第一批随常书鸿所长来敦煌的考古人员仅苏莹辉、李浴、史岩三人,来敦煌学习的青年美术工作者有龚祥礼、董希文、张琳英、张民权、邵芳、周绍淼、乌密风、赵冠洲、潘絜兹等9人,是考古人员的3倍。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的鞭炮声响起后,国民政府忙于南迁复原,就给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送来一纸撤销令,好不容易创建的研究机构立即陷入困境。一群热情工作的年轻人马上失去留在敦煌的条件,何况久居荒漠的寂寞也促使人人思归,只有所长常书鸿先生又奔赴当时的陪都——重庆,联合学术界人士奔走呼吁,于1946年才恢复了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机构恢复后,艺术研究所招聘到自愿来敦煌的郭世清、凌春德、范文藻、段文杰、霍熙亮、张定南、钟贻秋、沈福文;1947年又从四川招聘了孙儒、欧阳琳、黄文馥、薛德嘉、李承仙、肖克俭;1948年周星翔自费来敦煌临摹,同年史苇湘从四川来敦煌。这时考古人员奇缺,新来的青年中除添了学建筑的孙儒之外全是一批艺术家。
40年代的敦煌艺术研究所建立在交通不便、消息闭塞、经济落后的边陲小县的荒漠中。对一群来自鱼米之乡的内地青年来说,冬季只有萝卜白菜、土豆加大葱,阳历五六月才有少量韭菜的生活确实是艰苦的。可是对于那些敢于来敦煌的美术工作者来看,生活中的苦不算苦,只有创造条件工作才是真正的“斗争”。从艺术研究所走过来的前辈画家潘絜兹先生回忆当年开展工作的困难,他说在敦煌几乎买不到绘画材料,画纸是四川带来的质次连史纸,吸水性太强,不能着重色,工作前人人要学会矾纸、裱褙,将一张普通的川纸加工成适宜临摹的绘画用纸才具备工作的条件。敦煌也买不到像样的毛笔,旧笔用到无锋时想方设法剥去表层,令笔锋再现又继续使用。最困难时用染料代色作复原画。为表现历史沉淀后的壁画古旧效果,就地取点黄土加工也可代色。说来有趣,他们寻找的代用色白灰、红土还真是古代敦煌壁画原用色之一,尤其是红土,就地取材,永不变色,在敦煌壁画中是历代沿用不衰的基本色种之一。纸、笔、色的困难克服后,唯有窟内光源不足最难办。许多保存好,色彩鲜丽的壁画往往隐藏在日光照射不到的洞窟深处,或中心柱背面。为了一睹“庐山真面目”,或用一面镜子将洞窟外面的日光反射到洞窟内(用镜面反射日光一直沿用到60年代,严格地说反射日光进洞不利于壁画保护,可是在那条件困难的年月里,却是唯一能解决光源不足的办法之一)。只要能将壁画临摹出来,不惜采用各种简陋、原始的手段,苦中寻乐,就是第一代敦煌美术创业者的风采。
到1951年更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敦煌艺术研究所存在的时间只有短暂的五六年,但给莫高窟留下一批数量可观的壁画临本,虽然受条件的局限有时不得不缩小临摹,不过也有像董希文、李浴临摹的北魏254窟《萨埵本生》、《降魔变》,邵芳临摹的盛唐172窟《观无量寿经变》等数量不多的原大临本。1948年常书鸿所长将临本带到南京、上海等展出。美学家宗白华先生看过敦煌壁画展,即时写出《略谈敦煌艺术的意义与价值》一文,宗先生在文中写道:“天佑中国!在西敦煌莫高窟里,竟替我们保留了那千年艺术的灿烂遗影,我们的艺术史可以重新写了!我们如梦初觉,发现先民的伟力、活力、热力、想象力”。“这次敦煌艺术研究所辛苦筹备的艺展,虽不能代替我们必须有一次敦煌之游,而临摹的逼真,已经可以让我们从‘一粒沙中窥见一个世界,一朵花中欣赏到一个天国’了!”宗白华先生看一次小型的敦煌艺术展,就发现了敦煌艺术丰硕的内涵,不能不说是对敦煌美术工作的鼓励、肯定。第一代的敦煌美术工作者,也将我们从敦煌学到的民族艺术的精华融入他们后期的艺术生涯中。董希文、潘絜兹等画家就是从传统中继承、发扬敦煌艺术传统的佼佼者。
二、敦煌文物研究所时期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1951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更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常书鸿先生任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一批坚守工作岗位的艺术研究所业务人员也留下来了,他们是霍熙亮、孙儒、段文杰、欧阳琳、黄文馥、李承仙、史苇湘等,他们都是随常书鸿所长开拓敦煌文物研究所事业的先驱。1951年在敦煌工作的业务人员中除了学建筑的孙儒一人,其余都是清一色的美术工作者。敦煌文物研究所将前考古组一分为二,社保管组(即今保护研究所)、美术组两个专业组。
1951年文化部调集敦煌壁画临本去北京举办敦煌文物展,展出期间,适逢抗美援朝战争,敦煌艺术的精湛,敦煌文物流失海外的伤心史激起了普遍的爱国热情,敦煌艺术深厚的文化内涵在首都掀起广泛关注,于是文化界纷纷根据敦煌壁画临本提供的资料各抒己见,1951年的《文物参考资料》为此专门出了一期《敦煌文物展特刊》上下两册,刊载各家论文。仅论及艺术方面的就有常书鸿所长的《敦煌艺术的源流与内容》,向达的《敦煌艺术概论》,王逊的《敦煌壁画的临摹工作》,阴法鲁的《从敦煌壁画论唐代的音乐和舞蹈》,梁思成的《敦煌壁画中所见的中国古代建筑》,宿白的《敦煌莫高窟中<五台山图>》等,都是对敦煌文物展的积极反响,其盛况应了宗白华先生的一句话——“我们的艺术史可以重新写了!”
敦煌文物展结束后,中央人民政府对敦煌的保护、美术工作给予最高的荣誉和奖励,特颁奖状和奖金给全体员工,奖状中写到:敦煌文物研究所全体工作人员在所长常书鸿领导下,长期埋头工作,保护并摹绘了一千五百多年来前代劳动人民辉煌的艺术伟制,使广大人民得到了欣赏研究的机会。这种爱国主义的精神是值得表扬的。特颁奖以资鼓励。
中央人们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
一九五一年六月于北京
北京展览的成功,中央人民政府的表彰,极大地鼓舞着一群久居沙漠的敦煌人,敦煌的美术工作者进一步明白做好敦煌工作,用临摹手段变不动的敦煌艺术为可移动的敦煌艺术乃时代的呼唤!
1952年,为改变前艺术研究所用粗劣的纸张、染料代色的尴尬,国家特别给予照顾,一次性地从北京买回上等绘画材料——当时最好的宣纸,北京名厂的各式毛笔,传统的矿物质国画颜料。工作条件的改善缩短了闭塞的敦煌与内地的距离,人人兴高采烈。
1952年,我从部队转业来敦煌。1953年初,曾随张大千工作,擅长裱画的敦煌人李复来了。秋天,刚从西安西北美术学院绘画系毕业的关友惠、杨同乐、冯仲年,雕塑系毕业的孙纪元等四人来敦煌。不到两年时间,敦煌的美术工作者扩大近一倍,临摹壁画彩塑、负责装裱各有专业人员在岗,人员配备齐全之快,在敦煌艺术研究所是想都不敢想的。
从1952年开始,临摹工作由单幅临摹转向整体临摹,也是敦煌文物研究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制定工作计划最重要的一年。根据文化部“……临摹是研究工作的基础,也是研究院所的基本工作……临摹的过程就是锻炼的过程……”的指示,美术工作者一致投入以临摹为工作核心的任务中去。同时,敦煌的美术工作也变艺术研究所单兵作战的个人临摹为集体合作;变只临摹一角为临摹整幅乃至复制,整窟的原大洞窟模型;要求临摹效果达到与现存洞窟色彩破损同步的乱真程度,方便不能来敦煌的专家学者借助临本进行研究。于是西魏时期保存好,有造窟纪年的第285窟就定为1952年整窟临摹试点。
临摹整窟原大壁画是敦煌美术工作一次创举,没有经验,没有借鉴,更不允许直接从壁画摹印画稿,怎么办?于是几个年轻人自己动手测量画面,凭借对敦煌艺术的一腔热情面壁起稿,起稿完成后,着色时就出现光源不足的矛盾,支起比原壁略大的画板,一窟之内最多容纳二至三人,就采用你出我进着色起稿参差进行的方法争取时间。两年左右五六个人全力合作,第一次画成总面积百余平方米的285窟原大洞窟模型一座,以及一部分壁画代表作。1953~1954年又集中力量临摹以敦煌藻井为主的图案专题。敦煌装饰图案内容丰富,遍布洞窟各处,其中尤以藻井、边饰图案最多姿多彩,形式规范,是敦煌装饰艺术的精华所在。若采用忠于现状的客观临摹方法,必然达不到将精美的敦煌图案介绍出去的目的。因此临摹图案专题时又采用了能显示敦煌图案变化规律,色彩组织规律的整理临摹。
临摹成为美术工作的中心任务后,如何提高临摹水平,保证临摹质量,对不同的专题应采取什么方法临摹,都是敦煌文物研究所的美术工作者应研究的课题。听说日伪时期,有一批日本人在我国东北临摹的辽阳汉墓壁画质量一流,临本已经留在沈阳博物馆。为寻找借鉴,开阔视野,1954年特向沈阳博物馆借来供美术组研究、临摹,意欲从中揣摩日本人的临摹手法,比较潮湿环境中的墓室壁画与干燥气候下的敦煌壁画之间的差别。
1954年敦煌文物研究所迎来第一批专程来敦煌考查的同行。由中央美院、杭州美院的叶浅予、邓白、金浪三教授率领的研究生考察团来敦煌工作数月,也给敦煌的美术工作带来一次交流的机会,考察团离开时敦煌文物研究所收藏了方增先、刘勃舒临摹的196窟《张议潮出行图》(局部),詹建俊临摹的57窟《说法图》(局部)等部分临摹本。1955年中央美术学院刘凌沧教授来敦煌考察,行前也留下一幅220窟《净土变》(局部)壁画临本。他们用创新的眼光接受敦煌艺术的熏陶,对敦煌的美术工作者多有启发。
1955年10月,敦煌文物研究所携带第一批新作去首都展出,一座未经周密设计的原大洞窟模型(285窟),居然在故宫奉先殿外的空地上耸立起来。展出了六十余幅大型敦煌藻井,边饰图案,大型壁画《劳度叉斗圣变》(全图30平方米),及其它新作。敦煌彩塑也第一次以她光艳照人、和谐完美的艺术形象走出莫高窟,陈列在奉先殿供人观赏,使观众于千里之外就能欣赏到敦煌彩塑、敦煌图案,自由出入285窟模型、增加身历其境的真实感受,体会敦煌经变画的恢弘气势。1955年的首都展览虽无1951年的轰动效应,但展览是成功的。
1956年,由李承仙、关友惠携带敦煌壁画临本去印度新德里举办规模盛大的敦煌艺术展,这是敦煌艺术首次在国外举办大型展览。印度展结束后由孙纪元、潘絜兹赴前捷克斯洛伐克举办敦煌艺术展,第一次将莫高窟艺术介绍给欧洲观众。
1956年,研究所组织第一次大规模临摹榆林窟壁画。保护、摄影、美术工作者全体去安西县境内的榆林窟工作。美术组以榆林窟第25窟为第二个整窟临摹的目标。25窟是一座保存好的唐代中期洞窟,此外榆林窟还有莫高窟缺少决定西夏、元时代的晚期艺术,恰好补敦煌艺术之不足。
榆林窟比莫高窟还荒凉,当年的托管员郭元亨称榆林窟是一个“除了吃饭不张嘴”的地方,是人迹罕至的遗址,它距最近的村庄也不少于40里,若去榆林窟工作,必须备足全套工作生活用品,要有炊事员,两三月的口粮,用牛车、马车开路,一路浩浩荡荡,打着火把走进榆林窟。略清积尘安家后,几盏汽灯,几本佛经陪伴美术工作者面壁临摹。在收音机都视为稀罕之物的50年代,终年不见行人的榆林窟除了榆林河的淙淙流水滋润着沿岸几棵胡杨,凝紫的丛丛红柳外几乎是一个没有生灵的世界。工作之余踏着夕阳余晖去戈壁慢走就是最好的消遣,生活单调寂寞连做饭的炊事员都感觉无奈,也凑近画家,拿起画笔帮助在图案上填色,于是五六人围着一盏汽灯转,人人凝神着画,这时只有吱吱的汽灯声划破万籁俱静的夜空。
50年代以临摹为主,研究也紧随其后,临摹研究相结合,1955年常所长下达编写《敦煌艺术小丛书》一套12册,是敦煌文物研究所第一次以通俗读物的形式介绍敦煌艺术。1952—1957年是敦煌美术工作安定的几年,是敦煌美术工作自觉追求质量、数量的几年。这时临摹认真,一致追求提高临摹质量,形成一个老带新,学线描、传经验的集体,还制定评比制度,促进临摹质量不断升张,短短五六年美术组靠十一二人完成了莫高窟285窟、榆林窟25窟两座整窟的临摹以及一批壁画、彩塑代表作的临摹复制,并补充了榆林窟西夏、元代壁画大型图案代表作。
敦煌的临摹从40年代开始积累,已有临本千余件,敦煌文物研究所以前的临本常由常书鸿先生保管,1951年北京展览后全部运回敦煌。1957年常所长决定建立敦煌文物研究所临本库,派我和李复负责于每年冬春不能进洞工作的季节,剔除不合格的废本,重新建账入库。李复负责日常保管,为敦煌艺术外出展出提供方便。今日,美术所的临本库房已是敦煌艺术的一笔重要财富。
临本与研究总是相辅相成,莫高窟的内容,石窟分期断代的质疑,在那考古缺人的年代,解决的路只能在自己脚下。例如50年代认为莫高窟没有北周的石窟,从北魏、西魏直接过渡到隋唐。可是从临摹工作所见,根据壁画彩塑造型,表现规律,美术工作者产生了疑问,带着这些不解的迷雾,史苇湘终于在第442窟找一条“第……主簿鸣沙山县丞张恩供养佛时”的北周供养人题记,后来万庚育复查莫高窟供养人画像题记又在第428窟发现“晋昌郡沙门比丘庆仙供养时”的题名。在不同的洞窟找到两处北周供养人画像,说明北周确实在莫高窟修建了一批洞窟。
临摹工作中经常碰到那些不知名的故事画,经变画,或定名有无的壁画,这些都是美术工作想要解决的问题。从50年代到文革前,美术工作人员日积月累相继发现不少新内容新题材,如《睒子本生故事画》、《微妙比丘尼姻缘故事画》、《福田经变》、《贤愚经诸品连屏画》、《佛教史迹画》、《瑞像画》等。此外如对中晚唐是的屏风画与经变的构图关系,285、249窟窟顶壁画中佛教内容与民族传统神话并存的新认识,都是对石窟内容研究的新成果。值得一提的是“文革”前的美术工作者都有种“述而不作”的朴实,一个个新内容被解读后往往是集体听一人介绍后即认可,解决问题的人不写文章,听过的人也不记是谁的发现权,但是丰富的学识终使史苇湘、段文杰两位从临摹走向研究,成为敦煌学带头人而脱颖而出。
1957年后敦煌美术工作就进入运动频繁时期,反右斗争后紧跟着就是“大跃进”。
1958年大跃进、大炼钢铁将莫高窟也搅得沸沸扬扬,干部、工人、家属全动员起来,大泉河边一座座炼铁小高炉烈火熊熊,美术工作者日夜加班,临摹、炼钢两不误。还破除冬季不能临摹的常规,给洞窟安装临时玻璃门,点上汽灯日夜工作。全民炼钢的狂热违背常理,虽然时间不长就结束了,可是美术工作依旧热气腾腾。
1958年所长常书鸿、李承仙夫妇携带壁画去日本,在东京举办规模盛大的敦煌艺术展,是敦煌艺术第三次走出国门,也是第一次将敦煌艺术介绍给日本观众。“大跃进”期间被跃进精神驱使的美术工作你追我赶地制定跃进计划,即使有出国展览也未曾影响日夜兼程的美术工作。这期间美术组临摹了敦煌盛唐壁画中的杰作第217窟、第172窟的《观无量寿经变》。北京十大新建筑落成,美术组为人们大会堂甘肃厅临摹《唐代净土变》、第220窟《大型舞乐》各一幅;为中国历史博物馆临摹第159窟西壁带佛龛的模型一座;
第156窟长卷画《张议潮出行图》、《宋夫人出行图》各一幅,另外还进行敦煌服饰、供养人、飞天三大专题的临摹工作。随着临摹任务的增加,人力不足的矛盾十分突出。当时常书鸿所长已兼任甘肃省兰州艺术学院院长,为此特调艺术系毕业班同学来敦煌实习,协助美术组临摹第156窟、第159窟,同时调艺术系的雕塑老师何鄂来敦煌工作,加强敦煌的雕塑力量。1959年就有刘玉权、何治赵两人大学毕业后来到敦煌,加人美术组,充实了美术研究的力量。
1959年国庆后不久,接到甘肃省委通知,敦煌文物研究所与甘肃省博物馆共同承担武威天梯山石窟的抢修搬迁任务,研究所由常书鸿所长亲自带队,除保护组全力以赴外,美术组也抽调李承仙、段文杰、万庚育、冯仲年、李复等人去天梯山协助石窟内容调查、壁画临摹和搬迁,工作结束后带部分天梯山壁画临本作资料保存。
听说在天梯山参加抢救工作的人,在简陋的条件下克服困难,成绩突出,留在莫高窟的美术工作者也不敢怠慢,为临摹飞天专题做准备的人立即行动,每人扛一架木制人字梯,带上计划中的目录穿梭于各层洞窟间,每找到一个目标就架起人字梯爬上去起稿,飞天画幅虽小却分散在不同的洞窟内,往往是寻找目标的时间比起稿时间还多。在大跃进的时期谁都不敢落后,于是急中生智,不约而同地在画稿一角记上分分秒秒的起稿时间备查。
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虽说是一次缺乏科学依据的狂热,可是“敢想、敢干”的口号也给美术工作带来突破常规的机会。有人画南瓜大于车轮,飞天驮着麦捆上天的“跃进”画,并集体创作了一幅“叫高山低头,河水让路”的大壁画,真有点敢想敢干,意气风发的味道。这些创作虽说都是些赶形式的冲动,却真地勾起了美术工作者压抑多年的创作热情,因此常书鸿所长特许美术工作组部分人去牧区深入生活,带回李承仙的《姑娘追》,霍熙亮的《猎归》两幅小稿,命美术组创作完成,画完后送到牧区深受欢迎,虽在美术界虽有微词,却不减敦煌美术工作的创作热情。1960年完成了天梯山工作后又有几人去临洮县,在当年名噪一时的引洮上山工地深入生活,最后还是由李承仙主持在兰州饭店内画了一幅规模更大的《引洮上山图》。虽说三幅大型创作都不算成功之作,但是对于被局限与临摹的敦煌美术工作者来说,总算获得一次创作实践机会。
三年自然灾害刚过,1962年秋天,敦煌飞天、图案专题艺术展于上海展出。1963年敦煌的美术工作又恢复到以临摹为中心的工作中去了,临摹的大经变代表作、盛唐的第217窟列为第三座洞窟模型的目标都在有序进行中,并很快完成壁画起稿。
1962年,敦煌又迎来一批新人,他们都是大学历史、考古专业的毕业生,当年还邀请北大宿白教授来敦煌做了《敦煌七讲》的学术报告,敦煌文物研究所再建考古组的时机已经成熟,美术组也抽调霍熙亮、关友惠、刘玉权三人转入考古组,史苇湘调出美术组,负责新成立的敦煌文物研究所资料室,美术组开始有人转入其他组室适应敦煌事业发展需要。
1966年是莫高窟创建1600周年,常书鸿所长计划筹备大型活动。鉴于莫高窟有彩塑2000余身,敦煌仅有两人临摹彩塑很不适应工作需要,特邀请鲁迅艺术学院雕塑系高秀芝、李克勤、李仁章三位教授支撑。1964年他们三人各自完成一身泥塑正等待上彩时,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的喜讯传到莫高窟,人们无不欢欣鼓舞,得到喜讯的李仁章急不可待地想跟研究所全体人员在食堂共同分享喜悦,为走捷径而从工地脚手架(1962年莫高窟加固工程全面施工)攀缘而下,不幸从第三层高架上失手落地,造成重伤,不治身亡。李仁章是一位年轻有为的青年雕塑家,在莫高窟献出了才三十二岁的青春年华,李仁章也是第一位在莫高窟因公献出生命的雕塑家。李仁章牺牲后,莫高窟人将他的遗体火化,安葬在三危山麓大泉河岸的沙丘中,面向他曾工作过的隋代第419窟,让我们永远地怀念他。
自1952年改用矿质颜料临摹已十余年,壁画临摹的效果自有公论,按“忠于现状的客观临摹”的标准要求在社会上也有良好反应,但是纸本是否就是临摹敦煌壁画艺术唯一的途径?为什么不可以像临摹彩塑一样按原作的规律,用同样的材料临摹?很快研究敦煌壁画制作的规律的设想形成共识。恰巧筹划中的莫高窟建窟1600年纪念活动的,要制作一座洞窟模型,半是创作画,半是临摹,为仿制壁画提供了机会。限于时间不可能按部就班地搞,临时采用在纤维板上刷泥浆做成画壁表面效果,两三个人先在简易的泥壁上试临323窟南壁壁画,临完后果然效果不错。因此促成美术组人人研究壁画地杖制作规律的热情,很快,一批大小不等的试验泥壁画临摹出来了。
1964年、1965年常所长又从中央工艺美院壁画系争取到李振甫、何山、樊兴刚三人来敦煌。他们都是学壁画的,专业对口,他们还是“文革”前敦煌文物研究所最后吸收的三位专业人员。1964年以后,阶级斗争的弦一天紧似一天,莫高窟创建1600年纪念活动无疾而终。
十年“文革”打乱了一切秩序,文物研究所的业务人员走的走,散的散,骨干力量无存。1972年,美籍华人作家韩素音来莫高窟居然找不到相应的接待人员,这时才想起已被遣送农村的段文杰,又匆忙召回临时应付接待任务。为恢复敦煌的工作,甘肃省委在文物研究所落实政策,将无端受惩罚遣送全国各地农村的业务人员先后召回。1978年继续“文革”前计划的217窟临摹工作,1979年常书鸿又以教学基地接纳兰州西北师大艺术系毕业班学生常嘉煌、薛小玲、张保东等来莫高窟实习。1979年甘肃省委再次来敦煌文物研究所落实政策,彻底清理了1957年以来运动中遗留的问题。
这一时期援外任务多,例如1972年欧阳琳、万庚育、关友惠三人去西安支援陕西省博物馆临摹懿德太子墓壁画;1973年欧阳琳和我去陕西省博物馆支援该馆汉唐壁画出国展的临摹工作;1978年美术组派赵俊荣随关友惠、霍熙亮、刘玉权去新疆克孜尔石窟临摹壁画;1988年关友惠调回美术组,还去酒泉丁家闸、嘉峪关支援甘肃省博物馆临摹墓室壁画。
经过“十年动乱”,敦煌美术工作人心涣散,青黄不接,人员断层严重,迫不得已敦煌决定自行培养人才,第一次招收学生还不能强调专业,结果以失败告终。几年后总结经验,吸收受过中等专业训练,或经过考核选拔有发展前途的青年在工作中培养,使美术组新增赵俊荣、杜永卫、霍秀峰、吴荣鉴、高鹏、马强等六人,1980年前后又接受工农兵学员邵宏江、马复旦、李月伯三人。新来的年轻人缓解了敦煌美术工作老龄化的危机。
三、敦煌研究院时期
1979年以后常书鸿所长移居北京,段文杰任敦煌文物研究所副所长主持日常工作。1980年国家文物局下达中日合作出版《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五卷本的任务,像一针强心剂激活了敦煌人的热情,预示一个以研究为中心的时代即将开始。把敦煌艺术浓缩成五卷图册来进行全面介绍是前所未有的大事,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大部分研究人员都调动起来,参加了这项重要的工程。80年代以后敦煌艺术图录及论著的出版频繁,显然坚冰已破,敦煌工作已迎来春天。1984年敦煌文物研究所扩建为敦煌研究院,原来的美术组提升为美术研究所,业务范围由临摹为主拓展为“临摹、研究、创新”的六字方针,它是敦煌美术研究所10年梦寐以求的愿望。六字方针结束了以临摹为基本工作的局限,但是美术所人员短缺、素质不高的问题在院属各所中尤为突出。1984年孙纪元调去天水麦积山艺术研究所任所长,敦煌雕塑工作立即后继无人,由关友惠、欧阳琳、万庚育、李其琼、李振甫、樊兴刚、李复领着七八个青年在新的机遇面前,尽失昔日人多势强的优势。研究、临摹、出国展等工作,使新形势下的美术研究面临空前的压力。
1982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十周年,中央决定在东京举办敦煌壁画展。鉴于1958年已在日本举办过大型敦煌艺术展,1982年是“文革”后敦煌艺术第一次办出国展,应该有较多的新作品介绍出去,而出版《敦煌莫高窟》五卷本的工作也不能放松,于是就组织孙纪元、关友惠和我筹备展览,为解决临摹缺人的矛盾,有一次向西北师大美术系借来王宏恩、鲁迅美术学院借调王占鳌、西安美术学院借调陈之林、四川美术学院借来杜显清、杨麟翼、施肇祖等教师,于1981年全年在莫高窟临摹,暂时解了人员短缺的燃眉之急。
1982年在日本举办的敦煌壁画展相当成功,法国人在日本看到过敦煌壁画展后,立即洽谈于1983年将同样的内容移至法国巴黎展出。
敦煌壁画在日本展出时,日本创价学会提出收藏敦煌艺术研究所创始人、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常书鸿先生临摹的第217窟《化城喻品》、敦煌研究院首任院长段文杰复原临摹的第130窟《都督夫人太原王氏供养像》以及李其琼临摹的第220窟《帝王图》、第98窟《于阗王后曹氏供养像》四幅参展壁画临本。四幅临本作品包括忠于现状的客观临摹、旧色整理临摹、复原临摹三种临摹方法。三代美术工作者的临摹作品在展出时被观众提出收藏,这种巧合说明敦煌美术工作者充满热情、激情的临摹能如实地反映敦煌艺术精神,研究性的复原。整理临摹是对敦煌艺术的在创作,均为社会认可。
继这次临本收藏后,创价学会又提出代临第275窟、第407窟、第329窟藻井图案的要求,国内的博物馆也常向敦煌文物研究所索要壁画临本,50年代由段文杰、冯仲年、李复三人临摹的安西榆林窟第25窟的《观无量寿经变》,为日本秋田县收藏。
1982年展览取得成功后的同时,美术工作呼唤人才已成燃眉之急。1982年敦煌文物研究所委托甘肃省艺术学校为敦煌招收一期美术班,由敦煌送去中央美术学院附中培训三年,成为具有中等美术专业人才。三年学成后,李林、华亮、沈淑平、关晋文、马玉华、李开福、牛玉生、张伟文回到敦煌,补充了美术工作的队伍,但是仍缺学有专长,经验丰富,能胜任研究工作的高素质人才。1982年敦煌向全国公开招聘专业人员,1984年相继有一批艺术院校的毕业生、研究生以及在美术岗位工作多年的人先后从全国各地会聚敦煌,他们是谢成水、高山、娄婕、王峰、马军六人,这批受过高等专业训练的美术者,有的自愿长期留在敦煌,已成为敦煌美术工作的骨干,一支包括不同专长的美术队伍在敦煌研究院茁壮成长。
使用人、培养人、知识更新是适应事业发展的必由之路,是美术研究所始终不渝的目标。敦煌文物研究所的美术组是一个有美术、雕塑、装裱等专业,能独立完成临摹、展览任务的业务组。
“文革”后期到80年代两位雕塑家的相继离开敦煌,为顺利完成新老交替,美术所又采取内部培养办法,杜永卫、李林两位自愿学雕塑的青年在孙纪元指导下学雕塑,入门以后杜永卫被送中央美院雕塑系进修;李林去四川美院雕塑系学习三年。此外,马强由美术所提供条件考入中央美院国画系。
裱画是一般人不太注意的专业,老裱画师李复出身老艺人世家,身怀绝技,美术所主动劝他将技艺传授给自己的儿子李晓玉,后又收一徒周河,使这一技艺得以延续,也才顺利完成敦煌美术工作新老交替。
敦煌研究院在培养高素质人才方面也不遗余力,随时根据条件尽力而为,对已经学有专长的美术工作者,也无例外地为他们创造继续深造提高的机会。自段文杰先生担任敦煌研究院院长时开始,就先后请国内艺术院校为敦煌培养美术人才,继而创造条件送已有工作经验的美术工作者去外国深造,目前已有侯黎明、娄婕、高山、杜永卫、赵俊荣五人先后去日本东京艺术大学进修。他们学成归来,已成为敦煌美术工作的骨干。敦煌美术研究所已初步越过断层,进入不断提高素质的时代。
进入80年代,敦煌研究院的工作进入了以研究为主的阶段,敦煌美术在六字方针的指导下,研究敦煌艺术理论义不容辞,配合展览稿临摹提供展品责无旁贷。研究临摹的双重任务同时落在美术所少数人的头上,其困难是可想而知。尽管已有两位从临摹走向研究工作的段文杰先生、史苇湘先生担任撰写著作的主将,但也还需要合作者与助手。于是面对刚出台的六字方针,有人说今后不断有敦煌艺术的出版物,介绍宣传敦煌艺术不发愁,美术所老人们的眼也花了,应全部转入研究,创新刚纳入规划,今后的美术工作应以创新为主攻方面。敦煌美术工作既不是单纯的理论研究所,也不是画院式的创作单位,从研究、继承、发扬敦煌艺术的实际出发,美术所即时制定了美术研究所应该是以临摹为基础,临摹与研究相结合,临摹与创新相结合的工作原则。
根据需要,老同志万庚育第一个全面转入研究,参加《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中国石窟·安西榆林窟》、《中国美术全集·敦煌彩塑》中的部分图片说明的撰写工作,编撰《中国壁画全集》十卷中的五代、宋分册,并参加撰写《敦煌学大辞典》的部分辞目,还发表了不少敦煌艺术研究的论文。欧阳琳、关友惠和我则游移于研究、临摹之间,都是《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敦煌石窟·安西榆林窟》图片说明、《敦煌学大辞典》辞条的撰稿者之一。我为《敦煌莫高窟》五卷本撰写《隋代的莫高窟艺术》,我和关友惠分别是《中国壁画全集·敦煌》十卷中的中唐卷、晚唐卷的编撰人。
1985年敦煌艺术应邀再次赴日展出,这次日方提出新的参展目录,为加强中日文化交流,美术所新老工作人员齐上阵,避免了向外求援。从此,年轻的美术工作者成为临摹的主力,相继画完第217、249两座整窟,并独立完成第275、419、220、3窟等整窟临摹,其中第275窟为仿泥壁地仗,第3窟是在仿制沙泥画壁上临摹的。
美术研究所的老同志在敦煌研究院时期,工作之余个人发表研究文章亦成风气,如关友惠有《敦煌莫高窟早期图案纹饰》、《莫高窟隋代图案初探》、《敦煌壁画中的供养画像》等;万庚育有《谈谈莫高窟的早期壁画及其装饰性》、《敦煌壁画中的技法之一——晕染》、《珍贵的历史资料——莫高窟供养人画像题识》等;
欧阳琳有《谈谈隋唐时代的敦煌图案》、《敦煌壁画中的莲图案》、《敦煌图案简论》等;李振甫有《敦煌花砖艺术》、《敦煌的手》、《敦煌佛像画造型艺术初探》等等,都是他们个人近年研究成果之一。值得庆幸的是今日美术研究所已走出人才断层的艰难时期,80年代美术研究的年轻人不仅成了临摹敦煌艺术的主力军,敦煌艺术研究也崭露头角,发表不少文章与专著。如谢成水《看敦煌壁画——也谈中国绘画透视》、《敦煌艺术美学巡礼》、《莫高窟第296窟的艺术》、《谢成水敦煌壁画线描集》;侯黎明《新的超越——写在“敦煌研究院成立50周年美术作品展”之际》、娄婕《试论敦煌艺术的空间构成》、李月伯《莫高窟第305窟的内容和艺术》、《敦煌莫高窟第156窟附第161窟的内容及其艺术价值》;霍秀峰《敦煌唐代壁画中的卷草纹饰》、《敦煌觅珍——李月伯、霍秀峰敦煌壁画临本集》、杜永卫《莫高窟彩塑艺术》。另外有吴荣鉴、马玉华、关友惠、关晋文、赵俊荣等五人分别绘制敦煌飞天、伎乐、供养人、图案、菩萨白描集五卷,并获甘肃省第六届优秀图书奖。一个能画会写的年轻化的敦煌美术工作队伍正在成长。
推陈出新一直是敦煌美术工作者由衷的愿望,敦煌文物研究所时期受体制限制甚少实践机会,成功的作品不多,50年代还是有孙纪元创作的雕塑《瑞雪》为中央美术学院收藏,改革开放初期常书鸿先生创作的《勇攀珠峰》为中国科学院所收藏,《莫高窟风景》为日本创从学会所收藏,何鄂离开敦煌后创作的《黄河母亲》获得全国城雕铜牌奖。80年代敦煌研究院正式将“临摹、研究、创新”作为美术研究所工作原则,1982年研究院新办公楼落成,组织美术研究所中青年为办公楼创作新壁画部分作品发表在《中国美术报》,其中李振甫创作的《日月同辉》为院部采用,该作品同时获甘肃省美术作品展览一等奖。1988年应日方邀请,我绘制的《菩萨行》、李振甫绘制的《飞天颂》两幅仿唐壁画送日本东京日中友好会馆收藏。侯黎明创作《辉》为日本东京艺术大学收藏。此外尚有侯黎明、娄婕合作的《芨芨草》、《创造奉献求索》获甘肃省美术作品展览一等奖;侯黎明、娄婕、关晋文四幅作品获甘肃省美术作品二等奖;吴荣鉴、马玉华分别有作品获甘肃省美术作品三等奖……
敦煌美术工作已迎来了春天,但敦煌美术工作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