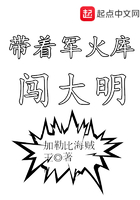在一座孤独的山中有很大的力量。有许多的时间,许多的空间,许多的实在的规律在它的石头中有许多的思想。在它的坡上,灌木和松柏就像白色灰尘中的许多黑色的符号它们像是汗毛,头发,眼眉。几只鸟叫着,在悬崖上空慢慢地盘旋风在石罅中穿过,古怪地哼着歌儿,隐蔽的溪流发出很温柔的响声。一切都来自于它,空气、水、土、火。甚至云也生自于它,在很高的地方,在绝壁之间。它们冉冉女卩火山的烟气。
有时山也是遥远的,灰蒙蒙的,被水包围着,人们只能看见它的臀部、腰肢、乳房和肩膀的柔和曲线,只能看见它的斜落进谷底的长发的波状线条。当晚霞中一切都消失的时候,或者当城市和道路像人被困在房子里一样被烟气笼罩的时候,山也远去了。它在拒绝中睡着,裹着沉寂和冷漠。女性的巨人,白色的女神,它突然厌倦了,闭上眼睛,不愿再让人看它。美是聋的、哑的,孤独地躲进它的蚊帐谁敢靠近它?他将迷路,因为那已不再是坚硬的石头、牙齿状的绝壁、直立的悬崖了。那已不再是骄傲的生命的努力、德行、美的力量了。那是一种很单薄、很柔弱的命运,仿佛幻影,在沉睡的大地之上的半空中飘荡,也许是一句话,一段音乐,人们可以用脸上的皮肤感知到,而你则瑟瑟地抖起来。这时,没有人能发现它。
飞机在云的后面飞过,没有人看见。海天一色。太阳已远。于是目光模糊了,没有什么再发亮了。慢慢地,慢慢地,夜来了。这几天它来得更早了。带着蝙蝠走出所有的洞穴。
这一切过去了,到来了,散走了,周而复始。山是这样的美,然而没有注意它就不存在。而注视若没有山就一直向前,如子弹般穿过空气,在空中打着转儿,变小,什么也没有发现就消失了。名称,地点,词语,思想,有什么关系?我只想谈谈永恒的美,谈谈人的注视,谈谈在阳光中很高很高的一座山。
(郭宏安译)
(1942-)英国杂文家、小说家和旅行作家;为他赢得声誉的作品有:《阿拉伯:穿过迷宫的旅行》和《古老的光荣》;后者写他在密西西比河上的旅行,被《纽约时报》誉为“比百分之九十的写美国的书都更成功”。本篇散文写他与父亲二三十年的关系,构思宽广,细节生动;描绘的是一条父子之间亲情深厚的纽带,体现出来的却是英国社会从二战到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变迁,是英国从传统走向现代的缩影。
吃老本
我觉得,每个人都真的是他们自己家族的祖先。我们把它们虚构出来,那些私人的祠堂、监狱以及快活的乌托邦。造访别人的家庭,我总是发现很难验证我所见到的传说,如同在途中汽车上听到的东西一样。人物总是夸大或缩小,要么好得过分要么坏得不行,脱离了他们应有的样子。这好比看一出戏,照着一个错误本子背一周台词便登场演出一样。一个人自己的传说更是双倍地靠不住。对一出既当主打导演又做领衔主演的人来说,写一篇评论是极其难以左右逢源的差事。那一定是一则传奇,不是每笔记下的流水账,也不是赤裸裸的现实主义;如同所有的创造神话一样,它的花园、它的拱梁以及树上的果子,都是象征物。这事轮到自己的家族,谁都没有本事做一名原教旨主义者。
曾有一段时间,在“家庭”这个观念还没有成形之前,家里就只有我的母亲和我。我们住在一个温馨的小房子里,那真像过着一种田园般的婚外恋的生活。我的父亲出门“参战”去了,他只是壁炉上方的一幅照片;他是那份早邮报;他是收音机里一点钟新闻的一部分。他与其说是我的父亲,不如说是我与之生活在一起的那个女人的讨好的丈夫一我害怕他回来。日子在继续,太阳灿烂的时候我们晒干草。我得过一场名叫乳糜泻的消耗性疾病,我便像一个享有特殊待遇的情人,被喂着专门进口的香蕉和煮熟的脑髓。我们习惯一起看报,因此我在三周岁前就能够癒癒绊绊读几段《泰晤士报》了。我们在蛋壳底部做烘烤,这样一来,巫师们也无法用它们当船只耍弄了。我们节省下我们的汽油定量,驱车到i射林汉姆看望外祖母。我母亲的福特八型AUP595是她于一九三九年用她为多家妇女杂志写爱情故事挣下的钱购置的,对演义浪漫是无可挑剔的交通工具。行驶在诺福克的窄道上,三十英里的车速令人毛发发痒,因窗大开,鼻子里充满花粉、皮革和汽油味儿。我觉得这才是生活。我所认定的是怎么开始就怎么过下去;在车前座上乘车,动不动就是亲吻和安慰话,篮装食品上方又是里贝纳瓶子。
我痩得皮包骨。不过我早已学会了像老练的靠女人生活着的生活方式。我体弱多病,让我有权利得到无微不至的照顾。我的脑门儿靠在我母亲的手中,病病歪歪,咳得嗓子直出血。我没病没灾时,我叽叽喳喳说开没完。我母亲也只有和我能说说话,因此我无意中学到了极富表达的词语,越发喋喋不休,加了许多新词。我弱不禁风,没法与别的孩子玩耍一我站在老远的地方看他们是一群没有教养的野孩子一我看出来大人们器重我,欣赏我,显然是我才配有的。我害怕很少几个被允许(“听着,不准胡闹啊!”)到我这玻璃世界里来的孩子取笑我。我的一个朋友是医生的儿子,因害着脊髓灰质炎成了跛子,套着跟他本人差不多一样大的钢架走来走去。我三岁时,母亲告诉我,说像他和我这样的孩子会上好学校,把书念下去,获得一个又一个学位,但是乡村的孩子都去上像马路那边的那所学校一样的不入流学校。我于是看见我自己和我母亲乘着我的学位之舟扬帆出海,帆儿张满了谢林汉姆海滩吹来的海风,威风凛凛的船头驶向浪漫浓酽的落日,把岸上那群嘲笑的乱糟糟的孩子抛在远处。
我一直没有把我父亲当回事。有一回我还把母亲气哭了,因为我问到我父亲会不会让德国人打死了;看到母亲收到新来的一摞信,先是来自北非、随后是意大利、再往后是巴勒斯坦,看得全神贯注,我经常感到不解。奇怪的是,父亲请假回来探亲,我一点记忆都没有留下。我一定是和别的来我家偶尔拜访的人一他们中许多人都穿着制服一弄混了。抑或就是那个带着我们娘俩星期天到那家费肯汉姆饭店吃午餐的男人?我记得那里人声嘈杂,卫生间里引起一阵恶心。我拿不准。
不管如何,看到他一天上午晚些时候回来了,背着一个卡其布长形军用袋,穿过海姆普顿草坪一对我来说它是家庭生活开始的时刻一他完完全全是一个陌生人。我对他的第一个印象是粗糖得令人难以接受。壁炉上的那张相片是一位年轻的下级军官,一脸娃娃相,看上去年少稚嫩,用不着刮脸。我父亲的下巴却像砂纸的颜色和结构。他的复员军人服装也看上去是玉米茬须织成的。眼见我的母亲和他紧紧拥抱,就在海姆普顿草坪空旷地上,我觉得痛苦极了。我仔细看了看他背包上的褪色的白字皇家炮兵J.P.C.P.拉班陆军少校。这个穿着一身别别扭扭平民衣服的高个子大兵,有什么权利在我们家呆着?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好几年后才开始有了答案。
我的父亲也一定有点感到吃惊。他的儿子像麻秆儿,一脸严肃,一点不是他一心期望的嘻嘻笑笑的三岁孩童。他显然不会应付孩子,一开口讲话就吱哇乱说一气的早熟的小病秧子,更让他手足无措。他尽量装模作样,用心用意地对付这种混乱局面,与我交朋友,好像他在与一个特别生嫩的下属愉快地相处。他回家的当天下午,提着我的脚把我倒悬在后花园的大水桶上。倒悬在这种蚊虫滋生的黑水汤上,我哭叫起来,我母亲冲出房子来保护我。
“只是玩玩,”我父亲说。“我们爷俩只是玩玩。”但是我可不这么看。这个要命的西哥特人刚刚从人杀人的屠场归来,等不及我们喝上午茶就一心想把我弄死。我哭诉着跑到母亲跟前,乞求她把这个可怕的家伙送回他显然只配呆在那里的战场上。我父亲的种种担忧也得到了证实倘若不在此时此地在父亲影响方面使出一些铁石心肠的东西,我日后一准变成一个不折不扣的懦夫,一个让人受不了的小窝囊废。
我父亲关于“窝囊废”的种种感受可能是由他自己的焦虑加重的。战前,他曾一直是个害羞的年轻人,在一所无名的私立学校里勉强获得一张毕业证书。后来又去一家教师培学院深造,教了一年预习课(这事他干得并不顺手),正好赶上应征入伍,做了本土军士兵。在军队里,他如鱼得水。他很快得到提升。他结了婚。他突然间变得人五人六,成了一个有名有分的人物。战争结束时,他本打算转入正规军,但是未能如愿以偿。我们爷俩相遇时,他二十七岁,在他曾经可以风光一时的行业里已然穷途末路了。他总是一副做张做致的官气十足的滑稽相,一种极不自然的不苟言笑;他学会了显摆男子气魄,跟一个托钵僧差不多。我父亲在二十来岁这个年龄层成了一个深有责任感的年轻人,晚发展却成长快。他生硬,拿大,严厉,遇什么场合做什么样子。我想,他感觉到我多愁善感的性子,隐隐约约威胁到了他自己的男子汉气,于是打算把我磨炼磨炼。
我惧怕他。我害怕他动不动就一言不发,让人摸不着头脑;害怕他突然阴转晴,心情又好起来;害怕他莫测高深的派头;而最让我害怕的是他事后算账式的川斥,这在他的书房是按军事法庭方式进行的。一件玩具丢在车道上过夜会让我屁股挨揍;过完四岁生日没有记住向我的女主人说声“谢谢”也会被打屁股。他领我走进一个冰冷的世界,充满了责任和惩罚——个十分复杂、不原谅人的地方,顶尖男儿在其中能够希望的是一声不吭挺过去。也许我的父亲有理由相信世界就是这个样子,在不遗余力地把我从我母亲不明智地为我创造的那个傻子天堂拯救出来。不过我当时只是觉得他因为我和母亲的亲密在吃醋,实施他的报复而已。
战后几个星期里,他在房子和花园里出出进进。他在母亲的旧便携式奥利弗蒂牌打字机上给潜在的雇主们啪啦啪啦打求职信。他嗖嗖地挥杆练习高尔夫球。他身穿复员军人制服围着花园鸟池转圈圈。他在计算尺上做炮术计算。我在一旁充当情侣之间的绊脚石——名郁郁寡欢的孩子潜伏在走廊里,气鼓鼓地窥视我的父母。我觉得当了“乌龟”,便显示出这种情结。还好,我的父亲终于找到了工作,做了当地退役军人联谊会的秘书,他因工作几乎每天晚上都得外出,一等他开车去威兹比奇和彼得博罗和金斯林,我就使些伎俩勾引我母亲,重温我们往曰的温情甜蜜。我们俩喝着可可茶收听收音机里的《迪克·巴顿》,然后我会发起一次喋喋不休的漂亮谈话,希望拉回她的注意力,不让她一门心思用在查看钟表上。我觉得出她喜欢我父亲呆在家里,而且我想我也感觉到因为我显然不和她共享那种快乐她心中不快。我感觉到我们娘俩的温馨令我有几分羞愧难当。跟着我父亲,我开始逐渐明白我的行为举动明显缺乏男子气,这些温情脉脉的晚上因此笼罩上了罪过感。我父亲一星期会念叨好几次,说我“你要下狠心学会自己站起来呀,老儿子”,我听了不敢直面这层意思,但是我心下知道这话没错,无可争辩。
然而,我和我父亲对老天压在我们肩上的种种责任,渐渐地严阵以待。我认为我们爷儿俩都感到十分无奈。他在生活中已经承袭了一个他只能用最老式的条件扮演的角色;他不得不做一个维多利亚时期的丈夫和父亲,家族的中流砥柱,走向衰败的拉班家道的继承人。我则已继承了他。我们爷儿俩双双在这些遗产重压下焦虑不安,爷儿俩都势单力薄,无法按任何方式把它们发扬光大。他对我恃强凌弱,反过来他又被家族的亡灵欺负着。如果我惧怕他,那么他得面对自己的复仇女神一即列祖列宗和由来久远的亲戚,他们早给他立下尺度,而他却屡屡告败,无一。
我的父亲不是长子,他的父亲也不是长子。让他扮演长子角色的,无疑是他的严肃,他身上那股敢于负责的年轻人派头,他对自己父亲毫不含糊的责任心。不管因为什么,好像每位满肚心事的伯伯叔叔或者执拗的老伯母婶母,都点名要他做他们的遗嘱执行人。家族里只要有人亡故,我的父亲便会忙得团团转,与拍卖商和律师打交道;我们家开始摆满祖传宝物。一辆辆马车拉来了家具和一箱箱藏画和文件。一件件古董“深藏起来”,却随后不得不因为保存它们费用过高而取出来。我们家深陷于我父亲的列祖列宗之中。
他们从每堵墙壁上神情不满地俯视着我们。有的是大而无当的陈迹斑驳的油画像,有的是铅笔水洗速写像,有的是精致的小画像,有的是侧面画像,他们从他们的镜框里向外逼视,眼神满是阴郁。他们中间有孟买的刑事法院法官,有爱德华爵士将军,有伏案写作的爱玛表姐,有数不清的印度军队上校和不足挂齿的预备修士,有爱德华爵士将军摆在玻璃盒里天鹅绒上的军功章。在那台无线电收音机上,摆放了家族纹章(由渡鸦、野猪头、几牙雉蝶和一句我记不清的铭文组成图案)。它们是令人不快的压抑的战利品。它们体现了在军队和教会的等级中模糊的中产阶级一百多年的苦苦奋争。这些列祖列宗的脸庞如同他们的家具一笨重、粗夯但制作讲究,外省英格兰样式,同时容量很大。他们不讲究风趣,只是体现了一点点才智。他们看上去像早已看透生存艰辛的人,为了活下去只得死守住寄宿学校灌输的那些原则。
我们尊敬他们,这些难以相处的家神。我们蹑手蹑脚地在他们的呆板家具间走动(“别在游戏桌上玩耍呀;那可是件古董一”我们用他们的饰章叉子吃鱼鳍;我们循规蹈矩地把我们自己的生活局限于蛮横的家族祖先留下的几个寒碜的角落。我父亲买了一些关于家谱的书(例如L.G.派恩着的《如何看你的家谱》),埋头整理索引卡和钻研一九二八年版的《伯克土地贵族考》。夏天的假日全用来进行一轮又一轮的寻祖活动,这不应是顶尖英格兰中产阶级所为,倒更适合虔诚的中国人去做。坐着布拉福特乔韦特客货两用车(我母亲的福特车卖掉了,我这下只好坐在后面的二等车厢里了)。我们在萨默塞特奔波,寻找远房亲戚们推测的埋藏墓地。我父亲用餐刀刮掉墓碑上的苔藓,我则在掉落下的苔片里寻找蛇蜥。在下雨的日子,他自己去汤顿和埃克塞特的档案馆,一页页翻阅教区登记册,核对十八世纪乡村的生日、婚姻和死亡情况。“我们祖上是,”他说,“自由民出身。循规蹈矩的自由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