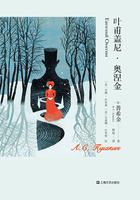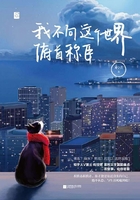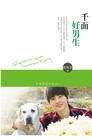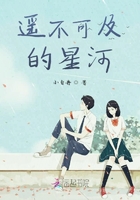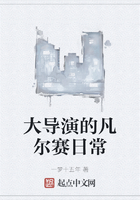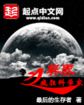让物件和姿态首先以它们的存在去发生作用,让它们的存在驾临于企图把它们归入任何体系的理论阐述之上,不管是感伤的社会学、弗洛伊德主义,还是形而上学的体系”(【法国】罗伯·葛里耶:《未来小说的一条道路》,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编,《现代主义文学研究》(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31页。)。的确,好的文学要让对象本身说话,而不是让对象仅仅成为主体的代言。但是对象又如何言说呢?没有主体的理解与感受,对象还是缄默的对象,永远没法成为有情的对象。随着我们所面对的现实变得越来越复杂,而每个人的感受又是如此的不同,想要在文学中呈现一种大家都认可的现实的努力变得越来越困难。
因为对象不仅是越来越难以把握,还很难再现。早在1882年莫泊桑就指出:“我们每人在他的心里和身体里都携带着各自不同的现实,我们的眼睛、耳朵、嗅觉、味觉都不同,因而创造出就像世界人口那么多的现实。”(【美国】转引自丹缅·格兰特等:《现实主义·浪漫主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66页。)这么多的现实是如何成为我们所面对现实的一部分的,而究竟是哪一种现实可以成为为大众所普遍理解和接受的现实都成了问题。显然,与我们的生活没有密切联系的现实,不管它多么真实,对我们的生活而言都不具有直接的意义。因此,我们必须设法再现与我们生活相关的现实或者从中找出与我们现实有关的成分加以强化。
当我们力图实现这一点时,一个更严峻的问题就出来了——现实本身是无法再现的。以前,我们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就是用约定俗成的符号将这些现实描述出来,从而默认现实就是我们反映出的那个样子。随着语言学转向的发生,新的问题就出来了。即便是我们自欺欺人地用符号表征现实,这种假定的合法性也受到了根本的质疑。索绪尔结构语言学的关键在于指出了“符号和意义并不像人们一般所认为的,是一一对应、自然而然的关系,能指与所指的关系完全是任意的、约定俗成的。能指与所指的交会是随意的,符号与外部现实不存在先天的、固定的联系。符号的意义不是实然的、本质的,它的意义来自于与系统内其他符号的差异。
树之所以是树,是因为它不是属、熟、住……,不是花、草、人……,它的意义是能指、所指区别的结果”(【瑞士】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4页。)。这也就是索绪尔所说的“二项对立原则”,语言就是这个原则造就的关系的产物,而非实在的代表。“现实是无法再现的……我们不可能使一种多维系统(现实)与一种一维系统(语言)相互对应。”(【法国】罗兰·巴尔特:《法兰西学院文学符号学讲座讲职演》,《符号学原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231页。)二、形象距离现实越来越远,虚构的媒介不可信符号与现实的这种不对应关系,我们可以从对两幅画的解读中得到更多的解释。1929年,比利时超现实主义画家马格利特画了一幅名为《形象的叛逆》的画,这幅画设置了一个矛盾的场面:画面中央是一个巨大的烟斗,而下方则写了一行法文,“这不是一只烟斗”。1966年他又画了一幅更具迷惑性的作品,题为《双重之谜》:画面的左上方有一个悬浮着的烟斗形象,右下方立着一个画架,上面摆着一幅画,就是先前的那幅《形象的叛逆》。据说第二幅画的构思曾受到福柯思想的影响,并且福柯在《词与物》中还专门讨论过关于这两幅画的问题。
而《词与物》这本书据福柯本人所讲乃是令人厌烦的晦涩之书,不过是写给少数对思想史感兴趣的学术界人士看的。现在看来,画与书的关系却变得非常微妙,这两幅画不仅将书中的某些思想具体化而且深化了。书与画的这种关系又构成一个悖论:在画中作者努力要做的是解除形象符号和语言符号之间的确认关系,然而事实上画本身又充当了思想的阐释者的角色。非但如此,画用最具体的方式让思想得到了更普及的传播,以至于无论是画还是书到最后都违背了它们所努力要证明的问题。
笔者认为对这个问题的解答本身就是尴尬的,自从我们发现在形象与符号之间还实实在在的存在人的控制因素,而人本身在我们这个时代是不断受到质疑甚至在被彻底否定时,这个问题就演变成一个令人头痛的三角关系。在形象与符码之间人作为潜在的第三者是逐步被发现,被排斥又不得不被召回的,从《这不是烟斗》到《双重之谜》正好演示了这一变化过程。
在《形象的叛逆》这幅画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明显的矛盾,即画面形象陈述与画面文字陈述之间的否定关系。画面中央呈现出一个巨大的烟斗,这个形象只要你用日常生活经验来判断就知道这是一只烟斗。可是,画家又在画面下方的文字叙述中,给出一个判断句:“这不是一只烟斗。”形象再现与语言再现(叙述)之间如此对立,且彼此抵消。画的形象是肯定的:这是一只烟斗;文字叙述则是否定的:这不是一只烟斗。形象与符码之间明显的相互背叛使我们不得不产生它们之间一定有一方是说了假话的设想。可我们究竟该相信哪一方呢?如果没有经过那么多文明的包装我们会毫不犹疑地相信形象的真实性。
因为“眼见为实”,我们看到什么便是什么。而在文明高度发展的今天,符号已经把我们改造得见到什么都要请示大脑,在符号之网里,我们才更懂得如何与世界交往。符号不仅可以替代不在场的对象还可以纠正或取代对象,那么究竟我们看到的是假象还是符号的描述是假象,这才成其为一个问题。可是这个困惑又是怎样产生的呢?为什么一直以来符号与形象之间的确认关系被默认为合法,究竟是谁赋予的呢?很显然,人创造了符号,在符号与形象之间建构了一种被人可以接受的约定关系。然而,人看到的形象其实只是他所理解到的形象,符号的真理性一直只是作为主体的人一厢情愿的认可。形象应该有它本身的意义,符号也不单是对形象的说明。
在传统的符码认知中,形象与符码是相互确认的关系,形象是对符号的图解而符号是对形象的说明。不错,形象会唤起读者的真实感觉,并且这种感觉与我们见到的事物的体验是相近的,所以一直以来符号作为一种替代不在场的事物成为历史中最鲜活的因素而被人们追捧。但是形象尤其是艺术形象和实物是有根本区别的。形象只是艺术者从他或者她关注的某一点出发,突出对象的某一方面特性。这个形象可能是对实物某一方面的再现也可能是对实物的扭曲,更可能是对对象的变形甚至是否定,而符号总是以判断的方式确证我们所见到的形象。
这样尽管我们运用了符号、形象等因素来认识世界,却一直生活在自我蒙蔽里,把世界本来的样子理解成我们看到的或能感受到的对象的样子。《形象的叛逆》终于让形象与符号作为独立的个体呈现出来,人不再自欺欺人地站在事物的背后充当指挥者,该画明显地反映了形象从符号中解放出来的狂喜。长期以来形象充当图解的作用,人们试图用符号去定义形象的意义而淹没了形象本身,这幅画的特点在于看到了形象可以脱离符号而独立存在,形象就是形象本身。无需符号的干涉,终止了形象对符号的确认功能,也解除了人与对象之间借助符号一厢情愿地感应的关系。
那么,形象与符号的意义又将如何表达呢?在《双重之谜》中我们看到双重危机。形象独立出来以后,获得了释放的快感,但在解放的同时,形象的意义也同时被取消了。我们要了解形象还是要用另一个符号系统来表现,要进入意义的系统形象难免还是要借助符号的帮助。而随着形象的叛逆,符号具有的合法性也被取消了,符号又怎能去解释形象从而表达自己呢?形象与符号要表达自己必须进行新的组合,而这在把自己当为主体的人看来是不能容忍的。
以往人是作为被构想出来的主体决定着他所观察到的对象从而建构了认知体系,形象与符号的随意搭配证实了人不过是多重视角中的一支,从而解散了以人为中心建立起来的符号与形象之间对应的知识体系。然而此后我们该以什么立场去认识对象呢?这又是更大的难题了。我想这也是作者将该画命名为“双重之谜”的原因之一吧,至少表明在当时,他还没有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马格利特的《双重之谜》,利用两个不同的烟斗形象以及它们与其背景的复杂关系,昭示了人作为失去主体地位的旁观者后面临的尴尬。
在《形象的叛逆》中,他让我们看到在形象与符号的关系中,我们始终可以隐约感到有个幕后黑手在操控,就是人好像总是在决定着什么,于是我们欣然地拿掉这个第三者。然而,在《双重之谜》中则表现了当人的主体地位被彻底取消后,我们所面临的更大的困惑。首先是形象与符号谁也不能说明谁却不断自由组合出一个个混乱的场面。当多个符码争着以相同或相反的方式表征同一对象时,我们难以说明对象究竟是怎样的。以前我们还可以找到片面的真实,现在瞬间的真实都将成为奢侈的幻想。其次是多种表现符号指称与实物发生了对立,形象与符号的冲突居然是发生在争议对象实物不在场的语境中。我们什么时候变得可以完全脱离实物而去认识实物了?
在认知体系中,实物是否存在,以何种方式存在抑或根本就是视觉欺骗?符号只是标定了解读的一个视角,而符号越发展我们越是令自己陷入困境。在符号之网中,实在已经变得不那么真实了。而我们周围那些实实在在的对象又绝不是虚无的,为了再次弄清事实,我们不得不召回那个被驱逐了的人。因为在人的世界,人始终是万物存在的语境。
而人的这一特点是通过共同的视觉经验体现出来的。在两幅画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一个明显的事实:形象之下的文字“这不是烟斗”是用法文写成的。对于一个不懂法文的人,这种符号的权力根本上是无效的,这也是一句显而易见的废话。而一个从未见过烟斗的人,这是不是烟斗也不是一个问题。共同视觉经验表明,形象与符号的对应只会发生在有共同视觉经验的同一主体上,形象与符号的对应关系只是一种约定性的合法。一旦超出了这个语境,这本身就是一个假问题。象征论很早就指出,符号的指涉意义是要受到它所属的特定符号系统的制约的。
换言之,意义不是独立自主的,它有赖于特定的符号情境或语境,可见象征关系的发生是要有特定的语境的。其实,主体与万物的交往都是在假定的前提下完成的,主体自身就是认识的盲点,主体既更好地认识了对象,同时对对象的认识又被自我的局限所蒙蔽。从《形象的叛逆》到《双重之谜》,让我们再次强烈地感觉到,在我们所能感受到的世界里,人既是天空也是囚笼。在知识体系中,认识是涅槃式产生的,在“人死了”的喧嚣之后,人的复活也是必然的,在每一次的生死转化中人才成为真正的人。由于“形象”(文本)与现实的距离越来越远,符号的过度繁殖与自我增值,从文本中解读现实的可能性已经越来越小了。符号正在生产甚至是取代现实,现实本身究竟如何存在又该如何言说也就成了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
三、文学表征滞后于现实,虚构的主体不得力
与此同时,知识分子通过文学回应现实的能力也越来越弱,至少失去了表面的号召力。2001年由《上海文学》发起的“纯文学”的讨论再度提出了文学如何介入现实的问题。2001年第3期的《上海文学》发表了李陀的《漫说“纯文学”》一文,该文对“纯文学”的概念进行了历史性的反思并针对当下文学现状提出了批评。随后《上海文学》组织了系列文章对此回应(见《上海文学》,2001年,第3期至第9期。)。
此后,《上海文学》的执行主编蔡翔也发表题为《何谓文学本身》的文章,对“纯文学”与当代文学的发展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思考(见《当代作家评论》,2001年,第6期。)。这次讨论的出发点是检讨面对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发生的深刻变化,文学的回应显得相对贫弱的问题。当下文学似乎丧失了对现实发言的热情,也无意于和历史对话,如童庆炳先生所说文学面临着历史和理性的双重缺失,从而文学介入现实的能力大大减弱。面对这样一种现实,文学表征现实的有效性也大打折扣。于是,文学究竟该以一种什么样的姿态来介入现实,作为描述文学与现实关系的“现实表征”
该如何言说就必须要重新进行思考了。
十九世纪经典现实主义对人与社会现实关系的重视,对环境、历史氛围、人物命运不屈不挠的追问,都是值得我们汲取的宝贵文学遗产,但它并不意味着现实只能用写实的方式来呈现。知识分子要想继续保持文学回应现实的能力,重要的是找到切合他对现实的体悟与洞察的最适当的形式,不管它是现实主义、现代主义或是他所发明的什么都不是的名称。创造深刻描述现实的文学形式,就是文学知识分子介入现实的最有力的方式。
文学虚构的对象不清晰,虚构的媒介不可信,而虚构的主体又比较疲软共同造成了文学表征滞后于现实的现状。文学要想获得新的发展,必须从研究文学表征现实的特殊性出发,从而为文学实现有效言说提供某些途径。如果只强调文学表征现实的现实性则容易陷入就事论事的肤浅,从而令文学沦为社会生活的记录或者说是“时代的传声筒”;同样,只关注文学表征现实的虚构性则容易让其成为失去现实依托的狭隘纯粹的个人精神游戏,对文学的发展都是没有好处的。可见,关注文学表征现实的现实性和虚构性是同等重要的,这就是当下文学发生的现实语境,也是重新研究“现实表征”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