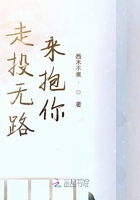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
——明·汤显祖
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
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
生而不可以死,死而不可复生者,
皆非情之至也。
梦中之情,何必非真?
天下岂少梦中之人耶!
——明·汤显祖《牡丹亭·作者题词》
公元一九一三年六月徽州·渔梁
在黄临渊的梦境里,徽州是一幅淡爽的山水画,白描出的粉墙黛瓦,浓墨重彩的四季繁花,都是遍野媚惑人的风情。
可以入梦的风情,便是缭绕于心、不得解脱的。于是,他不远千里万里的来了。
那夜行的渡船沿新安江一路浅摇慢划,艄公将一竿竹橹斜斜插进水里,然后泼辣地吆喝一声,荡漾着一抹清白月色的江水便划开了一脉柔波。
前方是渔梁坝,在那里上岸,临渊想徒步走到宏村去,在几十里的逼仄山路上走走停停,顺便画些不着色的写生。
在写给巴黎导师的信中,他戏谑自己是到深山野冢间放生去的,说他要完成一次性灵的回归。其实,对于这片僻静、偏远的故土,从未谋面的他又知晓些什么?说他是来此猎奇的,或许才更贴切。
艄公的脚边燃着一盏昏朦的渔灯,三五只飞虫撞着乌吐吐的玻璃罩子,梦游似的啄着明灭不定的如豆灯火。
飞虫的头顶衔着一点跃动的光,那是突兀圆瞠的眼,细小而又锐利,亦如艄公在临渊身上来回琢磨的那一双。
临渊见了,颔首一笑。也难怪艄公会这样看他,这一身精工细做的洋装一旦融入了闲淡的清山秀水,让他也感到好不自在。
多年不曾回国的他,已不了解国内当下的局势。在上海租界寻亲访友的那几天还说得过去,长辈守旧的长衫、旗袍可以不予理会,身边一色的青年,又有谁不是攀比着招摇。
此刻已有些更漏人初静的意味了,临渊向艄公打听,船儿何时才能转入练江?艄公伸手含混地一指,“前一个洲头便是入江口,行不了多远,龙船坞就到了。”临渊听了,略一点头,又轻声道:程伯早等得心急了吧?
程伯是父亲黄秋水的旧乡邻,俩人青年时曾结伴到上海经商,可几年后,程伯因轻信他人,蚀尽了家底,再没振作起来,万般无奈之下只好回乡开起了相馆,不曾想,生意反倒日渐兴隆。
多年后,他又在渔梁的老街盘下两处店面,贩卖起上海时兴的洋装,乡下老户人家的太太小姐有了新式的打扮,便想着留个纪念,于是又来相馆拍照,生意人的精明真让程伯做到了极致。
而此番,临渊之所以舟车劳顿地赶来,就是为了寻访十年前,最后一次还乡的父亲在这里,和咫尺之遥的宏村留下的一番行迹。
临行前母亲曾一再叮嘱他,一定要先在渔梁落脚,好去拜访疏远多年的程伯,因为了解当时详情的人,如今也只有他还在世了。
船儿在清寂无人的江面上行至深夜,时逢盛夏,夜雾般的蚊虫猖獗得活像一头狂野叫嚣的巨兽,临渊却连驱赶的念头都没有,他只是一味沉溺在内心难言的苦闷中,嘴上还有一句没一句地跟艄公搭着话。
“也不知明天是怎样的天色,我起早奔赴宏村,入夜前总能赶到吧。”
艄公“吼哟”了一声,劝他道:“徽州这地方,多的是穷山恶水,少的是平路良田。前几日暴雨引发了山洪,把落脚的地方冲得一处不剩,明天日头一出来,你只管放眼去瞧,哪里会有什么路哟!你既是头一遭来,这不成全人的节气就由不得你了,不急的话还是多等几日,眼瞧着山洪褪了,道路干了,你还得找个乡亲结伴行走,不遇风雨的话,也总要两三日吧。”
临渊转头,向横陈在浓云密布的天幕下的远山眺望了一眼,那黛色的山影有着少见的柔美轮廓,在此刻静谧的夜色里,实在看不出艄公所说的险恶,倒更像一位安然入梦的处子,有着一种撩拨人心的媚态。
凉爽的江风吹来遍野的古树独有的馥郁香气,以及入夏后绚烂于每一处绿荫中的繁花袭人的醇厚气息,让临渊一时发作的焦燥也被轻易地化解了。
他抬起右臂,在夜空中划出一道优雅的弧线,一根芦苗般修长的手指缓缓向远山伸去,想是要去亲近,可嘴里又带着几份打趣似的轻挑,向艄公问道:
“听家父说,六月的徽州已过了梅雨时季,泛溢的江水平息后,便是数月的烈日当空……”
艄公不以为然地把嘴一撇:“今天的雨水充沛得出奇,早春撒在地里的种子已经泡烂了,荒草倒是着了魔似的疯长,一夜之间就能蹿起一人高!”艄公的话像直泄的江水,没边没际地漫延开来,临渊知道他是深夜行船,奈不住困倦,就借着没滋没味的聒噪在强打精神,便微微含笑,任由他忿忿不平地说下去,“世人都说徽州是七山一水一分田,好像多有风光似的!要我说:前世不修,才会生到这儿来,长不到十三四岁,便丢出家门。小小年纪就要出外经商讨生活,随身带的除了充饥的徽饼,只有三根绳子,说是这样就能万事不求人!如果只是包袱破了、扁担断了,那还好说,碰上走投无路的时候,也只能用来上吊了!”
“原来是这样……”临渊心灰意冷地应了一声,之前那么多天难耐而又热切的憧憬都被这一番话仓皇地驱散了,好像那一切也不过是一片美妙而又轻飘的泡影。
“你来得还真不是时候!”艄公又找补了一句,临渊那一脸的沮丧倒让他很意犹未尽似的。
“是啊,真不是时候……”忽然,他又自嘲似的笑了,“可能我压根就不该来!”
“那你又是为何而来呀,走了一路却没听你提过。”
“我……”临渊半仰着头,难堪地咬住下唇,这令他苦闷了一路的原由真不是轻易就能出口的。一想起这些,他的脸上又泛起了一阵羞愧的燥热。
“像你这样腼腆的后生还真少见,愧你还是从上海来的,如今大户人家的少爷可不是你这种做派喽!”
临渊暗自叫屈,他这哪里是腼腆,分明就是有口难言呀!
临渊向来乐于跟人亲近,心思又过于敏感细腻,跟艄公从换乘的渡口一路聊到这里,早已像老熟人一样,很有些无话不说的意思了。
这会儿,见艄公因为自己支吾着不知该怎么做答,以为是不想跟他说,就带着几分不快扭过头去,临渊便慌张地撩了撩被夜风吹到眼前的长发,又多此一举地“嗯”了一声,正要随便找个话题,再去跟艄公攀谈。
可紧接着,他却冲不远处的岸上惊叫道:
“那是谁?”
艄公被临渊的叫声惊到了,竹橹在手里一滑,险些掉进江里,他慌乱攥紧,也转头看去,只见岸上立着一个朦胧的身影,苍白得像一缕凝然不动的烟尘。
“看着像梅老板……”“
“梅老板?”
“他是昆曲班子的教习。”
“渔梁也有昆曲班子?”临渊着实吃了一惊,沿途他听到的除了村野的小调,就是牧童的笛声,而清雅的昆曲向来是废尽人的情趣与耐心的,这里的乡亲们又如何听得了?
艄公也是一脸的不以为然,甚至带着几分不解的怨气对临渊道:
“早先是没有的,还是这位梅老板多方张罗,才汇集起一批人,办起了戏班子,后来又在渔梁长驻下来,别的乡镇也很少去。可你说这有多希罕,根本没几个人听的玩意儿,却在我们这儿唱了十几年,亏了徽州的地界上别的没有,戏台可随处都是,你走不出十步就有一座,还都像天宫似的,要多堂皇有多堂皇。那就随他们折腾去吧,我们也只当看那不要钱的热闹,凑不打紧的趣!可台上唱得再起劲,我们也只是在下面捂着嘴笑,谁知道他们咿呀呀,一个字拖上一顿饭的功夫到底在说道些什么?”
临渊又去看那个人,也瞧不出他穿着什么,只见白惨惨的一抹在身后飘出了好远。
“您慢点儿划。”
“要不要靠过去?”
“我不想平白打扰了人家……他手里拿的什么,怎么还泛着光?”
“哦,那是一盏琉璃灯,离得远了,您看不清。”
“这么晚了,他在等人?”
“谁知道呢?不过,他好像也往这边瞧呢!”
“哟,可不是!”
随着渡船一点点向岸边靠去,临渊已看清那提灯的教习,真的也在向这边张望。映着白晃晃的灯光,临渊看到了一张近似惨白的面容,可那张脸又是如此的精致,就像用极细的利器在一块温润的玉石上一点点雕出的,让临渊在初看之下也感到了一阵莫名的心惊。
而他的身上又似乎凝结着一股寒气,内敛,却又直袭人心,会让人在与他目光相对的一瞬间感到心头一紧,瑟缩得像要窘迫地躲藏。
可这样罕见的俊美之中又混杂着一种逼人的妖媚,这就更令临渊感到匪夷所思,他把身子尽量向前探去,想要看得更清楚些,可猛然间他又像受了不知来历的袭击似的,慌张地躲进了渔灯照射不到的船头的阴影里:“他在看着我!”
那样锐利而又执着的目光他从未见过。
“难道他在等我?”临渊暗自发问,不过这令他感到的可笑要远胜过疑惑,“怎么可能呢,我们素未谋面,他又为何要深夜在此等我?”
临渊刚想到这儿,就见梅教习转过身去,动作是那么的漫不经心,那盏闪着柔和白光的琉璃灯在他的身前鬼魅似的晃动着,好像早已迫不得已地想要离去。
一闪神的功夫儿,他已踏上泛着水光的青石板,离开岸边也有十几步远了,“走得还真匆忙。”
临渊望着那渐渐远去的背影,梅教习身上那件不知名的着装白得像是透了明,夜色一点点渗入,像在沁染着他,最后竟一下子不见了踪影,恍若被一只藏在暗处的巨手无声而又轻易地抹去了。
临渊将这一切看在眼里,只感到一种说不出的诡异,他抬手捂住心口:“这位梅老板还真是……”
“让人捉摸不透。”
临渊怔怔地点了点头,艄公看不出他在想什么,又不好多问。过了一会儿,却冷不防听他问道:“宏村有座闻名的戏台,你可知道?据说,富商汪紫陌衣锦还乡那一年,曾花费十万两黄金,在那戏台上连演了三天的全本大戏《牡丹亭》……”
艄公把竹橹在船梆上一磕,吆喝道:“谁不说呢!老年间的事儿,不能想啊!那是金砖金瓦搭的戏台,金箔金片裁的衣裳,金粉金沙描的脸面?整整十万两黄金,一台戏!该是怎样的排场?不能想哟!”
艄公的憨态又把临渊逗笑了,他接着问:“您天天在这江上周游,听闻八方事,迎送千处客,我向您打听一句,那戏台如今还在么?”
艄公想也不想,赶忙订正道:“你该问那座宅院还在不在!比起一方名胜‘碧落轩’,那戏台就不值一提了,一处消遣的陈设而已。”
“还在么?”临渊笑盈盈地看着艄公,故意问得漫不经心。
“在是在,”艄公叹息了一声:“不过破败了。满园子的雕梁画栋、亭台水榭,也都被虫蚁糟蹋了……汪紫陌回乡那年是何等的风光?碧落轩的流水席摆到了月沼池边,恨不能把那池子里的水漂净,全盛满了酒!可谁能料到……唉!”
临渊听到这里,也有些黯然。艄公在一旁打量着,似乎看出了他的心事,便叫了一声,“你是去看那戏台的?”
临渊迟疑着点了点头。
艄公“哟”了一声道:“来之前你怎么不打听清楚?那里早就荒废得不成样子,去了怕要失望的!”
“我……也是来找人的。”
“是那汪家的人?”
见临渊点头,艄公又叫道:“可那家人早就散光了!还有那宅子,已经空了十几年,根本进不去了!”
“您怎么知道?”
“前年我载过一位绩溪的道士,说去那里驱鬼,回来时在龙船坞一处闲扯了几句。听说那宅子里早年屈死过一个偏房小妾,也真凑巧,就是唱那出十万黄金大戏的女戏子,汪紫陌暴亡后,受不了另外几房的排挤,没多久就溺死在了一片池子里。打那以后,女戏子的冤魂便时常在院子里出没,尤其瘆人的是,还总是哼唱着戏里的曲子,在园子里游荡。邻近的几户人家实在不堪其扰,就凑钱请来了道士,可道士推开院门便傻了眼,哪里进得去哟!荒草蔓过头顶,甬道上的石板被草根一片片拔起,手腕粗的长虫在那缝隙里伏地而行,从脚边擦过,就像吹过脊背的一阵冷风!除非点一把火,否则根本无从下手清理。为难的是,那园子后来异了主,乡亲们只知道是被一位黄姓茶商花了四万大洋买走的,至于那黄姓茶商现在置身何处,又根本没处打听。万一这火烧起来,损失了宅子里的东西,那又如何交代,所以最后也只好作罢了。”
临渊喃喃自语似的接口道:“如此一来,又让我到哪里去找?”
艄公见他失落的样子,虽不知他要找什么,也禁不住叹了口气:“找不到了,听说那小妾的女儿命运更不计,后来沦落到青楼,做了雏妓,为的就是给母亲立一座牌坊。黄姓茶商是为给她赎身后,让她有个落脚的去处,才买下那宅子的,可没过多久,她也不知了去向。”
一听到“牌坊”这两个字,临渊立刻从暗地里探出头来,“那牌坊还在么?”
“在是在,不过……那也是宏村立的最后一座,说是贞洁牌坊,可因为是立给一个女戏子立的,乡亲们也一直颇有微词,要不是那牌坊实在气派,为村里人也攥足了体会,怕是早就被人推倒了呢!”艄公说着,又厌嫌似的撇了撇嘴。
一看到艄公的表情,临渊就像被什么激到了似的,胸中猛然腾起一股无名火,直顶到喉咙,让他不吐不快:
“我知道,这些妇道、贞洁一向是你们徽州人最讲究的,可你们有没有为那些女人想过?她们嫁人为妻,之后却要独守空房几十年,葬送了大好的青春,埋没了所有的情感,指望的不过是身后的一座牌坊。可那牌坊又是什么?几块冰冷的玉石,一个孤苦终生的名讳,又与立在坟前的墓碑有何区别?而写在上面的‘贞洁’就像那所谓的墓志铭!”
临渊深吸一口气,想要平复激动的情绪,可他发现自己根本做不到,因为接下来他就想起了儿时长住的扬州,那是客居他乡奔走经商的徽州人最集中也是最向往的地方,可他们向往的又是什么?一想到这些,临渊就感到一阵心痛,
“你到过扬州么?那些妻子在家乡望眼欲穿,等待回还的夫君,在那里过的又是怎样的生活?人说‘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人生极乐,风月情场,直教人贪生忘死,狠不能忘却了前世今生!想一想这两种人生的对比,用一生的留守去换取一座牌坊,你还认为这是一种奢求?再说宏村那一对母女,她们身世的可怜之处你为何不想?要知道,碧落为母亲立起的牌坊可是用她最宝贵的清白换来的!而她这样做,完全是在效仿她的母亲,那位名叫胡珀的小妾早年是为了安葬父亲,才卖身做了戏子;十几年后,她的女儿又为了给母亲立一座象征贞洁的牌坊,卖身做了雏妓。你就不觉得这样的献身真是感天动地、可敬可叹的么?”
艄公面红耳赤地站在那儿,一脸愕然地瞪着临渊,这一顿驳斥让他有些气恼,但那是一种由衷的羞愧,临渊说的每一个字都像一击惊雷,在他的头顶震聋发馈地炸响,他从不曾想到,女人为丈夫守节,这样一件再天经地义不过的事儿,原来也是一种伟大的献身?
“你这后生不得了啊!你这话是咋想出来的?简直像叫魂似的,把我也鬼使神差地说服了!不过啊,我还是好心提醒你一句,你这话跟我讲不打紧,但到了宏村,你可要把自个儿的嘴管住了,不管在那里看到什么,或是听说什么,这种话千万都不能讲啊!”
“为什么?”
“你可知道宏村汪氏族长,汪敬亭的厉害!现在虽说是国民了,可在徽州,凡事还都要听凭族长的发落,而这个汪敬亭在宏村,那可是一手蔽天啊!你只知道当年的汪紫陌是富甲一方的徽州总商,在两淮,甚至大半个江南,那都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人物,但你可知道这汪家是怎么败落的,那汪紫陌又是怎么暴亡的?说到底,就因为他娶回了那个女戏子,让他们汪氏宗族都跟着蒙羞了啊!”
“娶一个女戏子做偏房,这不是再寻常不过的事么?”
“但你可知道那女戏子是怎么沦落到这般地步的?她怎么会为了葬父而要卖身啊!”
“这我就不知道了……”
“她的父亲当初可是南湖书院的学监,她家祖上曾出过三位翰林学士呢!可就因为……”
“就因为什么?”
“就因为她父亲一次酒后无德,玷污了族中一位长老家少奶奶的清白,长老得知此事后羞愤难当,当即便口吐鲜血一命呜呼了,长老的家人抬着尸首吵吵嚷嚷闹到祠堂,定要让族长主持公道,这是汪氏宗族百年不曾出过的丑闻啊!族长当然不会善罢甘休!但你知道他使出的是什么手段?”
临渊已经预感到,那将是他不能想象的强硬与残忍,所以他呆坐在那儿,只是摇了摇头,但脸上已写满了悲愤。
艄公长叹了一声,也有些说不下去了似的,“族长先是命人将那位姓胡的学监拖进祠堂,一桶冷水兜头浇下,看他醒将过来,就命人将他绑在猪笼里,推到街上,任凭恼怒的乡亲唾弃、殴打,直到天色将晚,猪笼已被劈成了碎片,而那胡学监,也已倒在月沼池边,那副衣不遮体、皮开肉绽的惨相啊,真叫人不忍目睹。可你说他的女儿有多泼辣,她父亲刚被拖入祠堂,她就疯了似的追过去,在享堂里当着列位汪氏先祖的牌位和族中大小长老的面,居然口口声声说,她父亲与那位少奶奶是情投意合、两情相悦,根本就不是她父亲酒后无德,玷污了人家!族长早已怒火中烧,哪里会听她的申辩,叫人把她哄了出去,她转头就冲进那位长老家,拖出那个已半傻掉的少奶奶,到月沼池边让她为父亲平反昭雪。少奶奶哪受得了这等羞辱,要不是乡亲们死命拉住,她直要跳进月沼了断了自己!这么一来,乡亲们被激怒得更甚了,劈头盖脸打向那胡学监,连一点起码的斯文都不顾忌了!”
“可族长为什么不先审问胡学监,他这样听信老长家人的一面之辞,真有可能冤枉了好人啊!”
“其实,谁心里都犯嘀咕,你说胡学监一位饱学之士,依照情理真不该是这等人面兽心的货色。可就算他女儿说的都是实情,他与少奶奶干出这等苟且之事,也是族规所不容的呀!所以啊,胡学监头一天暴尸在月沼池边,第二日那位少奶奶就被家人沉入了后院的深井!你可知那是一种怎样的死法?那种井里的水并不深,挖在宅院之中最隐蔽的地方,就是为了惩戒这种有羞门楣的妻妾!把她们绑牢了手脚,再扔进深不见底、阴气袭人的井里,如果一下子摔死了那还是造化,可十之八九只是断手断脚,之后井口就被一块石板封住了,留下来的就只有无边的黑暗与疼痛,那人在井底总要受尽四五天的折磨,才会慢慢地死去……”
“别再说了!”
“唉,不怪你听不下去,我也实在是说不下去了。但你现在总该知道,那小妾为什么要把自己卖到扬州去,才能安葬自己的父亲了吧?她可是扶着灵柩,一路走到那里的啊,村里的乡亲没一个人为她送行,更别说帮她一把,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女子,走上千百里路,只为了给父亲寻一个安身之处,如今想来,也的确令人动容啊!”
“也就因为她父亲这一段无头案,汪氏族长就容她不下,甚至要以败尽一个汪家为代价来清除她?”
“是,也不是吧!唉,这汪家里的蹊跷事,自打汪紫陌执掌门庭那天起就没断过。不光是宏村人,这徽州一府六县的百姓谁不把他家的事像一本热闹天书似的传扬,所以这年头一久啊,真真假假掺合在一起,也就捋不清了!不过有一点倒是错不了的,那就是这汪家啊,如今看来虽然破败了,人口也散尽了,但谁都知道,他家那份富可抵国的家财可是一分也没失散掉,但你可知道这样一笔天大的财富被谁牢牢地攥在手里?”
“我怎么会知道?”
“就是族长汪敬亭啊!”
“怎……怎么会是他?”
“就因为汪紫陌无后,为了在身后安置好偌大的一份家业,他才把一切都托付给了汪敬亭,可谁曾想他刚在祠堂里一怒而亡,汪敬亭就下手逐尽了他的家人,把一座碧落轩占为己有了不说,说连汪紫陌身前许诺给各房妻妾和两位女儿的钱财也被他揽入了自己的腰包,一个子也没给那一家人留下!”
“身为一族之长,他这不是在以公谋私么?”
“但说来也怪,得到这笔家产后,族长却分文未动,这么多年来,族中的账册上始终清清楚楚地记载着入库的这笔巨款,而族长更是对它严加看管,每年都要亲自核实一遍。”
“那他这么做又是为了什么?为自己招置了一身骂名,却一点好处都没有落下!”
“谁不说呢,真叫人弄不明白呀!”
“那如今这汪家就一个后人也没有留下?”
“有是有,不过是一个疯子。就是汪紫陌的大女儿清卓,父亲暴亡后,她母亲在黄山殉了情,倒是保全了自己的名节,可她的丈夫也在几天后离奇死去了,之后又遭逢了太多的变故和打击,她一个弱女子如何承受得住?汪敬亭一味逼她殉夫,她也一心想死,可几次三番又都绝处逢生,令所有人都啧啧称奇!老天爷是不想绝她的命,可她早已生不如死,最后到底是在村口的牌坊下疯魔了,而那九座堂皇的贞洁牌坊可是她父亲在世时就已为家中的妻妾和她这个女儿立好了的,你说,这岂不又是汪家的一桩奇闻?”
“是啊,哪有丈夫为还在世的妻妾和女儿立牌坊的,难道是他早已料定了自己的结果,才这么做的?可又不对了啊,既然汪紫陌已经立了牌坊,碧落为什么还要卖身为她的母亲再立一座?”
“就因为族长和各位长老百般阻挠,不肯让汪紫陌为他珍爱的小妾立这座牌坊,他才在祠堂中好一番声讨和顶撞,最后暴怒而亡的呀!”
“想不到这位汪老爷如此的重情重义,真着实让我敬佩啊!”
“这话也只有你敢说,徽州人直到今天提起这件事还笑他死得好不值哟!就为了一个偏房小妾,还有那样一番不堪的身事,他竟把一切都抛却不顾了,拼命也要为她争一个贞洁的名讳!可在徽州人的眼里,一个女戏子就算嫁为人妻,就算再如何有操守,她又哪里有什么贞洁可言啊!”
“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父亲在临终前要留下那样一封信给我。他要我无论如何都要回到宏村,找到碧落,将她好生安置后,再为她立一座贞洁牌坊。他这是在效仿汪老爷啊,但由此可见,他也像汪老爷一样是真心珍爱碧落的啊!”
临渊喃喃自语着,他是被艄公讲述的那一番陈年旧事完全的震住了,此刻他的内心翻涌着太多的情绪,都是那么的激烈而又矛盾。要知道,十几岁就远赴异国求学的他是无论如何都无法理解这一段段支离破碎的人间惨剧是如何生成,又为何上演的。也因此,他感到的愤怒、悲痛,受到的触动、震撼才是最为真实而又深刻的,而这一切更是眼前这位生于徽州长于徽州的艄公终其一生都无法感受和体会的。
所以,当他隐约听到临渊的自语时,他冲口而出的就是一声足以震碎整片深沉夜色的惊叫:
“你在说什么?原来你去宏村是要为汪老爷的小女儿立一座牌坊,那你就是……”
“我就是那位买下碧落轩的黄姓茶商的儿子。”说到这儿,临渊忽然倍感释然地一笑,在他内心郁结了一路的苦闷似乎都被悄然化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