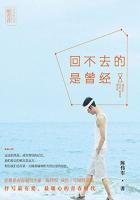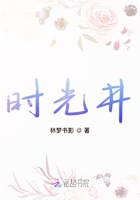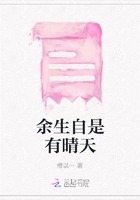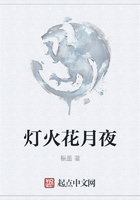在小说艺术的探索上,一些作家受到诸如福克纳、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启发,把对于生活情景、细节的真实描述,与象征、寓言的因素加以结合。在一些作品中变换叙述方式,以“现在时”和“过去现在时”的叙述来处理历史,在叙述者和故事人物,叙述时间和故事时间上构成复杂关系,以此来强化叙述的意识。采用以现代意识,来审察中国传统小说并作为主要借鉴的艺术方法,也成为一种潮流。这种艺术方法,首先表现为小说整体情调、气氛的营造的重现。其次,在小说语言上,或者向着平淡、节制、简洁的方向倾移,或者直接融进文言词汇、句式,以加强所要创造的生活情景和人物心理的描绘。另外,小说的章法、结构、叙述方式,都可以看到向古代小说取法的情况。汪曾祺、贾平凹、阿城等,都曾广泛运用过这样的艺术手段。
百姓生活小说
在80年代,小说观念、小说创作都发生了重要变化,小说创作的“农业题材”、“工业题材”等概念逐渐被废弃不用,“市井小说”、“都市小说”、“乡土小说”、“乡情小说”等反映普通群众实际生活的小说替代了这些反映一个特定时期的小说。列入“市井”和“都市”一类的创作,有邓友梅、陆文夫、冯骥才、刘心武的一些作品,而归入“乡土”、“乡情”一类的,则是高晓声、汪曾祺、刘绍棠、古华、张一弓、路遥、陈忠实、贾平凹、张伟、矫健等几乎所有写乡村生活的作家。因为反映不同的地域特色,作家的类型被划分为“京味小说”、“津门文化小说”、“齐鲁乡土作家”等名目,或从文化格局的中心与边缘关系上,作出了“湘军崛起”、“陕军东征”的描述。
邓友梅因1956年的描写青年人婚外恋情的短篇《在悬崖上》而引起争论。“文革”后的小说,主要分为“写北京的和写京外的”。京外小说有《我们的军长》、《追赶队伍的女兵们》、《凉山月》、《别了,濑户内海》。引起文学界注意的则是北京小说:即《话说陶然亭》、《寻找画儿韩》、《那五》、《烟壶》、《索七的后人》、《“四海居”软话》等。其中,分别塑造不同性格、走着相异生活道路的八旗子弟形象的《那五》和《烟壶》,是他这类小说的代表作。这些作品的主人公(皇族后裔、八旗子弟、工匠艺人、落魄文人),大多联系着传统文化的某些方面,同时又在19世纪末期以来急剧变动中,与社会大潮发生激烈冲突,而处于社会的边缘。在人物命运的叙述中,穿插各种风俗民情、仪式礼节、典章文物的细致描写。在他的小说中,社会风俗的描写,是人物命运的组成部分,并成为推动情节和人物发展的内在动力。邓友梅以温和的态度处理人物之间的矛盾冲突,避免过分和外显,这使各种冲突的因素得到平衡的控制。但“平和”也会走向“平淡”,人物命运悲剧色彩受到削弱,影响了面对历史和现实时的体验深度。邓友梅运用经过提炼的地道的京白作为小说的语言,在叙述上,能做到从容却不拖沓呆滞。
冯骥才“文革”后一段时间的小说,主要写与“文革”有关的题材。影响较大的中短篇有《雕花烟斗》、《铺花的歧路》、《啊!》、《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感谢生活》等。他在写残酷历史和非人遭遇时,常表现人与人之间的温情,以作为苦难生活的寄托。1984年的中篇小说《神鞭》主要写清末民初天津的“闲杂人和稀奇事”,写出了“地道的天津味”。因此,评论家称这些小说为“津味小说”。除《神鞭》外,还有中篇《三寸金莲》、《阴阳八卦》、《炮打双灯》和系列短篇《市井人物》。它们中的相当部分,取材于那些“文化遗迹”:男人的辫子,女人的缠足和道家的阴阳八卦等。在他的小说中,人物的命运、生活方式和这些“文化”现象有密切关联,甚至人物就是某种“文化”的化身。小说体裁常采用章回体,并以天津方言、俗语作为小说语言的主体。在描述这些“文化遗迹”时,作者表示是在“沿着鲁迅先生对民族劣根性批评的路走”,同时,企望以历史的眼光来廓清复杂、丑陋现象产生的根源。其中,《三寸金莲》是一部存在较多争议的中篇。作品试图揭示女性缠脚这一陋习产生的历史文化的依据,探索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这一丑恶现象最本质的根源。冯骥才在写作这些“怪世奇谈”的小说时,会考虑加强娱乐性的传奇因素。他不愿放弃严肃的思想批判深度,不过这种批判又相当有限。
贾平凹因在1983年以后陆续发表的有关陕西商州地区农民生活变迁的小说引起了文学界的注意。这些作品是被称为“商州系列”的《小月前本》《鸡窝洼人家》、《腊月正月》、《远山野情》、《天狗》、《黑氏》、《古堡》、《火纸》和长篇《商州》《浮躁》。作者说,“欲以商州这块地方,来体验、研究、分析、解剖中国农村的历史发展、社会变革、生活变化”。小说中,以陕南山区农民生活为背景,通过对自然和人文景观的描写,展现了80年代中国农村进行的经济改革,农村发生的剧烈变动,以及在改革过程中不同价值观的选择和相互“较量”,这是这些小说持续开掘的主题。小说重点描写了社会转折期出现的“悲剧人物”,在经济改革发生以后,他们原先的社会地位和在世人面前所树立的形象发生动摇,陷入恐惧,但他们仍坚持原有的生活准则,想挽救将要失去的东西。作者描写了他们必然“被剥夺”的命运,但也给予了深切的同情。因此,也使他这部分小说难以摆脱视域上的单一性,故事不免重复。90年代初开始,贾平更重视作家的人生体验,抵拒了宏大单一的主题的诱惑。这一思想变化,体现在他的有极大争议的长篇《废都》中。
以古城西安(小说中的“西京”)为人物活动场所的《废都》在1993年出版,是当时小说界和文化界引人注目的事件。这部表现作者所说的苍茫、悲凉的“废都”意识的小说,被一些批评家誉为“深得‘红楼’、‘金瓶’之神韵”,“内容到形式都颇为惊世骇俗”之作;认为在人物刻画上形神兼备,“几近炉火纯青”,标志作者的走向成熟。贾平凹的小说,在叙述方式、语言风格和艺术韵味上,力求对于中国明清白话小说艺术的吸纳,在文体上力求形成自然、含蓄、富内在韵味的格调。
莫言1985年在解放军艺术学院学习期间,发表了《透明的红萝卜》。次年,中篇小说《红高粱》的发表,产生很大反响。随后,他又写了与《红高粱》在故事背景、人物等有连续关系的几个中篇,它们后来结集为《红高粱家族》。这些小说,主要以对小说中的故乡高密的记忆为背景展开。《红高粱》系列,以及发表于1995年的长篇《丰乳肥臀》,表达了作者对于中国民族的骁勇血性的寻找,他所营造的图景,来源于他童年的记忆,在那片土地上的见闻,以及他的丰沛的感觉和想象。在这片充满野性活力的生活场景上,叙述了“我的爷爷奶奶”奔放热烈的生命和无所拘束的传奇性经历。他的另一些小说,写当代的乡村生活,农民的情感、生存状态,人的本性所受到的压抑和扭曲。如《透明的红萝卜》、《金发婴儿》、《枯河》等。他的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作品构成鲜明的对比,隐晦地批判了“后代”的怯懦、孱弱。
莫言的小说,表现了富于感性化的风格。他的写作,采用一种不受控制的、重视感觉的叙述态度。在描述中,心理的跳跃、流动、联想,大量的感官意象奔涌而来,展现出一个复杂的、色彩斑斓的感觉世界。这种强烈的感性体验的写作方式,与作者对于带有原始野性生命力的向往有关。
“先锋小说”
1985年前后,是小说界创新意识高涨的时间。这一年,一些作品进行了先锋性探索,如韩少功的《爸爸》,莫言的《红高粱》等。但由于文学“寻根”所涵盖的创作,从艺术思维和表达方式看多样而复杂,因此,作为文学潮流,它一般不被统一地作为“先锋”文学看待。真正被评论家看作是“先锋小说”的起点的是马原的作品。
“先锋小说”(或“实验小说”)在开始阶段,重视的是“文体的自觉”,即小说的“虚构性”和叙述方法上的意义和变化。马原发表于1984年的《拉萨河的女神》,是大陆当时第一部将叙述置于重要地位的小说。他的小说所显示的“叙述圈套”在那个时间成为文学创新者的热门话题。后来他陆续又发表了《冈底斯的诱惑》、《西海无帆船》、《虚构》《康巴人营地》、《大师》等作品。洪峰受马原影响,依循马原写作路线相续发表了1986年的《奔丧》,1987年的《瀚海》、《极地之侧》。但洪峰的小说不仅限于“文体”的实验,而有着对于“叙述”与“意义”关系的探索:这是马原最初的小说所着意回避的。
在1987年间,这种创作,成为一股潮流。除了马原、洪峰外,这一年“先锋小说”的重要作品,有余华的短篇《十八岁出门远行》、《西北风呼啸的中午》,中篇《四月三日事件》,格非的《迷舟》,孙甘露的《信使之函》,苏童的《桑园留言》、《一九三四年的逃亡》、《故事:外乡人父子》,叶兆言的《五月的黄昏》。在此后的几年里,上述作家还发表了许多作品,如余华的《现实一种》、《世事如烟》、《劫数难逃》,苏童的《罂粟之家》、《仪式的完成》、《妻妾成群》,格非的《没有人看见草生长》、《褐色鸟群》,孙甘露的《访问梦境》、《请女人猜谜》等。
重视“叙述”,应该说是“先锋小说”开始最引人注目的共同之处。作家们关心的是故事的“形式”。他们把叙事本身看作审美对象,运用虚构、想象等手段,进行叙事方法的实验,有的则把实验本身直接写进小说中。马原明白地指出他的小说就是一种编造,“我就是那个叫马原的汉人”是经常在他的小说中出现的句子。在他一篇名为“虚构”的小说里交代小说材料的几种来源。在讲述故事时,只是平面化地触及感官印象,而强制性地拆除事件、细节与现实世界的联系。这种写作,一开始就给小说界带巨大的冲击。它们拓展了小说的表现力,强化了作家对于个性化的感觉和体验的发掘;同时,也抑制、平衡了当代小说中“自我”膨胀的倾向。
当然,“先锋小说”那些出色的作品,在它们的“形式革命”中,总是包含着内在的“意识形态涵义”。它们对于“内容”、“意义”的解构,对于性、死亡、暴力等主题的关注,归根结底,来源于中国社会性会现实。“先锋小说”总体上的以形式和叙事技巧为主要目的的倾向,成为它的局限性并使其不可避免地走向形式的疲惫。“先锋小说家”很快分化,他们的创作也不再作为有突出特征的潮流被描述。
残雪是早期的“先锋”小说作家,作品主要有《山上的小屋》、《苍老的浮云》、《公牛》、《我在那个世界里的事情》、《阿梅在一个太阳天里的愁思》、《黄泥街》《天堂里的对话》、《突围表演》等。她的小说将现实与梦幻加以“混淆”,以精神变异者的冷峻感觉和眼光,创造了一个怪异的世界。乖戾心理的描述,将读者带入精神欲望的内心世界,展示了在特定社会文化环境中人性的卑陋、丑恶。残雪主要关注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内容:他们之间的对立、冷漠、敌意。这种情况,不仅存在于广泛的生活环境里,也存在于以血缘、亲情为纽带的家庭成员之间。残雪创造这个世界时,更多的是诉诸个人的感觉、潜在经验以及记忆。不过,残雪的作品所体现的精神世界的范围和深度是有限的,特别是从对人的生命、人性等的发掘的角度去衡量时,更是如此。这导致了她的小说出现的某些单一和重复的现象。
苏童1987年发表《一九三四年的逃亡》,引起文学界注意。其主要作品还有,中短篇小说《罂粟之家》、《妻妾成群》、《红粉》、《离婚指南》,长篇小说《米》、《我的帝王生涯》、《城北地带》、《紫檀木球》等。他的小说,大多取材“历史”。在有关旧时中国家族的叙事中,流露着忧伤、衰败的情调和气息。苏童的小说,既注重现代叙事技巧的实验,同时也不放弃“古典”的故事性,叙事流畅,风格突出。事实上,从《妻妾成群》开始,他的小说对于红颜薄命等主题和情调写得富有韵味,这削弱了小说中的创造性的文化内涵。流畅而优雅的叙述风格,对女性人物的细腻的心理描写,使他在“先锋作家”中,拥有最多的读者。
在众多的“先锋作家”中格非更具浓厚的“先锋性”。《追忆乌攸先生》是他的一部中篇。除中短篇小说以外,90年代,他还发表了多部长篇,如《敌人》、《边缘》、《欲望的旗帜》等。他的作品常让一般读者感到晦涩难解,经常出现的是一种被称为“叙述的怪圈”的结构。这在最初的《迷舟》(1987)和《褐色鸟群》(1988)中,就有令人印象深刻的体现。在《迷舟》中,传统小说故事的重要关节出现了“空缺”,而使故事的推进变得扑朔迷离,也阻隔了读者的阐释、想象路线。《褐色鸟群》在主旨和叙事方法上,更为晦涩玄奥。此后的写作,沿着开始的这一“路线”展开,即面对具体现实和历史情景,持续地思考人的生存等一系列令人困惑而难解的问题。由于小说作者的知识分子背景,和叙述方式上的沉思的品质,他的小说在90年代,被有的评论家称为“知识分子式叙述”。
在80年代末被称为“先锋小说家”的还有孙甘露、叶兆言、扎西达娃。叶兆言以《枣树的故事》知名,在这个中篇里,讲述了一个名叫岫云的女子的故事。他的《状元境》、《追月楼》、《半边营》等中篇,被称为“夜泊秦淮”系列,表现了浓厚的“文人”情调。其他重要作品还有《艳歌》、《挽歌》、《去影》、《绿色陷阱》等。除了中篇以外,他还发表了长篇《死水》、《一九三七年的爱情》。孙甘露1986年发表的《访问梦境》连同随后出现的《信使之函》,在80年代后期,与格非的《迷舟》,常被作为“先锋小说”在文体创作上的典型文本加以讨论。《信使之函》等小说,采用“极端”的“反小说”的文体形式,表现了孙甘露创作始终坚持的“先锋性”和“实验性”。在这些作品中,缺乏可供辨析的故事情节和主题;孙甘露后来的作品还有《请女人猜谜》、《夜晚的语言》、《眺望时间消逝》,《忆秦娥》,和出版于90年代的长篇《呼吸》。
比起80年代以来的许多小说家来,余华的作品数量并不多。余华1983年开始发表作品,直到1987年的短篇《十八岁出门远行》和1988年的中篇《现实一种》,才引起文学界和读者的注意。在这些作品(连同《四月三日事件》、《世事如烟》)中,余华对于“暴力”和“死亡”的精确而冷静的叙述,和在“冷静”后面的巨大的愤怒,让当时的许多读者感到惊骇。这些小说以一种“局外人”的视点,用冷漠、不动声色的叙述,以其想象力来挣脱“日常生活经验”的束缚。余华发掘了过去被遮蔽、掩埋的那部分“现实”。在他看来,为人的欲望所驱动的暴力,以及现实的世界的混乱,并未得到认真的审视。他坚持以一个艺术家对这个世界的独创性发现为出发点,来建立对于“真实”的信仰和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