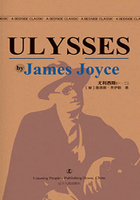这一次流亡的结果,令我益加了解人生的意义和对于革命的决心。我明白现时人与人间的虚伪,倾陷,欺诈,压迫,玩弄,凌辱的种种现象,完全是资本社会的罪恶和显证。欲消灭这种现象,断非宗教,道德,法律,朝廷所能为力!因为这些,都站在富人方面说话!贫困的人处处都是吃亏!饥寒交迫的奴隶,而欲和养尊处优的资本家谈公道,论平等,在光天化日之下同享一种人的生活,这简直是等于痴人说梦!所以欲消灭这种现象,非经过一度流血的大革命不为功!
中国的革命,必须联合全世界弱小的民族,必须站在反对资本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上,这是孙总理的遗教。谁违背这遗教的,谁便是反革命!我们不要悲观吧,不要退却吧,我们必须踏着被牺牲的同志们的血迹去扫除一切反动势力!为中国谋解放!为人类求光明!国民革命和世界革命的终必成功,一切工农被压迫阶级终必有抬头之日,这我们可以坚决地下着断语;虽然,我们或许不能及身而见。
流亡数月的生活,可说是非常之苦!一方面因为我到底是一个多疑善变的知识分子,是一个对着革命没有十分坚决的小资产阶级人物,故精神,时有一种破裂的痛苦。一方面是因为家庭既根本不能了解我,社会给我的同情,惟有监禁,通缉,驱逐,唾骂,倾陷,故经济当然也感到异常的穷窘。我几乎因此陷入悲观,消极,颓唐,走到自杀那条路去!但,却尚幸迷途未远,现在已决计再到W地去干一番!
我相信革命也应该有它的环境和条件,为要适应这种环境和条件起见,我实有回到W地去的必要。在这儿过着几个月的流亡生活,一点革命工作都谈不到,做不到;虽说把华侨的状况下一番考察,也自有其相当的价值,但总觉得未免有些虚掷黄金般的光阴……
你的近况怎样?我很念你!你年纪尚轻,在社会上没有什么人注意你,大概不至于有什么危险吧!这一次不能和你一同出走,实在因为没有这种可能性,经济方面和逃走时的迫不及待的事实,想你一定能够谅解我吧!
这十几天来,由暹罗到新加坡,由新加坡到这H港,海行倦困。此刻更遇飓风,海涛怒涌,船身震簸。不寐思妹,益觉凄然!妹接我书后,能于最近期间筹资直往W地相会,共抒离衷,同干革命!于红光灿烂之场,软语策划一切,其快何似!倦甚,不能再书!
祝你努力!
之菲谨上七月十日夜十二时
他写完这封信时,十分疲倦,凄寂之感,却减去几分。风声更加猛厉,船身簸荡得更加厉害。全舱的搭客都睡熟了。
“唉!这是一个什么现象!”他依旧叹息着。但这时,他脸上显然浮着一层微笑。过了不到五分钟,他已抱着一个甜蜜的梦酣睡着。
二十七
邮船到黄浦江对岸浦东下锚了。船中的搭客都把行李搬在甲板上,待客栈来接。朝阳丽丽地照着,各个搭客的倦脸上都燃着一点笑容,十余个工人模样的山东人,他们围着他们的行李在谈着,自成一个特殊区域。
和之菲站在一处的除秋叶外,便是两个厦门人,和两个梧州人,亦是自成一家的样子。
两个厦门人中一个穿着白仁布,铜钮的学生装的——这种装束南洋一带最时髦——从前是北京工业专门学校的学生,现时在新加坡陈嘉庚的树胶厂办事。他的眼圈有些黑晕,表示出他有点虚弱。他对于社会主义一类的书,似乎有点研究。口吻像个无政府主义者。第二个厦门人是个现时尚在上海肄业的学生,著反领西装,样子很不错,似乎很配镇日写情书一流的人物。
两个梧州人,都是五十岁前后的老人。一肥一瘦,一比较好动,一比较好静。他们每在清晨起来便都盘着腿静坐一会。他们都是孔教的热烈信仰者。那肥者议论滔滔,真是口若悬河,腹如五石瓢。他说:“仁义礼智信,夫子之大道也!此大道推之百世而皆准,放之四海而皆验!是故,此五者皆人类所不可缺之物;而夫子倡之,夫子之足称为教主,孔之成教也明矣!”他说话时老是象做八股文章似的,点缀着一些之乎者也,以表示他对于旧学的渊博。同时他把近视眼圆张呆视着,一面抱着水烟筒在吸烟。
对于人类的终于不能平等,大同的世界的终于不能实现他也有他的妙论。他说:“君者,所以出令安民者也;臣者,所以行令治民者也。今虽皇帝已去,而总统犹存;总统者亦君之义也。然总统时代之不如皇帝时代,此则近十余年来,事实可为证明,不待老夫置辩。倘并此总统而无之,倡为人类平等之说,无君父,无政府,是禽兽也!若禽兽者斯真无君父,无政府矣!当今异说蜂起,竞为奇伪,共产公妻之说,溢于禹域!安得有圣人者出而惩之,以挽人心于既坠!孟子曰,能言拒杨墨者,圣人之徒也。余之不得不极端反对共产公妻,盖亦此意焉。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不易之理也……”他说话时老是摇着头,摆着屁股,神气十足。
那瘦者是个诗人,他缄默无言,不为而治。他扇头自题《莲花诗》三首。中有警句云:任他风雨连天黑,自有盘珠似火明!
这两位老友,是从H港下船来上海的,他们的任务,是到上海来夤缘做官。他们前清时都是廪贡生,民国后,宦游四方,做过承审,知事等类官职。
这时客栈的伙计们已来接客了。两位老人和之菲,秋叶都同意住客栈去,由肥的老人和伙计们接洽。
“到我们的栈房去,好吗?行李一切都交给我们,我们自然会好好地招呼的。”一个眇一目,穿着深蓝色衫裤的客栈伙计向他们说。
“我们这里一总行李三件,到你们客栈去,共总行李费几多?”肥的老人问。
“多少随你们的便吧,不要紧的,不要紧的。”眇一目的伙计答。他一一地给着他们一张片子,上印着“汇中客栈”四个字。瘦的老人向他索着铜牌。他很不迟疑地袖给他一个鹅蛋形大小的铜牌,上面写着什么工会什么员第若干号字样。瘦老人把它很珍重地藏入衣袋里,向着之菲和秋叶很得意地说:“有了这牌,便是一个证据,可以不怕他逃走了!”
之菲和秋叶点头道是。过了一会,行李已先给小艇载去,他们便都被这眇一目的伙计带去坐小轮船渡河。
这时那两位老人步履很艰的在踱来踱去。眇一目的伙计向着他们说:“坐我们栈里头自己特备的汽车去吧。”
“恐怕破费太多,我们坐黄包车去吧。”
“不,这汽车是我们自己特备的,车资多少任便,不要紧的,不要紧的。”
“真的是这样吗?”
“怎么不真!”
两老和之菲,秋叶都和这眇一目的伙计坐上汽车去。这时忽然来了一个流氓式的大汉,向他们殷勤地通姓名,打招呼,陪着他们同车到客栈去。
汇中客栈是一所房舍湫隘,光线很黑暗的下等客栈,两老同住一房。之菲和秋叶同住一房。两老住的房金是每日一元八角。之菲秋叶的是一元六角。过了一会,他们的行李都被送到,他们都觉得心满意足。
之菲和秋叶在房中,刚叫伙计开饭在吃的时候,那眇一目的伙计和那流氓式的大汉,和另外又是一位大汉忽然在他们的门口出现。
“先生,打赏!”眇一目的伙计说。
“我们是替先生一路照顾行李来的,”流氓式的两位大汉说。这两位大汉,贼眼闪闪,高身材,一脸横肉,声音蛮野而洪大。
“那两位老先生打赏我们九元五角。你们两位照样打赏吧!”两位大汉恫吓着说。
“我们两人只是一件行李,行李费讲明多少不拘。我们又不是个有钱人,那里能够给你们那么多!”之菲说,他觉得又是骇异又是愤怒。
“你先生想给我们多少!”他们用着嘶破的口音说,声势有些汹汹然了。
“给你们一元总可以吧!”之菲冷然地答。
“哼!不行!不行!最少要给我们九元!那两位先生给我们九元五角。难道你们一路来的给我们九元都不能够吗!”他们说,露出十分狞恶的态度。
“出门人总是要讲道理的!照普通客栈的规矩每件行李不过要二毫钱。难道你们要几多便几多,不可以商量的么?”之菲说,他觉得他们这种敲诈的办法真是可恨。
“最低限度要给我们八元!快快!快快!我们现时要到外边吃饭去!”两个流氓式的大汉说,露出很不屑的神态来。
“一定要我出这么多钱,有什么理由,请你们说一说!你们要去吃饭吗?不要紧的,我这儿可以请你们吃饭!”之菲带着笑谑的口吻说。
“快!快!最少要给我们八元,分文是不能减的!快!快!快!你们的饭不配我们吃,我们到外边吃饭去!快!快!”大汉说,他们握着拳预备打的样子。
“给你们两块吧,多一文我也不愿意给!你们要怎么便怎么,我不轻易受你们的敲诈!”之菲说。他望也不望他们只是吃他自己的饭。
“快!快!快!快!我们到外边吃饭去!给我们七元五角,再少分文我们是不要的!快!快!快!”大汉再恫吓着说。
为要了事,和减去目前的纠纷起见,最后终由之菲拿出六元纸币打发他们去。这时秋叶吓得面如银蜡色,噤不敢声。
“全世界,全社会都充满着黑幕!”秋叶说,抽了一口气,倒在榻上睡着。
“这里比新加坡暹罗所演的滑稽剧还来得凶!在暹罗买好了船票,还要避去公司们——暹罗私会(为太平天国失败后流亡海外的成员所组成。经多年变化后,分成许多个帮会组织)彼此吃醋(船票须由公司们抽头,此私会与彼私会常因争夺这项权利斗杀,酿成命案),在岸上藏匿着,直到轮船临开时,才敢下船。在新加坡遭福建人的糟蹋(新加坡海面,福建人最有势力。他们坐货船由暹罗到新加坡时,船在离岸数十万丈处下锚,由福建人的小艇来把他们载上岸去。别处人的小艇不敢来做这项生意,这些搭客都要拜跪陪小心,由这些福建人每人要三元便三元,五元便五元,才有上岸之望),出了钱惹没趣!来这儿又遇了这场风波!唉!黄大厚说的真是不错,在家日日好,出外朝朝难!”之菲说,他这时正在饮着茶。
“所以,人类这类东西,到底可以用革命革得可爱些与否,这实在是成了一个大疑问!”秋叶很感伤似地说。
“这个解释很简单,他们的种种丑态,都是受着经济压迫演成的结果!在这些地方,我们益当认为革命!我们益当确定革命所应该走的路,是经济革命!”之菲说。他这时对刚才那几个流氓的愤恨,似乎减少了几分。
“或许是吧!要是革命不能改变这种现象,别的愈加没有办法了!唉!只得革命下去吧!”秋叶说,他的怀疑的目光依旧凝视在刚才几个流氓叱咤暗呜的表演场上。
二十八
W地也发生党变,他们都不能到那儿去,只得滞留上海。之菲这时,差不多悲观到极点。他和秋叶在F公园毗近的×里租着一间每月十元的前楼住着,预备在这里过着卖文的生活。他这时差不多变成一块酸性的石头。他神经紊乱时老是这样想:“虽然醇酒妇人的颓废和堕落的生活,断非一个在流亡着的狂徒的经济力量所能胜。但,在可能的范围内,且从此颓废下去吧!堕落下去吧!我虽不能沉湎在鸩毒的酒家,淫乱的娼寮中;但到四马路去和那些和我一样堕落的‘野鸡’去碰碰,碰着她们高耸的乳峰,碰着她们肥大的屁股,把神经弄昏了,血液弄热了,然后奔回寓所来,大哭一场,这总是可以的!有时,减衣缩食去买一两瓶白玫瑰,以失望为肥鸡,嘲弄为肥鹅,暗算为肥鸭,危险为肥猪,凌辱,攻击为肥牛,肥蛇,饱餐一顿,痛饮一番,大概是不至于没有这种力量的!沉沦!沉沦!勇往的沉沦!一瞑不返的沉沦!不死于战场,便当死于自杀!我的战场已失去了!我的攻守同盟的伴侣已经溃散了!我所有的只有我自己的赤手空拳!我失去我的斗争的立场!我失去我的斗争的武器!在我四围的,尽是我的敌人!我不能向他们妥协,屈服!我只有始终站在反对他们的地位,去从事我个人的沉沦生活!”
但,当他神经清醒时,他觉得这种办法实有些不对。他便这样想着:“革命这件东西,是像怒潮一样,一高一低,时起时伏。这时候中国的革命运动虽然暂时消沉下去,不久当然会有高涨的希望。我应当忍耐着,冷静地考察着各方面的情形怎样,我不应因此而失望,悲观,堕落,颓丧。我应当在这潜伏期内,储蓄着我的力量去预备应付这个新局面……”
这两种思潮,各有各的势力平分占据他的脑海。他因此益显出精神恍惚,意志不专。
秋叶的态度,益显出颓丧。他的否认一切的言论发得真是太多!他的失望,灰心,颓丧,不振,无生气,没有丝毫力量的倾向,一天一天地厉害起来!“希望”这个名词,在他的眼里,简直成为一种嘲弄。他永不希望。譬如做文章寄到杂志编辑部去,别人总是希望或许可以发表的吧。他寄去时从未尝有过热烈的倾向。寄去后,好像他的工作便算完了。他不曾多做一层希望的工夫。结果,他的不希望的哲学大成功。因为事实证明,他们对于这些是永远用不着希望的!
他们睡的是楼板;穿的是从朋友处借来的破衣服;食的是不接续的“散包饭”;所做的文章,从未尝卖到半文钱。他们实在是可以不用希望的。
这天,他们在报纸上看见一段S埠,T县都为工农军占据的消息。之菲决意再回去干一干,秋叶不赞成,他们的辩论便开始了。秋叶说:“第一点,这支工农军,子弹饷械都不充足,日内必定败退溃散,我们没有回去跟他们逃走的必要。第二点,我们现在需要竭力保持灰色,这一回去,色彩益加浓厚,以后逃走,更加无地自容。第三点,干革命工作,不必一定到工农群众里面去做实地工作。在文学上,我辈能够鼓吹一点革命思想,也算是尽一份力量。我根据这三点理由,绝对不赞成回去。”他说话时,一面正在翻译逖更司的Tales of Two Cities(《双城记》),态度很是冷静镇定。
之菲这时,全身的血在沸着,他对于文学本身已起着很大的怀疑。在这样大风雨,雷电交闪的时代,他觉得安安静静地坐下去从事文学创作,这简直是一件不可能的事。他觉得月来的郁积,有如火山寻不到爆烈口一样沉闷,现在须让它爆烈一下!他觉得月来的苦痛,有如受缚的鸷鸟一样悲哀,现在须让它飞腾一下!他的青春之火,他的生命之火,他的为民众的利益而牺牲的壮烈之火,镇日里在他胸次燃烧着,使他非常焦灼,坐卧不安!他的灰白色的脸,照耀着一层慷慨赴难的表情,他的眼睛里有一种恳挚的,急切的,勇往的光在闪着。他听见秋叶的话老大地觉得不舒服,立起身来说:“第一点我们必须回去,因为我们从暹罗奔走到新加坡,从新加坡奔走到上海来,为的是要到W地干革命去。W地现时既不能去,而W地的革命势力现时几乎全部集中在S埠,T县;故此我们必须把到W地去的决心移到S埠,T县去。工农军的是否失败,现时不能武断,假使失败,我们只有再事逃亡,并无若干的损失。第二点,我们必须回去,因为我们的战地久已失去,战伴久已分离,战斗的力量和计划大半消失,这一回去可以把这些缺陷统统填平。保持灰色这一层,现在大可不必;既已在流亡通缉之列,尚有什么灰色可以保持?第三点,从事革命文学对社会当然也有相当的贡献。但既已决心从事革命文学而不作实地斗争,这种文学易成蹈空,敷衍,而失去它的领导时代的效力!根据这三点理由,我绝对地主张回去!”他说话时,声音非常亢越,有一种演说家的表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