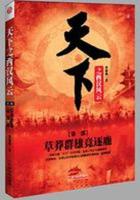还在上高一时,我从同学那里借到一本《圣经的故事》,对里面的《诺亚方舟》印象深刻。《诺亚方舟》说的是上帝耶和华对于人类无休止地相互撕杀、争斗十分忧伤,他后悔当初在地上造了人,他决定将所造的人从大地上统统消灭,只留下守信义、守本分的挪亚一家。于是降了四十昼夜的大雨,让洪水掩埋了大地上的一切,只有挪亚一家坐在方舟里得以活下来。
那个时期,我常常想起这个故事,我想如果世界上真有一个耶和华,他是不是应该再下四十昼夜的大雨,再来一次洪水,难道现在人们犯下的罪恶还少吗?城里人天天在相互武斗相互撕杀,多少人看着“文化大革命”如同魔鬼,肆意地撕裂着国家的肌体又毫无办法;农村人倒是没像城里人那样忘乎所以,没有离开土地,但又是这么一种精神现状,这么一种生存状态,如果真有上帝,他真应该再一次改造改造这个世界了。如果这一次他还想将他所造的人再一次从大地上消灭,只留下守信义、守本分的,我可以大言不惭地说:我,当之无愧。
当然,当之无愧的人不止我一个,中国八亿(当时有首歌唱的是八亿人民八亿兵,万里江山万里营)人口,农民就占六亿,有良心有责任感一心想把集体日子和自家日子过好的人还是有一些,前边提到的老丁老白是集体大家庭的当家人,他们应该有责任心,而提我当标兵的老农,则完全出于一个农民的良心,这个老农干集体活也是实心实意,不摆样子不玩弄花架子,平日对年轻人败家式的干法也是忧心忡忡,所以当他发现了还有那么个拿集体活当自家活干的傻瓜蛋,就如同发现了稀世之宝,就一心想树起我这个傻瓜蛋给众人当个榜样。
尽管那个老农建议我当妇女中的标兵出于公心,是为集体着想;尽管我当上这个标兵对集体有百利无一害,但我却没有勇气接受,黑五类子弟根本不具备用以身作则来教育他人的资格,我不愿意让这个对自己并无多大益处的标兵破坏了我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群众关系,把自己重新孤立起来。女人们本来就心眼小,爱妒忌,是非多,现在,一个四类分子子弟突然像羊群里蹦出来的骆驼,一下子盖了大伙,劳动工分居然比贫下中农子弟还多0.5,她们能服气吗?而且在当时阶级斗争天天讲的大趋势下,也没有这个理。看看坐在炕上的几个妇女谁也不吭气的表现,就会知道我果真接受了这个标兵头衔,以后处境将会多么艰难,我只怕坐不了挪亚的方舟,倒坐上了在风浪里飘泊的独木小舟,别人安然无恙,自己却翻到风浪里了。
于是,在大多数人同意,少数妇女们不吭声的情况下,我自己站起来反对自己,言不由衷地一再申明我不够标兵资格,独给我加一级不合理,还说其他妇女谁的活都干得比我快,比我好,选标兵也应该从她们之中挑选等等,等等。
但是没用,果树队这次也不知发的哪门子神经,而且在那一刻他们似乎忘记了果树队之外是个什么样的世界,还真真把果树队当成了“文革”中的“桃花源”,非要树一个“阶级异类”来教育其他妇女。不管我怎么不想当这个“骆驼”,想留在羊群里夹着尾巴当只老实羊,最后还是少数服从多数,标兵还是硬按到了我的头上。
在果树队妇女的无声抵抗中,在我自己像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在妇女中格外唯唯诺诺格外小心翼翼中,我当了三天标兵,三天以后,不用我再反对,我的标兵头衔就尴尬地消失了。
每个星期三下午是果树队法定的政治学习时间,全队人脱产学习。偏巧那个星期三我因为要去车站送来我家探亲的二姨提前请了假,没有参加。第二天去果树队上工,发现不少人见了我表情有点异样,有点怪怪的,好象昨天我没参加政治学习去外边闯了祸,别人都知道了,惟有我自己还装成没事人一样。尤其是队长老白和组长刘春波,见了我立即躲开了,好象我是个不祥物,会给他们带来晦气;又好象是他们做错了什么,不好意思面对我。
怎么回事?怎么一个下午不见大家都变了脸?难道我真做错了什么?还是说了我不该说的话?我犯了核计,心里七上八下,直觉告诉我昨天下午一定发生了跟我有关的什么事。
那个上午,我被分配去种香瓜,在提前打好的地垄上刨坑,浇水,捻种,封窝……一个上午,我的头木木的,两手机械地往浇好水的小坑里捻种,不是捻多了就是捻少了,老得返工。
在我头上,天是那么的碧澄,在我四周,树是那么的葱绿……温馨的风吹过面颊,欢快的鸟叫传进耳膜……暮春的天气不冷不热,风光比什么时候都怡人。而我却一丝精神也打不起来。多少年的风风雨雨,使我这个政治上的弱势者神经异常敏感也异常脆弱,稍有风吹草动就忐忑不安。我暗暗祈祷这一切都是我心理作用,其实什么事情也没发生。
中间休息时,我找了个僻静的地方坐下,想清理清理纷乱的思绪,想想我这几天都做了什么事,说了什么话,哪些地方做得不对劲了,什么话说得不得体,让人家挑上了……我刚坐下,一个和我一起种香瓜的叫何静的姑娘就悄悄找了过来,她看看四周没人,才小声跟我说:你不知道吧?昨天下午政治学习,老白、小波还有其他一些人都被郭云红批评了。
为了什么?我虽然问了一句,但脑袋里已经敏感地意识到是为什么了。
果然,何静告诉我:因为你当标兵了呗。
那又不是我要当的啊!那天的事你都看见听见了,关我什么事?我说。
正如我所料,因为这个标兵,这两天果树队的妇女明显跟我生分了,疏远了,连和我关系不错的何静见了我,笑都不自然了,干活时还尽量躲着我。现在她主动告诉我昨天下午发生的事,我疑心她是幸灾乐祸。
所以郭云红才批评队长和组长呀!
郭云红批评他们什么了?
批评他们阶级路线不清,和……和子弟站到一个立场上。何静有意省掉了子弟前边的定语。
还说什么?
还……还说树子弟当标兵,是长敌人志气,灭贫下中农威风。
长敌人志气,灭贫下中农威风,我的头“嗡”的一声胀得老大。这是那个年月大部分人都熟悉的口号,原句是“长贫下中农的志气灭阶级敌人的威风”。郭云红不愧当了几年大队干部,毫不费事就把它活学活用到我的头上,轻轻松松就把我打入阶级敌人的行列,在郭云红口中,我想当个可以教育好的四类子弟都不够格了。
老白、小波怎么说?我昏头胀脑地问。我内心觉得对不起老白和小波,好像评我当标兵真是我的错了,是我连累了他们。
他俩都没说什么,其他人也没说什么,现在的人都学“鬼”了,明知郭云红是拿出身压你,可谁也不敢表示什么,就连提你当标兵的“大嘴子”也哑巴了,真是能请神不能安神。何静这阵似乎为我不平。她说的“大嘴子”就是提名让我当标兵的那个老农,也姓何,外号“大嘴子”。
人家不说是对的,为我这样的人说话有什么用?我也真他妈的不是个吉祥物啊!谁沾着谁倒霉。我恨恨地说,使劲控制着不让眼泪流出来,世界如此之大,怎么容我安身的地方又如此之小呢?
评标兵的风波过去了,谁也不再提那回事。自然我也不再是什么标兵,仍和其他妇女挣一样的工分,只是多受了一次伤害。后来,郭云红成了大队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标兵,准备到外地巡回讲用,郭云红小学都没毕业,自己写不了讲用稿,果树队就指派余福江替她写,余福江那段时间就天天脱产为郭云红准备讲用稿,有人就传言说余福江在追求郭云红。
1967年的夏天,全国武斗打到白热化的时候,农村相对安宁了不少。农村毕竟是农村,在批斗了几次当权派和牛鬼蛇神,糊了些纸帽子给他们戴上游了几次街,再学上海“一月革命风暴”夺了当权派的权,就没有什么新花样可玩了。农民没枪没炮也没时间,打不起武斗,除了少部分好事者去抓革命,去和这个派那个派辩论,大部分人还是在第一线上抓生产,尽管好多人抓的是不负责任的生产,但毕竟在抓。
我那个公社在“文革”初期也曾像一场大雨后冒出许多蘑菇一样冒出许多战斗队,这些战斗队大部分用毛主席诗词里的一句或几个字命名,简单的像“全无敌”战斗队、“千钧棒”战斗队啊,复杂的像“六亿神州尽舜尧”战斗队、“宜将剩勇追穷寇”战斗队啊等等。到1967年的夏天,那些名称五花八门的战斗队并成两大派系,一派叫作“红色革命造反者”,简称“红革派”;一派全名为“无产阶级大联合筹备委员会”简称“大联筹”(红革派骂其为“连臭”)。两派都说自己最革命,最誓死捍卫毛主席,两派之间又势不两立,互相攻击。一些热衷于吃革命饭的,今天说自己是“联筹”的人,明天又郑重其事地声明脱离“联筹”,说“联筹”是反革命组织,是拉着大旗做虎皮的假革命,要加入“红色革命造反者”。其实他们自己都不明白到底谁是真革命,谁是假革命,只不过觉得这样折腾来折腾去好玩罢了。
而大部分老实巴交靠干活吃饭的人就更糊涂了:明明都打着毛主席的旗号,都在誓死捍卫毛主席,怎么就知道这个派是真革命,那个派是假革命呢?支左部队还煞有介事地支持这个不支持那个,弄得两大帮派像狗咬仗似的吵个没完。听说城里为这个还动用了真枪真炮,像当年国共两党交战一样打得你死我活,把好端端的大楼都炸平了。国共两党交战为了争政权,夺天下,这两派动枪动炮图个什么?老百姓想不明白了,想不明白后就得出这样的结论:哼!什么也不该,就该又吃了两天饱饭,撑得不知怎么好了,弄不好再来个“低标准”,再饿他们三年就老实了。
那年夏天,在山西教学的三哥三嫂回来了,他们那儿武斗更激烈,因为附近有兵工厂,武斗全用真枪实弹,打死不少人。三哥他们学校早停课了,呆在学校没事干,索性回老家躲躲满天飞舞的枪炮子弹。
三哥在我们兄弟姐妹中是最有主意也最拿事的一个,在几个儿子中父母最器重三哥。三哥在十二三岁时就能在家独挡一面,土改父亲被关,母亲领其他几个哥哥去要饭,扔下三哥一人在家做饭,给父亲送饭……弟兄好几个,母亲惟独留下三哥在家最放心。土改以后,大哥二哥成亲,和女方家的一些事情全是三哥出面去跑,母亲说三哥个头小,骑车够不着脚踏子,把腿从车架底下伸过去硬蹬一百多里地。1952年,母亲的腿生了个痈,腿肿得老粗不能动,痛得夜里睡不着觉,父亲在家却拿不出主意,只能消极地用些偏方治,干治不见效。三哥当时在皮口读初中,星期天回来一看,马上决定把母亲送往皮口医院,并埋怨父亲当了半辈子教师遇到这种事竟不知怎么办。三哥立即去学校把正在教学的二哥找回家,又去屯中一个小卖铺子借了辆手推车,和二哥推着连夜把母亲送往四十多里外的皮口医院,据医院大夫说,再迟两天,母亲的腿就得截肢。
还有一件事我也记忆犹新,在我十一岁的那年夏天,我的扁桃体发炎,不敢吃饭不敢咽唾沫,母亲说我生了嗓扼子,要请邻居老太太来用偏方治……当时三哥从北京回来过暑假,立即制止了母亲,说当年二哥的女儿就是用这个偏方送了命,还不接受教训,妹妹这是扁桃体发炎,必须打针消炎。
三哥像当年用手推车送母亲去皮口医院一样,立马去村里小卖店借了手推车,一人推着我跑了十几里地去了地区诊所,诊所大夫根据三哥的提议,给我打了一支青霉素……
往回走的路上,我的嗓子轻松多了,天很热,我想下来走,三哥不让,说刚好一点,别再累反复了,我只好再坐在手推车上。三哥热了,把上衣脱了放在车上,只穿一件印有“北京大学”的背心。可能因为出汗缘故,三哥的眼镜频频往鼻梁上滑,三哥也就用食指频频地往上戳……路上有行人与我们迎面而过,都回过头来看三哥几眼,我望着他们脸上露出的又奇怪又羡慕的表情,心里很是骄傲。路上,碰到几个卖水果的小贩,为庆贺我嗓子不疼了,三哥一定要买点水果犒劳我,可摸了半天兜,兜里竟没有多余的钱,最后只好买了两角钱的葡萄……
那次三哥回来要解决两件事,一是把弟弟送走,送给我小姨当儿子;二是把我弄到山西,在山西给我找工作,办法是在山西他工作的地方先给我介绍个对象,这样去就容易多了。按三哥的意思老家已经没有任何可以留恋的地方,应该解散了,至于儿女都走了父母怎么办,三哥还顾不得多想,只说走一步算一步,车到山前必有路,总会有办法的。
现在应该说说弟弟了。
东北有句俗语,说“黄瓜茄子两头鲜,老儿老闺女宠上天”。意思是生在最后的孩子最有福气,最得父母和哥哥姐姐们的宠爱。可我和弟弟正相反,我和弟弟是父母的老闺女老儿子,可我们都是不受欢迎的多余者。如果当时有今天的计划生育,我和弟弟都不会来到这个世界。
我的境遇前边已经交代,但因为我是女孩,多少粘了点“物以稀为贵”的光,而且父亲和哥哥们也根本不相信我是扫帚星,是我给家中带来厄运一说,对我仍然是宠爱有加,而弟弟的境遇就不如我了。他在众人眼里是不折不扣的多余者。
弟弟是梁家兄弟姐妹里命运最不济的一个。也不知怎么搞的,父母生的前四个儿子都一表人才,两个女儿也算漂亮。惟独这个弟弟长得不出奇,跟帅气的哥哥们比显得又小又丑,真是应了那句老话:越不当人意,越长得遭人弃。
其实弟弟也并不难看到哪里,只因有哥哥们的比照才显出他的劣势。和街上的小孩一起玩,弟弟还是很出眼的,父兄们之所以忽略了弟弟,最大的原因还是因为当时的环境和大家的心境。弟弟的成长阶段不像我,还赶上了家中和社会上那一段相对安宁时期,还有过那么一段值得回忆的美好时光,而弟弟从懂事起,就活在阶级斗争的阴影里,活在接连不断的厄运中。
在我的印象里,父亲从没爱过这个弟弟,他连名字都懒得给弟弟起,弟弟就按排行叫“小五子”。而在这之前,父亲兴趣十足地给大哥起乳名叫“林”,二哥叫“顺”,三哥叫“升”四哥叫“成”;哥哥们也从没喜欢过这个弟弟,哥哥们年节回家给我和姐姐买礼物从没有弟弟的份,这使我现在想起还为弟弟不平,而弟弟当时也不知是小还是懂得自己在家的位置,从不争要。
只有一个人时刻呵护弟弟,那就是母亲。弟弟小时不光长相不讨人喜欢,脾气也拗得出奇。由于种种原因,他在外边经常受人欺负。受了欺负受了委屈回家也不说,就知道扯着母亲的衣裳撕打母亲。而母亲总是耐着性子忍受,让弟弟发够脾气。母亲说,小五子家里家外没人疼,我再不疼他,他不就更可怜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