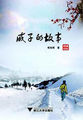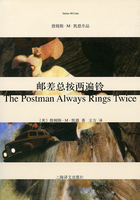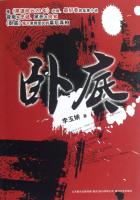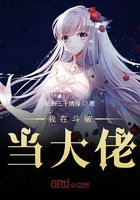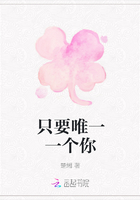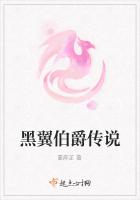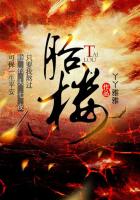侄女得的是急性肺炎,一得病就气喘不止,但邻居的一个据说懂点医道的老太太硬说侄女是嗓子坏了,生了嗓扼子,气喘是因为嗓子眼堵了,得用她的偏方治。用她偏方的结果是耽误了侄女的病,侄女硬是喘了两天两夜,难受得她把脚后跟都蹬烂了,最后不治而亡。可话又说回来,即使侄女的病没有被耽误,在当时的情况下也不一定能治好。那时方圆二十多里的唐家地区只有一家小诊所,所里只有一个二百二大夫(当地人对不懂医术只会抹二百二红药水大夫的“尊”称)当地小孩得了类似侄女的病,大都保不住命。
侄女死后的第二年春天,二嫂也死了。二嫂的病来得更突然,一发病就呕吐不止。这次二哥没敢耽误,立即送到区诊所,“二百二”大夫说是胃病,开了药回来吃,结果不但没好,还抽起风来……也是折腾了几天几夜,受尽了罪才去。至死不知得的是什么病。
多少年后二哥才明白,二嫂得的是急性脑膜炎,娘俩得的都是当时棘手的病,也可以说在当地是无法医治的病。
二嫂母女的死对母亲打击最大,土改中的霹雳闪电都没有改变母亲,二嫂母女的死却让母亲一下子衰老了。在母亲的思维里,土改是国家的事,是国家规定的,谁能与国家抗衡?何况被斗争的不是她一家,所以她不怨恨谁。而白发人送黑发人,就是家门的不幸了,她一面说是自己前世造了孽,所以要遭这样的报应,一面更加重了对我的怀疑。而我的那颗小锥牙的及时出现,仿佛就为证实母亲的猜疑,证实我是个不折不扣的扫帚星。
母亲那时还没有料到,在以后的年月里,还有更多的坎坷更多的磨难在等着她呢。
应该感谢母亲,她没有特别关爱过我,但也没有歧视我,我在这个灾难重重的家庭里还是健康活泼地成长起来,而且在我的记忆里,童年时代是我最幸福的一段时光。
我的家乡属于丘陵地区,辽南地区到处丘陵起伏,辽南地区的村村落落都选择在这些丘陵环绕的低洼地带。
我居住的叫大郭屯的小村,地形跟中国的地理特点相反,中国的地理特点是西高东低,而大郭屯地势是村子东边高,西部平坦。
从我出生直到1958年,我们家一直住在别人家的五间土平房里,五间房子呈“一”字排列,中间的一间做灶屋,东西各两间用来睡觉和陈放杂物。灶屋面积较其他房间要大一些,有前后门,靠前门的两侧靠墙各盘一个锅灶,锅灶和睡觉屋的土炕连通,这样做饭时产生的余热就能穿过土墙壁加热睡觉屋的土炕,帮助一家人在四处漏风的土屋里熬过一个个严冬。
灶屋靠后门的地方还放有一张长条桌,桌两旁各有一条长凳,天一暖和,全家人就不在炕上围着小饭桌吃饭了,而是坐在比较凉快的长条桌边吃。夏天的中午,因为土炕热,我常常爱把两条凳子并成一张“床”,然后舒服地躺到这张没有热度的“床”上,在屋外树上蝉的“鸣——呜、鸣——呜的叫声中,在院子里母鸡咯咯——嗒、咯咯——嗒的叫蛋声中进入梦乡。”
每年到了春节,父亲就把长条桌横过来,仔细地擦拭一番,在桌腿上系上漂亮的桌帷,这张桌子就成了供桌,用来摆放香炉、烛台和供品,供奉请在墙上的家谱。
房子间数不少,院子却不大,小时候的我,每天从做饭的灶屋出来,一路蹦达到院门口,正好三十下。现在想想,那个院子从北到南也就十五六米吧,院子东西能宽一点,也宽不了多少。
在那近二十米方圆的院子里,父亲在东屋窗前养着蛰人很痛的蜜蜂,有时是十几箱,有时是七八箱。到春天采蜜时,蜂群就增多,并且每箱上都要加几层套箱,像现在人住的火柴盒式的楼房,最多时套箱达到四层。快入冬时,父亲就要给蜂群并窝,十几箱蜂并成七八箱或者更少,用软和的草严严实实地裹起来,让怕冷的蜜蜂安全度过严冬。
每年春天,父亲还爱在小院门口种几墩葫芦,葫芦爬满架时,院门口就有了一片绿荫。
出了院门就是一条横惯东西的土路,土路很窄,并走两辆牛拉车都很勉强。但在当时却是东来西往的交通要道,其地理位置上的重要性不亚于今天的国道。每天每天,当我还没从早晨的睡梦中完全清醒过来,就朦朦胧胧听见从东山上下来的马拉胶皮轱辘车因下坡轧闸发出的吱嘎吱嘎声和赶车人的吆喝牲口声,有时声势大的就像杜甫诗里形容的那样:车辚辚,马啸啸……只是赶车人没有弓箭,这些车大都是农村供销社雇用的拉货车,到西边离我们家三十多里路的普兰店镇为供销社拉货的。
紧挨着土路的是一条小河,由村东“高原”上沟沟岔岔里流出的雨水和涧水汇聚而成,弯弯曲曲,涓涓淙淙,终年不息地向西流去,最后汇入西边的大沙河。
母亲因为家里祸事连连,除了对我疑心,对这所临街又临河的房子也一直心存芥蒂,说屋子不能距街太近,天天街门前那些东来西往的人把家中的福气都带走了;说房前更不该有河,家中的运气就是被门前那条终年流淌的小河冲走了……
可直到1958年以前,母亲和全家却不得不一直住在这所她认为地气风水都不好的临街又临河的房子里,而且因为房主要房子而全家又没地方住母亲和房主还打了好几年官司。
不管母亲对自家的住处怎样腻歪甚至深恶痛疾,少不更事的我对这所房子却情有独钟,它给我的童年留下了太多太多的温馨记忆。
先说养在院里的那些蜜蜂(我把它们看成是那所房子的一部分)。
蜜蜂一般是不蛰人的,父亲打开蜂箱看蜂,连防护衣帽都不用,他用手指在聚满蜜蜂的蜂板上任意地趟,那密密匝匝的蜜蜂竟会自动地闪开,为手指让开一条道,仿佛父亲的手指是它们的蜂王。父亲经常指着又长又大的蜂王给我看,我看到一箱蜂的首领蜂王每走到哪里,哪里的蜜蜂就很懂事似地为蜂王让道,让一箱之主畅行无阻。
但仿佛认识父亲的蜜蜂爱蛰我和弟弟,用母亲的话说是专蛰不像个人样的人,每一挨蛰,父亲就会找个小盆命令弟弟赶紧往里撒尿,然后用热尿涂抹蜂刺刺过的地方。父亲的偏方很管用,只要用新鲜尿一涂抹,疼痛立刻就减轻了,挨蛰的地方肿得也不厉害了。
尽管有父亲的偏方对付蜂子蛰,小时候的我还是有点害怕蜜蜂,一遭了蜂子蛰就大哭大叫,吵着嚷着让父亲把蜂子卖掉,一箱也不留。父亲则一边帮着我们往挨了蛰的地方涂尿,一边笑着说还是蛰得少了,蛰多了产生抵抗力就不痛了,现在蜂子蛰他就不怎么痛,也不肿。还说卖了这几箱蜂你们靠什么上学,就你哥哥挣的那俩钱够吗?
父亲坚持不懈地养蜂,不光是指靠养蜂供子女上学,还有个原因是父亲特别喜欢蜜蜂,他对蜜蜂有一种特殊的感情。
每天每天的早上,父亲都会早早起来,蹲在院子东边的蜂房前,看着蜜蜂们淌淌如水地迫不及待地从蜂房里“蜂拥而出”,(“蜂拥而入”这个成语,没准就是哪个养蜂人的妙手偶得)再目送它们迎着朝阳嗡嗡嘤嘤地飞出院门;到了傍晚,又守候在蜂房边,迎接蜜蜂嗡嗡嘤嘤地满载而归。为此,父亲常半开玩笑半骄傲地说他是屯里最富有的人,每天有千军万马在为他效劳。
父亲养蜂在家乡一带颇有名气,方圆几十里内,凡有养蜂人家,都来向父亲讨教养蜂技艺,跟父亲切磋养蜂经,他们的蜜蜂遭了病,会老远地跑来请父亲前去诊治。
当然,父亲养蜂对我也不是一点快乐没有,到了甩蜜的季节,不光是我,全家都像过节一样地喜气洋洋。因为甩蜜时蜜蜂脾气容易变得暴躁,父亲就不敢像平时那样轻装上阵,父亲穿上蜂衣戴上蜂帽,活像深山古刹里走出来的老道士,滑稽得让人发笑。全副武装的父亲轻轻地、充满爱意地打开蜂房,把蓄满了蜜的沉甸甸的蜂板上的蜜蜂小心翼翼地抖搂掉,赶紧再放进一块稍沾了点蜜的空蜂板,让被抖搂掉的蜜蜂有个新窝。等一箱蜜蜂在父亲细心的操作下全部换上了新窝,父亲才把退下来的蓄满了蜜封了盖的蜂板拿到屋里,用在热水里加过温的蜜刀削掉上边的蜡封,然后放到甩蜜机里嗡嗡地甩起来……
通常甩两箱蜂板,就得用桶接一次蜂蜜,接蜜时,我会瞅大人不见飞快用碗盛一些蜜端到街上招摇,几个早已拿着饼子等在那里的小伙伴看见我端着蜂蜜出来,就像看见主人端着食盆子出来的小鸡,哄地一下围上来,迫不及待地用饼子蘸蜜吃,苞米面饼子蘸蜂蜜,吃起来又香又甜,绝对胜过馒头面包,看小伙伴们吃得兴高采烈,而且时不时讨好似的望着我,我就感到风光无比也快乐无比。
啊!挨了蜜蜂蛰时大哭大叫也好,吃苞米饼子蘸蜂蜜时快活无比也好,多少年后回想起来,都成了一生中最美好的记忆。
再说门前那条“国道”。
童年的记忆里,每天每天,东来西往的人凡是要走这条“国道”,就必须经过我家门口,白天在街上玩,我就有好多风景可看,那些来来往往为供销社拉货的胶皮轱辘车(半夜常有人敲门说车陷进道边的小河沟里要借铁锹或者灯笼)我不大感兴趣,我最爱看的是农闲季节坐车走亲戚的女人和孩子,东来西往的娶媳妇队伍,不管农忙农闲都有的出大殡,还有脱了裤子满街跑的“彪子”(精神病患者),或者结了婚三天回门的新郎和新媳妇……
小时候的我,最羡慕那些坐在牛车上走亲戚的妇女和孩子。那些牛车有的是轻巧的木轱辘车,乡里人称花轱辘车(后来从电视剧上看到,过去有钱人家出门,坐的都是这一类的车,只不过车上有棚有帘子装饰得像花轿一般),有的是车身和轱辘都比花轱辘车大,大大的木轱辘外圈还箍着一圈厚铁皮的车,乡下人叫它铁轱辘车。铁轱辘车很笨重,走起来咯噔咯噔的很慢。一般来说存得起这样车的人家都是日子比较殷实的庄稼户,铁轱辘车虽然笨重,但拉泥拉粪秋天往家拉庄稼还是比花轱辘车顶用。
走亲戚的牛车上一般都铺着秫秸或者稻草,上边再铺一床褥子,女人和孩子们就悠闲自得地坐在褥子上,大冷天时身上还围着被子,任由老牛拉着慢腾腾地走。
童年的我没见过现代交通工具,我家又不像别的人家,附近有姥姥舅舅等三亲四故,闲着时可以跟着母亲坐上牛车去兜风,我的活动圈子只能在家门口和同龄的伙伴“跳房子”(就是在地上画出方格子,单腿一格一格地跳,跳完所有的格格就要房子);“打牢瓦”(就是找一小石片支立在地上,另一个人在一定距离拿着石片把它打倒);“抓猪拐”(就是找五个猪腿关节上的骨头,留一个在手中做“天”,另四个做“地”。那骨头都有坑有凸,有耳有平,用手把四个“地”在地上抛出或“分”或“角”或“元”的形状,再一一地单手抓起,并立即接住抛在空中的“天”,就赢得了或“分”或“角”或“元”)……虽然这些游戏至今想起来也活泼有趣,但在当时怎能跟坐在车上悠哉乐哉串亲戚,在亲戚家还能吃上好东西相比拟呢?所以那时觉得坐牛车走亲戚就是活人的最高享受。如果看到车上妇女身边坐着一个像我一样大的女孩,我就觉得那个女孩是世界上最有福的人。
街上东来西往娶媳妇用的车叫“轿车”,那种“轿车”一般是用马拉花轱辘车装饰而成,乡里一些日子过得不错的人家娶媳妇要排场,娶媳妇进门这天都是四辆“轿车”,前边两辆车上都用芦席搭了篷子,篷子上贴上喜字挂上花,打扮得花花绿绿,车上坐着新郎和新娘,后两辆车只用芦席简单搭个篷,是为媳妇娘家送亲的人准备的。另外还得准备一辆普通车,上边坐着吹手班子,一路上二胡、笙、唢呐齐奏,外加锣鼓助兴,比今天从电视里看到的皇帝成亲还热闹。
从街上经过的死人大出殡最好看,尤其是那些家境不错的人家出殡。这些人家发丧老人一般比较讲究,通常是十六个或三十二个人抬着棺材,棺材上蒙着花花绿绿的棺罩。棺材前边是各色各样的幡旗,有条儿幡、葫芦幡、罗圈幡……幡旗后边是穿着孝服的孝子孝孙。棺材后边是穿着孝服用哭的方式跟亲人告别的女人,女人后边跟着吹手班子,吹手班子专门吹奏哀乐为或悲伤而哭或不悲伤也得哭的女人们伴奏。
那些用一块缝成三角状的白布套着头遮着脸的女人与其说是哭,更不如说是唱,她们随着悠长凄凉的哀乐,拖着长韵有板有眼地数念着正走在黄泉路上亲人的诸多好处,述说自己心中如何想念如何悲痛,有的还忏悔亲人活着时自己对亲人太怠慢,凉水烧成热水都没做过一次,现在追悔莫及等等等等。白花花的一片出殡队伍用两秒一步的速度在大街上晃悠,还时不时放下棺材谢杠(即家属向抬杠的人表示感谢,让抬杠的人休息)。谢杠时,就是吹手班子大显身手的时候,他们会拿出所有的看家本事,吹出或悲伤或快乐的曲子,每吹完一曲主家都得赏钱。吹手班里一般常有几个专门跟着唱曲的,专门唱曲的这时就会随着音乐又唱又闹地折腾……所以每一次“谢杠”就是一次热热闹闹的小型音乐会,让围观的人大饱眼福。那时的农村没有广播没有电影,(村里第一次放映电影是1954年,用发电机发电,放给村里驻军看的,有线广播安于1957年冬天,且只安在大队门口)每年春节,村业余剧团能演几次剧,除此之外,看谁家娶媳妇或发丧人就是村民最大的精神娱乐,尤其是大出殡,无论本村还是外村从门前经过的出殡队伍,都能让大家兴奋好几天。
不过,给死人出殡不是娶媳妇,大家虽然爱赶那份热闹,内心还是忌讳,每有出殡队伍从门前经过,母亲就赶紧拿一面箩蒙上红布挂在门口,说这样能避邪。
还有,就是门前那条小河了。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门前小河的好处数不完道不尽,每年的春夏秋,小河还没结冰封冻时,村里的大姑娘、小媳妇,还有那些丫头小子养了一炕的大娘们、大婶们,常常三五成群,端一盆衣服来到河边,找一块合适的石板,就一边唠着自家长邻家短,一边不慌不忙地搓洗起来。到了夏天,她们还要把家里因受潮而长白毛的碗橱、门扇、案板、盖帘——凡是能拿来的东西,统统搬到河边,洗呀刷呀,没完没了。
春末夏初,天气干旱,男人们就在小河里筑起一条条“拦河坝”,圈起一个个清凌凌的小“水库”,从“水库”里挑水浇灌河边的菜园子,那时节,我们村里的黄瓜豆角茄子辣椒总是又肥又大,掰开都淌水儿。
紧挨小河的南面就是我家和邻居家的菜园地,那是一片平坦地,由北到南被划成一条一条的,每家根据人数的多少或宽或窄地拥有一条。童年的我喜欢栽花,比较宠我的父亲就把菜地最北头靠近小河那儿划出一小块来做了我的花圃,我在属于我的花圃里种满了六月菊、扫帚梅、步步高、鸡冠子、指甲花等等,每天用把喷壶从小河里提水浇灌,忙活得满头大汗。